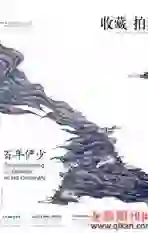国家优先购买权:文物收购的新思路?
2009-08-21本刊编辑部
本刊编辑部
今年春拍,中国嘉德拍卖行推出一批珍贵的信札,其中包括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13通27页、梁启超致胡适词稿信札11通34页,徐志摩致胡适信札3通9页,为胡适家族珍藏,信札内容涉及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徐志摩等人之间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与史实,是研究其时其人其事的宝贵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这批珍贵的信札引起了众多私人藏家以及国家文物部门的兴趣,国家文物部门首次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以554.4万元人民币的拍卖成交价从嘉德优先购得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此举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本刊特邀国家文物局、嘉德拍卖行以及法律界的相关人士从多方面对文物优先购买权进行解读,带读者走进这事件的背后,就这一事件对我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展望。
国家首次行使文物优先购买权事件回放
5月中旬
·有关部门在审核嘉德2009春拍拟上拍的标的时,发现27封陈独秀、徐志摩、梁启超等人致胡适的信札,
希望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予以征集。
5月22日
·国家文物局组织国家鉴定委员会专家对这批信札的真伪和价值进行了评定。
有关部门跟拍品委托人沟通,希望可以协商收购,但在价格上未能达成相近的意见。
国家文物局通过拍卖公司发出公告,表明国家将对此场拍卖中的某些拍品按成交价行使优先购买权。
5月28日
·在“中国嘉德2009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的预展现场、竞投登记处和网站上,出现了嘉德拍卖的《重
要声明》,“政府有关部门将对古籍善本专场中的部分标的,根据拍卖结果考虑优先购买。本公司于拍卖结束
后七日内,将政府有关部门是否优先购买的决定通知相关标的买受人。”
5月30日
·嘉德举行古籍善本专场拍卖之前,拍卖师再次重申国家文物局的这一声明。
5月30日
·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13通27页以554.4万元人民币成交;梁启超致胡适词稿及信札11通34页以78.4
万元成交;徐志摩致胡适信札3通9页以112万元成交。
国家文物局经过商议,决定使用国家优先购买权购买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13通27页。
6月5日
·国家文物局向嘉德拍卖发出《关于优先购买“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的函》:对“中国嘉德2009春季拍卖
会古籍善本专场”第2833号拍品“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按照成交价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
在获悉国家文物局的决定后,嘉德于第一时间将文件内容通报给第2833号拍品“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的
现场买受人。得知有关部门的决定后,这位买受人在深表遗憾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于国家收藏机构的理解。
宋新潮(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
国家首次行使文物优先权
这次购买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是我国政府第一次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最开始,我们还是准备根据以往的经验,跟委托人进行协商,但在价格上未能达成相近的意见。实际上,长期以来在拍卖之前商定价格,就一直是制约珍贵文物征集的一个瓶颈,因为文物价格受市场波动影响比较大,而且即使是同一领域里的专家也会给出不同的估量。所谓“优先”应该如何实行?价格应该如何确定?这其中有很多难以操作的因素。
此次为了不再让这批信札流失,或者被藏隐难以用作公众研究和展示,国家文物局决定借鉴有关国家优先购买的做法,在拍卖前通过拍卖公司发出公告,表明国家将对此场拍卖中的某些拍品按成交价行使优先购买权。在拍卖结束后的7天之内,国家将根据拍卖情况作出是否征集的决定。最终国家以拍卖当时的成交价554.4万元购买了其中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
国家优先购买权是否会成为一项常规制度?
此次优先购买权的使用对于文物行政部门而言是一次尝试,更重要的是,根据法律规定和市场经济的原则,进一步制定完善的国家优先购买文物的规则。有关部门和博物馆在近年来的文物征集工作中逐渐意识到,国有收藏机构在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则、如何确定征集文物的公平价格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原来对拍卖市场出现的珍贵文物,有几种处理方式,如限制出境,或者指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定向竞买。但实际上,最后的价格不论是高是低,都有可能被认为不合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价格的判断标准。而且委托人和拍卖公司也会担心被指定的单位如果不出价,其利益会受损。国家优先购买权的实施需要权衡几方的利益:委托人、拍卖公司和公众利益,这些都俩个尺度,需要找到其中的平衡点。
圆明园兽首不属优先权使用范畴
政府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针对的拍品应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如果不由国家出面,则可能会流失海外,拍品在由政府购得后也将转交给博物馆或者公共研究机构去发挥其价值。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针对的拍品必须合法,类似于圆明园兽首等因战争原因被非法掠夺的文物,被不法分子偷盗、偷掘以及非法出境的文物,国家坚持通过追索的方法促使文物回归。
嘉德拍卖文献典籍收归公藏案例
·1995年嘉德秋拍:当时推出一批鲁迅信札,按照国家当时的规定,此件拍品“只限于国家博物馆、图书馆及其他企事业单位购买:私人购买必须捐献给国家”,这批鲁迅信札后被一新加坡人士以7.15万元购得,并捐献给上海鲁迅博物馆。
·1995年嘉德秋拍,孙中山的三封书札,分别以18.7万,10.12万和7.7万元被广东省某国家金融机构购得。
·2000年嘉德春拍:在翁万戈先生珍贵藏书拍卖前,上海图书馆与翁万戈先生达成协议,不通过拍卖,以协商转让的方式将这批珍本人藏上海图书馆。
·2002年嘉德秋拍:钱镜塘所藏的《明代名人手札》,最终通过定向拍卖的方式以990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格最终入藏上海博物馆。
·2003年嘉德春拍:故宫博物院在拍卖前与中国嘉德协商,出2200万元从嘉德购得中国现存书法孤品《出师颂》。
·2004年嘉德秋拍:大金融家陈澄中先生的国宝级藏书在拍卖前整体出让给国家图书馆,这是陈氏书藏第三批收归公藏。
·2005年嘉德秋拍:北京大学图书馆直接参与竞拍1200册程砚秋藏《玉霜簪戏曲钞本》,最终以500万元购得。
·2009年嘉德春拍:嘉德拍卖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国家文物局使用文物优先购买权,以拍卖当时的成交价554.4万元购买。
拓晓堂(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经理)
从“不允许私人购买”到“国家优先购买”
我在嘉德已经工作了十六年,亲身感受到国家对拍卖行的拍品进行收藏所经历的变化。最初,对那些有必要由国家收藏的文物,按照国家当时的文物政策是不允许私人购买的。拍卖时会在图录里写明:“此件拍品只限于国家博物馆、图书馆及其他企事业单位购买;私人购买必须捐献给国家。”这种方式也叫做”定向拍卖”,即国家级别的文物单位以捐献为目的进行的拍卖,参与拍卖的也是一些国家
规定的文物机构、企事业单位等。这样一个政策在1995年之后陆续使用了一段时间,如1995年鲁迅和孙中山的信札和书札的拍卖。但这种形式是在一种没有完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购买,国家买了,但没有人竞争;私人买了,但最终要捐献给国家。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国家在拍卖之前提前买断拍品,不介入拍卖,而是以拍卖公司作为中介,进行转让。比如像翁万戈和陈澄中等藏家的拍品就是以协商转让的方式被国家文物机构收藏的。也有一些博物馆和文物机构直接参与过市场购买,比如北大图书馆就以直接参加拍卖的形式拍得过程砚秋的文献资料。
随着国家《文物法》、《拍卖法》的确定,以上这些不成文、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条款就已经取消了。新的条款规定,所有拍卖品都可以被私人收藏购买,但国家在购买中具有优先权。这个条款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确定,但事实是,国家并没有实施过,因为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规定到底优先购买权该怎么来执行。现在优先权的提出,有一些问题需要考虑,比如说如果国家文物局或文物机构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有可能会对市场的价格产生影响,为了防止有人哄抬价格,国家尽量不参与直接的竞拍,所以近年来国家文物局、文物机构几乎没有直接出面参与竞拍。
法律细则将尽快规范
其实国家在私下通过拍卖公司这样的中介和委托方协商进行提前购买有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国家并没有以市场价格进行直接的文物收购,而是以一种商议的价格来收购。从市场角度看这样做没有完全保护委托人和拍卖行的利益。当然,作为中介,拍卖行为国家做一些贡献,让出一些利益也是应该的,但作为委托人来讲,他们的利益长期得不到保护,是不利于市场健康的法律程序制定的,而且也会导致很多藏家不愿意把藏品出手。这次的胡适信札,国家一开始也是希望进行提前收购,但没有协商成功。因为出品人对自己的利益有所考虑。国家在协商不成功的情况下才第一次动用国家优先购买权。这是个很大的进步,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在这过程中,嘉德和文物局就文物优先权的使用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包括如何告知竞拍人这条政策,同时也参考了海外的经验。
我们在拍卖之前先公示国家文物局的相关指令,即国家有可能对这几件拍品实行优先购买权。所以在竞拍之前,所有竞拍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嘉德在拍卖现场也做了告示。
通过这次国家优先权的成功使用,我觉得新的文物拍卖的细则很快就会出台,而且以后这种优先权的使用会扩散到所有的拍品中。文物细则的出台一方面确保了国家文物收购优先的权利。另一方面,如果以后国家对所有拍品都具有优先购买权,那么就不存在对竞拍人公不公平的问题了。这次是一个案例,中国的法律细则就是在有了案例之后,才慢慢完善起来。
我觉得这次国家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一个最大的进步体现在把国家文物购买纳入到不影响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又保证国家走向法制的轨道,确保了委托人的利益,从多方面来讲都变得规范了。
此信札现场买受人的大度与远见
有很多人都为拍场上拍得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的藏家感到可惜,毫无疑问,他在心理上肯定也会有一些不平衡,但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位藏家感到不平衡的地方不在于国家把他拍到的东西优先购买,而是他在失去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的同时,也没有拍到随后举行的徐志摩致胡适信札。这位藏家在徐志摩致胡适信札的拍卖过程中喊价喊到一半,后来一想,自己已经拍得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所以就没有尽全力拿下徐志摩致胡适信札。谁知道后来两件拍品都与自己失之交臂。其实国家优先购买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这位藏家觉得挺光荣,因为他觉得自己看重的拍品,国家也同样看中,说明自己的眼光很独到。
而且这位藏家也非常大度,很懂得这件事在法律上的意义。我也跟他说过,当相关的法律健全起来之后,对他的收藏也是一种保护。万一有天。这位藏家把自己的藏品拿出来拍卖,就有法可依,自己的利益也可以得到保障。如果国家能走上正常的法律轨道,将实现多方的共赢。
当时国家优先购买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后,还提出由国家文物局领导见见这位藏家,给与他一些表扬和表彰,但这位藏家非常支持国家这次的举动,而且也希望可以借此早日完善相关法律,所以很安然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没有向国家提任何要求。对这样的藏家,我们也感到非常敬佩。
文献档案之于国家的意义
从多年来国家收购拍卖行的文物来看,信札或者古籍是收购比较多的类型。这是因为,对任何个习家而言,艺术品在国家的收藏中,远不能跟那些有助于国家的法制、思想、文化等的典籍相比。跟一张画或一个瓷器相比,珍贵的文献资料在国家的法制和文化建设上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国家屡屡在典籍这方面出手。
刘洋(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律师)
从法律角度解读优先购买权
优先购买权是一个民法概念,它属于物权法律范畴,但国家先买权在我国民法上只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十八条:“文物行政部门在审核拟拍卖的文物时,可以指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优先购买其中的珍贵文物。购买价格由文物收藏单位的代表与文物的委托人协商确定。”这次国家文物局使用优先购买权,就是依据这一条款,当然是合法的。
此次国家行使优先购买权与之前的拍前协商、定向拍卖等相比起来是有很大进步的。首先。国家购买文物体现的是一种国家民事权利,体现了各类民事权利主体的权利平等观念,(至少从形式意义上较之于拍前协商、定向拍卖进步)它是符合现代法的理念,是国家进步的一种表现。
希望以后国家文物局能制定一个规章,把这个问题规范化起来。首先,应该有个权利层级的分配。比如,国家级的文物管理部门如何行使优先权?省一级文物管理部门又该如何行使优先权。为了避免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之间相互抢购,哄抬物价,使得文物偏离本身价值,有必要详细规定各个部门具体的权利,指定具体的优先权实施单位。
第二个就是程序管理问题。不能说任何一个文物管理单位认为这件拍品有价值,那么这件拍品就有价值了。上级的文物管理部门,应该制定一个审批制度,避免优先权行使上的随意性。
第三,在具体规定了国家优先购买权如何行使之后,国家就不需要对每一个拍卖会都提前进行声明。这样可以避免一些道德上的风险那就是,一旦出卖人知道国家要对某件物品行使优先购买权,很可能会串通另外一个“托”来举牌,拉升价位。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认为,这个规章可以规定:所有的拍品,我们的国家都应该享有潜在的优先购买权。所有的拍品在拍卖之后,应该给予国家有几天的沉默期,在这段沉默期之内,国家随时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过期作废。
文物购买权的跨国尝试
国家行使优先购买权,必须在国家法律所管辖的范围内行使,但现实是,我们抢救流失文物很多情形都是发生在国外市场。面对这种情况,我想我们在立法上可以进行一些创新尝试。我建议国家指定某一个部门和外国的一些大拍卖行,比如说苏富比、佳士得等发出一个邀约,希望可以签订一个协议,用协议的形式确定我们的国家优先权。一旦形成协议,拍卖行将会将其写进“拍卖章程”,当这些拍卖行在拍卖中国文物的时候,无论是出卖人还是买受人还是中介人,必受这个拍卖章程的约束。这样一来,我们的国家优先权即能在境外实现。如果国外拍卖行和中国有着良好的关系,而且在不影响它以及委托人利益的情况下,这种台同是有可能签订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国家优先权通过合同的形式拓展海外的空间。
在海外行使优先权为我们文物追索创设了一个很好的建设性的思路,但仅限于那些合法的文物,对于那些通过非法途径流失在海外的文物,我们不光不行使优先权,不参与拍卖,而且还要对这些文物进行追索,希望借助这次国家文物优先购买权带给我们的启示,可以探索出更多保护文物、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