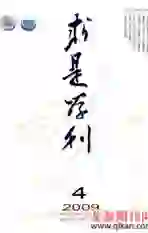明代文学生态与帝王的诗歌态度
2009-08-04郭万金
摘要:封建体制下的至尊君王对诗歌发达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有明十六帝,勤荒仁暴,群象各异,但对于诗歌却没有太大兴趣,部分君王虽以形式各异的赋诗、赐诗行为维系着自己作为国家文化最高象征的天子形象,但这种诗歌行为大多有着逸出文学指向之外的政治色彩和文化意义。明代君王对于诗歌并无特别的爱好,更无着意的提倡鼓励,而此则成为明诗难及唐、宋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明代;帝王;诗歌;关注
作者简介: 郭万金(1979—),男,山西阳曲人,文学博士,山西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明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4-0112-06收稿日期:2009-03-23
传统的文学并没有太多的独立品格,就一般的职能分工而言,作为被边缘化的“杂学”,并非必须的社会构成,亦非如道德功业般有着必须履行的追求义务,故而,文学的发展更多地取决于社会主体的态度与兴趣。封建体制下的至尊君王是传统社会中最具号召力的主体,特殊的政治地位与文化身份,使得帝王的个体行为通常有着超乎寻常的社会张力,亦成为文学生态中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历览群史,文学的称盛大抵来自上层统治者的关注与兴趣,且不说采诗观风、润色鸿业之类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学态度,单是文学“自觉时代”的造就即与三曹的文学兴趣关系甚深,而历代史书的《文学》、《文苑》列传中,帝王的诗文关注更是文章盛业的关键所在,诸如《南史·文学传》、《旧唐书·文苑传》、《宋史·文苑传》中的君王莫不扮演着奖掖文学的重要角色。降及蒙元,草原民族的统治者于汉家诗文并无太多的兴趣,《元史》中的“文苑”被纳入“儒学”之中,以“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1](P271)一笔带过,其中固然夹缠着明代史官的文学判断,但从史实现象的陈述分析中亦可看出,缺乏君王关注的元代正统文学实难称盛①。
朱明王朝以恢复汉统为志,标举盛唐,文士彬彬,亦颇成景观。然《明史·文苑传》中却不见帝王踪影,君王的缺席大致表明了明代帝王的诗歌兴趣与文学态度,复汉归唐虽是国家的文化理想所在,但最高统治者于诗歌的推扬鼓励实在有限。除蒙元外,明代君王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乏文采的帝王群体了,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所载,有明十六帝中,有诗留世者不过太祖(五卷)、仁宗(二卷)、宣宗(六卷,乐府一卷)、英宗(诗文一卷)、宪宗(四卷)、世宗(诗赋七卷)、神宗(诗文一卷)七人而已,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明史·艺文志》大略相承,唯《艺文志》增录《孝宗诗集》五卷。此外,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有建文帝诗三首,武宗诗12首,却无英宗、宪宗诗,陈田《明诗纪事》称,明成祖有集,并录其诗五首。姑且不论历来帝王诗文数量中含有的大量水分,单是这10位君王所留下的诸体混杂也不足30卷的分量已经说明了明代帝王们的文采如何了,亦可见他们对诗歌有多少兴趣了。文艺是“有闲阶级”的专利,朱元璋是明代帝王中最勤政的一个,但他的诗歌数量却名列前茅①,可见,在其身后的“有闲子孙”实在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明太祖朱元璋废相集权,威柄独操,成为朝廷文化的绝对核心,其于文化建设的决策、态度,文章诗赋的关注、理解,乃至个人的审美趣向,莫不成为影响一代文学生态的日照因素。有明一代的文化建设于重修礼乐、汉统恢复的核心价值中全面展开,而朱元璋的文学关注亦于其恢复礼乐的文化心态中凸显出来:
古乐之诗,章平而正;后世之歌,词淫以夸;古之律吕,协天地自然之气,后之律吕,出人为智巧之私;天时与地气不审,人声与乐音不比,故虽以古之诗章,用古之器数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伦矣。手击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与乐,判然为二,而用以动天地,感鬼神,岂不难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难,卿等宜求诸此,俾乐成而颁之诸生,得以肄习,庶几可以复古人之意。[2]
立足于礼乐修复的诗歌关注虽非纯粹的文学态度,但复古倾向已是十分明确。所谓复古,固然在远承三代、近续汉唐的文化统绪,就其美学意义而言,则还包含着一个关于“古”的审美认知——古朴、古雅的美学宗尚。以峻法治国的朱元璋身上当然有着好质恶饰的法家思想,幼遭艰辛的贫民经历更培养出其节俭质朴的生活观念,当这些个人因素与复古的文化心态相结合时,质朴古雅自然成为最为凸显的审美诉求,并成为其文学观照中的一种普遍美学观念。朱元璋曾说过:“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诰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3](P49)复古思路下的文风改革所体现的正是不事雕琢的美学主张与讲求实用的功利取向。“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4]于作为对象的“文”而言,简古无饰为其审美趣向,于作为主体的“人”而言,质朴通达为其取用标准,朱元璋的基本文学关注大抵如此。《明史·本纪》赞其“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5](P50), 颇为中肯。在朱元璋的立国思想中,法家的治国模式与儒家正统的礼乐提倡中都不曾给诗文以特别尊崇的地位,其诗歌态度大抵包含于文章关注之中,并无特别的爱好提倡,至多不过是点缀升平的余事,而且必须合乎古朴的美学规范。
朱棣少长习兵,戎马一生,堪为一代雄主。尽管也有尊崇儒学、编纂图书的兼修文治,然溯其情性志趣,并不在诗赋文章。其对皇长孙朱瞻基的讲学儒臣即言,“夫帝王大训,可以经纶天下者,日与讲说……不必如儒生绎章句、工文辞为能也”[6]。“经纶天下”不以“工文辞为能”的帝王气度实已透露出这位永乐皇帝一如其父的文学关注。
一般而言,守成君主大多有着较好的教育背景,除去个人因素外,通常都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作为明初二祖之后的守成之君,仁宗朱高炽的才学素养自然远胜父祖,然而太子时代的诗歌兴趣因杨士奇“非帝王之事”的进谏打消不少[7],登基后沉溺酒色,不过一年短祚,自然不会对诗歌有特别的提倡。倒是他的儿子明宣宗朱瞻基“天纵神敏,逊志经史,长歌短章,援笔力就”[8]。《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自十四卷以后为诗词,各体皆备,并有乐府小令,总数当在千首左右,居明帝之冠,亦可跻身列代帝王诗人之列。朱瞻基无疑是明代诗歌兴趣最浓的帝王,然这位风流儒雅的青年皇帝,自幼即在宫廷文化的熏陶之下,沾染了不少贵族子弟的玩乐习气。举凡书画游猎、斗鸡促织、抚琴作乐,莫不投入。诗歌非其独爱,在诸多兴趣的分散之下,对于诗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提倡。朱祁镇七岁即位,虽然每日修习经书,却更愿意接受以王振为首的太监们为其设计的各种娱乐活动。当他以一代帝君身陷囹圄,也未见有寄情诗歌的表现;复辟之后,励精图治,敬天法祖,遗命废止宫人殉葬,颇有些贤主的味道,于诗亦无太多关注。全部诗文合起来不过一卷,微薄的分量已是很好的证明了。明景帝朱祁钰继统于危乱之际,这位守成之君的文治关注亦在尊儒、存书数事,并无特别之处,几部相关的明诗文献亦未提及景帝有诗作留世。至于宪宗朱见深,《明诗综》称:益庄王《勿斋集》有《恭次皇祖宪宗皇帝四景连环诗韵》四首,今不得而见,然所作亦不过游戏文字耳。可知,明宪宗虽也“间留意于诗章”[9],但宠万妃,溺佛道,好方术,喜游乐,善绘画已然耗去了全副精神,又何暇顾及诗歌呢。
孝宗朱祐樘无疑可算做明代守成之君中的佼佼者,除却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这些儒家规范下的必须行为外,其后宫生活同样可圈可点。不近声色的朱祐樘无疑成为贴合儒家帝王理想的道德典范,然而,诗歌并非正统帝王观念下的必为之事,全在君王个人兴趣。朱祐樘体质孱弱,“上体稍不佳,即诵诗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其善于颐养如此”[10](P10)。又“孝宗在御日,遇午节曾于便殿手书一桃符云:‘采线结成长命缕,丹砂书就辟兵符。盖圣主好文,宴衎自娱又与后圣不同如此”[11](P68)。这明白无疑地表明了孝宗的文学兴趣不过“宴衎自娱”而已。朱祐樘“置《永乐大典》于便殿,暇即省览,又命儒臣集历代御制诗以为规范”[9],儒臣于历代帝王诗作的取裁中当然有着合乎道统的判断,其终极指向原在为君之道的借鉴,并非诗歌的关注。指向自身的文学态度,同时又要服从于传统明君观念下的形象塑造,朱祐樘于诗歌的提倡自然有限得很。明武宗朱厚照亲女嬖,建豹房,荒淫放荡,无所不为,自封大将军,禁令杀猪,莫不体现出这位正德皇帝的率性而为,诸多的爱好中并无诗歌。明世宗朱厚熜以藩王继位,锐意求治,无论是理国观念,还是施政方式,大抵皆是依照儒家明君观念的形象塑造。少年时的诗歌濡染并未因入继大统而转移,“世宗初政,每于万几之暇喜为诗,时命大学士费弘、杨一清更定。或御制诗成。令二辅臣属和以进,一时传为盛事”[11](P38),然而,这样的盛事不久便因“大礼议”而中辍了,“张璁等用事,自愧不能诗,遂露章攻弘,诮其以小技希恩。上虽不诘责,而所出圣制渐希矣”[11](P38)。张璁的抨击对象虽不是嘉靖,但他竟然引以为戒,“圣制渐希”,即此可知,对正统观念熏陶下的嘉靖皇帝而言,诗歌不过“小技”而已,虽然有着一定的兴趣,却远不能与制礼作乐、模范天下的天子职守相提并论。略微的间接指责便足以令其轻易放弃,自然不会有特别的提倡了,更何况还有压倒儒学帝王观的道教崇拜。仅有的文学兴趣亦全部转移于青词撰写,取媚道教神祇的文字成为后期朱厚熜唯一的文学关注,其中的韵文体青词虽也可纳入广义的诗歌范畴,但嘉靖的提倡却实在算不上是对诗歌的积极态度。
明穆宗久居藩王,生活清贫,躬行俭约,即位后,却以纵情酒色的方式宣泄着久被父皇压抑的积郁,溺于女色,且喜驰马武事,自然不会对诗文发生兴趣。明神宗朱翊钧十岁登基,早岁励精,唯一兴趣便是书法,却因张居正“帝王之学,当务其大”[12]的进谏而取消,赐书臣下的行为也减少了不少。被纳入文章之属的诗歌则同样被目为技艺之流,不足为帝王留心。偶然的诗歌关注夹杂于“文史篇什”的整体留意之中,最为隆重的仍是事关君王进德修业、治理天下的经筵讲习,朱翊钧对于诗歌实无特别的兴趣。而后期的明神宗沉溺于酒色财气,消极怠政,原本就兴趣不高的诗歌就更不予理睬了。仅有一月帝祚的明光宗,生前“梃击”,亡于“红丸”,故后“移宫”,三案构争,党祸益炽,自然不会对诗歌留意。匆忙继位的朱由校成为明史上唯一一位未曾出阁讲读的皇帝,“好儿弄,既即位,当东西交閧之日,耳目不及文书”[13],怎会留心诗文呢?继统于危难之际的思宗朱由检“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5](P121)。虽有儒者风范,却无文人习性,甚少诗作。且身处末世欲力挽狂澜,一生勤勉,更无暇文艺了。
有明十六帝,群象各异,几可缩微历代君王图景,或勤勉或荒怠,或暴戾或仁懦,然而,传统观念下的君王行为中,诗歌本身并不属于可以提倡的规范行为,帝之留心,当务大者。纳入明君体系的帝王或者有些兴趣,却不能有意提倡,当然也包括那些庸碌平常的中材之主,接受了为君之道,却无力完成,守成无为,当然也不会于诗歌特别鼓励了。至于被归入昏君、荒君之流的皇帝们,流连声色嬉戏,哪里还会眷顾诗文雅兴——明代帝王的一般诗歌态度大抵如此:并无的特别的爱好,更无着意的提倡鼓励。
虽然未获得传统为君之道的合法认可,但较之声色犬马,诗歌作为帝王万机之余的性情陶冶、文治点缀,无疑有着更为合理的存在意义,而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一般观念更为诗歌的文化价值提供了理论辩护。更重要的是,从先秦时代诗礼、诗乐的绾结到以赋诗行为为标志的春秋礼乐文化,再到“不学诗,无以言”的立身准则,“诗”成为君子修养的最佳文化体现。尽管《诗》三百后来被尊为圣经,褪去了文学的色彩,但已然浸染了“礼”之文化品质的诗歌,实已成为士人阶层的一种行为标志,并在“礼以别异”的等级社会中积淀为彬彬君子的文化身份。作为一般君子文化身份象征的诗歌同样可以应用于“奄有四海”的天下之君。日理万机的君主虽有着不事诗歌的合理借口,位极人伦的帝王亦不需要以诗赋风雅来证明自己的至尊身份,然而,作为统治阶层的最高代言人,无论是礼乐表率的职责所在,还是融洽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政治需要,抑或是点缀升平的文治建设,都要求帝王在一定的人文生态下以赋诗、赐诗的文学行为维系自己作为国家文化最高象征的天子形象。
朱元璋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于戎马军旅中征访耆儒宿学,勤于学问,乃后遂能操笔成文章。其尝谓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14],将“无师成文”认作“天生之圣”,自我夸耀的背后或可想见朱元璋钦慕文雅之情状;或者说,即位后的锐志雅乐固然有着恢复汉制的文化心态,亦隐含着这位平民天子文治粉饰的形象塑造。
明人陈宏绪称,“高皇帝以至正壬寅幸龙兴,谒孔子庙,过铁柱观,复出城,开宴于滕王阁,诸儒咸赋诗为乐”[15](P21)。时为吴王的朱元璋虽未亲自参与,却已然表现出了融洽君臣、修文为治的积极态度。他登基之后,勤政不倦,然同游唱和亦屡为举行,“当时儒臣,每侍上游观禁苑,凡亭楼台阁。靡不登眺,以通上下之情,成地天交也”[16]。朱元璋借同游开言路,融洽君臣,以促进统治集团整体化的施政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而偃武修文的立国方针亦于升平点缀中体现。更重要的是,朱元璋这位出身微贱的马上皇帝已然在诗赋风流中褪去了“不识诗书”的草莽气息,君臣同游,燕享赓和的熙熙皞皞中俨然营造出一派有德有言,文武兼备,足以代言天下的圣王形象。然而,继承帝业的朱家子孙却大多没有这样的思路,这些长于深宫的皇家子弟一般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却没有创业甘苦的直接感触,自然不会有洪武开国时刻意的形象塑造,而宫廷生活所培养的唯我独尊、颐指气使更令其难以融洽于未曾共事艰辛的群臣僚属,对于“君臣同游”的理解自然有限。
依照守成君主模式所培养的建文帝于朱元璋的“君臣同游”领会颇深,靖难烽烟四起,尚且“宴群臣于奉天殿,大祀庆成也。是日,群臣大欢会,赋诗纪成,颁天下”[17]。惜其在位仅及四载,未见规模。明成祖以武力篡权,于帝王形象倒是颇为留心,其用力之处原在耀兵域外,四方咸宾的天朝规模,标志文治的重头戏则是《永乐大典》的编纂。皇皇巨制正是天朝大国之文化表征,其后所蕴则为“大一统”的帝王心理:江山一统,四海咸宾的气象规模方是夺了侄儿皇位的永乐帝的用心所在,以一代垂统之君,燕享群臣,点缀文治的诗赋行为亦多为此心态下的产物。但朱棣并没亲自加入赋诗之中,所保持的仅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赏赐行为,洪武时君臣同游的政治意义实已开始消退。 宣德间,“海内宴安,天子(宣宗)雅意文章,每与诸学士谈论文艺,赏花赋诗,礼接优渥”[5](P1092),“当是时,帝(宣宗)励精图治,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5](P1077)。这位多才多艺的太平天子倒是颇为准确地贯穿了“君臣同游”的祖训意图,更增添了些刻意媲美前贤帝圣的标榜心态。若“宣宗御文华殿,召大学士杨土奇、杨荣、金幼孜,特赐鲥鱼醇酒,加赐御制诗,有‘乐有嘉鱼之句,士奇等霑醉献和章,上嘉曰:‘朕与卿皆当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几不忝祖宗之付托”[18](P165),朱瞻基志在有为,不甘落后父祖,比附前王的帝王心思于中可见。然而,宣宗之后的明代帝王于诗歌大多没有特别的喜爱,更循着守成之君的荒废规律,步步堕落,略不以帝王形象为念,“君臣同游”自然也便成为阁臣、学士、亚卿偶然得“沐”的天恩,至于赋诗更是少见。
明代君王的赋诗情状大抵如此,作为帝王的一种示恩方式,赐诗与赋诗一样,有着融洽君臣关系,维系帝王形象的文化寓意。相对于赋诗行为的集体性而言,帝王的赐诗虽有着不可避免的政治动机,却也包含着更为明显的个人色彩。
朱元璋对于开国规模的营造以及天子形象的树立颇为关注。除却频繁的同游赓和之外,亦屡屡赐诗臣下:张紞出为云南左参政,“陛辞,帝赋诗二章赐之”[5](P1087),范常乞归,“帝赋诗四章送之,赐宅于太平”[5](P1022),“(陶安)坐事谪知桐城,移知饶州。陈友定兵攻城。安召吏民谕以顺逆,婴城固守。援兵至,败去。诸将欲尽戮民之从寇者,安不可。太祖赐诗褒美。州民建生祠事之” [5](P1024),“遣(李质)振饥山东,御制诗饯之”[5](P1035),不难看出,朱元璋的赐诗多是“因事而作”,“有为而赐”,褒美鼓励之意多于诗中,就赐诗的赏赐意义而言,还可以延伸出另外一种“赐诗”行为——因诗受赐。文学侍臣的职责多在“点缀文治”,因之获得奖赏自不算稀奇,但适合帝王脾味却是必要的前提,而君王的文学好尚亦可于中折射一二。“一切谀词艳曲皆弃不取”[5](P415)的朱元璋对于一般的称颂拍马颇为厌恶,但于 “龙兴”、“帝业”之类的颂美拍马却颇欣赏,所谓的“称旨”全在皇家气象的烘托,圣王天子的形象凸显。
同为马上皇帝的朱棣却于诗歌不甚留意,甚少诗作,解缙、胡广虽多次侍驾游宴,然赐诗殊荣却仅见于与其关系特殊的姚广孝,朱棣于姚广孝的天恩眷顾或多因个人情意,而其赐诗外国的动机则全在帝王形象的维系:“永乐五年,授交趾明经甘润祖等十一人为谅江等府同知,赐勅慰勉,仍赋诗一章各送之。”[19](P235)交趾所举的明经进士竟然有等同姚广孝的赐诗殊荣。朱棣屡次加封外国之山,必亲制碑文,赐以铭诗。朱棣对诗歌并无太大兴趣,接连亲为的赐诗之举所体现的正是明成祖的核心关注。古所未宾之国的朝贺臣服最是辉煌帝业的政治标志,炳耀夷裔的御制铭诗无疑有着维系天朝圣主形象的文化意义,永乐皇帝慨然赐诗的真正动机亦在于此。
“尤喜为诗”的朱瞻基当然是赐诗最多的明代皇帝,宴游赋诗时的主角独唱、不重赓和实已有着面向群臣的赐诗色彩。朱瞻基长于宫禁,受学儒臣,缵继大统后,守成父祖鸿业,按照儒家圣王理想的塑造明主形象自然成为这位太平天子的历史使命。“宣庙尝诏令临御以来三科进士御文华殿亲试之,拔其尤者……进学文渊阁,其优礼给赐,一循永乐甲申之制,仍赐御制诗以示勉励。”[20]近乎雷同的“君臣同游”中正可窥见朱瞻基继踵先祖的守成情结,当然,较之祖辈,朱瞻基的身上有着更多儒家观念下的“仁君”色彩,赐诗中每每体现出仿效古圣贤王的民生关切,这些赐诗作为“王道”、“仁政”思想的文学体现,自然有着“亲民”帝王的形象塑造,却也不乏指向现实的政治意义。朱瞻基是天资聪颖,颇富诗才的太平天子,享国十年的安定气象更为其提供了“自是太平多景象,偶因临眺一题诗”[21]的创作动机。因兴而就的诗作并无特定用意指向,而赏赐的对象自然也就随意了许多。如此的赐诗行为中显然有着更多个人感情的投射,而略带游戏色彩的文采炫耀亦仅能以内侍作为对象,毕竟在儒臣眼中,这样的行径都属于帝王不当为的“余事”,其实,朱瞻基本人所接受的帝王观念中亦有着同样的认识。故而,这位明宣宗的赐诗一面有着关切民生的仁政体现,一面却保持着偶尔为之的“余事”态度。
帝王的赐诗多与个人兴趣、文学修养相关,宣宗之后的明代帝王大多于诗歌没有太大的兴趣,赐诗的恩典自然也就少了许多。以赐诗而论,有明一代,堪与宣宗相比者,唯有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初,励精图治,与朱瞻基确有相似,均为颇喜为诗的有为之君,赐诗臣下均系常事。相似的知识背景亦使得朱厚熜的赐诗内容多与朱瞻基相似,均为王道思想下一以贯之的民本关注。唯朱厚熜颇重礼法,赐诗之恩仅及朝臣,不像朱瞻基,将太医、内侍都纳入赐诗对象。至其深溺道教后,赐诗行为绝少为之,以严嵩之专宠,却未见有太多的赐诗殊荣,由之亦可知其诗歌兴趣之转移。及至末世,思宗朱由检虽甚少作诗,却赐诗武臣杨嗣昌、秦良玉,勉励旌表中满是殷勤寄寓,朱由检帷幄无人,孤注一掷的深层心理亦可于中读出。刚愎个性下的自我辩护虽有着十七年为帝的品行依据,然而,君临天下的帝王形象却已在其诗篇背后的无助心态中崩溃了。
明人胡震亨称:“有唐吟业之盛,导源有自。文皇英姿间出,表丽缛于先程;玄宗材艺兼该,通风婉于时格,是用古体再变律调一新,朝野景从,谣习寖广;重以德宣诸主,天藻并工,赓歌时继,上好下甚,风偃化移,固宜于喁徧,于群伦爽籁。袭于异代矣。中间机纽,更在孝和一朝,于时文馆旣集多材,内庭又依奥主,游燕以兴其篇,奖赏以激其价,谁鬯律宗,可遗功首。虽猥狎见讥,尤作兴有属者焉”[22],并将唐代的“吟业之盛”归于君王的表率与倡导,又称“唐人诗集,多出人主下诏编进。如王右丞、卢允言诸人之在朝籍者无论。吴兴昼公,一释子耳,亦下敕征其诗集置延阁。更可异者,骆宾王、上官婉儿,身既见法,仍诏撰其集传后,命大臣作序,不冺其名。重诗人如此,诗道安得不昌”[22]。由“更可异”的不解到“安得不昌”的心态转折中,既有对唐诗昌盛的艳羡,更暗含着对本朝诗歌失宠于君王的叹惋。胡云翼先生曾将“君主的提倡”列为“宋诗的发达”首要原因,并指出,“历代文学发达,与君主的提倡都是有很深的关系。如汉赋、唐诗都是受了政治的特别提携,才得格外发展。宋代虽不是诗的时期,然那些帝王都有些诗癖,竭力奖励提倡于上,一般文人为了升官发财起见,自然风靡于下”[23](P18)。然而,明代帝王却没有这样的诗癖,所表现出的仅仅是作为一般惯例式的有限提倡与鼓励,既没有特别的排斥,也没有特别的热情。
帝王以一身系天下,诗文小技,固非所重。传统的为君之道实已极大限制了帝王的诗歌行为。然而,君王的赋诗与赐诗大多有着逸出文学指向之外的政治色彩和文化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为儒学意识所认可的合法性,亦为帝王的诗歌兴趣开辟了一条合理的表现渠道。明代以理学开国,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观念对列朝帝王的一般诗歌态度自然有所规限,然而,即使在颇为许可的赋诗与赐诗中,我们同样没有见到明代君王对于诗歌的特别提倡。十六朝中仅有洪武、宣德、嘉靖前期略有规模,足见明代帝王对诗歌兴趣实在有限。算不上热衷的诗歌态度并不足以成就有明一代的“吟业昌盛”,缺乏最高权威的有力支持,明诗生态中的日照时间大大缩短,自不足以重现唐宋诗歌的文学生态,所谓的承唐越宋,在诗歌生态的初成之际,便已经大打折扣,生态要素的缺乏更使得这一口号只能停留在理想层面的美学讨论之中,无法再现。
参 考 文 献
[1]宋濂等. 元史,卷189[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2]李之藻. 頖宫礼乐疏,卷1[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余继登. 典故纪闻,卷3[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廖道南. 殿阁词林记,卷5[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6]明太宗实录,卷49[M]. 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8.
[7]杨士奇. 东里集,卷2[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钱谦益. 列朝诗集,乾集卷上[M]. 影印清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
[9]朱彝尊. 明诗综,卷1[M]. 清乾隆刻本.
[10]陈洪谟. 治世余闻,上篇卷1[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卷2[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明神宗实录,卷33[M]. 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8.
[13]查继佐. 罪惟录,帝纪之十六[M]. 四部丛刊本.
[14]不题撰者. 翦胜野闻[M].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15]陈宏绪. 寒夜录,卷中[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16]廖道南. 殿阁词林记,卷12[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姜清. 姜氏秘史·卷4[M]. 豫章丛书本.
[18]余继登. 典故纪闻,卷9[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19]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卷14[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20]蒋一葵. 尧山堂外纪,卷82[M]. 续修四库全书本.
[21]朱瞻基. 江亭晓望[A]. 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35[C].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22]胡震亨. 唐音癸籖,卷27[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3]胡云翼. 宋诗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1993.
[责任编辑杜桂萍]
Literary Ecology and the Emperors Attitude
of Poem in Ming Dynasty
GUO Wan-jin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China )
Abstract: The emperor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ha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em. But the sixteen emperors in Ming Dynasty who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 have no interest in poems. The emperors in Ming Dynasty compose and grant poem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image as the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 but the poetic behavior is mostly associated with the political color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beyond the domain of literature.They do not have special hobby of poems, needless to say to promote it. Therefore this explains the fact that Ming poems have not restored the prosperity like that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emperor; peom; foc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