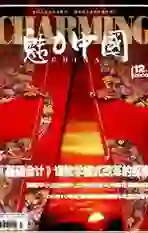浅论职务侵占罪主体与身份
2009-05-14李江武金涛
李江武 金 涛
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具备特定身份或资格的自然人。如何理解《刑法》第271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内涵是确定主体身份的前提。此外,职务侵占犯罪属于典型的身份犯,欠缺此身份不能单独成立本罪,但可以和有特定身份者共同实施。这就涉及到共犯与身份结合,如何定罪量刑问题。
一、职务侵占罪主体范围认定
现今世界上多数国家刑法中没有单独规定职务侵占罪,而是把这种犯罪行为包括在侵占罪或者盗窃罪中,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加以规定。不过,和大陆刑法相似,台湾刑法则进行了详细的区分。台湾刑法首先分别规定了业务侵占和公务侵占。公务侵占或公益侵占相对应的是大陆刑法中的贪污罪,而业务侵占罪之规定,则与大陆刑法职务侵占罪有一定区别。业务侵占罪是指行为人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而侵占对于业务上所持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构成主体同样是特殊身份者,以从事某业务为限。
大陆刑法从法律规定上看,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是清楚的,但是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具体范围的界定,司法工作者乃至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是否必须是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非国有单位的人员
多数学者认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也就是说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的性质不影响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有观点认为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从事职务的人员不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因而,应将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劳务的人员,视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是否限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的含义,即职务应既包括公务行为也包括劳务行为,对刑法第271条第1款中所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仅应理解为从事公务活动中主管、管理、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也应包括从事劳务活动中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将本单位数额较大的财物占为己有的,当然应以职务侵占罪论处。
据此,笔者认为,对于职务侵占罪主体身份的界定,只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公司性质在所不问),利用职务便利即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的人员(既包括公务活动便利也包括事务活动便利)。
二、共同犯罪与主体身份分析
身份,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包括构成身份与加减身份。前者又称纯正身份、定罪身份,是指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身份,不具有此身份,犯罪就不能成立;后者又称不纯正身份、量刑身份,是指虽非构成要件但影响刑罚轻重的身份,法律规定对具备这种身份者予以加重、从重或减轻、从轻处罚。日本学者认为“共犯与身份”的实质问题就在于如何解释第65条的规定,而该问题的核心又在于,在第1项中,“ 身份”连带作用于非身份者,尽管非身份者并无“ 身份”,但仍作为“有身份者”加以处罚;而在第2项中,“ 身份”却发挥个别作用,对身份者与非身份者分别予以处罚。
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职务侵占罪的共同犯罪主要表现为以下类型:一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之外的人员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侵占本单位财物的,即无身份者加功有身份者;二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侵占本单位财物的,即具有不同身份者勾结作案。对于以上的类型如何定罪量刑,理论界观点林立,众说纷纭,争论症结在于,无身份者勾结有身份者共同犯罪时,无身份者取得共犯地位的理论基础以及在定罪量刑中如何分辨无身份者与身份犯。这也和上面论及的日本学界的争论实质相似。目前,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主犯决定说
该说认为应以主犯的身份来确定共同犯罪的犯罪罪名,主犯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应定贪污罪,对其他共同犯罪人也按贪污罪定罪判刑;主犯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对其他共同犯罪人也按职务侵占罪定罪判刑;主犯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以外的人员的,应认定侵占罪,对其他共同犯罪人也按侵占罪定罪判刑。主犯决定说,是解决司法困境的无奈举措,但在身份和供犯罪问题上存在漏洞。但这一观点并未得到理论界的普遍认同,理由有三个:一是主犯和从犯是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划分的,解决的是量刑问题,而非定罪问题;二是主犯若为两人以上,且多人身份不同时,无法以此标准定罪;三是依照此标准在只有一名主犯的情形下,虽然共同犯罪的性质很容易确定,但是却牺牲了从犯获得公正一致的刑法评价为代价的,违反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二)分别定罪说
该说认为,身份对身份犯的成立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身份意味着主体负有专门的身份义务,身份犯是基于身份义务而设立的,没有身份者就没有身份义务,因而不可能构成身份犯。如果无身份者和有身份者一起共同实施犯罪,应当按照无身份的犯罪和有身份的犯罪分别定罪。据此,如果主体具有不同身份,则应根据主体的不同身份分别定罪。即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定贪污罪,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定职务侵占罪。存在的问题是,如果分别定罪就体现不出共同犯罪的特性,就无法与单独犯和同时进行区分。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明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与身份犯共同犯身份犯罪时,无身份者以身份犯所犯之罪定罪的情形。
(三)实行行为说
该说认为,应以实行犯实行行为的性质来决定共同犯罪的性质。所以,无身份者帮助、教唆有身份者实施或与之共同实行纯正身份犯的,应依有身份者的实行行为来定罪,即构成身份犯的共同犯罪。在职务侵占罪中,无身份者不可能单独成立实行犯,只有公司、企业或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犯可能成立实行犯。该说的缺陷在于:首先,在定罪的依据上存在理论争议。我国通说认为认定行为性质的依据是犯罪构成,实行行为只是犯罪构成的一个方面,不能替代犯罪构成。其次,当不同身份者同为实行犯时,到底应依哪种身份犯的实行行为定性,没有定论。
笔者认为,虽然以上各说均存在一定缺陷,但根据实行犯的犯罪性质来确定共犯的犯罪性质和其他学说相比较,仍具有进步性。批判认为,我国通说认为认定犯罪的依据是犯罪构成而不是实行行为。笔者认为,这一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实行行为说并不是否认犯罪构成通说。以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公司、企业人员各自利用职务便利,共同实行犯罪行为为例,两种身份犯都是实行犯。按照犯罪构成理论和共同犯罪学说,双方虽不具有对方的身份,但仍可以共同犯罪,这是毫无疑问的,据此,可以得出双方同时构成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现在不是罪名的确定问题,而是出现罪名选择问题,一行为触犯两罪名,属于想象竞合范畴。即实行行为说并没有否认犯罪构成的地位,其解决的是罪名选择问题。这也引出了另一层批评意见,即如何依据实行行为确定罪名。依上例,在共同犯罪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实行行为,选择哪种行为作为依据,笔者认为,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两种实行行为地位不同:那么高度行为吸收低度行为,例如如果贪污实行行为在两种行为中处于主要地位,则认定为贪污罪;另一种情形:两种实行行为地位相当。笔者认为,实行行为说虽然主要视线集中在实行行为上,但是根据联系观点,实行行为也不能脱离犯罪实际情况,在这种情形下,赋予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考量,从而确定罪名。当然,罪名相同,量刑仍应考虑身份差异,以达到和谐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