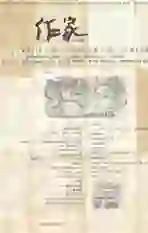《花堡》:为深化农村改革的探求者立像
2008-10-13朱晶
朱 晶
乡土题材一直是现代文学的传统母题。然而,近年真正切入当下农村社会主义改革的文学作品并不多。杨廷玉的长篇小说Ⅸ花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5)就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一部。小说笔走偏锋,故事去向似乎难遂读者意愿却又颇具警策意味。开头,先进村下花堡党支书兼村主任孙天鹄的身姿清新而引人注目,接着,上花堡的牛逵、中花堡的石富相继卷入与孙竞争的迷阵。可孙的处境急转直下,与人们的期待不同——在几成败局的境况下,孙天鹄竟毅然辞职下海寻求新的突破。读到小说结尾,返观整个情节脉落,你才会从孙天鹄引入“双高大豆”的波折中领悟改革大势与关东农民命运的密切关联,才会痛切感受到市场条件下现代农业的科学发展对于继续调整经济机制的深层要求。在此,杨廷玉针对深化农村改革的现实课题,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不同凡响的思考。
《花堡》的反思效应,首先取决于它不俗的构思。
小说结构最触目之点是,每章“花子堡”老奶奶与主体文本构成一种双重话语。这类似廷玉先前的长篇《不废江河》中每章由老子言论引出一段情节。不过,前者是抽象古训与故事文体的对应,而Ⅸ花堡》的章前引文则是极为鲜活生动的关东口语:
“……你问我当年讨饭怎么个讨法儿?怎么跟你说呢?好比一块漂白布掉进大染缸,花花啦!有善讨、恶讨、赖讨、玩讨、骗讨、笑讨、哭讨、喜讨……我要挨个给你说呀,三天三夜说不完……”(第三章)
这样翻“老箱底”的引子,不仅与小说正文形成古与今、野与文之比照,而且它本身又是一个活动的轨迹——小说最后,讲述者,99岁的老奶奶绝望于孙子王小适为发财投身南方丐帮而吞金自尽。“花子堡”已渐行渐远,其行帮遗留的游民意识病毒仍在得以传延,甚至出现了可怕的历史循环。我认为,这是《花堡》相当精彩的一笔。
小说另一个看似平常实则蕴含深意的隐性结构是,以穿插叙述的方式分别展现孙、牛、石“三连襟”对于三村“共建双高大豆育种基地”的不同态度。其中,阎家是个中间环节:前乡长阎四海作为岳丈被乡里任命为三村“顾问”,他的巡行起到了一种联结作用,而他的儿子阎新强娶了农业科学家杜一樽的小女儿,充任杜的科研助手,更是把杜一樽与下花堡的改革联系起来。这种家族组合运行,便于叙事的集中,既符合当下农村地缘伦理的真实特点,又与花子婆叙旧共同构成新农村改革的地域背景与历史惰性。就是说,尽管“三连襟”都是各据一方的基层党政头头,可这种家族身份及其纠葛拘囿其眼界,暴露出农村改革舞台上这些角色的“小农尾巴”,从而为他们的飞翔背上了沉重的翅膀。
《花堡》的反思效应,主要还是通过孙天鹄的形象塑造来完成的。小说并没有在篇幅上全力突出他,然而,无论是在情节进展中的重要性,还是人物心理和行为揭示的充分性,其他人物都远不能与他相比,因为他是搅动豆儿河畔变革风浪的弄潮儿。
孙天鹄有一颗不安分的灵魂。作为农村最基层的带头人,他超越一般平庸者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其不满现状,勇于不断开拓新路的品格。在主观气质上,这可能和他那神秘的弃婴身份相关。这个长着“斗鸡眼”的帅气小伙儿,降生于“文革”爆发那年深秋。是村里的老光棍儿从庄稼地里抱回来的,当地一些农民称他为“野种”。有的论者认为,孙天鹄的命名意味着他的命运应当“与农民割断脐带”;有人还推断他并非乡下人后代,而会是“来自城市的弃婴”,用以作为“城市向乡村介入的一种暗喻”。二者观点自有其道理。我觉得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孙天鹄与那片土地的关系。下花堡养育了他,他能够放弃高考回家护理病重的养父,表明他对那里的农民和土地有着不可割舍的深情。弃婴的身份虽然刈除了他的乡土伦理网络,促生他一种自由不羁的秉性,甚至敢当“使阎新蕊未婚先孕的坏小子”,但是与阎新蕊的婚姻反而扎深了他植入那片乡土的生命之根。
下花堡老支书提拔孙天鹄,是相中他的精明。其实,他真正高于同乡人之处是他的文化素养。在下花堡,孙天鹄的知识水准和生活方式每每比乡亲们超前地步入“现代化”层次——自学取得大学文凭,后来买电脑频上网,积聚家资百万,开上新型奥迪车。所以,他一旦出任“二把手”就主张:精简村班子成员,将村外荒甸子无偿供给省农科院做实验基地。两项提议立即遭到村干部强烈反对,他退而取其一,着力支持农科院在村外搞科技农业示范:建蔬菜大棚,试种玉米良种。结果,次年不用动员,村民群起效仿。1995年秋下花堡就脱了贫,玉米产量翻两番,种菜户收人多的高达联产承包十余年的总和。接了老吴的班,他引领下花堡人走上富裕道路,打开了玉米外销市场,经济总值在“整个松苑平原名列前茅”,村民的居住环境和文化设施大为改善。但他仍不想止步,掌握“双高大豆”研制信息后,决心把它引入多年“未种过一垄大豆”的花堡田野,再建个育种基地,以闯出“高科技与土地结合”的新路子。小说的主线,就是描写孙天鹄谋求三村共建杂交大豆育种基地“胎死腹中”的过程,亦即他不弃乡土而尝试角色转换的过程。
近年,长篇小说在叙事时空、文体类型、语言调式、人性情境等诸多方面大有拓展。廷玉深谙乡土民俗,语言驾驭或文体把握也不乏造诣。但他似乎更倾力于文本结构多重意韵的营造以及人物关系错综交织的探究,从《不废江河》《危城》到《花堡》皆如此。由于廷玉有过研究和写作戏剧的经历,具体创作路径演化为小说与电视剧并举,各自都成就斐然,因而他的小说更富于戏剧性:时空相对集中,情节悲喜交加,人物关系呈现矛盾或紧张的态势,结局往往发生命运的转折。《花堡》的孙天鹄形象,应说是农村题材创作一个新的发现、新的创造。这个“村官”引进农业高科技的失败,带有极大的尖锐性。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曾提出这样的见解:“艺术家在作品中除表现自己以明显意图置人其中的东西外,似乎还合乎本能地表现出一种无限性,而要完全展示这种无限性,是任何知性都无能为力的。”(见《先验唯心论体系》269页,商务印书馆,1983)这种“无限性”,就是文学作品中超越作家意图的、由艺术符码耗散的形象或精神的世界。《花堡》正是通过孙天鹄与几组人物的冲突、扭结,碰撞出不同人物的性格火花,在表现花堡三村农民多姿多彩的生存图景的同时,发人深省地揭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生机与困境。
其一,孙天鹄与杜一樽。
二人关系,着墨不多,却避开了俗套,是小说最为重要的人物组合。省农业大学教授杜一樽研制的高油量、高蛋白、高产(因尚未推广只叫“双高”)大豆,的确是现代化大农业所急需的良种;下花堡成功的带头人孙天鹄的确具备引进“双高大豆”的识见与魄力。然而二人的沟通却万分艰难。小说开局,孙天鹄到省外贸公司农产品销售处逯长河那里确证他从网上得知的新品种大豆研制消息,跑到省农大访杜却受阻,直至作品结尾,孙天鹄辞去职务一个多月后,杜一樽才答应把实验室搬到松苑平原豆儿河畔,并要求人股参与孙的农作物良种股份公司。
其间障碍何在?有主观方面隔阂也有客观条件的不成熟。二人见面前,杜看电视得知下花堡与上花堡因豆儿河污染打官司,对阎新强说:“你这两个姐夫都是什么素质啊?窝里反,乌鸡眼,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一辈又一辈不断复制这种劣等角色,我敢断定,像他们这类屁股上长着长长小农尾巴的人,根本就没资格搞现代农业!”这当然是带有成见的偏激之语。之后,有孙天鹄反诘的气话,有杜教授助手阎新强的拆台,有杜的大女儿杜荔的力荐,这些,把二人的关系弄得更复杂。借杜小女儿杜媛与阎新强的婚礼,孙天鹄使了“小手段”(让阎新强的面包车“‘慢撒气”),得到开奥迪送杜氏夫妇回城的机会,两人终于有了一次坦率的交谈。由《周易》《论语》说到《道德经》,虽然双方语含讥刺:一个说“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败矣”,一个说“视之不见名日夷,听之不见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日微……”杜一樽终于露出浅笑,特别是听说孙为养父而放弃高考,脸色才“柔和起来”。谈话进入到“直奔主题”,孙提出,赞助实验室一百万元的条件是“独家拥有双高大豆的育种专利”,杜断然拒绝:“我不会把我的试验成果作为你垄断市场的工具。”而当孙放胆承诺把下花堡三分之二耕地(50垧)用做育种时,杜一樽的回答是:“至少需要三个下花堡可耕地面积的总和!”一村一寨的求变发展,与高科技落实的条件显然存在巨大差距和错位。尽管后来孙天鹄反思时曾质疑杜教授也拖着“小农尾巴”,可二人关系的实质则是土地如何适应高科技的问题。“双高大豆”育种大面积实施的要求,是下花堡一个村分散的个体经营农户承担不了的,是行政指令下的三村联合也难以完成的。
可以说,是杜一樽启发孙天鹄校正了自己的改革目标,“双高大豆”促使孙天鹄痛下决心辞职办公司。而孙天鹄成为农民企业家所体现的改革理念是:不离弃乡土,放弃行政权力,寻求能把新科技引入市场,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农民联合体。这里,显示了作家对阻碍农村改革深化一大症结的洞察,呈现出小说破解人物困境的强有力的现实主义锋芒。
其二,孙天鹄与牛逵、石富。
这“三连襟”分别被称为“野种”、“犟种”、“孬种”,都是个性鲜明的人物。他们三人的纠葛,在孙说服、争取牛、石进入“共建”(育种基地)过程中,实际上掀开了当下农民不同的生存状态。小说以“村官”作为聚焦点,独具匠心,这样可能更逼近农村的真相,有助于彰显大农业高科技与小农个体经营的反差。加之“三连襟”的家族因素,就会集中而真切地透视出一场变革所引发的种种波动。不必讳言,狭隘、自私、守旧的“小农尾巴”确实是推进农村改革的顽固障碍。
三村矛盾的激化起自于1999年上花堡下管一家假酒假化妆品厂所造成的老撇河、豆儿河污染案。受损失最大的是下花堡,责任方上花堡却毫无悔意,牛逵还庇护责任人赵来发,足见他的偏狭。当时石富尚未上任,中花堡也牵扯其中,此后又引出涉及县民政局局长的更大贪腐事件,村支书王彪、村主任沈贵双双落马。类似的乡村行政弊案显然也是农村改革的障碍之一。
豆儿乡农民运动会,可看做三村竞争的象征。场面火爆,声势不小,却让人觉得有点虎头蛇尾。石富干脆逃避;牛逵逞强争锋,闹个丢盔卸甲,拉着人马退出闭幕大会;孙天鹄本要开展项目宣传战,找机会缓和与牛逵的矛盾,最后全都事与愿违。那么,二人积怨究竟如何解决?一是孙发扬风格,推举牛逵代表全乡参加省里村干部培训班;二是在一次突发事件中,孙挺身而出,救下牛逵的儿子。这自然是一种戏剧性的安排。平心而论,牛逵抓粮有功,敢抗上,不听邪,是个直筒子脾气,他那样的“犟种”,大约也只有动真格的才会被感化。
相形之下,石富是个更难缠的角色。这个人物不可爱但真实。村干部中此类“孬种”、“滚刀肉”不少。他是在“军师”张尔的谋划下靠家族势力上的台,他滑头、装熊,专“往自己脸上糊泥巴”,信奉“走小路比走大路安全”。在对付上级摊派上,这一招有保护村民的作用。倘若带着农民闯新路,石富的缩头战术便会成为农村改革的一种惰性因素。当然,他也有自己的致富“小九九”,为了踢开“头三脚”,孙天鹄出一百万元“无息贷款”,
石富就签下了参与“共建”的协议。
然而,孙天鹄没想到的是,上、中花堡两村很快又解除了“共建”协议。不是牛、石二人反悔,而是两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民投反对票。
小说这样描写孙天鹄此刻的心中感受:
“他好像从一个充满希望的端点出发,费尽心力地往前跑啊跑啊,跨过了一个个障碍物,踢开一块块绊脚石,涉过一片片沼泽地,翻过一道道小山梁,忽然发现前面仍然是最初的端点!”
与牛逵、石富打交道,他“费尽心力”,不乏精明,时而也痛感自己拖着“小农尾巴”的弱点,但更令他震惊的是“自己好像还没有跳出多年形成的老套套旧圈圈”,他仍然迷信“大锅饭时代村委会这个权力平台,恰恰忽略了村民这个农村经济活动的主要角色”。在这一点上,他并不比牛逵、石富高明。
其三,孙天鹄与杜荔。
这是《花堡》浪漫的一笔。杜荔,原豆儿乡党委书记,现松苑县副县长,即将迁任省农业厅副厅长,她倾心孙天鹄,一直支持他的事业。他们之间是上下级、心灵知己,还是网友,一个已婚39岁,一个未婚37岁。如果说他们有婚外(对孙而言)的恋情,那也是异性间相互的精神倾慕,至少目前还是发乎情止于礼(作品最后将孙妻阎新蕊写成“植物人”,人为痕迹重)。
小说设置这条人物关系线,并不单单为了增添作品的色彩。作为推心置腹的对话者、志同道合的战友,孙、杜之间的交流特殊而透彻,是情节进展所需要的。从性格塑造来说,这种双向的情感和心理的揭示,尤其丰富了主人公孙天鹄的内心世界。小说以孙、杜默默走上豆儿河大堤收束全书,情调凄婉忧伤。“雄浑浩荡的豆儿河在秋风中亘古如斯地流淌着,好像一位老者在浅唱低吟一首悲怆的乡村俚歌。”听着悼念王小适祖母的爆竹声和祷告声,他们意识到,随着世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也许另外一种贫穷和饥馑还在延续”——“两双忧郁深邃的目光渐渐融入波光粼粼的豆儿河水中”。细心的读者不禁会由此感慨于他们的命运与共,并对其未来的并肩奋斗怀以期望。或许这里还有作家对续作的某种暗示吧。
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改革正深入到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已成为中国老百姓生活的主旋律。改革是谁的改革?不单单是改革家的改革。这可能是《花堡》特别强调的主旨。小说通过孙天鹄的教训告诫人们:“农业,农村,农民,核心还是农民。…无论什么伟大的事业,没有老百姓的参与,全都等于零!”这既为不难理解的常识,又是难以落实的真理。但愿改革家们不会忽略或遗忘它。
2008年1月15日
青任编校逮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