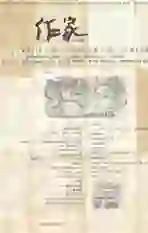我的写作不是一场自我表演
2008-10-13于坚
于 坚
——2007年答记者问
(2007年,沈阳《华商时报》记者杨东城和深圳《晶报》记者刘敬文分别采访了我,但限于篇幅,只发表了一小部分。这里是全文。)
答沈阳《华商时报》记者杨东城问
1,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再到鲁迅文学奖,这些奖项对您坚定地走诗歌的道路是不是一种鼓励?
我不需要任何鼓励,冷落、批判对我也一样是无效的。其他方面可以妥协,在写作上我一意孤行。
写作是我自己热爱并选择的,通过写作我获得存在感。这是我个人的存在先于本质。
文学奖鼓励的是文学事业,获奖者只是偶然被选中而已,别太当真。作品要面对的是时间,时间可不给你什么奖,所以杜甫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借此机会,我想谈谈鲁迅:
1966年我12岁,秋天的下午,父亲拉起窗帘,在卧室里秘密烧书。我看着那些美丽的书籍一本本化为灰烬,内心迷惘。我家书架上最后剩下的书籍中,有一套《鲁迅全集》,我少年时代有许多时间,是在阅读鲁迅作品中度过的。
作为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变革者。
鲁迅不仅仅是变革者,也是最杰出的作家。鲁迅们的写作使白话文的写作合法化了,在他和他那一代作家之后,用白话文写作,已经天经地义。
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主题与古典文学不同,古典文学的主题可以用李白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大块假我以文章”。20世纪文学的主题则是批判以及“生活在别处”。
批判,从更内在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从世界中出来。自从鲁迅那一代人的写作之后,中国没有人能够再在世界中混沌地写作了。
我们的写作是从世界中出来,再回到世界中去。
鲁迅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人”,对人的批判是他开创的一个伟大主题,文学因此成为中国生活的一面镜子。他是为“人”生的作家。
没有变革就没有新文学,但变革的结果必须是文学的产生。
中国文学已经有五千年以上的写作经验。文学并非横空出世。鲁迅不仅变革了文学,也重建了文学的常识。鲁迅的写作激活了汉语,激活了汉语身体的繁殖力。
在中国,文学具有宗教的作用。
文学就是文明,以文字照亮心灵世界。
文章为天地立心,鲁迅的写作创造了中国文化的现代灵魂。
汉语不再是清末那种墨守成规、日薄西山、失魂丧魄的面貌。
摧枯拉朽、青春激荡、意气风发,在20世纪,吸引青年生命者,莫过于文学。
文学不仅仅是抒情诗歌和风花雪月。
文学重新成为中国精神世界大解放的旗帜,20世纪的民族复兴乃文学所领导。
鲁迅的写作重建了汉语的青春气息、批判力、幽默感、讽刺力量、愤怒、悲剧精神以及对未来的信心,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现空间。
作为1966年开始的读者,我的幸运是,通过对鲁迅的阅读,我意识到何谓中国新文学的经典。我意识到,写作必须有直面人生的勇气。
鲁迅是我写作的指南之一。
我从1970年的冬天开始写作诗歌,我一直试图继承的是“为人生而艺术”。
谨此表达我对鲁迅先生的敬意。
2,在2000年上海主办的百名批评家推荐上世纪90年代1 o部代表性作品的活动中,于坚成为排名第一的当代诗人,您现在怎样看待这种成就?
批评家只是读者的一部分,职业读者吧。我更重视的是普通读者的看法。有一天我在游泳池里遇到一位读者,他说,我的诗改变了他的人生,这就够了。
3,您曾说,诗歌的声音已经降低到草叶的高度、泥巴的高度、盐粒的高度、甲壳虫和稻米的高度,今天,人们只有贴近大地,才听得见诗歌的声音。您现在是不是感到有些孤单?
在中国,写诗已经成为声名狼藉的事情。开汽车比写诗光荣得多。开着奔驰那就名正言顺可以羞辱诗人了。在孔子时代那可不敢,肉食者鄙。我深知我的写作是位于1966年的革命之后。“文革”之后,写作,肯定与过去五千年不一样了。写作就是文化世界,而诗是文的核心,是最高的写作。“文革”是对文化的革命,在“文革”之后写作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选择。我父亲是一位文学才子,1966年秋天,我跟着他把自己家里的藏书烧掉,他目光炯炯告诫我千万不要写作,几乎告诫了20年。
我拒绝了我父亲的忠告,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拒绝。
我早已充分意识到写诗的背时,孤独就是存在,我喜欢孤独。
4,能简单谈谈您过去创作诗歌的经历吗?
我1970年的冬天开始写诗,第一首诗是填词。我专心写了大约两年的古体诗词和古文。后来才开始新诗的写作。在中国遥远的外省、边疆,书籍和资料非常匮乏,而“文革”又全面禁书,这使我生活在20世纪,却像古典诗人那样学习写作。早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民间暗中流传的Ⅸ唐诗三百首》、王维的《辋川集》,还有《古文观止》和《史记》。西方文学给我的影响来自俄罗斯、法兰西和惠特曼。契诃夫是一位永远不会过去的作家。有的作家只适合于青年时代阅读,比如泰戈尔。我曾经对《飞鸟集》刻骨铭心,我与朋友在1976年秘密刻写印刷了这本书,出版了11本。杜甫和苏东坡是永远不会过去的诗人。《论语》《老子》《司马迁》千秋万岁,值得一读再读。那时代没有文学刊物,也没有所谓文坛,我最早的作品都是在朋友之间传阅,这是古代的方式。我1980年进入大学后才知道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存在,我已经写下上百首诗。80年代是一个激情的年代,我写了大量诗歌。1983年,我与韩东、丁当相识,创办了《他们》。90年代,是我写作的重要时期。我写下了《0档案》《飞行》,争议不休。2000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于坚的诗》,这也许是20世纪出版的最后一本汉语诗集。2001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便条集》。2003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诗集与图像》。《只有大海苍茫如幕》是2003年到2006年之间的作品。我同时也写作散文,最近的散文集是《火车记》和《暗盒笔记》。
5,《只有大海苍茫如幕》,现在很难再看到这种如此有气势和有力量的诗歌了,能谈谈这组诗的创作背景吗?
2005年的春天,我去渤海旅行。与我想象中的大海完全不一样。我少年时代通过地理课知道渤海,但那时我看见的渤海完全是末日的景象,令我迷惘。然而自然仍旧是有力量的,海水污染了,辽阔继续,依然是惊涛拍岸,这令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何谓之“天地无德”。我曾经担忧大地之死,其实在终极的意义上,会终结的是人,人与大地的对立使人处于危险的境地。人只是物种之一,而不是大地。如果人也像今天的大地那样被污染的话,人早就消亡了。人以为牺牲大地可以保全自己。人类不知道,他们永远比永恒少着一口气。
6,很多诗人已经不再写诗了,比如说舒婷,现在食指也很少写了,那么想问您,到底诗歌带给了您什么,让您如此执著?
他们不写了吗?我不太清楚。
我想这是一个中国问题,中国的现代传统。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确实有许多诗人放弃了写作,其实
50年代也一样。我记得涅克拉索夫有首长诗叫《在俄罗斯谁能过上好日子》,这是20世纪的世界目标,干什么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写诗也一样,日子好过或者难过了,就不写了,无可厚非。人们总是有各种借口停止写作,革命啦,战争啦,市场经济啦,写作不是被选择为存在而是机会。我只是一个常识意义上的诗人,就像一位农民,种地而已。塞尚说,他活着,他画画,他死了。这本是一个常识,但20世纪是一个全面反自然的世纪,许多事情都不自然了。
7,您诗歌的语言都是来自于心灵的流露,还是也有写作上的技巧?
两者都有,前者是天性,无法习得,养着就好。后者需要自己不断地学习、觉悟,子日:“三人行,必有我师。”
8技巧是重要的吗?雕琢技巧或者醉心于技巧的创造往往忽略了技巧或形式给诗歌带来的内部精神,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诗是通过语言招魂的艺术。没有灵魂的写作玩弄语言,而才子们又往往忽略如何说的智慧。
在中国,诗具有宗教的作用。中国精神的核心不是宗教而是文化。中国是通过文来引领精神生活,文章为天地立心。在古代,文就是诗。诗人如果放弃了“为天地立心”,写作就无足轻重。现在许多诗无非是自我的人微言轻的戏剧化,却埋怨读者冷落。通过诗的形式顾影自怜无可厚非,但也就别指望大众的喝彩了。古代写诗的人比今天多,但没有人太关心自己是否被冷落,写诗首先是一种个人的文化修养。不学诗,无以言嘛。
9,诗歌中有趣的现象是一个词语的构造、一个好句子的产生,都会有愉悦的快感,您是追求一个好句子还是整体的节奏?
我喜欢的是王国维所谓的“有篇无句”,这是混沌之诗,重要的是创造一个语言的场,而不是苦吟一二名句。炼句是古诗的风气,有句无篇,主要是贾岛这一流诗人的风气,在杜甫那里,炼句是次要的,文以气为主是主要的,气就是场。过度锤炼的结果是使某些句子脱离语境孤立出来,所以有名句选。现代诗更像格律诗成熟前的“古风”,篇终接浑茫。
10,模仿是诗人的硬伤吗?
写作开始的时候都是模仿的,模仿其实是深入经验,身体性的阅读,没什么可耻的。
11,您说现在诗坛的冷清和当今的物质丰富是不是有关系?
诗坛很冷清,但写诗不冷清。许多人在诗坛外默默地写着,像养石养兰花那样,将写诗作为个人修养者大有人在。
诗坛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这必然使诗人陷入自以为是的小圈子。
12,我觉得诗歌应该是有血液的,它带着人生命中最激情的东西,当物质生活充裕时您还会有这种血液和写作的快意吗?
诗肯定不是贫穷的产物,也不是富贵的产物。诗的冲动与经济无关。歌德一生衣食无忧。生计不成问题,诗的品格才不会只停留在无产者的愤怒层面。富贵于我如浮云,诗人因此可以与宇宙精神独往来。
13,可否谈谈在创作时的感受和心态?灵魂和生命都是诗歌中最为沉重的东西,而生命于人只有一次,您在创作中灵魂会产生巨大的震撼吗?您是否认为诗歌就是生命最大的热情?
是的。诗人要对人生世界怀有巨大的热情。而这个热情是没有是非的,是对世界本身的热情,是意识到“天地无德”的热情,而不仅仅是对所谓盛世怀有热情。热情,不仅仅是亮色,也是卡夫卡那样的灰色,卡夫卡的绝望就是一种伟大的世界热情。
14,一首诗歌可能是读者和作者之间交流的通道,也是座桥梁,您是怎么去建筑这座桥梁的?
读者是基于文明史的一种阅读经验,诗人要建立与历史的联系,而他的写作力量却来自非历史的原始冲动。我认为,有效的写作其实并非标新立异,旁枝逸出很容易,顺着文明的主干生长一毫米很难。伟大的诗人都不是所谓标新立异的,当时也许是,但在时间中,你发现不是。李白的写作在当时“世人皆欲杀”,而在文明史中,却是基于“大雅久不作”(李白诗句),是为了回到文明的“正声”。
15,诗歌和生活的关系,您是怎么看的呢?
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是从世界中出来,作为世界精神的代言者通过文(纹)文化世界,为世界文身嘛,而作品却要回到世界中。或者说,写作是创造一个作者的世界,而这个作者虚构的世界与世界之间绝非格格不入,写作是出世,作品是人世。
16,您认为诗歌中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不知道。
l7,您认为诗人生存的土壤是民间好还是仕途好?
无所谓,听其自然。古代中国的仕途可没有今天那么声名狼藉,许多大诗人都在仕途上奔波过。美政与仕途是两回事。民间是一个比那些自谓民间的小圈子广阔得多的地方,重要的不是你置身何处,靠什么谋生,而是你写下了什么。作为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者,并不妨碍卡夫卡在这种异化最严重的公司中作为最优秀的职员工作一生。
18,您常去国外参加一些诗会活动,说说国外诗人的生活状态吧。
一般来说,他们很少因为写诗而自命不凡。比较低调,生活就像诗一样的雅致、朴素,像金斯堡那样的狂热的诗人已经不多见了。其实他们那一代诗人对西方现代化异化人性的反抗已经失败,现在的诗人看起来更像一种热衷于自我修养的动物,如中国明清的诗人那样。诗歌不再是反抗的武器,而是生活的乐趣之一。
前面已经说过。
19,文学创作中,诗歌是离身体和心灵最近的,您怎么看待身体写作这个现象?
身体是存在的载体,没有身体就没有一切。身体就是大地。中国20世纪以来受本质主义的影响,不重视身体,任何事,隋从观念主义出发。观念主义正确,身体遭殃,请看看今天大地的状况,许多宏伟的东西发展起来了,道路高速,河流、湖泊却死亡了。许多基本的事物被摧毁了。没有大地,圣经、民主制度、诗歌都是虚无。海啸一来,一片白茫茫啊。
20,诗人的情结里经常有悲剧,容易走极端,比如海子,您怎么看?
这是20世纪诗人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自我迷恋,将死亡悲壮地戏剧化地从世界中分裂出来。对于我来说,死亡并不存在,所谓死亡只是世界的变化,五行而已。如果你知道庄子所谓的“吾丧我”,你就不会将死亡戏剧化。生死的分裂,是现代的观念。
21,如何看待现在流行的口水诗?比如前些时候热炒的梨花体。
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个铁一样的世界中,诗是每一种力量都可以轻易粉碎的东西。诗人们却把自己想象成一支别动队。这种顾影自怜与过去美人幽草式的顾影自怜其实一样。
22,生活和诗歌的距离之间是虚无感吗?
不知道,这是黑暗问题。
23,创作诗歌现在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谈谈您现在的生活状况,读者都很关心一个一直坚持诗歌创作的优秀诗人的生活。
只意味着我是于坚。
我大学毕业后被国家分配去一个文艺评论刊物当编辑,现在也是这里的编辑。
我的写作不是一场自我表演,所以没有收场的时候。这是我的存在方式。我并没有坚持什么,我只是作为于坚在做于坚想做的事而已。
答深圳《晶报》记者刘敬文问
1,你听力不大好,这对你诗歌创作有关系吗?似
乎你更注重视觉带给你的影响,你说过“从此我再也听不到表、蚊子、雨滴和落叶的声音。”这是否会让你进入自己的安静当中,不受外界打扰?
我童年时期因为生病,生命垂危,过度注射链霉索,损失了一点听力。为此,作为普通人,我在中国社会深受歧视。1970年我被国家分配到工厂工作,分工的时候,我要求分到声音小些的车间工作,结果回答说,听不见更好,我被分配到工厂最响的铆焊车间工作,整整十年,我的听力再次损失。在中国社会,人J陛中有许多黑暗的东西,隐藏在日常生活中,它们甚至是幽默的形式,非常残忍。比如相声演员动不动调侃生理有缺陷的人们而万众欢呼。人们甚至通过我的耳朵获得自我的优越感,前年,我发表了《朗诵》一文,许多诗人居然认为这是我出于听力障碍的一种偏见。
我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中写作,我是深刻体会的,卡夫卡比我幸运得多,粉碎他的力量永远不会来自令我刻骨铭心的那些方面。我的经历使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人道主义者。西方文明,在人道主义上我是高度肯定的。我的耳朵是我衡量人性的一把尺子。我从青年时代就意识到,这个世界很在乎的是聪明人,他们对我的耳朵很不耐烦,人们可没有耐心把同一句话说匕两遍。尚义街六号那些朋友是少数尊重我的耳朵的人们之一,这些金子般的朋友因为与我多年的友谊,都成了很耐心的人。
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我难忘的是我少年时代大街上的每根电线杆都挂着高音喇叭。我其实大多数时候就像梦游者,这个世界没有声音,人们在动,但动作并不安静。我依然看见喧嚣。这个世界对于我,是一个巨大的哑剧现场。我的听力戏剧性地使我和世界之间建立了旁观者和表演者之间的关系,我是一个天然的旁观者。世界的物的那一面,我看得更清楚,声音经常遮蔽着世界的物性。
中国的传统是感受人生,把日子对付过去就算了,很少思考“为什么”。米兰·昆德拉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用于中国,真是用错了地方,他说的“人类”,指的是西方人。西方人最喜欢问“为什么”,这种追问来自对大地的不信任,这种追问使他们登上了月球。中国人相信“大块假我以文章”,还思考什么呢,道法自然就是了。中国人其实很不喜欢思考,你见过那些无边无际的打麻将的人何时思考过?现代的知识分子思考吗?他们也不思考,他们只是拿来而已。中国真正思考的人不多,我其实也不喜欢思考,但我听不见,我得想想那些哑剧的含义,我不得不思考这个世界,在这方面,我真的是个另类。
中国讲聪明,聪比明重要。事实无所谓,重要的是听话要听音嘛。尤其是北方文化,“想当然”真是根深蒂固。“看见”其实不是中国的近代的传统。我是“看见”的诗人,而不是闭着眼睛天马行空的诗人,虚构其实很容易。
混沌一开,七窍流血。我比较混沌,因为上帝使我在耳朵上永不开窍。
2,现在不少人对诗人存在偏见,认为他们都是一群生活混乱神经兮兮的家伙,而据我知道,你的创作通常是在很正常的状态下进行,你是否认为诗人根本不需要所谓的“诗人气质”?你总说诗人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诗人”生活在世界上,那诗人只存在于他的诗歌里吗?
在古代,诗人就是文人。我喜欢文人这个说法。诗人有点高蹈了。文人就是文身的人,人本来与野兽无异,文身,使人从野兽中升华出来,成为人。文(纹)后来发展成字,就是语言。又发展出高于日常语言的诗。文人在最古老的时代,就是部落里的巫师,巫师负责的是与神灵的对话。
神灵,也就是诗性、心灵。它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中,只是大部分人的诗意永远是黑暗的,它需要文来照亮。许多人都会在生命的某一瞬被自己生命中的诗性照亮。但巫师是专门研究如何祛除黑暗遮蔽的人,他比普通人的自我照亮更有力量,法力更大,所以部落将巫师养起来,专事灵魂的呼唤。语言的发展,文人取代了巫师的角色。文与政治结合,是中国的传统,就像西方的政教合一。中国是文政合一。想想中国的哪个皇帝不同时是政治家也是文人?他要领导政治也要领导灵魂。
古代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文人,做官的也首先要写好诗。这是一个制度,文官制度,就是文人(诗人)领导社会。古代中国没当过官的诗人不多,大诗人也是大官僚。1840年以后,这个制度永远衰落了,就像日本明治维新后,武士制度一去不返。
作为现代诗人,要写诗,先要把自己的人生处理好。白话诗不仅仅是语言的革命也是诗人命运的改变。
文人操持的是灵魂方面的事,这种事只与“无”有关,无法用现金衡量,所以古代有“养”。李白杜甫都是养出来的,不是靠打工挣稿费奋斗出来的。
现代是唯物主义的社会,1966年又革命了文化,一切都用物的占有量多寡来衡量。
惟一没有改变的是文人依然要用汉语写作。文人作为身份已经丧失了话语权,但语言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所以,今天的文人比较矛盾,一方面,他没有身份带来的权力,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又是要依靠影响力而存在。
在古代,作为文人是加入到文明的普遍中去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今天,写诗是一种个人立场、个人的修养。
许多诗人意识不到这个根本变化,以为诗人依旧是风流人物,通过写诗来寻求功名,碰壁是必然的。
今天的文人要写诗得先把自己的生计对付住,写诗已经成为业余活动,人们可不在乎灵魂空虚。
其实没有诗人气质这种东西,或者“诗人”这样的人。有的话,那肯定是根据李白普希金或者金斯堡的传记进行的夸张表演。
诗人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写作是黑暗的。世界只看见作品,看不见你作为诗人在写作。写作的那些时间你是诗人,完了,你上街,买菜,与普通人一样。我经常去云南的少数民族部落,与大家一起吃饭喝酒,到了祭祀的时候,身边一老农忽然一歪,念念有词起来,才知道他就是巫师。
文人的没落在于,传统的话语权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传说中的诗人形象在空转。
文人,是基本的写作。诗人是文人的碎片之一,诗人其实小掉了。现代写作分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什么的,是西方的影响。古代中国,文人写的是一切,文人也不是表现小滴滴的自我,而是为天地立心。
人们也喜欢把写诗的人戏剧化,以为必有异常之处,诗人其实只是语言异常,其他方面如果异常,那就是表演。许多诗人表演人们想象中的诗人形象很成功,作品只是狗屎。
表演诗人也未尝不可,只是别像海子那样走火入魔。这个时代诗人角色受西方某些影响,自我的、自杀的、自恋狂的、自白的、唯我独尊的,相当乖戾。扮演这些形象很容易,一杯咖啡,几瓶啤酒再找个网吧,酒吧就行。但扮演李白、杜甫、陆游那样的诗人形象就太难了,陆游远行时,看见路上有老虎挡路,路人瑟瑟,写过“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零落成泥辗做尘,只有香如故”这种诗句的大师几个箭步冲上去,一把揪住副领,老虎嗷嗷怪叫逃走了。有一年我去三峡,看到李白一首诗,题记的意思说,这首诗是他登神女峰下来后写的,就望望神女峰,我靠,那就是摩
天大楼,李白肯定有飞檐走壁的功夫。老杜,别以为只是“读书破万卷”,人家也是“一日上树能千回”的!这个时代难怪普通人看不起诗人,想到诗人,想起的是个徐志摩的苍白,我靠!大部分普通人没那么势利眼,只是因为诗人穷就轻视,他们之所以轻视,我看还是因为诗人们自己表演的角色太次。你表演李白那样的试试,那就是大英雄。有些读者见到我很失望,不是徐志摩,许多诗人也拿这个说事。在中国写作,你就得忍受这些相当低级的恶俗。
我当然看过许多诗人传记,但我不表演诗人,我干吗表演诗人角色?诗人只存在于作品中,在作品中,你怎么呼风唤雨都可以,只是别在诗歌之外表演。现在最需要警惕并保持距离的是网络,网络可是一个很便宜的表演诗人角色的现成舞台啊,上去表演一场愤世嫉俗,有几百个点击率,就很有成就感,成功感、今天的诗人竟然沉浸在这些里面,可惜观众也就是两卡车就运走了。没戏。
3,据说有本时尚杂志把你称作“暴走一族”让你很无奈,为什么老会出现这类把正常的状态当另类的事情?是我们社会太缺乏正常了吗?
今天,一切正常的事情都不正常了。我已经“暴走”了一生,走路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难道开着汽车从襁褓里出来才是正常?我怎么就成了“一族”了?忽然之间,走路,不开汽车;在冷水里游泳,每天六点起床,十点睡觉;结婚,传宗接代……都成了“一族”了,这是李白杜甫们延续了千年的生活方式啊。
已经不正常到这种地步,举个例子,像德国人顾彬那样的弱智言论,什么“中国作家写得不好是因为不懂外语”(我多年前说大部分汉学家只有小学生的水平还真是说中了),都被作为真理来争论,真是可耻。
今天,我判断一个人的最高标准就是“正常”。在这个全面反自然的时代,“道法自然”的自然而然相当不容易,相当前卫,相当先锋。先锋派从来都是寂寞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艺术上的标新立异是先锋一族的潮流,我最近看到连798都已经上了CCTV的头条,可想见标新立异已经多媚俗了。许多先锋派的归宿其实不过是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承认,例如《时代周刊》、威尼斯双年展、诗歌节……相当媚俗啊。《时代周刊》,就是美国人的国家级刊物嘛。现在的标新立异其实很容易,有“文革”的传统做底子,只要胆子大,翻脸不认任何底线、规则。我劝大家躲远些,因为与这些先锋族没啥道理可讲,出名就是硬道理。只要能出名,怎么都行,这是后现代的新发展。
正常的写作,回到“正声”的写作相当困难。李白说,“大雅久不作”,我深有同感。
4,“诗歌是盐巴”,你不喜欢写脱离日常经验的东西,不喜欢凌空高蹈的东西,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诗歌观念,这跟你十年工人生涯有关吗?
这与时代有关,不仅仅是我的工人生涯。顺便说一句,我曾经也是打工诗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我的诗歌观念不是来自既定观念,而是行动、经验与思想的结果。
5,你推崇行动能力强的知识分子,如玄奘,你自己也是这样做的,“行动”对于诗歌重要吗?
不是我推崇,孔子就是一个在路上的伟大知识分子。中国最伟大的一个传统就是知行合一。论语是在路上完成的,而不是像康德那样在书房里苦思冥想。西方,行动与知识往往分裂。后来,杜威的实用主义有所纠正。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规。”这意思就是,知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人生的一个漫长过程。孔子的思想在朱熹那里成了“知难行易,知先行后”。为后来猖獗中国的本本主义、主义先行、本质主义埋下了伏笔。王阳明做了一个伟大的纠正,他反对对知行分先后轻重,提出知行合一。先知而后行就会终身不行,也就终身不知。“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凡是不行的,“不足谓之知”。但在中国没有引起重视,王阳明后来影响日本韩国。今天中国教育的灾难,就是将“知行分作两事”。在诗歌上,行,就是从个人的体验去感悟世界,而不是从先验的概念、理论、现成的文本、知识出发去写作。但是行,在极端的口语写作那里,也成了文盲运动,完全的无知了。“文革”给中国的两个影响是:迷信西方知识、本本,轻视中国传统文化。
6,你从小读古诗,喜欢李白,会背诵《唐诗三百首》,还写过古体诗,中国古诗的传统现在对你意味着什么,李白现在对你意味着什么?据说你还讲过,“我潜在的读者是古人”。
古代传统对我意味着“彼岸”。1840年到今天,可以看成是一个将传统中国彼岸化的过程。100年前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向往冒死拿来的那些“生活在别处”的东西,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的存在本身,传统中国的经典像圣经一样遥远。李白对于我是一个当代的大师,我总是能从他那里得到指点,说实话,新诗还没有一个诗人可以像李白、杜甫、苏轼那样给我那么多的启示。
7,我认为《尚义街六号》是很好玩的诗,我上次去昆明还特意到尚义街去找了一下,但也有人认为这首诗不太像“诗”,同样像《罗家生》这样的诗我也听过类似的议论,人们对“诗”的认识会如此不同?
在《诗经》写出来之前,诗是什么?出来个孔子,说是就是了。《诗经》的某些篇章是不是诗,到现在都还有争论。如果《诗经》是,那么玛雅可夫斯基写的肯定不是,里尔克写的肯定不是,你把庞德模仿李白的诗拿到唐朝去问问李白,我相信李白肯定说不是诗,韵都不押,一行有二十几个字,什么东西!
我还是倾向古代的说法,在古代诗就是文,文是从文身来的,没有文身,人是野兽,文身使身体有了花纹,区别于野兽,黑暗被照亮了,就是文明。诗就是文明世界,怎么写都可以,明就行。明,心就立起来了,只要立心,其实怎么写都可以,《诗经》为什么在先人无数文字中被确立为“诗”并且“经”,因为它的纹理,使人心大亮。就是今天,也是光辉灿烂啊。写着吧,是的话,它自然是,不是的话,它自然不是。
8,是否可以说每个人身上都有诗性?现在很多人说,我的生活没有诗歌不见得有什么缺憾啊,从你的经验来说,生活如果没有诗歌会缺点什么吗?
别的语言我不知道,但在汉语中,没有诗,人就无法生活。因为汉语是诗语。文人没落,诗修辞方式依然暗藏在语言中。中国人都善于含沙射影吧?什么是含沙射影,那就是言此意彼。说得知识分子点,就是隐喻。汉语是讲关系的语言,关系,就是要根据语境才能明白上下文,也可以说是空间感,点到为止,其中关系、奥妙要会听。言近旨远,说得好听是诗,说得难听是话中有话。这是普遍的汉语修辞,我说的拒绝隐喻也是要拒绝这种东西,太压抑了。诗是对这种日常语言的升华或叛逆,如果没有诗歌影响汉语,颠覆陈词滥调,这种隐喻模式就会僵化、黑暗,窒息生命。诗歌的力量在于使汉语保持着活力。
9,你经常读别人的诗吗?读哪些人的诗?
现在读得少了,我读得多的是古典诗词。现在青年诗人的作品也看,他们的写作是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的,只是好不好的问题,而不是是不是的问题。有许多诗人很不错,天津的诗人朵渔编了本《现场》,里
面的诗相当不错。
1O,你的女儿经常读你的诗吗?你希望她以后热爱诗歌吗?
偶尔。我不把任何非自然而来的爱好强加给她。我的书和所有的书都自然地放在家里,她读就读了。我不对下一代寄予什么希望,那是他们自己的命。我希望什么,如果与我希望的不一样,我是否要当个园丁,使用剪枝的大剪刀或者除草机?那些玩意是西方人发明的,经常在凶杀片里面出现。
11,你为什么不喜欢朗诵诗歌?除了朗诵,诗歌还能用怎样的方式亲近大众?
朗诵说到底是表演,与诗本身没有太大关系。朗诵是现代兴起的,其本质是宣传。无可厚非,我也偶尔朗诵一下。朗诵最糟糕的是,它取消了字的存在,成为声音的狂欢。汉语不是拼音文字,离开了字,只有声音,那是口语,不是诗。诗是写出来的,不仅仅是说出来,诗不是只是把口语记录下来,诗是在沉思默想后书写出来的,诗高于口语,也高于知识。为什么不把诗就写成拼音,听就完了嘛。西方诗也许更适合朗诵,只是拼音嘛。要朗诵的话我希望字也在场,强调一下声音,表演一下声音部分,也可以,只是诗并不会因此被表演出来,因为你不朗诵,它还是存在着,诗在沉默中存在。
诗要亲近大众干什么,诗又不是超级女声。是大众应当自觉地去亲近诗,而不是诗人自己去卖唱。诗人与戏子们不同,诗人不是靠卖诗吃饭的,所以大众亲近与否我真的无所谓。爱读读,不读拉倒。这不是清高,诗人与大众的关系,是在诗歌内部处理的。我理解为普遍性,人心向背。如果这个没有在诗里处理好,就是在央视上亲近大众也没戏。过去不是有许多诗在电视台什么的朗诵吗,结果只令大众更恶心诗歌。他们撒下的烂药,却要由全体诗人承担。我可没有看见李白杜甫从墓地里爬出来亲近大众。
12,海子也许是现在大众知名度最高的当代诗人,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传播率也很广,而你不喜欢海子的诗,同样,顾城的诗你也不喜欢,为什么?
他们也有好诗。但他们的诗基本上是青年学生腔。对于我这种读者来说,太轻了。这个时代在审美上太轻,大部分的诗人都是“青年诗人”,我不是说年龄,七八十岁的青年诗人多得是。重的东西恐怕得有些时间才能被接受。诗不是只写给青年学生看的,真正好的诗是没有年龄的。那是为天地立心。我欣赏的是杜甫、歌德、苏东坡那样的诗人,史诗。史诗很难写,这不是说诗歌技巧,而是说你要承担使命,面对时代和生命的黑暗面,还要有历史感。轻的诗很容易横空出世,有点才气即可。重的诗不仅需要天才,还需要自我控制,“从心所欲不逾规”。
13,最近写诗了吗?什么东西让你坚持写诗?
在写。我都在写,发表倒不一定。我过去三年又写了一本,是我的第四本诗集。看到的人不多,有些没有在刊物发表就直接出版了。我是那个叫做诗歌的村子里一心一意只知道种地的农民,大家都去深圳打工了,我继续种地,我与现在中国空掉的村庄里驻守大地的农民还真是相似。
2007年11月
责任编校速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