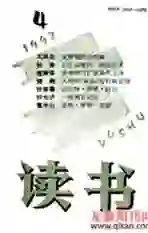关于日本史的开始
1992-07-15刘家和
刘家和
有文字记载的日本历史始于何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过,有关日本历史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不是出现于日本本土,而是出现于其邻邦中国。这正如有关日耳曼人历史的最初文字记载并非出现于日耳曼而是出现于罗马一样。因此,陶天翼先生所著《日本信史的开始》一书首先确定中国史籍中探究日本历史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可是,在公元七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文献中只有倭而无日本。那末,倭与日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就成了作者在此书中着重要论证的关键问题。正如作者所指出,在此书以前,日本已有学者对倭即日本的问题作了论证。(《日本信史的开始》,第57—58页。)他们的努力说明了倭可能就是日本,而作者在本书中则用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推理确证了这一点。
中国文献最早说到倭人的是公元一世纪后期班固所著《汉书》。当然,成书早于《汉书》的《山海经》中已经提到了倭。不过,司马迁作《史记》时即对《山海经》一书内容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因而不曾引其材料。为了慎重求信,作者也以《汉书》为最早记载倭人历史的文献。《汉书》对倭人虽然语焉不详,但是写成于汉与倭人刚有直接接触(光武中元二年倭使来朝)之后不久,所以其记载具有重要价值。这样作者就确立了一个可靠的基点。
自《汉书》以下,作者历举了《后汉书》、《三国志·魏志》、《晋书》、《南史》、《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隋书》及旧、新《唐书》等史籍中有关倭人的记载。这些记载说明,中国自汉至唐初一直以倭称今之日本,直至倭自身改称日本以后,中国文献才也作了更改。
作者不以征引中国历史文献为满足,又详引韩国有关倭国的史料,主要是成书于公元十二世纪中叶的《三国史记》。此书所载史料可以与中国文献相印证,而且所记倭国史事颇详于中国史书,可以补后者之不足。考虑到《三国史记》有成书较晚的弱点,作者又很重视第一手史料的探研。他不仅重视公元五世纪的《好大王碑》这样直接传世的第一手史料,而且精心从《三国史记》中辑出公元六六五年新罗和百济二国所订立的盟约原文及公元六七一年新罗文武王复大唐总管薛仁贵的信这样的第一手史料。他以第一手史料与第二手史料相契合、相印证的方法,提高了《三国史记》有关倭国历史记载的典据性。
当然,作者不会忽视日本本国方面的历史文献。他提到《日本书记》等六部日本国史。这些史书编纂于公元七二○年至九○一年之间,所记自神话传说时代至公元八八七年。作者提出,这些书“是研究日本古代史最重要的文献。不过六部国史都成书于倭国已经改名为日本以后。六部国史里日本已不再称自己为倭,也没有提自己曾经称为倭。倭字虽常出现……不过,倭是一个地方级的行政单位,不是代表全国的国名。”(见本书第53—54页)针对这一复杂情况,怎样证实中国正史里倭就是今天的日本呢?作者作出严密的分析和论证,其论证有以下四点:
一、作者指出,从中国与朝鲜的史料来看倭的位置和状况,它只能是今天的日本列岛。
中国正史自《后汉书》以下以至《旧唐书》,都说倭在朝鲜东南大海中,首先地理方位相符;同时又说明是远在大海中,从而排除了为近海其他小岛之可能;继则又说明倭的地域甚大,故非日本群岛莫属。朝鲜方面有关倭的地理方位的史料可以为中国史料之佐证,而朝鲜史料在说明倭为大国方面则远较中国记载为详。日本的地理方位与状况古今并无多大差别,所以既然中、朝两方史料所记倭的地理情况与今日本群岛相符,那末倭虽不能说就等同于今天的日本,但它就在今天日本境内是无可置疑的。
二、作者以中、朝史料中的倭与日本史料中的日本相校核,指出二者只是一国的二名。
例如,中国的《北史》和《隋书》记载大业四年(公元六○八年)裴世清(或作裴清)曾随日本使节小野妹子访问倭国,朝鲜《三国史记》于同年亦有同样内容的记载。在日本的《日本书记》中,同年也有相应记载,而且记事比中国史书为详。又,中国《旧唐书》记贞观五年(公元六三一年)唐遣使者高表仁访问倭国。《日本书记》同年亦记此事,记载尤较中方记载为详。中国(及朝鲜)史料中明言裴、高二人先后访问对象皆为倭国,而《日本书记》则但自称为日本,而不称倭。既然裴、高二人先后所访为同一国,而不同国家史料对此国竟有倭与日本两种不同称呼,作者由此证明,倭与日本只能是一国之二名。
三、既是一国,为何又有不同的二名?作者又征引史料,说明这是倭国自改其名为日本的结果。
中国《新唐书》记,咸亨元年(公元六七○年),倭国来唐使者“恶倭名,更号日本”。《旧唐书》中也有“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之说。朝鲜的《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也记载,文武王十年(公元六七○年),“倭国更号日本”。所以,倭国改名日本,在中国和朝鲜史料中是有确实证据的。至于改名的时间,尽管中、朝两国史料都说明在公元六七○年,作者仍然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因为这很可能是中、朝两方知道倭国改名的年代,而非其本国实际改名的年代。作者发现,《日本书记》虽未记倭国改名日本之事,但是其所记大化元年、二年(公元六四五、六四六年)的诏书中是明确自称本国为日本的。鉴于大化革新是日本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作者推定改名当在公元七世纪中叶。是否有可能更早呢?作者指出,《隋书》所记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倭国使者所呈国书中其君尚只自称“日出处天子”,如果当时已改国名,自然会自称日本天子。因此,他认为,当时尚未改变国名,不过想与隋朝平起平坐的愿望已经充分显露,所以也可说这是准备更改国名的先声。这样,作者虽然未确指倭国改名日本的具体年代,但是已经基本可以确定那是在公元七世纪中期了。
顺便说明,作者还告诉了我们一个有趣的道理:倭国改名日本,是为了倭字不雅,改名日本才可以摆脱掉对中国的某种顺从地位(按,《说文解字》云:“倭,顺貌,从人委声”。段玉裁注云:“倭与委义略同。委,随也。随,从也”。)可是,他们发现了或懂得了倭字还有不雅的意思,那只是到了隋唐时期在文化上接受了中国更深的影响以后。其实,倭的称呼其音也来自倭国自己,倭国改名日本以后,中国史书也就改称之为日本了。
四、由于《日本书记》始终没有说倭国改名日本的事,这就使得改名说总是立足不稳。作者在精研《日本书记》以后,终于发现在这部成书较晚因而只具有第二手史料价值的书中还以引证文献的方式保存了一些第一手史料,恰恰在这些第一手史料中就有日本确实曾经称倭的证据。
例如,《日本书记》卷二十六正文下的注里,保存了公元六五九年日本遣唐使伊吉连博德所写的在唐朝参加冬至朝会的回忆录:“十一月一日,朝有冬至之会……所朝诸蕃之中,倭客最盛。”这是日本使者自己称倭客的实证。又如,此书记载了公元六○八年隋朝皇帝的国书,其中写道:“皇帝问倭皇。”这是当时日本仍称倭的又一证据。又如,此书记载了公元六四七年(大化元年)孝德天皇的诏书,其中追述佛教传入的时候说:“于矶城宫御宇天皇(钦明)十三年中,百济明王奉传佛法于我大倭。”(第117—119页)既然国君诏书中都有自称大倭的字样,当然日本曾经自称倭国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
正是经过这样的论证,作者敢于断言,日本的确曾经称倭。
这无疑是一部史料征引详赡的书,但又不仅限于所引史料数量之多,值得指出者,尤为作者征引史料的审慎与精思。他从纵的方面注重所引史料在时间上的连贯性,如他引《汉书》以下各正史直至新旧两《唐书》,必使其中无间断可疑之处,此其特点之一。他又从横的方面注重中、朝、日三国史料之间的契合性,如他不仅引用中方史料,而且以朝鲜《三国史记》以及日本的《日本书记》等书,以作比勘佐证,必使其相互印证而无疑,此其特点之二。作者又注重对于史料本身作层次之分析,力求以第一手史料来印证或否证第二手史料的真实性。以好大王碑文及《三国史记》中所引原始文献以印证《三国史记》其他关于倭国的记载,是其以第一手史料证实第二手史料之例;以《日本书记》之所引原始文献中确有称倭与以大倭自称之事例,揭示日本并非如《日本书记》所说一向即以日本为名,是其以第一手史料证伪第二手史料之例。于此吾人可见作者于史料之引用既搏且精,足征其作为史学家之深厚之功力。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此书作者不但于史料考证方面用功甚勤,而且在总体论证中又十分注意逻辑结构之严谨。作者所要证明的命题是,日本始有文字记载之信史自中国之《汉书》始。而《汉书》所载为倭而不曰日本,故必证明《汉书》中之倭即今之日本之前身,然后作者所提之假设始能成立。
作者首先证明《汉书》中所说之倭(令之为A)即《隋书》中裴世清所使之倭与《旧唐书》中高表仁所使之倭(令之为B),又《日本书记》等六部国史中所说之日本(令之为C)即为今日日本(令之为D)之前身,此为不须证明之事实,故作者着力证明裴世清、高表仁先后访问之倭即是《日本书记》所记他们访问的日本。前已知A=B,又已知C=D,如今作者既证明B=C,则A=D,已无可疑。作者就是这样以近乎几何学的方法证实《汉书》中所说之倭即今日日本之前身的。
因此,我以为,这一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是重要的,作者在史料考据之精博与逻辑论证之谨严上皆可说是很出色的。这一本书本身无疑是具有其严肃的学术价值的,而且这一本书,如果稍稍细读一下,对于年轻一代的史学研究者来说,可能还具有治史方法方面的启发作用。
(《日本信史的开始》,陶天翼著,一九九○年台北三民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