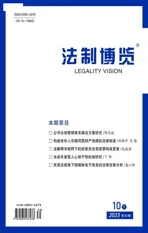《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研究
2023-12-01任宏涛
任宏涛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文法学院,河南 新郑 451191
当今时代,是一个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并且市场的发达水平与竞争的激烈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伴随市场的深化发展,市场竞争会变得越来越普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加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各式各样新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层出不穷。鉴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趋于复杂化、多样化,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难以对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详细列举[1]。所以,在面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未作具体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要依靠一般条款中的相关规定去进行判定。《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主要是指第二条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秉承自愿、平等、公平、诚信原则,遵守法律、商业道德”,主要适用于立法未进行涵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实践中,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赋予了法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倘若缺乏完善的判定标准,极易让裁定结果有失公允,以此引发种种问题。所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应做到细致、严谨,并有意识地对各方主体的利益进行综合衡量、考虑。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适用要求
(一)遵循立法目的
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条款不可与立法目的条款相违背,其一些不明确的构成要件、模糊性的术语概念,也有赖于立法目的的解释。《反不正当竞争法》旨在保护竞争,追求建立公平合理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其除了要维护经营者的利益,还应关照消费者及其他主体的利益,进而依托利益衡量,构建健全的保护体系[2]。而若是局限于关注经营者的利益,而对市场竞争秩序下其他主体利益视若无睹,则有违市场竞争秩序的应然要求。所以,近年来将“存在竞争关系”视作必要条件的观念,不断被司法判定所摒弃。正如2017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中,将第二条第二款中原本的表述“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修订成“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并放在“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前,以此构建起了一般条款价值序列与第一条立法目的条款的统一关系,明确确立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有着保护竞争的应然品性。
(二)实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有机统一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适用于难以依托类型化条款进行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该部分行为单凭合法性规则,不足以实现对其的有效规制,再加上一般条款鉴于其道德属性而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对于市场竞争秩序的判定还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开展合理性评价,所以一般条款的适用应趋于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有机统一。其中,合法性主要指的是一般条款适用应当立足立法条框内。虽然对于其的适用,主要是难以依托类型化条款进行规制的竞争行为,但其仍应遵循《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相关标准范式,不可超出立法目的条款对应建立的基本框架;《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适用的合理性则讲求在市场竞争秩序的指引下,依托对各方主体得失损益的全面比较,进而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视角评定竞争行为合理与否。总体而言,合法性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适用确立了基本方向,但对于一些原则抽象的概念术语仍应当开展合理性评价,进而依托价值补充弥合规范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三)保持必要的谦抑性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有着开放性的特征,可完成对一些难以用类型化条款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有效涵摄,并且其还讲究要保持相应的谦抑性,进而将行为规制限定在某一范围内。从根本上而言,《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一种对竞争自由的规制,由此决定了其务必要保持谦抑,进而防止将正当的市场行为纳入不正当竞争范畴。一般条款适用的谦抑性,切忌对自由竞争、公平竞争构成限制,并应当遵循《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目的,保障秩序与自由的全面统一[3]。对于市场竞争秩序运行而言,自由竞争不可或缺,同样的,自由竞争也离不开市场竞争秩序。《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适用并非为了限制自由竞争,而是依托保障竞争的公平有序运行,进而使市场竞争秩序得到有效维护,显然这与自由竞争并不相悖。所以,一般条款适用应保持必要的谦抑性,通过推进《反不正当竞争法》价值宗旨与市场竞争原理的有机融合,以防止一般条款遭到滥用,造成不正当竞争范围随意扩大。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适用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定标准模糊
我国现行法律对何谓不正当行为进行了正面列举,但鉴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使得法律难以对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列举,进而造成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定存在多种不同观点,在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定实践中总是有不同的看法。在一般条款看来,若是当事人有违法律规定,对市场秩序构成扰乱,并对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利益构成损害,即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而法院则遵循诚实诚信、商业道德标准,从另一角度判定竞争行为的不正当性。该种判定方式,让法官享有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并一定程度上扩张了法官对竞争行为的干预,由此表明这一标准不适合作为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直接依据。
(二)一般条款遭到滥用
对于一般条款在实践中的适用,滥用问题是有待研究解决的一项重点。基于司法视角,倘若法院在裁定案件过程中倾向于适用一般条款,则意味着法院过度适用一般条款,由此不仅会对双方当事人权利构成侵犯,还会造成裁定结果有失公允。此外,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当事人滥用一般条款的现象。也就是当事人可能会按照一般条款提出与反不正当竞争相关的诉讼。如湖南省王某1 诉河南王某2 侵犯其著作权,在这一案件中被告利用原告的知名度来宣传自己的作品,以此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并从中获取相关利益。基于此,法院裁定被告的行为可能会使得大众对其作品产生误解,从而判定被告对原告的合法权益进行侵犯。法院援引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相关条款进行判断。然而针对被告的行为应当适用更加具体的法律条款,此案依然适用一般条款就体现出对该条款的滥用。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一般条款滥用的情况趋向多元化发展,不仅有存在具体条款可进行规制,仍对一般条款进行适用的情况,还有先援引具体条款再适用一般条款进行判定的情况。
(三)侵权行为规制模式与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正当性衔接不当
通过既有适用一般条款判定互联网竞争行为正当性的裁决文书可了解到,其一般是将一些互联网商业模式予以合法权益化处理,进而以侵权行为模式进行判定。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该部分行为不正当性的判定,应当确定所需维护的是何种竞争秩序,而并非确定受损害的特定权益,由此进一步造成了侵权行为规制模式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正当性衔接不当的局面。一方面,互联网市场竞争中,不管是用户流量,还是经营模式均不可当然视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其中,用户流量作为互联网领域经营者彼此间竞争的一大重点,鉴于用户具有重叠性、流动性的特征,由此决定了用户流量不可当然成为某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同时,经营模式在互联网领域趋于同质化,基于此,企业为赢得用户流量、用户黏性、交易机会等,就必须要投入相应的成本,在此期间,不可因其投入多少成本而判定其经营模式为合法权益,两者不仅不应具备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更不可将其作为一项合法权益以对其他竞争者获得竞争优势进行限制。另一方面,结合一般条款相关规定而言,竞争行为对其他经营者合法利益构成损害,并非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充分前提,而应当对诚实信用原则、消费者权益、市场竞争秩序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所以,“只要出现侵权现象就代表着存在不正当性、违法性”的侵权判定思维,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定难以充分契合,实践中若广泛适用这一判定思维,则会影响一般条款在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有效适用。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适用的完善路径
(一)建立明确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定标准
就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定,可基于主观性标准、客观性标准为判定提供有力依据。其中,主观性标准主要是指行为主体的态度,其是否存在主观错误,其竞争行为是否为了满足自身最大化利益诉求,同时需要明确知悉自身行为是否会对其他主体合法利益构成损害;客观性标准主要是指行为主体对其他竞争者、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等的合法利益构成侵犯。经营者之所以进行竞争,主要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竞争行为必然会对其他竞争者构成影响或者损害,竞争行为构成损害与否,是需要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4]。由不正当竞争造成的利益损失,除去要考虑其他竞争者,还应关注消费者及社会公共利益。鉴于此,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定标准的建立,一是要观察竞争行为致使其他竞争者利益受损与否,以及对消费者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构成侵犯与否,这是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大前提;二是为实现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进一步判定,应从行为主体行为目的、竞争方式等方面入手,评价其行为存在不正当性与否;三是基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发展程度,以判定经营者所需承担的对应责任,具体承担责任方式则取决于利益受损程度轻重。
(二)建立一般条款的具体适用规则
不正当竞争行为涉及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多个领域。所以,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应建立明确、具体的适用规则,换言之,应当明确哪类案件可适用一般条款,以及一般条款适用相关的注意事项等。同时,对于一般条款的适用范围应进行明确限制,以此防范一般条款遭到滥用[5]。唯有在竞争行为不在立法规定的竞争行为范围之内,并且这一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商业道德时,方可判定其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方可对一般条款进行适用。此外,鉴于一般条款的不确定性,在对其进行适用时,法院应当作必要的说理,阐明一般条款适用的裁定理念,确保竞争行为判定的合法性、合理性,防止裁定案件向一般条款逃逸。
(三)由“三元目标”保护模式代替侵权行为规制模式
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在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适用,应摒弃以经营者合法经营模式视作合法权益保护的侵权行为认定范式,转而引入三元目标保护模式,适用一般条款开展判定。对此,一方面,应当明确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某种意义上而言,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离不开互联网领域较为自由的市场竞争有力支持,与此同时,互联网经济因其突出的创新性、动态性,决定了其有赖于法律为其创设自由竞争的空间,所以在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案件中适用一般条款,必须要保持必要的谦抑性。另一方面,谦抑性并不等同于对互联网市场主体的无序竞争行为不作任何规制,而应当结合一般条款内部逻辑,对竞争行为有损三元利益与否进行综合分析[6]。例如,在某奇艺与某狗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中,法院裁定某狗设置的推荐词并不会对某奇艺平台内部的呈现构成影响,进而不会影响到某奇艺的正常经营。同时,法院还依据经营者、消费者、社会公共利益受损与否着手,基于互联网行业之间的紧密关联性,判定涉诉行为未对互联网市场竞争构成扰乱,所以不需要进行司法干预。
四、结束语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旨在为解决法律未预见的新问题的处理提供帮助。在当前市场经济发展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对层出不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通过建立明确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定标准、建立一般条款的具体适用规则、由三元目标保护模式代替侵权行为规制模式等不同方式,切实助力一般条款适用的有效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