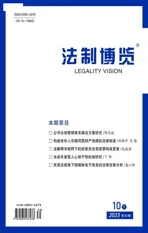法解释学视野下的妨害安全驾驶罪构成要素
2023-12-01毛溪浩
毛溪浩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妨害安全驾驶罪之设立,毫无疑问增强了民众的安全感以及对法律的认同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回应民众呼声的体现,也是紧跟社会发展的需要。但自妨害安全驾驶罪设立以来,学术界与实务界对于该罪的解释与适用存在分歧。实务界固可以按照四要件去界定妨害安全驾驶罪,但是各要件之构成要素的解释却会影响对各个要件的理解,这直接影响到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认定。有鉴于此,笔者以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法条和司法解释为线索,将该罪分为“使用暴力型”“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型”“擅离职守型”三种行为模式,对其中的要件要素——“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暴力”“抢控”“驾驶操纵装置”“擅离职守”“互殴”等进行解构与分析,以期求得一个相对明晰的标准。
一、对行驶中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之认定
(一)“行驶中”的法律界定
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行驶”之含义,因此对于“行驶中”的概念界定,只能诉诸语词原本的含义。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与《辞海》的解释,“行驶”是车、船的行进。但是对“行驶中”之界定却值得思考。通常而言,“行驶中”是指车、船发动并运行。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车、船发动但未运行与车、船运行但未发动,这两种情况能否认定为“行驶中”。
针对第一种情形,车、船发动但未运行。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情形,例如公交车司机到站停车但未熄火,此时能否认定为行驶中?对于此种情况,笔者认为以驾驶人员是否拉下手刹为区分点。假设,驾驶人员并未拉下手刹,只是踩下制动踏板,车辆并不处于一个绝对停止运行状态,如果此时乘客使用暴力或者抢夺方向盘,可能会导致驾驶人员在慌忙中放松踏板,极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危害公共安全,因此这种情况下应当认定为“行驶中”;假如驾驶人员已经拉下手刹,此时车辆已经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乘客与驾驶人员发生暴力冲突或抢夺方向盘,并不易造成车辆的失控,因此此时不应当认定为“行驶中”。当然,如果乘客抢夺的是手刹,此时车辆再次处于一种失控的风险中,应当认定为“行驶中”。综上,在车、船发动但未运行的情形下,以“驾驶员是否放下手刹和行为人是否抢控手刹”为参考点,综合该行为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性,进而综合判断。[1]
针对第二种情形,车、船运行但并未发动,这也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情形,例如车、船在行驶过程中突然熄火或者发生抛锚,但是车、船由于惯性而继续行驶,此时车、船就属于运行但未发动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交通工具所具有的危险性与正在行驶情形下无异,因此应当认定为“行驶中”。
(二)公共交通工具之法律认定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以列举的方式对公共交通工具进行了认定: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公共汽车、公路客运车,大、中型出租车等车辆。[2]这种认定方式是对过往发生过的案例进行总结而得到的。这种基于案例而列举的模式,一方面给其他类型的车辆进行实质解释留下了空白地带;另一方面将船只排除在解释之外,也不利于妨害安全驾驶罪对于水运交通的规制。
第一,《指导意见》将船只排除在公共交通工具之外具有不合理性:一是行驶的主体包括车和船,将交通工具解释为船只也没有突破其文义的范围。二是水上环境与陆地环境具有极大的差异性,一旦发生事故,其救援成本和难度更为巨大。而将商业运营船纳入公共交通工具的范畴,可以在法律层面上宣告此类行为的现实危险性,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三是妨害水上交通的安全驾驶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除去与陆上事故相同的撞击、侧翻和倾覆等危险之外,水上事故更多了一层溺水的危险。基于“举轻以明重”之逻辑考量,因此将商业运营船只纳入公共交通工具势在必行。
第二,从事商业运营的智能化无人汽车当属公共交通工具。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无人驾驶的智能网联汽车也逐渐进入人们视野。无人驾驶出租车、无人驾驶智能网联巴士已经在全国多个城市投入运营。由此便带来了一个问题:对无人驾驶的汽车实施妨害安全驾驶之行为能否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笔者认为这种行为依旧可以构成,其原因如下:一是无人智能汽车并没有超越汽车之文义范围。汽车的核心概念是使用自身动力装置行驶的交通工具,无人驾驶之汽车无疑符合该核心概念,因此不应该以是否有驾驶人来区分是否为汽车。二是将无人汽车纳入公共交通工具之范畴符合立法目的。妨害安全驾驶罪之创设目的在于刑法提前介入公共交通领域,以防范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保障民众出行上的安全。[3]在缺少司机的保障情况下,乘客抢控驾驶装置的行为往往更具有危险性,故将无人驾驶汽车纳入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规制之中,符合立法目的。
第三,小型出租车和网约车也应当属于公共交通工具。与一般的中、大型客车和出租车相比,小型出租车、网约车乘客较少、体积较小,相对而言对公共安全的影响较低,现实中发生在小型出租车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较少。因此,立法者基于刑法谦抑性的考量,并没有在《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小型出租车和网约车属于公共交通工具。但笔者认为此种规定不尽合理。妨害安全驾驶罪保护的是公共安全,既包括车内人员的公共安全,也包含车外人员的公共安全。在如今互联网普及之下,各种乘车软件层出不穷,同一出租车乘车人员具有不特定性,而且行为人妨害安全驾驶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进而与车外的行人和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因此,基于维护车内外整体的公共安全的考虑,应将小型出租车和网约车纳入到公共交通工具的范畴。
(三)“暴力”内涵之分析
暴力的实质是一种强制力。刑法基于其谦抑性原则,将暴力限缩为有形的强制力,将语言暴力、网络暴力排除在外。因此,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暴力首先应当是有形的物理暴力。乘客对驾驶人员的语言暴力、人格侮辱等都不能是本罪中的暴力。这种暴力作用的对象必须是驾驶人,两行为之间需要发生联系,否则即使存在有形的暴力,但不能联系到驾驶人,也不能构成本罪之暴力。例如在车内与他人互殴,抢夺他人财物等,这种不针对驾驶人员的行为不能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当然如果行为人在与他人打斗过程中对驾驶人产生干扰,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的,应当认为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同时,此种暴力需要达到危及公共安全的程度,即会干扰到驾驶人,并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
二、抢控行驶中公共交通工具驾驶操纵装置之认定
(一)“抢控”行为之认定
2019 年《指导意见》中仅仅规定了“抢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则将抢夺扩充为了“抢控”。基于文义解释,“抢控”应当理解为“抢夺”与“控制”两种行为。应当注意的是“抢夺”与“控制”是选择性的构成要件要素,行为人只要有二者之一的行为,便可构成抢控。例如,行为人与司机争夺方向盘,但最终没有成功控制方向盘,这种情况也被认定为抢控,并不因为行为人没有控制方向盘而构成“抢控”未遂。
(二)“驾驶操纵装置”之解读
《指导意见》明确规定驾驶操纵装置有方向盘和变速箱。但《刑法修正案(十一)》并没有列明具体装置,而仅仅笼统地规定了驾驶操纵装置。驾驶操纵装置是指能够影响交通工具安全行驶的控制装置,具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主要驾驶操纵装置,包括方向盘、手刹、离合器、加速踏板、变速杆、加速踏板;另一类是次要驾驶操纵装置,包括:灯光控制装置、雨刷器、除霜器、挡风玻璃、仪表盘以及车钥匙等等。
第一,主要驾驶操纵装置是交通工具安全行驶的关键。对主要驾驶操纵装置的抢控会直接危及交通工具的安全行驶,因此其无疑是《刑法》中规定的驾驶操纵装置。
第二,关于次要驾驶操纵装置能否被解释为《刑法》中的驾驶操纵系统,这需要参考多种因素综合认定。如果行为人抢控的装置能够危及当时情境下的公共安全,则该装置可以被评价为驾驶操纵装置,反之则不能。例如,行为人在雨雪天气抢控雨刷器,这会影响司机视线,危及公共安全,因此此时雨刷器应当被解释为驾驶操纵装置;再如,车辆在黑夜中行驶,行为人抢控灯光控制器,驾驶人看不清前方道路,也会危及车辆行驶安全;又如,行为人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抢控车钥匙,可能会导致车辆骤停,危及行车安全,因此此时车钥匙也是驾驶操纵装置。当然,如果是在万里晴空的白天,行为人抢控雨刷器或者灯光控制器,此时并不会对行车安全造成影响,因此此种情形不能将雨刷器和灯光控制器解释为驾驶操纵装置。
第三,无人汽车上所配备的自动驾驶系统上的摄像头、雷达、运算和定位等装置也应当解释为驾驶操纵装置。这些装置是保证无人汽车安全运行的关键。如果行为人抢控上述自动驾驶系统,无疑会影响车辆的安全行驶,危及公共安全。故无人汽车上的自动驾驶装置也应当被解释为驾驶操纵装置。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机动车上所配备的驾驶辅助系统不应当被解释为驾驶操纵系统。不同于无人汽车上的全自动驾驶系统,驾驶辅助系统的目的只是辅助驾驶人进行操控汽车,并不直接控制汽车,汽车依旧由驾驶人进行操纵。国内外部分车企开发的驾驶辅助系统,都要求驾驶人介入操控。如果行为人破坏了驾驶辅助系统,驾驶人依旧可以自行操纵车辆,并不会危及驾驶安全。故包括360 全息影像、车道保持系统、车道偏离系统在内的驾驶辅助系统,都不应当被评价为驾驶操纵装置。
三、驾驶人擅离职守,在交通工具上殴打他人或者与他人互殴之认定
此种行为模式主要针对驾驶人员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驾驶人员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必须同时满足擅离职守和殴打他人或与他人互殴两种行为。单有擅离职守行为或者单有殴打行为都不能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
(一)擅离职守之认定
“擅离职守”按照字面意思就是驾驶人员未经许可,在工作时间擅自离开岗位,未尽到职责义务的行为。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并未对驾驶人何种行为属于“擅离职守”进行解释,往往是公交公司、出租车运营公司的内部制度进行规定,这种规定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因此对“擅离职守”进行法律上的界定确有必要。
结合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立法目的,判断驾驶人是否构成“擅离职守”需要以驾驶人之行为是否危及公共安全为标准。如果驾驶人放下手刹或者熄火,确保车辆停止,不会危及行车安全,那么便不能认为驾驶人擅离职守。如果驾驶人并未放下手刹,车辆依旧处于启动的状态,即便车辆并未运行,也应当认定为驾驶人擅离职守。因为此时车辆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可能随时因为他人的误碰而运行,进而危及公共安全。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擅离职守”不易作扩大解释,不能将所有擅自离开岗位的行为都视为擅离职守,只有那些可能危及行车和公共安全的擅离职守才能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要素。
(二)互殴与正当防卫之间的博弈
“互殴”是指不法侵害者在其主观上的侵害故意支配下,客观上实施了连续互相伤害的行为;[4]“防卫”是指对不法侵害人采取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防卫权是公民之合法权利,而保障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运行也是每一位驾驶员的职责。当行为人殴打司机时,对于司机的反击是互殴还是防卫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其是否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在司法实践中互殴与防卫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驾驶人受制于维护公共安全的职责需要,其反击行为可能会面临不同定性。故笔者认为应当立足于正当防卫成立的条件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驾驶人员是否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进行综合判断。
2020 年9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曾规定了防卫与斗殴的区分,其认为互殴与防卫应当遵循主客观一体的原则,综合案件起因、双方的过错、是否准备凶器等多重因素进行考量。但是这种区分是针对一般情境下的行为,司机在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进行反击,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行车安全。因此,在认定司机是否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时,需要立足于具体的案情,充分考虑主客观要件、时空状况以及双方手段,并结合社会一般人在相同情境下所采取的手段方式,充分考量驾驶人当时的立场,不能苛责驾驶人的反击行为。当然驾驶人一般拥有丰富的驾驶经验以及处理类似情形的技能,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也应当考量驾驶人员履行保障安全义务的可能性,对驾驶人是否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进行综合认定。[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