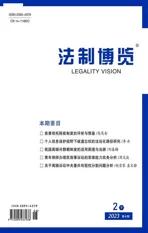不良PUA犯罪裁判标准的实证分析
2023-04-05苏姿铭
苏姿铭 王 轩
山东工商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0
PUA原本是一种搭讪的技巧,但在不断变异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精神控制和情感操纵的手段。其消极影响不断扩大并呈现出向恶发展的趋势,涉及领域由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逐渐扩展到各个主要社会成员之间,甚至有向未成年领域扩展的趋势,受侵害者由女性占多数逐渐转变为男女数目相当,并且其传播速度不断加快,行为手段更加系统化、专业化,但在裁判实践中有关涉PUA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依然模糊。本文根据裁判文书网中涉及不良PUA的犯罪实例进行实证分析,以图为涉不良PUA犯罪的定罪量刑提出建议。
一、不良PUA实施方式
目前我们考虑不良PUA不应局限于两性的亲密关系中,而应从多方人际关系考虑。
(一)在男女亲密关系中主要表现为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利
1.侮辱。不良PUA实施的第一步表现为侵害人对被侵害人实施人格上的打压,使得受侵害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受挫,从而方便进行下一步的情感操纵。
2.施暴。为了实现精神控制的目的,侵害人不只要在精神上实行打压,往往配合着实际暴力行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侵害人实施暴力行为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便于更好地控制被侵害者,起到威慑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宣泄情感。
3.诈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精神控制的存在,认定成立诈骗或胁迫的标准可能比一般情况下的要宽泛得多,甚至完全不符合一般理性人标准[1]。
(二)在其他人际关系中的表现
除了在男女亲密关系中还体现在其他人际交往方面。例如,在职场中上司对下属的打压,人民网发布一篇题目为《人民来论:杜绝职场PUA,需要全社会的合力》的文章,其中提到63%的受访白领遭遇过职场PUA;在家庭教育中和学校教育中家长与老师也会对孩子与学生进行类似的打击行为;随着社会技术水平和人们认知的提高,传播的方式也在逐渐更新,利用PUA更便于控制高素质人群。
二、涉不良PUA犯罪的定罪标准
(一)涉不良PUA犯罪的类型
我国现行《刑法》以及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对涉不良PUA行为进行法律定性,无疑对惩治这一犯罪行为产生了严重的阻碍。而现有涉不良PUA的犯罪的都是通过将其归入到不同的罪名中进行惩治,通过对现有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总结在不同罪名下涉不良PUA行为的特性,研究其定罪规律,总结量刑标准。在较为典型的涉不良PUA案件中,根据行为所侵犯客体不同进行如下划分:
1.强奸罪:以葛某某强奸案①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6刑终125号葛太平强奸二审刑事裁定书。与孟某某强奸案②山西省绛县人民法院(2015)绛刑初字第158号被告人孟祥茂强奸一审刑事判决书。为例,与普通强奸案相比两案皆违背了妇女意志,所侵犯的是妇女的性自主权,不同之处则在于两案皆对被害人采取心理控制与精神控制。葛某某通过每天与受害人交流的方式,逐步与受害人建立密切联系,在获得被害人信任后又实施了强奸行为,并对其进行精神强制和心理控制;孟某某利用欺骗、引诱、恐吓的办法达到了玩弄少女的目的,并通过长期且较为稳定的有形暴力与无形暴力方式并存行为在精神上达到控制被害人目的。
2.虐待罪:以包某案件[2]为例,因该案侵犯的客体是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与人身权利故划为此案范围内,与普通家庭成员间的虐待罪不同,在这里将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进行了扩大解释。被告人牟某翰在与包某的长期恋爱期间多次使用大量侮辱性言语,并以自杀为威胁,强制与包某维系恋爱关系,采取有形暴力与无形暴力相结合的手段对包某实施精神控制与心理控制。
3.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以高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①甘肃省静宁县人民法院(2015)静刑初字第38号高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一审刑事判决书。与王某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②甘肃省静宁县人民法院(2015)静刑初字第32号王春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一审刑事判决书。为例,高某案中被告人通过精心设计“授课”等方式对被骗人实施精神控制,进行封闭式“洗脑”;王某某也以相似方法采取逐步瓦解,专题沟通等方式对被骗人实施心理控制,该两案中采取精神控制的方法多以无形暴力形式为主并衍生出一套相对完整的程序。
4.诈骗罪:以韩某某诈骗案③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9刑终293号韩芬竹诈骗二审刑事裁定书。为例,该案侵犯的是公私财物所有权,韩某某通过封建迷信的手段长期且稳定地对被害人进行精神控制,最后致使被害人精神压力过大而自杀身亡。
基于上述及其他多起案件以及相关已生效裁判文书,我们总结出涉不良PUA犯罪的普遍构成标准。
(二)涉不良PUA犯罪的犯罪构成
综合上述裁判实践发现,涉不良PUA犯罪的构成要件如下:
1.从主体来看,本类犯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本罪的行为人相对于强奸罪与强制猥亵、侮辱罪等应做扩张解释,女性也会成为一般行为人,在本类犯罪中,不论男女性别的差异,其定罪量刑不会存在差别。
2.从客体来看,本罪侵犯的大多数是他人的身心健康权利,少数还会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不良PUA以精神操控和心理控制的手段,对被害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一定的控制,损害他人身心健康,从而由此满足自身的一些不法目的。
3.从主观方面来看,本罪的主观上出于故意,即具有利用PUA的技巧对别人进行精神和心理操控的直接故意。本罪的行为人在动机上通常表现出以控制他人、利用他人来达到自己的不法目的的意思倾向。对于不良PUA犯罪是否包含奸淫目的,我们目前暂时持保守态度,我们认为但凡行为人对他人实施了奸淫行为便应该以强奸罪或者其他相关罪名对其定罪量刑。
4.从客观方面来看,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违背他人意志,以精神操控、心理控制或者其他无形暴力的方式来对他人进行行为控制以满足自身非法目的。且该行为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行为人利用精神操控、心理控制等方式来非法控制他人行为满足自身目的是不良PUA犯罪的本质特征。该方式是对他人自由的妨碍,是违背社会主流价值的。我们应当注意,不管控制他人的行为是无形暴力或有形暴力,都不应该被社会所允许,特别是利用控制他人来实现自身非法目的的行为。
(三)非罪问题中不良PUA举证难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涉不良PUA行为中只有少部分行为满足入罪条件。就目前来看,以刑罚论处的案件占已发生事件的少部分,大部分事件是在道德上进行谴责,另一部分案件从其他法律领域进行规制,如江苏网警发布的首例PUA事件,该案件主要为搭建网站兜售非法PUA教程,最终以行政法方法处罚;李某某与廖某某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中,廖某某通过精神施压逼迫李某某流产,致其产生精神病态和抑郁症,该案从民法角度入手重点围绕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通过部分未入罪的案例来看,举证困难的原因如下:
首先,侵害者一方过错责任不明显。在传统的思维中我们常会认为一个人的心理问题是由于其无法调控好自己心态造成的,所以在考虑过错问题时,会将这种过错进行分摊。对于侵害者的心态我们无法用事实证据进行衡量,对于过错责任难以准确判断。其次,违法行为造成实际损害轻微,多集中于精神损害方面,难以确定侵害行为与损害程度之间的关系。不良PUA最终目标是击溃受侵害者心理防线以达到控制和操纵其精神,所以这类违法行为多以语言为主,难以收集,针对违法行为的证据多为陈述等间接证据,在裁判时法官无法直观判断该侵害行为的轻重,甚至无法判断该行为是否真正实施。最后,精神控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无法证明是主要问题,证据与事实联系是否密切是裁判案件的关键问题。大家一般会普遍认为,精神操控、心理控制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与导致其自杀并不具有绝对因果关系,但在不良PUA行为中,行为与结果的联系可能是直接教唆、煽动,也有可能是间接贬低、打击,这些需要利用大量证据的罗列、关联和推定。
三、涉不良PUA犯罪的量刑标准
涉不良PUA行为的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并未独立成罪,因此我们只能基于现有典型案例研究有关PUA手段对量刑的影响。一个行为只有符合基本犯的成立条件,才可能因为具备加重情节进而成立对应的加重犯,即不良PUA行为是否可作为加重情节的前提是该涉不良PUA犯罪需满足我国现行《刑法》的入罪条件。
我们以下列案件为例,根据具体量刑总结涉PUA犯罪量刑规律:葛某某强奸案:具体量刑为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因累犯而从重处罚;孟某某强奸案:具体量刑为有期徒刑六年,无从重情节;韩某某诈骗案:具体量刑为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因精神控制致人自杀,造成严重后果而从重处罚;高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具体量刑为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无从重情节。
通过典型案例所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涉不良PUA行为的犯罪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种加重情节进行惩治,这也是我国未来针对涉不良PUA犯罪应当解决之重点。按照当前刑法学理论,刑法的任务与目的可概括为保护法益,所以刑法所干预的只是侵犯法益的行为,即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当我们结合不良PUA表现来看,不良PUA性质的行为造成的主要是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也就是说不良PUA行为侵犯的是当前法律所保护下的自然人精神健康和自由。长期以来,我们对人身健康的关注点一直集中在了个人的身体机能的健全,对精神世界健康缺乏了相应的关注。伴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很多犯罪形式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衍生出来,如今的精神权益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重视。随着诸如包某案件的公之于众,更让人看到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公民精神健康权益的紧迫性。
随着当下人们精神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及对于精神权益保护日益重视,我们不断意识到无形暴力与有形暴力具有等值性,甚至有时精神暴力带来的伤害远大于有形暴力,精神控制行为制造了不被允许的风险。如不法行为人利用持续性的精神控制行为给受害人施加多种精神伤害,侵害行为极其严重,相较于一般的人际关系,恋爱关系中双方关系更具强制性,受害人在精神痛苦中进行自杀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受害人因为精神控制的缘故,其自杀行为被阻断的可能性也会小于一般的自杀行为。所以,一个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实施不良PUA行为对法益的侵犯以及对法益的威胁符合非难可能性。
尽管我们已经在理论上看到了不良PUA的非难可能性,但我们在实际的生活案例中,也应明确认识到不良PUA行为犯罪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涉及不良PUA行为的违法犯罪是随着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在王某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中,其利用精神操控的方式来控制其传销组织中的成员,已符合不良PUA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但最终定罪量刑时,法院并没有就这单一行为进行单独论证,认为王某某组织领导以“连锁销售”经营活动为名,按一定顺序组成层级,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与社会秩序,其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本案中以心理操控为特征的不良PUA行为被归纳到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引诱、胁迫”这一构成要件之中。在目前视角来看,两者间存在部分区别,因在很多情况中我们看到,不良PUA行为由于对被害人进行精神操控和心理控制会对被害人原有的精神世界造成严重冲击,这种精神痛苦极易引起被害人精神性疾病,这样的精神损失是“引诱、胁迫”手段难以企及的。如果仅仅依据案情中的行为表象而对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进行论断是不符合法益保护要求的,因此这也是我们认为不良PUA行为在犯罪中应当作为加重情节考虑的主要现实依据。
四、结语
应该承认,良性PUA为人际交往提供了便利行为手段。但在涉PUA犯罪问题上,我国现行立法并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因此需进一步结合现行司法实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良性引导。新提请审议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中提到禁止用迷信、精神控制(PUA)等手段残害妇女,这项草案的修订无疑使预防与规制PUA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采取“刑行兼理法”的具体规制模式,以处罚网络发布PUA相关信息为规制切入点,以司法惩治PUA具体行为为规制重点,同时结合社会预防作为规制补充。我们认为,因刑法本身的谦抑性在PUA事件还未完全发酵之前应尽可能用刑法之外其他法律来规制,防止其进一步扩大,而刑法应当成为最后一道保护受侵害的合法利益的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