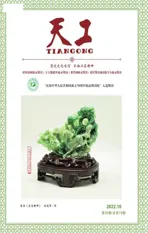浅谈中国夹纻佛造像题材与风格之变
2023-01-06陈国勇
陈国勇
正如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开篇中所写:“艺术之始,雕塑为先。盖在先民穴居野处之时,必先凿石为器,以谋生存;其后既有居室,乃作绘事,故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也。”自从人类用石头制造用具以来,制造方式经历了从原始粗加工到手工精细加工的转变。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天然大漆为主要材料的加工工艺应运而生,这就是中国漆艺。中国是最早开始在生活用器中使用天然大漆的国度,中国人把大漆视为一种温暖、有生命力的珍贵材料。
大漆的获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在艺术创作中既能独立作为主角呈现,又能以一种极具包容性的创作材料存在,并与中国雕塑艺术互相成就,诞生了夹纻佛造像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夹纻佛造像作为中国漆艺术和宗教艺术共同作用下的特殊产物,其时间跨度之大、艺术价值之高,放眼世界艺术史也实属罕见。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在中国传统雕塑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佛造像作为佛教最直观、最具象的艺术表现形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但都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发展、艺术文化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漆艺介入中国佛造像雕塑艺术已有很长的历史,其中夹纻工艺与佛造像的结合起源于战国时期,并且技法和材料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异,但核心制作工艺均是以漆结合木、麻等天然材料塑出造像结构,再经过多层上漆、打磨造型、表面髹饰等系列工序完成,体量大小差异极大,可以满足不同时期的实际使用需求,能在一尊佛像中同时展现出“漆性”和“佛性”两种特质。
中国不同时期的夹纻佛造像的表现手法也反映了该时期人们的审美意识。在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时,从哲学的角度看,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是有神论。这一时期佛造像作为佛教主要宣传手段之一进行大量制作,此时期人们希望通过朝拜佛像诉说愿望来改变生活现状。这一时期主流的佛造像沿袭的是外来佛造像的形态,更多的是高高在上的“神性”,夹纻佛造像也不例外。之后,随着佛教在中国不断地传播和发展,佛造像开始与以儒、道两家为主体、本土化宗教流派为特色的中国传统审美意象相融合,成为中国化的独立审美对象,并且逐步贴近人们的生活,“人性”渐丰。回顾各个时期的中国夹纻佛造像,可以发现其题材与风格变化中的时代烙印。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逐渐形成,人们将佛陀、菩萨造像作为独立的崇拜对象,并以此为题材在很多材料上进行雕塑创作,诞生了一批在中国雕塑史上地位举足轻重的佛造像,这些佛造像也被视为是中国佛教艺术独立发展的开端,是佛造像开始汉化的重要节点。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变化是佛造像的面相和表情,此前佛造像身上印度犍陀罗的影子很重,造像大多面相丰满、肢体肥壮,鼻梁与眉骨高耸,衣纹服饰厚重,像打湿了一般紧贴身上,是典型的古希腊造像艺术一脉,主要呈现的是神圣不可亲近的气氛。到了北魏后期,佛造像的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面相逐渐清瘦、清秀,出现汉人的样貌,身体比例也开始接近真人,服饰上可见南朝文人士大夫的着衣风格。这意味着佛造像已经开始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开始贴近民众的真实生活了。
随着佛教的快速传播,很多宗教仪式也逐渐兴盛起来,流行的宗教仪式中就包括“行像”。所谓“行像”,就是把佛像放在布满装饰的花车上进行公开巡游,以供往来群众朝拜。北魏杨衒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校笺》就记载着“行像”活动的盛大:“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部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为了方便花车巡游、满足群众瞻仰佛像的需求,“行像”活动对佛像的制作提出新要求——尺寸要大、重量要轻、材质要稳固、不怕风雨等自然环境因素的侵蚀。这些都与夹纻工艺所制作的器物特性一致:尺寸可大可小,外表坚固耐风雨,器物中空,整体轻便。由此,原本常用于小型生活器皿的夹纻漆工艺被大量运用到了佛造像的制作中。得益于漆的包容性和延展性,夹纻佛造像的尺寸日渐往巨型发展,也给了同时期的匠人足够的施展空间,古籍中记载着不少他们创作出的惊人作品。
关于夹纻佛造像最早制作者的记录出现在梁国释僧祐所著的《出三藏记集》一书中。他在书中写道:“樵国二戴造夹纻像记。”这里的樵国就是今天的安徽亳州市,“二戴”是指戴逵和他的二儿子戴勇。这里提到的戴逵是一位具有创造性的夹纻佛造像制作者。这位活跃在晋代的著名雕塑家、美术家,原本就以擅长雕刻及铸造佛造像而闻名。他率先将夹纻工艺运用到佛造像制作中,因此也被后人视为夹纻胎造像的创始者。
隋代是夹纻佛造像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此前,夹纻佛造像在汉代经历了灭佛风波,到了公元581年隋文帝恢复了佛教,开始大力修缮佛寺,夹纻佛造像的制作也随之恢复。隋代的佛造像风格是在北齐、北周的佛造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多延续了前朝佛造像体态丰满、服饰线条流畅、简洁的风格,其中陕西、山西等中国西部地区的隋代石刻、木雕佛造像最有代表性。隋代的夹纻佛造像同样留有北齐、北周遗风,题材上流行主尊佛陀、弟子、菩萨、供养者、力士、灵兽的组合样式,造像风格是典型的魏晋南北朝风格,骨骼清晰,线条轻盈,形象偏瘦弱,衣物刻画轻薄贴体,姿态更显优雅生动。面部表情的刻画主要展现神秘、无欲的感觉,虽然借用的是世俗人物造像的形态,却注入了一种平静、宁静、自然的气质。可见,隋代的夹纻佛造像反映的是佛陀的“神性”。
唐代夹纻佛造像的创作题材在此前以佛陀、菩萨为主的基础上有了新变化,开始出现罗汉像、天神像、祖师像。这种新题材的出现源于人们对佛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符合当时社会审美的佛造像气质是既内省又开朗、既沉稳又温柔、既有神的韵味又有中国传统的入世情怀。唐代的这种审美偏好让唐代夹纻佛造像的创作题材突破了原本佛教教义中佛陀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局限设定,向着更加生动鲜活、有血有肉的题材发展。这种变化是唐代时期佛教艺术进一步中国化的结果,是受中国本土思想深刻影响的结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罗汉和祖师这种从现实中的真实人物演化而来的题材受到了唐代民众的追捧。而唐代后佛教各个教派不断兴起,佛教的百花齐放也间接影响了佛造像的题材,人们对佛陀“神性”的崇拜开始淡化,更有“人情味”的罗汉、祖师、菩萨题材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青睐。
唐代夹纻佛造像风格是典型的唐代美学风格,整体塑造上肌肉感更强烈,胸部结实平滑,躯体肌肉有着起伏变化,衣物的处理也不像隋代那样贴身,而是更有厚重感,更喜欢使用高贵富丽的色彩。在面容刻画方面,唐代夹纻佛造像较隋代而言更为精致,人体结构设计更为合理,虽然依旧充满着佛像“神性”,但体态姿势和整体的精细程度更为细腻,这是因为唐代的佛造像艺术开始肯定现实,追求现实中的美感。因此,夹纻佛造像中自然蕴藏着唐代偏好华丽世俗的审美趣味。
宋代的夹纻佛造像相比唐代有了明显的衰落痕迹,流行程度远不及前朝。宋代夹纻佛造像在宋代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开始追求一种本真、淡雅的气质,少用金饰,常用素髹,这符合宋代漆器的审美。造像的衣纹更为简单,面部刻画具有典型的宋代世俗人物特征,十分流行呈游戏坐姿的菩萨像,造像鲜活灵动,体现了宋人的宗教信仰和审美情趣。宋代夹纻佛造像题材除佛陀、菩萨像之外,极为流行的题材之一是罗汉,这与宋代盛行的罗汉信仰关系密切。罗汉是梵语中阿罗汉(Arhan)的汉译结果,是阿罗汉的缩写,旧的翻译中也将其称为应真、应供等。按照佛教的说法,一个佛教徒可以在修行后达到四个不同的层次,分别为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四种果位一一对应。通过修行获得果位的人叫阿罗汉,简称罗汉。罗汉同时还有“应当堪受”的意思,就是值得受供养敬拜,因此在宋代人们的心中,罗汉是代表着高贵而博学的得道高僧,存世的宋代夹纻佛造像中就有不少的罗汉题材,对罗汉题材的偏好也延续到了元代。
元代各种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元代统治者推崇藏传佛教,所以元代夹纻佛造像也呈现出汉、藏、尼泊尔三种造像风格相互糅合的特点。在风格塑造方面,元代夹纻佛造像沿袭了宋代流行的写实风格,擅长将人的微表情和微妙情感植入佛造像中,在佛造像的“神性”之外力求表现“人性”和内在美。这种审美风格使得元代的夹纻佛造像比宋代的夹纻佛造像更加有气势,存世的元代夹纻佛造像往往体态饱满、舒展,举止优雅,气势磅礴。在表面装饰方面,元代夹纻佛造像配饰简洁朴素,喜用金漆和赋彩华丽的花纹装点衣饰,使元代夹纻佛造像更加繁丽华贵、精致的同时不落俗气,带着文人的审美趣味,这也是对尼泊尔风格的融合转化,也从侧面反映了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强盛。

《水月观音夹纻像》 陈国勇/作
元代诞生了许多位在夹纻佛造像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匠,其中一位著名的造像工匠是刘元,他师从阿尼哥,是曾为忽必烈造像的元代尼泊尔名匠。刘元非常擅长夹纻工艺造像,还创造性地将中华传统文化和佛教中的“西天梵相”相结合,积极吸收汉族风格,创作了大量精绝无比的夹纻佛造像,在元代人们对他的夹纻佛造像作品评价极高。以刘元作品为代表的夹纻佛造像刻画细腻、装饰华丽,尤其讲究线条美,佛造像往往宽肩细腰,面容表情安详谦和,面容和服饰存在一定程度的汉化。明清时期,夹纻佛造像的汉化趋势进一步加深,世俗化进一步加强。以明代流行的水月观音题材夹纻像为例,其大多是高髻,穿着长袍、长裙、丝绸帔帛,胸前戴着璎珞,风格更为雍容华贵,装饰愈加繁缛,这是明代观音菩萨的特征。同期的夹纻佛造像也有明显的汉藏风格,常见身着汉式偏衫。
进入清代之后,藏传佛教的传播更加广泛,清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形式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夹纻佛造像在这一阶段仍呈现出汉藏佛教艺术相互融合的特点。清代各种工艺技术得到不断改善,其核心都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精神需求,使得清代夹纻佛造像更加追求造像的工艺性和装饰性,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造像的精神刻画和创新。根据《圆明园内工佛作现行则例》钞本中关于清宫庭制夹纻佛造像的记载,清宫夹纻佛造像使用的材料有夏布、桐油、严生漆、笼罩漆、退光漆、漆朱等,制作方法是“佛像不拘文武,油灰股沙,使布十五遍,压布灰十五遍,长面像衣纹熟漆灰一遍,垫光漆二遍,水磨三遍,漆灰粘做一遍,脏膛朱红漆二遍”。由此可见,清代夹纻佛造像的制作工艺与前代相比有所调整,裱布和上漆层数明显增多,整体体量也小了很多,胎骨增厚,分量较重,加之愈来愈富丽堂皇的金饰和色彩叠加,整体造型偏向臃肿。
回顾中国夹纻佛造像不同时代题材与风格的变迁,可以发现佛造像正在逐渐走下神坛,融入中国人的世俗生活,越来越地方化、世俗化。这种变化的大背景是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一直与中国本土文化进行着交流与碰撞,逐渐吸收了儒、道、佛三家思想,在弱化了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同时,增加了人情味和亲切感。佛教在中国独立发展,兴起不少宗教派别,产生了顺应时代的新思想,对夹纻佛造像的题材与风格的变化有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论题材是佛陀、菩萨还是罗汉、祖师,也不论经过几个朝代,夹纻佛造像在技艺不断完善的同时,印证着所属时代的审美和精神。夹纻佛造像的题材都与人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密切相关。在夹纻技艺和大漆的加持下,夹纻佛造像不再仅仅停留于佛经和佛家故事中人们崇拜的偶像,更多地展现人们心中睿智、美丽、高尚的人格,是中国人美好理想的体现。为了更好地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夹纻佛造像在个体造像以外,还发展出了组合、场景展示等形式。回顾世界艺术史,凡是能进入世界艺术殿堂的作品,无一不是经过了时代的考验和锤炼,以其独特的民族精神魅力脱颖而出。夹纻佛造像作为中国佛像的主要分支之一,其艺术生命来源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民族精神,对现代夹纻佛造像的创作复兴和重塑现代夹纻造像艺术生态观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