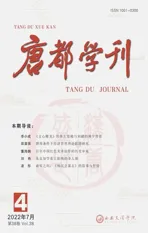《文心雕龙》的体大思精与刘勰的佛学背景
2022-11-21李小成
李小成
(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西安 710065)
《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结构宏大、体系严密的文学理论专著,章学诚以“体大而虑周”(1)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评价,最为贴切不过。言其“体大而虑周”者,因它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体大”者,因其以原道、征圣和宗经为核心,是自成系统的文学批评观;“思精”者,因全书五十篇,内容丰富,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方方面面的问题,追源溯流,梳理条畅。说它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论著绝不为过,一是《文心雕龙》论述的范围广泛、涉及的文体全面,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二是《文心雕龙》具有缜密的思维与严整的逻辑;三是《文心雕龙》自成体系,思理严密。在刘勰的前后时期,居然没有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与之相称。之所以如此,这与刘勰的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关于这个问题,早先饶宗颐、石壘有几篇文章谈及刘勰与佛教的关系,以及新疆大学中文系马宏山《文心雕龙散论》(2)参见饶宗颐《文心雕龙探源》《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文心雕龙与佛教》;石壘《文心雕龙与佛儒二教义理论集》;马宏山《文心雕龙散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台湾学者方元珍有专著《文心雕龙与佛教关系之考辨》(3)参见方元珍《文心雕龙与佛教关系之考辨》,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从刘勰生平与佛教之关系、刘勰和论文之时代背景、《文心雕龙》文原论、文体论、文术论、批评论等六个章节来探讨《文心雕龙》和佛教之间的关系,最后一章是结论,作者认为刘勰系出贵胄,家学渊源,因生计拮据,寄居桑门,辅佐僧祐,三次校经,书成于第一次校经之后,时为早年,佛学思想浸润未深,故其书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笔者以为,《文心雕龙》之体大思精与佛学关系密切,尤其受佛学思维方式的深层影响,有必要再探究。
一、身处崇信佛学的大时代
佛教自两汉之际由西域传入中原,到南北朝时期已成燎原之势,从社会高层到庶民百姓,信仰佛教成为风尚。孙昌武《南朝士族的佛教信仰与佛教文化》一文详述了南朝主流文化的佛教信仰:首先是高门(包括皇族)出家成为风气,其次是高门士族信众积极参与佛学典籍的翻译撰著,再次是南朝建寺形成高潮,最后是这一时期宗教信仰普遍诚挚、浓重。高门士族作为统治阶层对开展的上述活动有热诚的信仰来支持,十分活跃的信仰实践活动是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重要特点(4)参见孙昌武《南朝士族的佛教信仰与佛教文化》,载于《佛学研究》2008年。。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迅速传播导致儒学衰微,人们的传统观念被颠覆了,章句之学被时代所否定,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随之兴起。
首先,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动荡,用人制度方面只看门第出身,不重才学,读书人仕途迷茫,人心动荡,找不到精神慰藉,于是佛教就填补和满足了人们这一精神需求。生活在底层的百姓,处于战乱中,生活漂泊不定,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的太阳,只能将目光投向虚无缥缈的来生,于是就信佛拜佛,寄希望于来世。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给佛教的流行提供了适足的土壤。
其次,佛教自身的成长,及与社会各方面主动进行融合。南北朝时佛教信徒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发展壮大,已然成为当时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弘扬佛教,莫重于译经,自东汉以后,历朝都重视译经,柳诒徵《中国文化史》有一个统计[1],据《开元释教录》表之如下:
这些译本多据梵本译出,有些是凭口诵翻译。仅从对佛经翻译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佛教不仅重视实践,而且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构筑。
再次,统治者对佛教极力提倡。南北朝时期,无论南北,统治者都极力倡导佛教。西晋灭亡后,北方的前赵与后赵政权相继建立,石勒、石虎崇信佛教,他们是羯胡少数民族,对能否在中原称王信心不足,于是就借助佛教的教义,来增强他们入主中原的勇气和信心。石氏叔侄重用当时的僧人佛图澄,称他为“大和尚”。石虎做皇帝后,对佛图澄更为敬重,下诏曰:“和尚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匪及,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2]541当然,佛图澄也抓住时机,和弟子们大力弘扬佛教,使得北方出家为僧的人数剧增,也有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徭役和兵役而出家的。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经常聚集僧俗,讲论佛法,参与的僧侣多是高水平的义学沙门。他本人也有关于佛法之作,由僧祐辑录为《法集录》。据《全梁文》卷71《略成实论记》载:“齐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余人,请定林僧柔法师、谢寺慧次法师于普弘寺迭讲,欲使研核幽微,学通疑执。即座仍请祐及安乐智称法师,更集尼众二部名德七百余人,续讲《十诵律志》,令四众净业还白。公每以大乘经渊深,漏道之津涯,正法之枢纽。而近世陵废,莫或敦修,弃本逐末,丧功繁论。故即于律座,令柔、次等诸论师抄比《成实》,简繁存要,略为九卷,使辞约理举,易以研寻。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设三业三品,别施奖有功、劝不及,上者得三十余件,中者得二十许种,下者数物而已。即写《略论》百部流通,教使周颙作论序,今录之于后。”[3]南朝的统治者倡扬佛教更是不遗余力,最典型者当属梁武帝。《梁书·武帝纪》载:“三月辛未,舆驾幸同泰寺舍身。……冬十月己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若涅槃经义,迄于乙卯。前乐山县侯萧正则有罪流徙,至是招诱亡命,欲寇广州,在所讨平之。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义,讫于十二月辛丑。……二月癸未,行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高祖升法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讫于己丑。……兼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4]71-75作为皇帝的梁武帝不但崇信佛法,而且多次“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若涅槃经义”,还舍身同泰寺,如此现身说法,不言之教,可想而知老百姓对佛教的趋之若鹜。所以刘勰终身未娶,长期住在寺院,最后出家为僧,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长期在定林寺整理佛教典籍
据《梁书·文学传》载:“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乞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于世。”[4]710据穆克宏《刘勰年谱》所记:永明二年(484),刘勰20岁时到定林寺投靠僧祐,帮助僧祐搜集、整理佛经。其依据是《高僧传·僧祐传》:僧祐“永明中,敇入吴,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凡获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缮诸寺,并建无遮大集、舍身斋等。及造立经藏,搜校卷轴。……初,祐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2]690但这段记载与刘勰入寺的时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不知何据。
关于刘勰所居之定林寺有二:一在建康,一在莒县(5)王汝涛和刘心健等曾就田辰生“刘勰故居为莒县定林寺”说提出异议,他们认为“所谓定林寺,应该界定是建康钟山的定林寺,而非山东莒县定林寺”。文见《文史知识》1982年第12期。。牟世金的《刘勰总年谱汇考》以僧祐事迹推理刘勰行迹。僧祐为江南名僧,梁武帝非常敬奉。萧子良曾在建康聚众讲法,僧俗甚众,其中就有僧祐。再者,1963年,陆侃如为山东莒县刘勰纪念堂撰写《刘勰年表》,其中就说“这里所说的定林寺,应指京口的庙宇,现在山东莒县也有定林寺,恐怕是另一所了”。建康的定林寺有钟山的上定林寺、下定林寺之分,还有就是方山之定林寺,而钟山的定林上寺是南朝佛教活动的中心,许多名僧都曾在此活动过。据《高僧传》卷3“上定林寺云摩密多”“钟山定林下寺蜜多”和《续高僧传》可知,当时在定林上寺的高僧有僧柔、法通、道嵩、超辨、慧弥、法令等。齐梁时期的王侯萧子良、萧宏及名流周颙、何点等人经常到定林上寺活动,刘勰第一次所入即为此寺。刘勰死后不久,定林上寺荒废,宋代以后史书、诗词中所提到的钟山定林寺,即定林下寺。明初宋濂在《游钟山记略》中,记载了他游钟山定林上寺、下寺的情况。
刘勰与僧祐的关系,《梁书》已有明载,刘勰年轻时来建康即投靠于他,当时僧祐已为名僧,后僧祐去世,葬于寺侧,勰又为之撰写碑文。据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1:“释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于建业。……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等,并请祐经始准画仪则,今上深相礼遇,凡僧事硕疑,皆勅就审决。年衰脚疾,勅听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其见重如此。开善智藏、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请事师礼。梁临川王宏、南平王伟仪,同陈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贵嫔丁氏,并崇其戒范,尽师资之敬,凡凡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以天监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困窆于开善路西定林之旧墓也,弟子正庆立碑颂德,东莞刘勰制文。”[2]541因为刘勰与江东名僧僧祐之关系非同一般,故当细述之,以从中考知刘勰的蛛丝马迹。
刘勰为什么要入定林寺而投靠僧祐?孙蓉蓉的《刘勰与僧祐考述》认为,刘勰一生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僧祐的影响,从他的入寺到《文心雕龙》的写作,考述比较全面。“刘勰‘依沙门僧祐’,寄居定林寺,表面上是皈依佛教,但其实是为了入世出仕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庶族出身,无依无靠,使刘勰不得不通过依附僧祐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刘勰在定林寺十余年没有燔鬓发出家,奉朝请后为官数十年,这些经历便能够说明刘勰当初‘依沙门僧祐’的真正原因。”[5]王承斌《刘勰入定林寺依僧祐原因新探》认为,成为孤儿的刘勰不愿为家计操心,入寺相对来说生活稳定,又有较好的学习环境,可以积累才学,为日后仕途升迁做准备(6)参见王承斌《刘勰入定林寺依僧祐原因新探》,载于《中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陶礼天的《僧祐及其与刘勰之关系考述》一文(7)参见陶礼天《僧祐及其与刘勰之关系考述》,收入《文心雕龙研究》第7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考察了僧祐与刘勰的关系,认为僧祐在佛学上的成就不是刘勰捉刀,刘勰只是协助的角色,一个年轻人刚踏入寺院,不可能对佛学有太多的见解。这几年人们重视对刘勰年谱的研究,主要年谱有: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王金凌《刘勰年谱》,这是他当年的硕士论文,1976年嘉新文化基金会出版。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1988年巴蜀书社出版。蒋逸雪《刘勰年谱》,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朱文民《刘勰志》,200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刘勰的家世生平、《文心雕龙》、佛学、学术研究和历史遗存纪念物等方面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这些著作对刘勰当年在定林寺这一段生活都有不同的记载。
三、濡染于佛学的思维方式
刘勰在定林寺长期帮僧祐抄写佛经,时长日久,其思维方式必受影响。而大乘佛学流行于时,它作为佛学一种典型的思维方式就是遮诠法,就是让人们在不断的否定中认识事物的真相,而不是从正面直入真理。《金刚经》中说:“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6]11;“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6]12;“如来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6]25;“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6]26。这是一部大家极为熟知的佛典,许多人也经常抄写,我们看这是大乘佛典中出现的比较早的般若类经典,佛在解释这些事物时,所使用的“般若波罗蜜”“三十二相”“三千大千世界”“法相”,这些言语本身不能完全反映事物的本质,应该先理解这些名相概念。要了解《金刚经》的思维方式,就先看看它使用的句式,《金刚经》里面大量使用“说……,即非……,是名……”的句式,这种句式就是一种典型的遮诠法句式。《心经》里面也有大量类似句式:“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7]这里用“不”或“非”或“无”来开头的句子,就是名相概念的表述,是不可能表现事物本质的,因此用“非……”这种否定方式,即是“遮”,佛学就是采用这种不断的否定方式来达到对事物本真的把握。《维摩诘经》也有类似的表述句式,如卷上云:“法无名字,言语断故;法无有说,离觉观故”“说法者无说无示,其听法者无闻无得”。这里也采用了一种否定式的表述,让人们在否定事物的名相概念中去体悟事物的本质。
佛学思维中的遮诠法,不仅在般若中观佛典中有突出的使用,而且在瑜伽行派中也有不少使用。《成唯识论》卷7:“于唯识应深信受:我法非有,空识非无。离有离无,故契中道。……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8]这里讲的“非有非无”“非空非不空”,这种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禅语,就是采用“遮”的方法以达到他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作为印度佛教里的量说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思维方式,量论中四量说最具代表性。日本学者武邑尚邦在其《佛教逻辑学之研究》中有详细的阐释[9]85-90:所谓四量指的是现量、比量、譬喻量、圣教量。现量就是依赖感官与对象的接触而产生的直接认知;它是不可说的,语言是无法阐释的;因其为直接性者,故自身无错谬;现量知具决定性,故无模糊不确定等性质。比量是以直接性现量为先行,依此而产生的有分别的推理认识,它是一种超越了感性层面而跨入了一种间接性的认识。按乔达摩的《正理经》卷1所说,在现量的基础上又分为前比量、有余比量、平等比量三种。前比量,比如说,你现在看见烟,依此而推想具有烟这种现象的火之存在,烟与火两者不可分离性的认知,使我们产生一种有火必有烟的经验性认识;有余比量,如见河川涨水而知上游必下雨;平等比量,是由已知事件而推知与其具有相同特征的存在的一种类推认识。譬喻量,就是类比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依据已知物与未知物的相似来认识未知物。比如你没见过野猪,别人说野猪与家猪相似,后来你在野外见到一个长得像家猪的动物,头脑中出现了相关猪的比对知识,于是就断定这个动物就是野猪,那么,依次所获得知识的方式即为佛学里的譬喻量。圣教量,这里的“圣”指的是圣人,是佛、是释迦牟尼,借助权威的圣人而获得对事物的某种认知或启示,圣教一般指的是《吠陀》中所记述的各种言论和教诲。简单地说,佛教的量论就是关于获得知识的思考方式,是古印度佛教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思维逻辑形式的有机结合,它所思维的内容仅限于佛学。
佛学的思维方式类似于罗素所讲的神秘主义,罗素在《宗教与科学》一书中说:“神秘主义者则要求观察者通过斋戒、气功和止观,使其本身发生变化(有些神秘主义者反对这种修行法,他们认为神秘的其实是不可能通过人为的方法获得的;从科学的观点看来,这就使得他们的证词比那些信奉瑜伽的人的证词更难验证。但几乎所有的神秘主义都一致认为,斋戒和禁欲生活是有益的),我们都知道鸦片、大麻、酒精能在观察者身上产生某些效果,但我们认为这些效果并不是美妙的,所以在我们的宇宙理论中就不考虑他们。他们有时甚至能揭示出一破碎的真理;我们并不认为它们是全部智慧的圆圈。”[10]佛学中因明学的思维逻辑到了中国,与玄学结合但又不同。任继愈在《中国佛教史》中说:“一般来说,魏晋玄学致力于建立一种从肯定现实社会秩序的方面的本体论,般若学则致力于建立一种从否定现实社会秩序的方面结合有无的本体论。”[11]当时的道安和尚说:“夫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有何难也?”(8)参见《安般注序》,《出三藏记集》卷6。魏晋玄学的崇本是为了肯定现实世界,而道安(9)道安,即释道安(312—376),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州)人,东晋著名佛教学者、佛教领袖。道安12岁出家为僧,学习佛法,最突出的贡献是对汉以来的佛家典籍进行了整理,编纂目录,确立戒规,主张僧人以“释”为姓,慧远为其高足。从无出发则是要论证现实世界是虚幻的,从而教人摆脱世俗的社会,就是以否定的思维,把人们从现实拉到彼岸。佛学认知世界与世俗不同,它是给你指出一条路,教人以直观体认无相的真理,这种般若的认知与我们世俗人的认识不同。般若有些人说是智慧或大智慧,其实也不太准确,不妨拿道家的“道”作以类比倒是还有几分相似。佛学这种与传统思维迥异的方式,给年轻的刘勰一全新的感觉,使得《文心雕龙》的构思和写作观念与时人截然不同。
四、刘勰的世界观与《文心雕龙》的结构
《文心雕龙》全书50篇,分枢纽论、文体论、批评论等部分,基本的文学思想是宗经,其书庞大的结构与它的指导思想有密切的关联性,既有儒家的主导思想,也有道家注重对事物的深究与本质问题的探讨、佛学的因果思想影响到《文心雕龙》的创作。
总体来说,刘勰完成《文心雕龙》的时间是在他做官之前,这一时段刘勰的思想以儒为主导。刘勰在《序志》篇亦明言对孔子的敬仰;“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作为受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刘勰,本意注经,然不能超越前贤,只好另辟蹊径,论文叙笔。黄霖认为:“关于《文心雕龙》的具体成书时间,清人刘毓崧在《书〈文心雕龙〉后》中曾有考证,认为在齐明帝永泰元年(498)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之间。一般认为这个推断是可靠的。”[12]3依此,《文心雕龙》书成时,刘勰大概四十岁。按黄霖的说法,“当他三十岁以后,深感岁月飘忽,出仕无望,‘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文心雕龙·诸子》),面对着社会上‘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秀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文心雕龙·序志》)的文坛大势,就决心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撰写《文心雕龙》,以针砭时风。”[12]3就是说刘勰40岁以前,他还是一个儒生,崇拜圣人孔子,他的世界观主导思想是儒家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思维方式来完成《文心雕龙》这部巨著的。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不但要有指导思想,具体论文还应抓住要害,即“体要”,这一观念对理论著作非常重要,书中多处言及。在其书的枢纽论中,《徵圣》篇曰:“《书》云:辞尚体要,弗为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到《风骨》篇又引此言:“《周书》云:辞尚体要,弗为好异”;《诠赋》“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奏启》“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序志》“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奥,宜体于要”。刘勰反复强调论文一定要抓住要害、抓住要领。这里也有佛学的背景与熏陶,佛教也是从行为、语言与意识等方面强化对佛的认同与皈依这一要义的。佛学的著作也是强调“体要”,武邑尚邦在《关于〈集量论〉文本的诸问题》中说:“一般而言,在印度论类著作的情形中,一如世亲所著《阿毗达摩俱舍论》那样,首先要写出概要性的偈颂,之后就偈颂写出注释,这是一种常识。”[9]251“体要”还有“尚简”的意思,这个来自儒家的思想,人们有不同的认识,陆侃如、牟世金的观点是文辞应该抓住要点;詹锳认为是为文切实精要;周振甫认为是体现要领。这一点对《文心雕龙》一书的撰写非常重要,在《原道》等五篇的指导思想下,全书各篇都要“体要”,尤其是对后面20篇文体论各种文体的探根索源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体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尚书·毕命》,康王对毕公的训诫中有语道:“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13],刘勰改动了两个字,语言表达更为文雅。忘记了谁说过:批评的贫困源于概念的缺乏,刘勰对“体要”这一范畴的重视,对他全书五十篇的写作都具有非凡的指导意义。
《易传》思想与《文心雕龙》的整体结构也有密切的联系。《易传·系辞上》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14]这里的“大衍”是指推演天地变化,就这五十个数字。大衍之数,本该五十五,舍去五而取其整,故称五十。为什么要舍去五呢?因为六十四卦每卦六爻,第五爻是阳气的巅峰,极而必反,故舍去预示衰败的数字“五”。为什么《易传》又说“其用四十有九”呢?因为在正占筮演卦时,舍去一个阴数六,之所以舍去六,因为万物之变,主动方为阳,而六为阴,故舍之,占筮之时,所用竹签实则为四十九根。关于“大衍之数五十”说法很多,京房、刘歆、马融、郑玄、朱熹等等,说法各有不同。马融之说有一定道理:“《易》曰: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 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节气节。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运而用也。”[15]刘勰《文心雕龙》全书的框架设计为50篇,最后的《序志》篇是序言,而实际正文只有49篇,这个总体的设计理念就来自《易传》。《易经》与《文心雕龙》中各种文体源流问题的探讨也有密切关系,《易传》从天地而言及万物的思想,从源头探讨问题的思路,对各种文体的寻根索源,都有密切的相关性。
《周易》的宏观思维,对天地万物的总体把握,也影响到刘勰的思维方式,进而体现在《文心雕龙》的创作中。比如许多地方都体现出一个“大”字,《铭箴》:“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杂文》:“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体之大要也。”《诏策》:“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诠赋》:“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颂赞》:“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通变》:“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神思》:“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上列种种皆为宏观思想,亦含有归纳总括之意。刘勰论文有高度,“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对问题的宏观把握,而《周易》作为“六经之首”,读书人必熟读习之,《文心雕龙》必然是受到了它的影响。
通体观之,《文心雕龙》写作的指导思想是儒家的,道家思想也占了一定比重,第一篇《原道》所论文学之原就立足于道家。但刘勰长期抄写佛教经论,外来文化对问题的不同看法与新异角度,无疑会影响到他的思维方式,而佛学般若对他创作的渗透,是在《文心雕龙》的字面中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