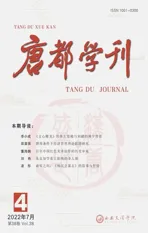儒家“为己之学”的涵义辨析
2022-11-21张开宇袁祖社
张开宇,袁祖社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西安 710119)
在孔子提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13的说法之后,“为己之学”便成为儒家哲学中的重要命题。自荀子对这一命题进行诠释以后,这一命题的主流解释,便形成了一种对孔子本意的误读,进而使儒家“为己之学”的真正含义被后学所曲解。这种曲解,实际上也体现了儒家思想内部理解的核心差异,进而导致后世儒家哲学产生了一种关于进学路径的内、外分化。
一、“为己之学”的代表性注释辨析
要明确这种内在分化,首先要弄清“为己之学”的最初含义。最早引用这一命题的文本是《荀子·劝学》:“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2]8这段对“为己之学”的解释中蕴含着两重含义:一是从行为的角度出发,认为“为己之学”在于“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将学到的道德准则当作“律己”的法则,并内化为品格,而“为人之学”则仅是卖弄学问的表面功夫;二是从动机的角度出发,认为“为己”是为了完善自身,而“为人”则是希望能够获得别人的肯定,从而达成某种目的。
汉代经学传统较多从第一种解释出发。如孔安国注“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为己履道而行之也,为人徒能言之也”。后世也有部分学者顺应这一理解,如南朝时期的皇侃主张“明今古有异也。古人所学己未善,故学先王之道,欲以自己行之成己而已也。今之世学非复为补己之行网,正是图能胜人。欲为人言己之美,非为己行不足也。”[3]
而宋明时期的大多学者则主张第二种解释路径,如朱熹将“为己”与“为人”解作“为,去声。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程子又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愚按: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4]156朱熹引用程颐的观点指出:为己之学,就是以自身作为目的,完善自身;而为人之学,则是想要被别人看到,获得别人的肯定,并希望借此达成某种目的。吕大临也主张“为己者,心存乎德行而无意乎功名;为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5]593这两种解释实际上都是继承了荀子关于“为己之学”的第二种诠释。这种解释固然有其道理,但其中所蕴含的问题,却都是荀子之后的时代才产生的。随着战国时期社会环境的变化与“养士风气”的鼎盛,以及其后种种选拔制度的诞生,导致“学识”成为得到诸侯、帝王任用的重要条件。在此种情况下,无论从行为还是动机的层面,都出现了这种功利化的转向。
如果依据这种解释,“为己之学”的含义就必然面临两个问题:首先是历史层面,孔子开创的私学是春秋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者。然而依钱穆先生所言:“当孔子时,学风初启,疑无此后世现象。”[6]钱穆先生显然注意到了春秋与战国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孔子时代,为学之风尚未如后世般普遍,且当时世卿世禄的制度还是社会主流,能够从事“学”的人大多并非平民出身,也不需依靠学来获得功名。即使是学风普遍之时,古时平民教育的内容本身也多是道德教育,而实际的为政能力的学习则在于政治机构中的实践。故钱穆先生这一观点是中肯的。因而,上述的“为人之学”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后世所出现的流弊,而非孔子当时所面对的现象。其次,依据主流的注解,将“为人之学”视为“小人之学”,显然是带有某种排斥态度的。朱子就明确指出:“为己之学”是“君子儒”,而“为人之学”则是“小人儒”。然而无论是前文所述的哪一种解释,均与儒家伦理精神存在矛盾。从行为的角度看,如果学者仅仅关注自身行为,那就无法构建整个社会的秩序,与儒家传统尤其是其哲学思想中对于群体的重视发生冲突。 同时,儒家伦理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若单纯以“律己”或者“完善自身”作为“为己之学”的内涵,虽然不会演化出自我中心主义,但也必然与儒家思想中固有的“利他”精神相矛盾。且儒家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227仕、学之间虽非完全一致,却也有相通之处,绝非相互排斥。如果依据此种诠释理路,显然也不符合孔子本意;如果将其理解为单纯从动机上衡量是“为己”还是“为人”,也无法避免这一矛盾。《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7]1161。如果以动机是“为己”还是“为人”作为标准,那么“大学之道”以“明明德”与“新民”作为动机,依照前述理解,均应当属于“为人之学”的部分。后文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更是明确将“明明德于天下”作为目的,被视为“为己”之术的“修身”则是渐次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此,在这种诠释理路下,即使单纯从动机角度出发进行衡量,“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在儒家内部依然是绝不可二分的,这也必然使得这一区分不再具有批判意义。
正是这种分歧,导致诸多儒家后学不再排斥“为人之学”,并尝试对“为人之学”予以肯定,如明末王夫之便不再将二者视为截然对立,这固然与时代变迁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包含着思想内在张力所导致的转向。显然这种试图调和“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的理路,更加符合儒家内在的哲学精神。但这种调和实际是先明确了儒家思想体系的内容后,再通过“反推”而得出的结论,似乎有所不妥,且这一理路事实上是对孔子“古今之别”描述的调和,这也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说“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是内在统一的,那么孔子提出的这一命题将会失去其对“为人之学”的批判意义。
相较之下,王安石尝试以“本末”关系解释“为己”与“为人”,强调在“为己”的基础上“为人”,这应该比前文提到的几种观点更贴近原意:“为己,学者之本也,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8]张栻在《论语解》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主张“学以成己也,所谓成物者,特成己之推而已。故古之学者,为己而已,己立,而为人之道,固亦在其中矣。若存为人之心,则是徇于外而遗其本矣,本既不立,无以成身,而又将何以及人乎?”[9]这种认为只有通过“为己”才能达到“为人”的理路,无形中契合了《中庸》所讲“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7]1029的本末关系,对上述矛盾起到了较好的调节效果。然而,由于其仍将“为己”视作学者的个体志向,而将“为人”作为最终目的的观点,依然不可避免地将“事功”视为根本目的,而非以个体的“自觉”,这显然是认为“为人”重于“为己”,因而也是不恰当的。
二、“为己之学”的文本分析
要解析“为人”与“为己”的本意,就必须要回归孔子最初的文本。首先要明确“为己”是指“学问”还是“学人”,即“者”字指“人”还是单纯的语气助词。如果认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中的“学者”仅是一个“连词”,那么“为己”则构成对“学者”的特定行为的描述。如果“者”是单纯的语气词,那么“为己”与“为人”则应当是“学”的内容。
从文字的角度来看,“学”字在《论语》中出现66次,除此处的两次以外,均为动词或者名词“学问”的含义,并没有出现“从事学业的人”的含义。而同时期文献出现“学者”连用的仅在《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叔仲子专之矣,子服子始学者也。”还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其中“者”或“者也”均为传统的语气词用法,《左传·昭公九年》则出现了“学人”连用,往往被人误解为是“学子”之意,然而依其语境则或是指“奏乐的人”;或是用作动词,指当学习他人“舍业厚遇之”的行为。如依当今“从事学业的人”来解释,则于上下行文之间显得十分突兀,故不当以此解。在《老子》《尚书》《逸周书》《大学》《国语》等被确定为战国中期以前的文献中,“学”也仅有动词“学习”和名词“学问”的含义,并没有出现以“学”或“学者”指“学人”的用法。与之相对的是,成书于战国中期的文献中,则较多出现了单以“学”字或者“学者”连用,代指“从事学业的人”的用法,如“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4]271“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10]“吾语汝学者之嵬容”[2]78。由此可以认为,这一用法应该是出现于战国时期,在孔子本人生活的年代及《论语》成书的时代并不存在。而这一用法的出现,或许是由于孔子之后,“私学”规模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出现了更多从事学术研究和传播的“学者”有关。这似乎从侧面佐证了前文提到的钱穆先生的观点。那么就可以确定,“古之学者为己”这句话中,“为己”的描述对象只能是动词或者名词的“学”而非双字词“学者”。由此可见,这里最恰当的理解,应当参照前文提到的《左传》中的“使学者制焉”,与其前文中的“使人学制”同义。这里的“为己”应当是“学”的内容,那么“为”就不应当是用来表示目的或原因,因此不应当读作“去声”。
从内容的角度来看,在《论语》一书中孔子有着明显的崇古态度,故而对孔子推崇“为己之学”的观点历来都是无争议的,分歧的关键在于孔子对“为人之学”的态度上。因此,后世学者理解的主要区别也就集中在这一方面。如果将“为人”的描述对象理解为当今意义上的学者,那么就必然面对前文所述的矛盾,进而只能肯定“为人”并不存在问题。而试图调节这一矛盾的部分学者则提出“为人之学”的问题仅仅在于“学”这一特定的行为之中。脱离“学”则“为人”就成了“褒义”[11]。这种说法意识到了“为人之学”指的是“学”而非“学者”,但由于其对这一点终究没有言明,导致了后世学者仍只能通过各种手段将二者进行调和。如明代学者罗伦就通过区分“学者”与“仕者”的志向不同,认为“学者”当“为己”而“仕者”当“为人”(1)参见罗伦《一峰文集》卷5,收录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95页。。这种诠释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忽略了孔子关注的仅仅是“古”“今”之“学”的不同,并不包含不同主体或不同身份;另一方面,这种说法在根本上依然是对二者的一种调和,淡化了原句中对“为人”的批判含义。可见,如果将“为人”视作对“学者”行为的描述,要么会导致其解释与儒家思想出现内在矛盾,要么会导致“为人”的理路失去了本身的批判意义,故而“为人”似乎不应当是对“学者”的描述,更像是“学”字本身的涵义。
明确了“为己”是指“学”的内容而非“学者”之后,对“为”字的涵义的分析就较为容易。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为”字本身不应当读作去声。由于继承了荀子关于“为己之学”的观点,朱熹将“为”明确注为“去声”,这种读法也得到了后世诸多学者的继承。然而这一读法也导致了“为”字只能被理解成“为了”,而行为主体也只能是“学者”,这就必然产生前文所述的冲突。此外,儒家思想显然包含有“利他”的倾向和内容,如果“为”字读作去声,那么“为”依照字义就必然包含有目的性。“为人”也就必然包含有“利他”的因素,从而导致“为人”不应被否定。在这种理解下,调和“为己”与“为人”则成为某种必然。可见,“为”字本身不应读作去声,而应当读作阳平,如果其描述的对象是“学”,那么“为己之学”的真正含义,也应当是以“为己”作为名词“学”的内容。陆九渊所谓“古之学者为己,所以自昭其明德。己之德已明,然后推其明以及天下。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在我者既尽,亦自不能掩。今之学者,只用心于枝叶,不求实处。”[12]似乎对此有所洞见,朱熹在解《中庸》时,也注意到“为己”内含有“立心”的意思:“古之学者为己,故其立心如此。”[4]40由此看来,以“为己”作为“学”的目标或着力点,是契合孔子本意的。
要证明这一理解的正确性,必须要先明确儒家思想中“己”的内涵。尽管传统中国哲学研究在面对当代社会的挑战之前,多数学者对儒家的“自我”观念并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然这一观念却真实地存在于儒家哲学体系之中。杜维明先生曾明确指出:“‘authenticity’(真实性)一词更适合于表达儒家学者为己的原意。”[13]儒家的“自我”是与“天命”息息相关的。唐文明先生也曾指出:“从原始儒家的思想来看,自我的本真所是在于天命。‘生命’就是‘生’作为天命而被给出,人之为人,就在于人身上承担的天命。”[14]将“天命”与“自我”相关联是历代儒者的共识。宋明以后更直接地认为“天命”是“真我”的体现,而从“天命”与“学”的联系来看,《中庸》开篇所讲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7]1007可以说是“为己之学”最准确的解释。“教”本身正是“学”字的内在含意。可见,所谓“古之学者为己”应当理解为“古学为己”具体说就是“教化个体,使其对于自身所承载的天命的觉悟”。如此也恰恰契合了“学”字“觉悟”的本意,也与儒家“心性之学”的主旨相契合。因此这种理解似乎更为合理。
在此基础上,不妨以对照的方式,分析一下“为人”的内涵。如果“己”所指的是“本真性”的“天命”,那么“人”则应当是指与之相对的“人为”。扬雄提出“命者,天之命也,非人为也。”[15]明确地将“天命”与“人为”相对,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过去的理解中总是将“人”理解为与“自我”相对的“他者”,这也是导致此前所述矛盾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为人”本身便有“人为”的涵义,“人”用以指代“人力之所为”,这也就与荀子所言的“伪”构成了相似性。依据这种思路,“人”的内涵就应当是“人为塑造的具化道德原则”。反观《论语》一书,孔子虽然提出了“仁”等价值原则,但从未对任何一种道德原则有过统一的具体化描述,而是因人因事予以针对性的启发。即使对于看似是标准原则的“礼”,也没有完全刻板地执行,如“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1]99可见,儒家并未对具体规范有所执著,而是更注重“礼”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并以此来启发被教育者,使其达到对“己”的觉悟。与之相对,“以人为塑造的具化道德原则”作为自我修养的目标,也更加贴合“为人之学”的真正含义。
三、“为己”与“为人”的关系
在明确了“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的含义后,就需要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人之学”究竟有何弊端。儒家究竟是否彻底否定“为人之学”?如果不是,那么其对“为人”的批判性又存在于何处?这是分析二者之间的演化和明确儒家思想的两重进路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要回应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确儒家并非一种复古主义,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7]1033然而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儒家对“古”的认可。尽管因相关文献较为匮乏,上古世界的真实样子当今无法得知。但“古”是儒家理想社会的范式却毋庸置疑。建立在这一思路上的孔子必定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同时又直面时代问题的现实主义哲学家。
其次,尽管孔子自身所处的时代以前均可以称作“古”,但孔子所谓的“古”指的是“上古之时”。从当前可见的史料来看,至少西周时期便已经是孔子所说的“今”的时代了。孔子认为,相较于“今”,上古时期的民众生活更能体现其本真性。“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1]210这种对于上古时代的向往也是春秋战国时代大多学者的共识。而“伪”应是在古今交界时期出现的产物,“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7]718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学”的内涵与外延也必然随之而产生变化,“为人之学”也就应运而生。而伴随着“礼乐”等“人为”的出现,“学”的方法也由过去“启发性的自觉”演变为“原则性的教化”。但从中也应当看出,“为己之学”到“为人之学”的转化本身也是顺应时代变化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这种因应变化,正是前文提到的陆九渊的问题所在,即陆九渊并未认识到“为人之学”也是对时代发展的因应,只将其视作枝叶,却没有看到“为人之学”内在的种种现实性考量。
春秋时期,以“礼乐”为代表的“人为价值原则”伴随着“礼崩乐坏”的加剧而瓦解。有鉴于此,孔子为了将“道”能够传承下去,不得已借作《春秋》 来品评是非,其功在于“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4]277。但是其罪仅仅是“非天子而议礼”吗?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为什么会有“非天子不议礼”的原则。《中庸》所言“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可见,儒家认为道德原则的建构者须同时具备“德”与“位”。显然,如果不具备良好的“德”,则必然无法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如果不具备“位”也可议礼,必将导致众说纷纭、各执一是。这也正是“为人之学”的弊病所在。 《春秋》的诞生,代表着古圣之道能够传承的同时,也标志着“道术为天下裂”的开端,这也就意味着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春秋》中孔子的“褒”“贬”在为后世议论是非提供了价值依据的同时,也带来了碎片化模仿的可能性。这种碎片化模仿的弊端被庄子深刻地揭示:其不仅会导致“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16]1296的问题,甚至为“盗亦有道”的逻辑提供了一种合价值的可能性。正因如此,孔子才会有“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4]276的自我评价。
荀子所提出的“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2]107正是前述路径下的集大成之作。在荀子哲学中尤为注重“法”的概念,而这里的“法”应当是“效法”之意。同时,在荀子的学说中,道德的具体原则化也已经形成。除了重新提倡“隆礼义”之外,由“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2]88等论述可见,这些具体的行为原则已经被认为是“天下之通义”。荀子所面临的时代困境是“道术为天下裂”,较之此前的“礼崩乐坏”更需要建立统一价值标准。因此“为人之学”也在此时达到了鼎盛。人为之“伪”成为价值的最终建构。由于“人”“己”从来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随着“人”的鼎盛,“己”也就彻底隐藏了起来。如此一来,也就实现了从“为己之学”到“为人之学”的转变,这实际上是伴随着社会现实的改变而发生的由个体觉悟到群体秩序的转变。如此看来,“为人之学”是一种顺应时代而兴起,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必然现象,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忽略“为人之学”的弊端。从“为己之学”到“为人之学”的转化终究是一种时代的不得已。这一进路的缺点可以在王阳明对朱子的批判中得到答案:“朱子解意在表明教是道的现实展开,如礼乐刑政之教化,故有‘品节’这一强调差异性的表述。而在王阳明看来,此种理解则是对道的分裂和碎片化,破坏了道的整全性。”[17]正如前文所言,“为人之学”的兴起也带来了“道术为天下裂”的必然结果,道德虚无主义的影子也在悄然出现。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实,实际上是准确把握了“为己”与“为人”之间的张力。由此可见,二者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仍需详细辨析。
儒家的进学路径分为“内向”与“外向”两重,这与陈来先生在《宋明理学》中阐释“朱陆之辩”时提出的“尊德性”和“道问学”的两重路径有所相似。这两种路径也正是“心学”与“理学”的分歧之所在。而这一路径的分歧也正如上文所述的“为己”与“为人”相似,厘清二者之间关系,是真正把握儒学核心精神的关键。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一派前人以“本”与“末”的关系解读“为己”与“为人”的关系。其将“为己”视作“学”的根本。然而这与实际是截然相反的,虽然从发生的角度看,“为己”是“本”,然而从“为学”的角度看,必须借助“为人”的工夫方才能够达到“为己”。正如《大学》主张“格物致知”后方能“诚意正心”。《论语》以“学而”开篇,而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结尾,足见其深意。
关于二者的关系,不妨借程颢“医术以手足痿痹为不仁”的比喻来予以说明。“己”本来是“仁”的状态。社会是“我”的身体,一旦身体出现问题,就必须借助药物(人为) 来进行治疗。然而这种药物(人为)并不是直接作用于“病”,而是通过刺激自身的免疫系统,使身体产生相应抗体,归根到底还是“己”的作用。然而,身体的绝对健康状态实在难以实现,因此必须要“对症下药”,即以“人为”为药物对疾病(社会问题)进行治疗,目的是使其“归仁”。如果单纯依靠自身,则会在面对较为严重的病毒时“束手无策”。这也就是为何纯粹的“为己之学”只能用于“古”而不能行于今的原因。上古之时,社会人口流动较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至多有些“小病”,完全可以“自愈”。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变得多元化、复杂化,因而必须要用“药物”来解决。此时如果单纯依靠“为己之学”来解决此类社会问题,或许会有少部分“身强力壮”的人能够“免疫”而直接达到对天命的自觉。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却难以应对。因此“心学”的传承中,往往只能出现部分“大贤”,却无法构造起一个普适性的传承路径。
如果因此认为仅是药物本身治疗了病症,而未能明晰其所依赖的最终依据仍然是个体“自觉”,那么个体的生存也只能是一种时时扮演“其所是”的角色的状态,甚至会因此走向一种虚无主义的道路。任何价值建构,如果脱离了人自身的“自觉”,那么其注定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或者只能凭空创造出所谓的“上帝”来当作价值的根据。正因如此,宋明以后多将荀子“性恶”的观点视作一种“谬误”。如程颐指责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18]朱子也曾言“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19]还应当注意到这一路径的另一个问题,正如徐复观先生所指出:“只愿把握现实性的现象,而不肯探究现象之所以然。”[20]如果不能洞察“药物”的作用原理,那么在面对新的社会问题时仍旧无法对症下药,甚至还会认为某种“药”能够“包防百病”。孟子性善论之所以常常被人质疑,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部分学者常以某种价值原则作为“善”的标准而对“性”进行衡量。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也是这一路径所必然导致的问题,正如牟宗三所言:“礼义之统不能拉进来,植根于性善,则流于‘义外’。”[21]
综上所述,孔子所言的“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区别,应当指“学”的内容是“对内在天命的自觉”还是“外在的规范的效法”。从历史的角度看,“为人”作为学的内容,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其作用在于提供了一种适应当时的、相对可普遍化的教育模式。然而,单纯以“人为”作为学的内容,也必然有所不足。后世的庄子则准确地看到了这一问题:“颜渊问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虽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16]772一味地遵守某种规范,并不能够达到至德的境界,就如同一个能够做到守法的人,并不一定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样。恪守规范、效法圣贤的人也不代表其能够达到“自觉其天命”的境界。此外,单纯的固执于“为人之学”,也导致了后世儒家的诸多流弊。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儒家之遗害于后世的,在于大同之义不传,所得的多是小康之义。……凡学术,固有变化社会之功,同时亦必受社会的影响,而其本身自起变化,这亦是不可如何的事。”[22]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作为“为人之学”内容的“道德原则”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言道德的内涵“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3]。如果对这种规范过于执著,也可能导致泥古不化的问题。只有透过“为人”的工夫,去洞见背后“为己”的本体,方才能够真正达到儒家所追求的“天命”的境界。这也正是孔子解释“仁”时所讲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138的真正含义,同时也是对儒家思想达到更深层次认识的必由之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