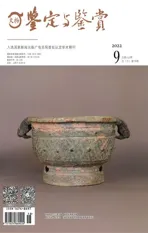秦战国五郡置年探究
2022-10-28李奉先
李奉先
(青海师范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8)
1 江胡郡
秦战国(为了区别春秋秦国、秦代,本文的战国秦国依刘瑞先生《秦封泥集》等用法,统称为“秦战国”)存在某些过渡性的郡名,鲜见于传世文献,譬如里耶秦简里的洞庭郡、江胡郡就是如此。关于“江胡”二字,陈松长先生于《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中指出“胡”可读为“湖”,“江”似可读“鸿”,鸿训大。又,《史记·夏本纪》云: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索引云“一作‘洪’,鸿者,大也。以鸟大曰鸿,小曰雁”,且古有“大”与“泰”“太”通用。据此,陈伟先生认为:鸿湖,或是太湖又一异名,被借用为郡名。陈伟先生此番“太湖论”确实颇有见地,但对江胡郡的置年研究是否有帮助尚由待出土文献实证。
有关江胡郡的出土文献,岳麓秦简有以下三条简文:
①J-0194、0383: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叁川、颖川署江胡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党□邦道当戍东故徼者,署衡山郡。
②J-0480:□迁其弗见莫告,赀一甲。前此令□□已入关阴密□环陷江胡而未出关及其留在咸【阳】。
③J-0706:绾请许而令郡有罪罚当戍者,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叁川、颖川署江胡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
据此简文内容分析,江胡地应该在有众多江河湖泊的吴楚地区。简文中出现的戍郡基本上可考所至之地。“署”字后的郡地,如四川郡,其界域所属最明显的秦县有今安徽淮北、宿州,江苏徐州;九江郡则有今江西全境和安徽及黄河以南、淮河以南地区如淮南、蚌埠、寿县、六安、滁州、合肥、巢湖、周口、驻马店、信阳淮滨一部等,九江郡与今九江市是完全不同的地理概念;衡山郡则包括今安徽霍山、怀宁,湖北黄冈、红安,河南信阳,北至淮河,南抵长江。
简文所陈之戍郡显然交代了文载的历史背景,秦战国戍郡已把军事前线推进至新攻陷的故楚地,年限可定为兴秦灭楚之际。此外,陈伟先生发表的《岳麓秦简中的两个地名的初探》一文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其文曰:
简文对这些屯戍秦郡的序列有其规律,即大致由北而南,由西而东。根据这个特点,江胡应该属于楚国之故地,位置很可能就在九江郡以东。由于在四川郡与九江郡北部之东,尚有东海郡的存在,江胡郡又应在东海郡之南。符合这个条件的,乃是我们熟悉的会稽郡。而目前披露的资料,岳麓书院秦简和里耶秦简,均未见会稽一郡的出现,也可从反面辅证这一推测。
上面这段引文前半部分笔者深以为然,但陈伟先生有关江胡郡与会稽郡历史沿革的推测稍有牵强。简文所述的戍郡地理位置分布,多呈现的是淮河上游走势,这与陈伟先生推测江胡郡是会稽郡前身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
由此可见,考察“江胡”二字拘泥于五湖四海的“鸿湖”“洪湖”本义,亦陷于先入为主的主观情绪。就目前所知,“胡”“湖”是否相通貌似与研究的课题无甚关联。
本文继续沿着笔者前观对简文的释读进程往前突进。按照陈伟先生部分正确的见解来梳理,如“这些屯戍秦郡的序列有其规律”,由这个特点可知,四川郡、江胡郡、九江郡、衡山郡这一顺序不可错置,盖其前后必然有地理方位性逻辑顺序,即四川郡位于淮河下游北部,九江郡位于四川郡南部,衡山郡位于九江郡西部,且九江郡、衡山郡均处于淮河下游南部。如此以来,江胡郡唯有处于四川郡西部、衡山郡北部才能吻合地理方块分布图。
按照陈伟先生的序列规律论,陈伟先生可推“由北而南,由西而东”,本文按照“由南到北、由东向西”亦是正论。如图1所示,江胡郡的位置亦在四川郡之西、衡山郡之北的淮河北岸,这一区域恰恰是战国晚期楚东国的核心地区。圈定了地理范围,再去讨论“江胡”名由,事情就容易多了。

图1 简文四郡位置效果图
现在便可查考与该区域与“江”“胡”或“鸿(洪)”“湖”有关的地名或古国名。《左传·僖公五年》有“江、黄、道、柏”文载;《史记·陈杞世家》云:“吴王僚使公子光伐陈,取胡、沈而去。”江国为殷商至春秋时期中原民系在河南一带建立的一个诸侯国,国名又作“鸿国”“邛国”,位于今河南省正阳县东南、淮水北岸一公里。胡国,位于今安徽阜阳西北。春秋时期古江国和古胡国地域皆在淮河北岸,足见“江胡”地名由来于两单字地名的合称。
最新刊布的岳麓秦简文第1647页和第1649页有“胡阳丞唐”的文载,从而可证“胡阳”为一县名。
再回头看之前的三条简文,提及九江郡、四川郡、衡山郡三郡。其中,九江、四川二郡为秦国所置,唯衡山郡不明。若能判断出衡山郡置年,那么同时代的江胡郡的存续年限亦可知矣。
现有的传世文献,《汉志》载秦初三十六郡名,既无江胡,亦无衡山。从简文的系年分析,秦代时江胡郡或为颖川郡所并,其后,复分颖川置新淮阳郡,江胡之郡名遂就此消失。
秦战国江胡郡的置年仍需新的出土文献的公布才能底定。本文的初步结论:江胡郡置年至少不晚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
2 衡山郡
衡山郡为秦所置此结论应无异辞,但具体置于何年各类文献皆无文载,唯有通过对衡山郡置年的考释,才能判断出该郡是否属于秦战国之郡。
传世文献唯《史记·项羽本纪》一语带过该郡:
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
谭其骧先生据此认为秦置郡衡山,且由《史记·秦始皇本纪》“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确定衡山郡置年为“秦始皇二十八年前”。即秦代已置有衡山郡。笔者认为:由“之衡山、南郡”句不难看出,“衡山”既然与“南郡”并列,自然不是山名。谭其骧先生的“秦代已置衡山”论亦可从,但其言郡置何年,不确。辛德勇先生所持看法与谭其骧先生有所不同,他认为该郡置年“不排除在秦始皇二十三年置,属于郡改置,或置于始皇二十八年的可能”。辛德勇先生表述的“两种可能”的郡置年虽略有模糊,但第一种可能的推测还是可信的。本文先查考郡置于秦国的文献依据,再继续讨论该郡置年。
由于出土的秦封泥有“衡山发弩”,发弩官为秦战国晚期至秦代所置,据此基本可以确证秦战国亦置有衡山郡。又,据里耶秦简J8-1234号载:“衡山守章言:衡山发弩丞印亡,谒更为刻印”,衡山守即衡山郡守,明确了衡山郡为秦代郡。《岳麓书院藏秦简(三)》J-1221亦给了本文新的关键线索。其简文曰:
五月甲辰,州陵守绾、丞越、史获论令癸、琐等各赎黥。癸、行戍衡山郡各三岁,以当灋(法)。先备赎,不论沛等。
又,据“残简227/1347”简文载:
廿【五】【年】六月丙辰朔癸未,州陵守绾、丞越敢谳之……
这里,二十五年,为整理者所补。据朱桂昌先生编著的《颛顼日历表》可查,秦王政二十五年六月丙辰朔,“癸未”,即二十八日。又因为“州陵守绾、丞越”于上述两简引文同时出现,显然为同一个州陵、守的名字。
据此,本文可以合理地判断:在J1221出现的“五月”当为秦王政二十五年五月。
有鉴于此,与衡山郡同现于一简的江胡郡,其置年于不晚于秦王政二十五,并由此可以初步结论:衡山郡置年至迟不迟于前222年。
笔者继续将该郡置年具体化。岳麓秦简有这样两条简文:
①J-0383: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党□(臣)邦、道当戍东故徼者,署衡山郡。
②J-0706:绾请许而令郡有罪罚当戍者,泰原郡署四川郡;东郡、叁川、颖川署江湖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
笔者认为,查出秦战国衡山郡具体的郡置年没必要那么复杂。既然这些郡在同一时期出现于同一简文,只要能查出除了衡山郡之外的最晚郡置年的郡,即可知衡山郡的郡置年。这里,四川郡、九江郡置年于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结合岳麓秦简、里耶秦简分析,衡山郡的置年当与四川郡、九江郡同时,即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
3 陶郡
战国时期,陶邑未为秦置郡前就已成为七国合纵连横必争的“午道”。
史载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前284),燕、韩、赵、魏、秦五国连横攻齐,轴心国燕国战功第一,“以三十万大军直攻齐都临淄,并连下齐七十余座城池,齐战国仅剩下即墨和莒城以及附属城邑。秦战国亦首先攻取了陶邑”。
陶邑的富庶盛名于世。昔春秋范蠡居于此,“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秦相魏冉对此地极感兴趣,后来遂成为魏冉的封邑。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秦谋伐齐,以广其陶邑;次年,拔齐之刚、寿。“刚,位于今山东宁阳东北;寿,今山东东平西南,穰侯取此两地,为的是进一步壮大陶邑的实力。”此亦为秦战国置郡陶地奠定了基础。
关于秦战国陶郡置年史书语焉不详。《史记·秦本纪》载:
(秦昭襄王)四十二年九月,穰侯出之陶。
又,《史记·穰侯列传》载:
穰侯卒于陶,而因葬焉。秦复收陶为郡。
有学者据此认为秦战国是第二次置有陶郡,笔者认为这显然是对“复”字的错误理解。笔者以为该句若需断句,可断为“秦复收陶,为(陶)郡”。“复”字是就封地“陶”而言的,而不是“复为郡”。王国维先生亦就此主张秦战国置有陶郡,当入列秦三十六郡之目。王国维先生认为:
秦昭王十六年,封魏冉陶,为诸侯。陶于齐、魏之间,蕞尔一县,难以立国。二十二年,蒙武伐齐河东为九县。齐之九县,秦不能越韩、魏而有之,其地当入于陶。三十六年,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予穰侯,则陶固有一郡之地矣。
由此可见王国维的观点是秦战国置陶郡应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之前,且存续于秦统一之后。此观点亦得到谭其骧、杨宽等人的反复论证,秦战国置陶郡已无疑问。只是谭、杨二人认为该郡在秦统一之后已未现也,且郡置何年出现了诸多争端。不过,谭其骧先生的观点最资参考。谭其骧认为:
《始皇本纪》五年所拔魏二十五城中,南有雍丘,东有山阳。《汉书·高帝纪》《曹相国世家》《绛侯世家》《樊传》并云“二世三年攻破东郡尉于成武”;陶地介在东郡治濮阳、雍丘、山阳、成武之间,是知东郡既置,陶必然遂即并入。三十六郡已有东郡,不得别有陶郡也。
据谭其骧先生所考,秦战国置郡陶,当在公元前265年,于公元前242年撤并,凡存续二十三年。但杨宽先生不完全认同谭先生的置年结论,他认为陶郡后来被魏国攻取,不再为秦战国所据。杨宽先生结合《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传世文献,在《战国史》“秦国设置的郡”中云:“秦昭襄王五十三年,陶郡为魏攻取,秦未再设郡。”秦昭襄王五十三年即公元前254年。
今按:谭其骧置年、杨宽之陶郡失郡论皆可信。但陶郡被魏国夺占后,其后被秦战国再度攻取,只是未再复郡,而是把原陶郡之地并入新扩大地域的东郡之下。又因秦战国陶郡置年于前265年,讫年前254年,存续仅短短的十一年,所以历来研究者鲜有发现陶郡为秦战国之郡。
4 东晦郡
东晦郡之名于《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中的“东晦司马”、《中国封泥大系》中的“东晦都水”等皆可见。“晦”“海”二字皆从“每”而得声,按律可通假。
今按:东晦郡,即东海郡,所说应是。且《淮南子》文载四方之极有云:“自九泽穷夏晦之极。”东汉学者高诱注:“夏,大也;晦,暝也。”此与《庄子》“北冥有鱼”相应。唐代成玄英释文:“溟,北海也。取溟溟无涯,故谓之为溟。”又,“冥”“暝”与“溟”互通,“夏晦”即北海之大。准此,“东晦”义同东海,为秦人的正式用法,汉代方有“东海”见诸史料,如《史记》《汉志》等传世文献,足见秦置东晦郡应无可疑。若以学术性严谨表述,或以出土文献务必求真而言,此亦可云:先秦、秦代没有东海郡,只有东晦郡。
目前我们所争论的则是该郡究竟是秦战国所置还是秦代所置。研究者亦因长期受到《汉志》“东海郡”条目下班固自注“高帝置”影响,所以多数人皆信班志,以为东晦郡为汉郡,其前身仅为秦代郡。《汉志》“泗水国下”班固亦自注云“故东海”,这给研究该郡的置年带来了某些分歧。毛岳生先生即代表着一种流行性观点,其文曰:
《汉志》凡止言“故”,若故淮南、故赵、故梁、故东海、故鄣郡之类,皆属汉初所置,义可考核。故说秦郡者,不当数鄣。
对照出土文献“东晦”实证,毛岳生先生的代表性观点不可立。关于该郡是否存在,这里有刘师培先生的主张,颇有见地,兹抄录如下:
泗水为东海郡分置之国,《班志》于东海郡下言“高帝置”,于泗水国则言“故东海”,以明东海亦为故郡,此乃互见之法。既增“故”字以为别,盖亦指秦郡言。
事实上,有关东晦郡,诸传世文献所载皆有差异。《史记·陈涉世家》云:“陵人秦嘉、柲人董柲、符离人朱鸡石……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水经·沂水注》云:“(郯)县,故旧鲁也,东海郡治,秦始皇以为郯郡。”据此,论者理解亦各有不同。全祖望、王国维等视东海为秦郡,指出郯地非秦置郡,如前出土文献观之,全、王两位先生所议可从。但就郯地与东海地理沿革问题,全望祖先生认为东海郡治郯城,是故亦名郯郡;谭其骧先生认为东海郡治郯,“秦汉之际亦称郯郡”;杨守敬先生主张“楚汉之际,秦东海郡,改名为郯郡,汉复如故”;刘师培先生则认为“疑于秦名为郯,(西)楚名东海。高祖初(年)名郯,又改名东海”。刘师培先生的观点恰好与杨宽先生的相反。
判断州陵是否为秦战国郡,本文还得从岳麓秦简的条文入手。关于东晦与郯的置郡研究,学术界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曰前后沿革关系,另一派曰亦名关系。两派皆有其合理的一面。对于前者,应通过分析系年断代确认先后关系;对于后者,则应尽可能穷究本名与亦名的缘起。本文从亦名说。
全祖望先生于《汉书地理志稽疑》一文指出:“东海郡,置于秦始皇二十四年。”其依据是:
秦置三十六郡前,置有东海郡,其后以鲁为薛郡,分为薛郡与郯郡。
钱穆、谭其骧两位先生推论东海郡置年为秦代后,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实为秦始皇十年,本文坚持秦国秦王政纪年、秦代秦始皇纪),所持文献依据为《史记·秦始皇本纪》。其文载:“(三十五)立石于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但钱、谭二人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仅凭“立石东海上朐界中”实难判断东晦郡为秦代所置。
今按:《元和郡县图志》云:“秦置三十六郡,以鲁为薛郡,后分薛郡为郯郡。汉改郯郡,为东海郡。”薛郡为秦国所置,秦灭楚后,是年,秦攻取楚东国郯县、襄贲、兰陵、缯县、东阳、广陵等大片土地,这些故楚地区域一度延伸至故鲁、故齐部分属地,当属以郯县为郡治的东晦郡地。
今依“亦名说”,再结合亡楚后薛郡与郯郡地志分析,那么东晦郡置年最早当于公元前224年秦战国置薛郡之年,至迟应不迟于秦统一之前。
5 州陵郡
判断州陵是否为秦战国郡,鉴于先秦出土文献有限,且很难在秦封泥中找到物证,本文还得从岳麓秦简的条文入手。兹抄录如下:
①J-0061:……州陵守绾令癸与□徙……
②J-0083:廿五年六月丙辰己卯,南郡假守贾报州陵守绾、丞越:子谳求盗尸等捕秦男子治等四人……
③J-0163:廿五年七月丙戌朔乙未,南郡假守贾报州陵守绾、丞越:子谳荆长癸等□□,男子治等告□□……
④J-1219:廿五年五月丁亥朔壬寅,州陵守绾、丞越敢谳之……
⑤J-1221:五月甲辰,州陵守绾、丞越、史获论令癸、琐等各赎黥。癸、行戍衡山郡各三岁,以当灋(法)。先备赎,不论沛等。
⑥J-1347:廿【五】【年】六月丙辰朔癸未,州陵守绾、丞越敢谳之……
在此批秦简中,笔者发现“州陵守”字出现次数颇为频繁。该“州陵守”与岳麓秦简著录的J-0319“东郡守”、J-0488“南阳守”、J-0921“洞庭守”、J-1954“河间守”相类,当为一郡之守。当然,我们并不能见诸“守”字一概视为郡守,有些“守”可以理解为县属“守丞”的“守”,如《史记·陈涉世家》就有“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的记载。秦战国、秦汉的“守丞”,多为临时摄县令、县长之丞。此外,里耶秦简中曾出现过的“田官守”,显然亦非郡守的“守”,而是“守吏”。
排除这种情况,笔者注意到“守”字单独出现时,“郡名+守”可以理解为“郡守”“泰守”或“大守”。尤其是若同一简文并列出现多个郡名,那么那个未知的地名可以断定为郡名,如上文笔者所考郡置年的衡山郡。
但以往论者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金布律》影响,误将汉县“州陵县”的前身视为秦县“州陵县”。我们看汉简确实有这样的文载:“孱陵、销、竟陵、州陵、沙羡……秩各六百石,有丞、尉半之。”这里的地名皆为县名,足见汉初亦确有州陵县。
由上六条简文来看,州陵显然是秦战国所置的郡。笔者花费将近三周的时间遍查各类传世或出土文献,未见有秦王政二十四年前(包括二十四)州陵郡的任何“蛛丝马迹”。就笔者目之所及有限的文献检索范围内,考古界未来若无新的发现,州陵郡应该是置年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后。也许,该郡是秦统一前临时设置的新郡,如岳麓秦简J-019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
同罪其繇使而不敬,惟大啬夫得笞之如律。新地守时修其令,都吏分部乡邑间。不从令者,论之。
陈松长先生据此认为该“新地守”是秦统一六国期间的地方临时看守政府,职权范围还不小,既可以“时修其令”,也可以“分部乡邑”,待兼并战争结束后,“新地守”便不复存在。陈先生之论,其实亦是间接承认了秦战国州陵郡的存在,只是该郡具备临时郡地的色彩。
笔者以为州陵郡并非仅仅担任临时“新地守”的角色,属于行政职权及其地位上与其他新郡平起平坐的秦战国实郡。岳麓秦简的J0061、J0083公务活动,显然属于州陵郡与南郡之间的平级性质的公务公文复报事务,简文内容及“报”式格式,按今官方公务文书分析,属于平行文。州陵郡或由于所辖区域有限,且经济实力、地缘政治影响力等皆不如邻郡南郡,于是在秦王政二十六年(此方可称“秦始皇元年”)重新调整郡县区划时降格为南郡的一个县了。
无论怎样,毋庸置疑,州陵郡应该是秦战国所置的实郡之一。该郡置年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前后。
(本文所有的古地名的书体一律以秦封泥等出土文献文载为主。)
①2008年年底,陈松长在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会主办的“以东亚资料学为可能性的探——以出土文献为中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一文,后发表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②司马迁.史记[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24.
③⑤陈伟.岳麓秦简中的两个地名的初探[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25(1):116.
④⑰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2):9-10.
⑥司马迁.史记[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1903.
⑦据《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等所载,江元仲,名恩成,字元仲,为伯翳之三子,前1101年受封于江邑,并建立了江国。周代江国国都则位于今河南省正阳县东南、淮水北。这里发现有江国故城,平面长方形面积约17.5万平方米,时代为东周至汉代。江国被楚国所灭后,一部分江人被楚国强迁于楚国内地的江亭,今湖北江陵南的江北,成为楚的臣民;一部分江人北逃入陈国,今河南淮阳地区,后由淮阳为中心向四方散迁,其中一支向东北方迁移至齐鲁大地。其后子孙以国名为氏,称江姓。
⑧司马迁.史记[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399.
⑨司马迁.史记[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314.
⑩谭其骧.长水集: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0.
⑪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M]//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86-88.
⑫刘瑞.秦封泥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1219.
⑬晏昌贵.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名录[J].历史地理,2014(2):147.
⑭⑮㊴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J].文物,2009(3):85-86.
⑯朱桂昌.颛顼日历表[M].北京:中华书局,2012:292.
⑱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使得陶邑的区位交通优势充分发挥了作用,“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迅速发展成为诸侯国间商品交易的中心城市,司马迁誉之“天下之中”。陶邑位于菏、济水系交通要道,自陶邑西溯济、河而上可达秦、晋;顺济水而下,能抵齐国都城临淄;东经菏、泗、淮可到南方的吴、楚地区。战国时期开凿“鸿沟”,更使陶邑水运条件锦上添花。
⑲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427.
⑳司马迁.史记[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3926.
㉑梁万斌.帝国的形成与崩溃——秦疆域变迁史稿[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173.
㉒司马迁.史记[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266.
㉓司马迁.史记[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2814.
㉔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秦郡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9:536.
㉕谭其骧.长水集: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3.
㉖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733.
㉗傅嘉仪.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M].杭州:西泠印社,2002:93.
㉘任红雨.中国封泥大系[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65.
㉙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436.
㉚成玄英,陆德明.释文[M]//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1:2-3.
㉛毛岳生.秦三十六郡说:休复居文集:卷一[M]//谭其骧.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1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79.
㉜刘师培.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255-1256.
㉝司马迁.史记[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2238.
㉞郦道元.水经注校证[M].陈桥驿,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721,722.
㉟谭其骧.长水集: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7.
㊱刘师培.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256.
㊲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问:卷一[M]//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铸禹,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483-2490.
㊳司马迁.史记[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323.
㊵司马迁.史记[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2254.
㊶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74-75.
㊷㊸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