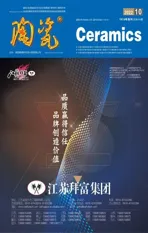“分析心理学”视阀下的宋代青白瓷艺术内涵阐释*
2022-10-25俞瑞林何颖然
俞瑞林 何颖然
(1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400)(2 景德镇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400)
心理学家旨在描述、解释、预测和影响人的行为,其中应用心理学在满足4种目的的同时更加注重人类的生活质量,而分析心理学作为其中一个类别,是由荣格提出的一套人类心灵深层理论。令人激动的是,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青白瓷作为宋代的艺术巅峰代表一直是中国人的宠儿,人们研究青白瓷的脚步也一直没有停止,利用分析心理学来阐释宋代青白瓷艺术内涵有利于丰富人们的审美方式,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和哲学修养,启迪人们对宋代青白瓷艺术内涵更深层次的思考。
宋代青白瓷的产生不只是单一方面促成的,而是由天时、地利、人和等综合面影响。笔者从分析心理学的角度,从宋代青白瓷的集体无意识原型入手,发掘出“尚玉”的集体无意识原型,再加上宋代青白瓷深受宋代政治、宗教、哲学、文人审美、书画意趣等的影响[1],宋代青白瓷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特别是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自性化追求,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宋代青白瓷艺术内涵上,还体现在宋人自身的自性化发展上。在此基础上,最终回归到宋代青白瓷的创作方式实践中,观察到宋代青白瓷的创作方式是一种移情式的审美态度和宋朝人的自性化发展。
1 “尚玉”的原型
原型不同,它的原始意象也不同,是一一对应的,例如“玉石器”是宋代青白瓷的原始意象,那么“尚玉”情结就是原型。原型是一种心理模式,类似于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但是它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是无意识的,当原型心理模式开始工作时,人自身是察觉不到的,就像被一种情绪影响,不知不觉被它随意支配。
中国儒家提倡玉文化最早出现在《礼记》中。书中通过敲打玉发出的声音,观察玉呈现的色泽光彩,抚摸玉的质感来决定一块玉是优还是劣,将玉石拟人化,赋予玉石以人的品格,来阐释玉石器的“九德”、“十一德”和“五德”。中国先秦的古书中都喜好把君子和玉作比喻,之后又把玉拟人化,比作德,其道德的人格化到东汉时期到了顶峰,许慎在《说文解字·玉部》中提出君子品格要温柔纯良如玉。“玉石比德”的思想经过古人的概括、精炼、修正,得出“玉”不单是外在表现出来的美,而且还是人们心灵层面感性的美,这里就侧面形成了“玉”内在与外在美的统一,这也是青白瓷“尚玉”的依据。
根据魏晋南北朝和唐时期考古发掘资料,与作为礼器的其他金银瓷器相比,玉器占很小一部分,这是由于除玉石器之外的器皿越来越来普及,制作原料和使用方式更为容易,玉石器渐渐失去了它作为礼器的身份。随着泥土火化而得的瓷器占据人们的生活,历朝历代在器皿的选择上逐渐减少了对玉器的使用。明朝《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将宋代景德镇的青白瓷称为“单纯的玉骨意象”。不可否认的是,玉作为美的象征和道德教化的载体却经久不息,她以另一个身份更加深入地影响着宋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个身份就是宋代青白瓷。

图1 景德镇窑青白釉双鱼碗
宋代青白瓷青白之间的釉色和如玉的质地一样都源于古人崇尚玉的美。宋代青白瓷釉色介于青白二者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这和古代的“五行说”和“五色说”有关。青居于五个颜色的首位,青、白两个颜色都在五色之中。古人使用的颜色都为正色,喜好单色崇拜。宋真宗时期有修书中阐述五行无色关系的“五德终始”说,“五色”也表示“五德”[2]。
然而青白瓷青、白两色的融合也恰好满足了儒家的中庸思想,加上“青”给人一种纯净、仁慈的感觉,青白瓷也成为儒家道德教化的载体被推崇。
总体而言,宋代青白瓷作为假玉器代替玉器在宋代社会风靡,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这不仅是玉石原料的稀缺,玉石器的逐渐减少,还是人们内心深处“尚玉”的集体无意识原型在发挥作用。
2 “天人合一”的宋代青白瓷
宋朝的儒释道合一的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特别是“格物致知”的理学思想和“制器尚象”的器道观,直接对宋代青白瓷的风格产生巨大深刻的影响,导致宋代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审美境界,孕育出宋代青白瓷“天人合一”的最高艺术境界。
“道”和“器”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对哲学范畴,还对工艺美学有非凡的指导意义。我国古代在描绘设计思想中,关于道与器的关系,可以说是各流派都能自圆其说,各有各的看法。此时,我们需要在广博深奥的古代设计思想中重新认识一下“道”和“器”,这可以精准地找到宋代青白瓷是如何设计构思的。
道器观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该书的注疏中释为:“道是没有实体,是看不到的,形是实体的称呼。无生道,先有道后有形,道在形的上面,形在道的下面。所以古人称形而上的为道,形而下的叫器。形虽然处于道和器两者之间,但是形目的在于描绘器,不在于解释道。所以如果拥有形质,那么就可以作为器物用于使用,所以就有人讲‘形下者谓之器’。”这种道器观念足以体现人们对人、器物与自然三者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在制造器物的工艺流程中,器物的设置、筹划和制作,到最后的产生都在它的“道”中完成[3]。
中国的传统哲学观念中从古代就有崇“道”抑“器”的说法。“道”被千万人推崇而居于庙堂之高,成为中国人朝圣和崇尚的信仰,“器”却只能被看作是匠人为生计奔波的手艺。工艺美术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以实用为目的,被君子视为三脚猫功夫,难登大雅之堂。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一直遵循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并重的造物宗旨,希望做到天人合一的和谐,在整个工艺流程里,古代的工艺设计者们很好地把握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以物品的整体性为先,尽力协调好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像天时、地理、原料、技法等。
古代工匠使用自然材料和设备。当然,创作的技法和技巧都是从自然中衍生出来的,符合自然规律,《考工记》提出了“审曲面势”。“审曲面势”在真实意义上充分利用材料。材料施工要求人们在创作策划中遵循原材料的特性和性能,以获得效益,避免破坏。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发挥工匠的主观创造力,以最少的精力,发挥最大的效能。所创作的作品才能浑然天成。审曲面势,道法自然,反映了古人的智慧和对自然的敬畏与借鉴,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器与道的共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简单理念,完美地体现在这一平实的造物观中。总的来说,宋代青白瓷艺术内涵是由宋人“制器尚象”造物原则、“物以载道”造物观和“天人合一”审美境界的综合因素形成的,其中“天人合一”境界也体现出隐藏在宋人心中的自性化。
3 宋人的自性化发展
3.1 自性化与中国文化
分析心理学也叫荣格心理学,它的核心就是自性化,最早被叫做“Ego”。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自我”、“我”,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还存在着一个自己,一个内在的自我,被称之为“自性”,荣格用的是大写的“自己”(“Self”)。荣格这里的自性,是一个完整和最高境界的自我。自性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甚至自己的人生都息息相关。荣格在寻找集体无意识过程中深受中国文化的启迪,中国文化就像是荣格心理分析的哲学理论来源。而自性化,将它放进中国文化的沃土里来描述,所追求的也正是“天人合一”的自我超越的境界。荣格的心理分析恰恰与中国的哲学文化不谋而合,是它的关键和目的。
梅尔在戴维·罗森《荣格之道》的序中直接提到,荣格是一位道家。好像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到荣格心理学中蕴含着对立统一的心理学,这从根本上讲是与道家思想的异途同归。人们所知荣格的样子并不是荣格的原本的样子。他一直与自然保持亲密的联系,与自然处在对立统一的关系里。然而荣格对道家是非常的憧憬的,当然也是满怀诚心的,这点他自己是最明白的。”[4]这里所提到的对立统一心理学也正是“自性化”过程中蕴含的心理科学,其与宋代青白瓷追求的“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别无二法。
3.2 宋人与自性化
廖奔的《宋艺术论》指出:“外部世界对宋人的心理影响是深远的,这使宋人失去了汉唐时期开阔、外向、激情四射的视野、抱负和理想,变得害羞、内化、软弱,他们把目光从外在的赌注、期待和研究中移开,转向了内心的内视、内省、调整和气质的自动控制,唐代气质大而宽广、外向自信,从那时起就迷路了。”[5]宋代的心理气质是控制自我保存、包容而不显露、温婉典雅、谨慎,人们追求的人生理想不再是唐代的外在成就,而是转变为一种音乐、棋艺、书画、诗歌、礼仪、弦乐、调息、滋养的艺术。汉唐以前的开疆拓土横向的视野转变为宋人对内纵向的自我调息。宋人对内在的反省思考正是自我内心自性在调息自己矛盾的心理,同时也追求着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精神境界,这是反思自身又超越自身的表现,体现了自性的真实性和超越性功能。
4 移情与宋代青白瓷创作
4.1 对移情心理的见解
荣格派移情心理学是对投射性认同的一种新的解释,认为移情是人自性化发展的必经之路。1946年克莱因提出“投射性认同”这个概念后,荣格也在同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移情心理学》的论文。这篇文章就是荣格自身对投射性认同的探索。论文中荣格利用了原始认同、污染、无意识认同、心灵感染、参与神秘感、归纳、感觉进入来阐述投射性认同的多个方面。并且1921年,荣格在《心理类型》中认为,“感受进入”的过程就是移情的过程。荣格说,“它是将我的品质客观化为一个对象,与我自己不同,质量对象化是否值得“感觉”,它通过感觉的作用传递给对象的一种基本的精神内容。通过这种方式,物体被内射。这一内容是由于它与主体的根本关系而产生的,后者指的是,在物体上,不是感觉自己进入了物体,而是感觉到了外表这一特点取决于投射将无意识的内容转移到对象的事实,在分析心理学中,情感转化过程也是如此。”
移情,是精神分析的一个用语,利用移情心理学来为患者进行治疗,荣格分析心理学中就有沙盘疗法和词语联想等方法对患者进行催眠,使患者情绪由原者转移到他者,把情绪发泄出来的过程。精神分析者也有可能产生共鸣的移情,这被叫做逆移情,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两种,这是分析师的一种防御心理。
“神秘参与”也是荣格描述投射性认同的关键词,他认为处理的目的就是实现主客体的融合,这种融合状态就称为“神秘参与”。他解释道“集体无意识是一种自然的、普遍的物质,它的表达总是导致无意识的身份,一种神秘的暗示状态”。
对于荣格学派的分析人士来说,投影识别中同时出现的“消失自我边界”和“融合”现象,正是人类精神的本质特征和自我定制过程中的必要步骤。因此,施瓦茨·萨兰特认为荣格早就看到了投射同一性的积极作用,尤其是投射同一性对审美意识和移情的影响。
4.2 宋代青白瓷的移情式创作
创作主体对创作对象的创作方式由宋朝人的移情式的审美态度决定,即宋朝人通过移情心理将自身的审美态度投射到青白瓷上,再创作而形成的。
中国传统美学大师朱光潜在《诗经》中论述了审美活动。他说,“静”自然是自由的,很容易找到。对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不同文化、不同审美趣味的人在同一作品中看到不同的意义和场景。朱光潜不仅论述了“从我到事”的移情,而且还论述了“从物到我”的移情,认为移情是事物与情境的融合[6]。荣格如何在书中阐释艺术创作的移情美学? 荣格认为移情是美学中一种客观的自我愉悦过程,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志活动,在不同的对象中进行。不断的经验和不断的追求。以瓷器为例,唐五代以来,瓷器的功用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不少变化,它不断地在适应和满足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要求;它既是精神审美的物质器物表现,同时也追随着精神审美观念与审美情趣的变化轨迹。这说明创作主体与作品的关系,是一种移情于物的创作方式。
从创作主体来讲,青白瓷的创作主题来自各个阶层,制瓷的工匠也不同,他们的制瓷技巧和对青白瓷的审美不可能都一样,但是宋人对玉的喜欢和追逐是一样的,这是青白瓷与宋人“尚玉”情结的双相呼应。

图2 景德镇窑青白釉刻花梅瓶
荣格心理学特别强调移情是主客一体融合的。令人惊讶的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与人的统一出发,认为人与自然不是主客体的二分法关系,而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主客一体的,人与自然不可割裂,必须在一个对立统一关系里。宋人在“尚玉”情结的支配下,寻找玉石器的替代品,在青瓷和白瓷的融合中,创造出莹缜如玉的青白瓷,它一经出世就受到宋人各个阶层的推崇和喜爱,将青白瓷作为宋代道德教化、艺术文化、时代精神的代表,汇集了宋代的政治政策、宗教思想、哲学思想、文人士大夫审美情趣和其他艺术门类风格。宋代青白瓷作为宋朝艺术审美的巅峰,同时又是各大家各流派的“推崇者”,这必定是宋人对青白瓷的有意为之,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青白瓷上。
同时宋人在自我超越的“自性化”发展过程中,将自身的“自性”集体无意识投射到青白瓷上。宋人自身追求着“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也体现在青白瓷身上,使得宋代青白瓷有着“天人合一”的艺术审美境界。
宋代青白瓷从它出世到顶峰,一直受到国人的推崇,南宋蒋祈称青白瓷为饶玉,到了晚清民国人们称之为影青、罩青、映青。可见从古至今,青白瓷独特的审美情趣都得到人们的喜爱。笔者选取应用心理学的理论,从宋人的心理学角度入手,从而揭示出宋代青白瓷艺术内涵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宋代青白瓷作为宋人审美情趣的巅峰,不仅深受士大夫阶层的喜爱,同时也符合市民阶级的审美,可以说宋代青白瓷审美是雅俗共赏的,时至今日,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在我们陶瓷文化建设、陶瓷产品设计都具有举重轻重的地位。宋代青白瓷的产生到发展都蕴含折宋代人精神生活,通过应用心理学可知,正是由于宋人尚玉这一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偏好、追求天人合一的个性化发展、道器并重的设计理念才创造出沉静素雅、雅俗共赏的青白瓷。笔者拓宽了古陶瓷研究新视野,基于分析心理学的角度,从更加深层次的审美情趣、古人心理审视宋代青白瓷的形成,在研究陶瓷文化的同时,更能回到人性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