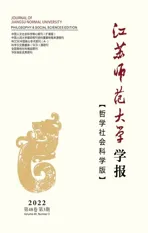贸易、探险与国家主义:华盛顿·欧文《阿斯托里亚》对远西部的“收编”
2022-03-18贾莹
贾 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北美皮毛贸易伴随欧洲殖民者瓜分美洲的过程而展开,自兴起就与帝国的“领土欲望”缠绕在一起。相比而言,欧洲皮毛商和捕猎者已在西部游荡了几个世纪之久,却只留下少数著名的日志和游记。美国独立后加入了欧洲列强在“远西部”(2)在美国历史上,“远西部”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它最初是相对于东部十三州而言的。根据早期历史和地理文献记载,远西部往往是对密西西比河以西至太平洋沿岸广阔地带的泛指,包括大平原、落基山脉、大盆地和西海岸等地理区域。美国独立之初,这些区域大多属于尚未被白人定居者占据的印第安领地,且处于英法俄西等国的争夺之中。随着美国领土疆界的扩张,国家势力不断向太平洋沿岸推进,直到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报告宣称“边疆线消失、美国人口中心西移、北美大陆再无未被定居的土地”,“远西部”这一概念也渐渐隐匿于历史。的贸易争霸,其相关探险活动成为西部叙事的常见主题。在作家的重新定义下,商人和捕猎者变成“帝国缔造者”,他们为财富和利益铤而走险的趋利性被表征为建造“横跨大陆帝国”的雄心。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作家关于远西部的贸易、探险和拓殖的大量想象性描述,为美国吞并西部制造了心理基础和文化支撑。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出版于1836年的《阿斯托里亚,或落基山脉那边一家企业的轶事》(以下简称《阿斯托里亚》)就是其中的经典。通过大肆宣扬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发起的皮毛贸易及相关探险对于美国扩张的意义,欧文将一位商人追捧为开疆拓土的英雄人物,从而把美国人在远西部的贸易和探险纳入国家想象,表现出自觉的疆土意识。因此,考察《阿斯托里亚》所映射的帝国/国家秩序及其意识形态话语一直是重要的文学议题,也是美国西部史的必要参考和研究对象(3)虽然《阿斯托里亚》因其浪漫化书写而被排除在严肃的历史著作之外,但其中关于远西部的贸易、探险及殖民活动的许多细节出自阿斯特提供给欧文的材料,包括探险队员的日志、笔记和回忆录等,《阿斯托里亚》因对这些一手材料的“吸收”而具有了一定的文献价值。同时,欧文关于“阿斯托里亚”的写作本身也是19世纪早期美国扩张欲望的表征,往往被西部史学家纳入研究考察范围。。但一个疏于深究的问题是:《阿斯托里亚》一面表达对国家主义观念的认同,一面却透过种种细节拼凑出一个异于表层叙述所彰显的美国命运及其意义世界,折射出远西部皮毛贸易的全球殖民性,以及西部土地的非美国属性,与欧文精心构筑的英雄叙事相互抵牾。而这一矛盾的对话暗示着民族国家建构与帝国之路的双重变奏,也是理解《阿斯托里亚》作为国家叙事的发生、形成及有效性的关键。基于此线索,本文将《阿斯托里亚》置于欧洲势力征服美洲的全球史语境中,尝试厘清皮毛贸易、帝国探险和西部书写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杰斐逊时代至杰克逊时代美国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中,思考欧文的创作与国家主义之间的互动。由此出发,意在探讨远西部的贸易竞争和殖民扩张如何通过文学的“收编”而进入美国的国家话语,以及作为“浪漫史学家”的欧文在何种程度上实践了对帝国领土权利的声张,进而为美国大陆扩张早期的文化精英关于国家身份和国家合法性的探寻提供一种解读。
一、从殖民商人到文化偶像
1834年9月15日,从欧洲回到美国不久的欧文在给侄子皮埃尔·门罗·欧文(Pierre Munroe Irving)的一封信中写道:“阿斯特极其渴求能有一部关于他在哥伦比亚河口建立阿斯托里亚殖民地的著作;这部作品也许会引起阅读界的关注,使他获得开创企业和建立殖民地的名誉,并在商业和殖民史上很可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4)Pierre Munroe Irving,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Washington Irving, Vol. Ⅲ,New York: G.P. Putnam,1863,p.60.。信中还提到,阿斯特已提供信件、日志、口述文献等相关资料,且开出了诱人的条件,欧文询问皮埃尔能否代劳整理繁冗的材料(5)阿斯特称愿意支付任何适当的酬劳,所产生的销售利润也属于作者。参见 Pierre Munroe Irving,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Washington Irving, Vol. Ⅲ, 1863,pp.60-61.。 作为出生于德国沃尔多夫、1784年移居纽约的德裔美国人,阿斯特靠皮毛贸易起家,为掌控北美皮毛资源、打造一个垄断性贸易集团,他于1808年、1810年分别成立了美国皮毛公司和太平洋皮毛公司,又于1810—1813年发起了从内陆面向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探险,并在1810年修筑了该地区首个美国贸易站——阿斯托里亚。到1830年代他退出皮毛市场时,已拥有千万资产。此时阿斯特希望借文学之笔使其事业的民族性和重要性得到理解(6)Washington Irving, Astoria, or Anecdotes of an Enterprise Beyond the Rocky Mountains, Vol. I , Philadelphia: Carey, Lea, & Blanchard,1836, p.4.。 肯尼思·威金斯·波特(Kenneth Wiggins Porter)认为,阿斯特终其一生的兴趣是赚钱,却执意要记录下那项给他造成重大财政损失的事业,原因在于他更想作为一个“帝国梦想家”被人们记住,而非“纽约地主”(7)Kenneth Wiggins Porter, John Jacob Astor: Business Man, Vol.I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 pp.242-243.。
就一部委托之作而言,阿斯特既是赞助方又是主人公,这意味着该作品可能会为了迎合委托人而牺牲部分真实性。而在现实中,欧文与阿斯特的交往始于1821年,当阿斯特向这位曾为哥伦布作传的知名作家发出邀约时,欧文刚好处于财政不稳定时期,正在寻求经济支持(8)See Axel Madsen, John Jacob Astor :America's First Multimillionair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Inc,2001, pp. 237-238.;加上读者对欧洲的老生常谈已产生审美疲劳,更期待美国主题的作品,而阿斯特的故事恰好能展示美国的巨变。在内外因素刺激下,二人一拍即合。写作期间,欧文常常居住在阿斯特位于纽约曼哈顿海尔盖特(Hellgate)的乡间别墅。根据他写给哥哥皮特·欧文的一些信件及皮埃尔在《华盛顿·欧文的生平及书信》中的描述可知,从1835年8月至1836年10月书稿出版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文都与阿斯特在一起,后者不仅为他提供了舒适理想的创作环境,而且随时接受其采访。也许是担心外在因素会影响《阿斯托里亚》的可信度,欧文事先在引言中勾勒出一个纪实印象:他细数了一系列文献准备工作,并提及1832年随同印第安事务官亨利·L·埃尔斯沃斯探索南部大平原的经历(9)位于今天的俄克拉荷马州,正是这次游览促成了《大草原之旅》(1835)、《阿斯托里亚》和《博纳维尔上尉探险记》(1837)等三部西部作品的诞生。。然而,就一位出生于纽约、旅居欧洲17年后刚刚返回美国的作家而言,他聚焦西部的角度及观察到的世界究竟如何,显然无法只依据作者的自述予以判断。
《阿斯托里亚》从对远西部皮毛贸易史的追溯开篇,简短回顾了阿斯特追求财富、投身皮毛事业、建立公司和开展商业计划的历程,其人生轨迹被欧文置于爱国主义光环之下,阿斯特的贸易活动因而具有了“把整个行业纳入美国渠道”(10)Washington Irving, Astoria, Vol. I , 1836, p.30.的重要价值。这一“引言”奠定了整部作品的基调,在它的统摄下,欧文展开了那场历时三年的探险故事。1810年,乔纳森·索恩带领海上探险队乘“汤昆号”从纽约出发,经南美合恩角进入哥伦比亚河,在北岸修筑了“阿斯托里亚堡”;1811年,威尔逊·普利斯·亨特率领陆路探险队先抵达圣路易斯,后穿越大平原、跨过落基山脉,两者在阿斯托里亚汇合。海上征程的目的是沿密苏里河和哥伦比亚河修筑一系列贸易要塞,陆地征途则为探寻一条横贯北美的贸易运输通道。虽然这场探险由于印第安暴乱、汤昆号沉船、英美战争等一连串意外事件而夭折,欧文却巧妙地将仅有的荣光归于隐匿在背后的组织者,声称阿斯特从事皮毛贸易并非受个人利益所驱使:“他的富裕程度使他超越了普通人的欲望,而今他渴望那种光荣的名声,这种名声的被授予者有着相似的精神境界,通过他们伟大的商业事业使得国家变得富裕、荒野得以居人,并扩展了帝国的边界”(11)Washington Irving, Astoria, Vol. I , 1836, p.39.。
欧文笔下的“爱国商人”及其“民族事业”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历史中的阿斯特其人其事?后来的史学家已给出了答案。如海勒姆·马丁·奇滕登(Hiram Martin Chittenden)指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欧文先生对事实的忠诚度遭到非难,他被指责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修饰作品。他被一位作家质疑,允许让自己与阿斯特先生的友谊影响对人与事的判断。最后,他被指控,即便不是直接抄袭,也是在未获得应有承认的情况下大量使用他人作品”(12)Hiram Martin Chittenden,The American Fur Trade of the Far West, Vol.I, Stanford, Academic Reprints,1954,p.239.。同时,阿斯特的爱国者形象及其光辉事业也为文学研究者所诟病。如I.S.麦克拉伦(I.S. MacLaren)就直指其虚构性:“假如他被欧文描述为民族英雄,阿斯特必须对他的性格作出很多调整,即便不是彻底修复这些缺点”(13)I.S. MacLaren. "Washington Irving's Problems with History and Romance in Astoria",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Vol.21,Issue1(Summer,1990),pp.1-13。为厘清个中纠葛,还需返回历史现场予以查究。
阿斯特进入美洲皮毛贸易行业之前,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海狸皮资源经过三个世纪的掠夺几近枯竭,这项贸易在欧洲各国的殖民地经济中也渐居次要。直到1776年,西北海岸的海獭皮资源被英国探险队发掘,詹姆斯·库克在日志中透露了对华皮毛交易的商机;1787年,美国人罗伯特·格雷前往太平洋沿岸收集海獭皮,随后欧美商船在该区域掀起了新一轮皮毛热。与此同时,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首航广州开启了中美交易模式,中国市场为美国皮毛商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14)1784年,纽约商人集资装备了360吨包括棉花、人参和皮毛等货物的商船驶向广州,命名为“中国皇后号”,由此展开中美通商。详见汪熙、邹明德:《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第92-102页。。 作为最早参与对华交易的美国人,阿斯特于1800年联合三位纽约商人、派遣满载皮货的商船前往广州,在当地赚得巨额差价后,换购丝绸、香料、瓷器、茶叶等中国商品,再转运到纽约或欧洲卖出,这样的资本积累为他构建“皮毛帝国”奠定了基础(15)Axel Madsen, John Jacob Astor,pp.51-52.。 然而,1807年的《禁运法案》中断了阿斯特垄断美洲贸易市场的计划,但他并未气馁,先是游说政府批准他成立美国皮毛公司,后又呼吁国会在太平洋沿岸建立军事基地保护美国贸易。约翰·厄普顿·特雷尔(John Upton Terrell)揭示了阿斯特的游说隐藏的真实意图:假如能获得官方支持,一方面可有效打击欧洲商人,另一方面可避免“工厂体系”(16)美国政府建立“工厂体系”(1795-1822)目的在于通过与印第安人交易而对其进行“文明教化”,使之放弃部落生活方式、归入联邦。非盈利性的“工厂体系”虽然不具备竞争力,但政府以低价大量收购皮毛对商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参见Eric Jay Dolin, Fur, Fortune, and Empire: The Epic History of the Fur Trade in America,New York,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10, pp.172-174.的竞争(17)参见John Upton Terrell, Furs by Astor, New York: Morrow,1963, pp.138-145.。当《禁运法案》被取消后,阿斯特立即重启计划创建了太平洋皮毛公司。这便是《阿斯托里亚》中海陆探险发起的背景。
虽然阿斯特推动的探险及后续尝试均惨淡收场,太平洋皮毛公司也在1812年英美战争中解散,但欧文却对一系列失败进行了遮丑美化处理,将原因归结如下:其一,由于探险活动代理人没有领悟阿斯特的思想精神,失去“汤昆号”、使“海狸号”偏离航线等失误都与他无关:“我们没有理由将这起伟大的商业项目的失败归咎于设计者在策划上的失误,或执行中的疏忽”(18)Washington Irving, Astoria, Vol. II, Philadelphia: Carey, Lea, & Blanchard, 1836, p.259.。 其二,政府应该对损失负责:“我国政府忽视了阿斯特先生的提议,错失良机,那时本可以悄无声息地完全占领这一地区,毫无争议地在阿斯托里亚建立一个军事哨所”(19)Washington Irving, Astoria, Vol. II, p.262.。 这里指战争之后,阿斯特向詹姆斯·麦迪逊提出协助重建阿斯托里亚的请求遭到拒绝,从而丧失了对太平洋海岸的所有权,欧文由此指责美国政府的漠视。但即便阿斯特进发西北地区的美梦落空了,现实也并非欧文营造的那样悲壮。特雷尔指出:“阿斯特拥有比所有其他圣路易斯商人加起来还要多的资源、金钱、头脑、人脉和政治权力。他在欧洲有代理商,能直接以最低的价格从工厂采购成品。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皮毛商,与英格兰、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最好的商行建立了联系。他自己的船只载着皮毛穿洋过海,并带回采购的商品”(20)John Upton Terrell, Furs by Astor, p.373.。 此后阿斯特转战密西西比河上游及五大湖附近,几乎垄断了密苏里皮毛市场。
通过与史实比照,阿斯特与其文学肖像之间有着不小反差,从一位追名逐利的殖民商人变成了“杰克逊式的企业家”“浪漫英雄”或“经由欧文的幻想净化的历史人物”(21)I.S. MacLaren. "Washington Irving's Problems with History and Romance in Astoria", pp.1-13.。 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时代的美国人经历着重要的社会转型,经过一系列反对政治和经济特权的改革之后,两党制初步形成,农场主、小生产者和制造商等获得了创业发迹的机会,整个社会处于资本主义的膨胀阶段。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从自由资本主义兴起的角度解读杰克逊民主:“它所追求的只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理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约束政府,使之对公民提供平等的保护,这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哲学;其宗旨不是扼杀而是解放工商业,为人民的创造性事业打开一切可能的途经”(22)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74页。。 霍夫斯塔特切中了杰克逊亲商业的一面,这位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靠个人奋斗进入白宫的平民总统,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美国梦的一个样板;同时,作为1812年战争中的英雄,杰克逊也把对联邦国家的忠诚信仰融入其社会哲学。而阿斯特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德裔商人,“代表了美国资本主义所有的精明和务实”(23)James P. Ronda, Astoria and Empire,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pp.1-2.,因而也是某种象征意义上的杰克逊人。欧文在阿斯特的个人事业与国家的未来发展之间精心设计了一种关联,使他与亚历山大·麦肯齐和梅里韦瑟·刘易斯等帝国探险家齐名,他疯狂投入贸易竞争被标榜为“为美国而战”的英勇行为,而杰克逊时代则为这类形象制造了天然的文化土壤。
二、国家主义的投射
关于欧文对阿斯特皮毛事业的书写,历来有多种解读,其中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欧文作为“浪漫主义史学家”,在描述事实时倾向于对历史进行浪漫化处理,这使他的视线停留在帝国扩张和西进运动的浪漫素材表面,没能像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那样触碰到西部现实的内核,即欧文“对现实的不敏感”导致他忽视了阿斯特投身皮毛贸易的实质。例如,沃浓·路易·帕灵顿就替欧文作出了婉转的辩护:
他对经济事务一无所知,从未理解过发生在身边的革命有什么重要意义,这种“天真”使得他无法看清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投资阿斯托里亚的真正动机,就好像无法看清同时代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一样。皮毛公司为夺取霸主地位进行了激烈竞争,他轻松地为其涂上了浪漫的色彩。但他不清楚的是,他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各公司的垄断性投资。(24)沃浓·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陈永国、李增、郭乙瑶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
然而,欧文真的如同帕灵顿所形容的那样对时代政治保持天真吗?他回国后便加入了一场美洲草原之旅来体验“不同于欧洲的新事物”,只是为了寻找美国主题的写作素材吗?其实稍加考察便可注意到欧文的浪漫主义与帝国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关联。早在《哥伦布的生平及航行》(1828)和《哥伦布同伴的航行及发现》(1831)中,他就对哥伦布及同伴探索海外殖民地的精神赞赏有加,把他们看作为了伟大“设想”而踏上探险征途的骑士,而所谓的“设想”就是在新大陆展开征服与掠夺;同样,皮毛商和捕猎者的冒险敛财活动在欧文眼中是“险象环生的骑士漫游”,其探险经历亦是“完美的罗曼史”(25)Washington Irving, Astoria, Vol. I , 1836, pp.3-4.。显然,这套话语背后的逻辑并不单是审美层面的。事实上,《阿斯托里亚》所关联的历史事件及创作本身就涉及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期美国社会的重要变革,以及欧洲势力在北美的变化,对于交织其中的各种力量关系的考察,或可从“阿斯托里亚”这一书名切入。
在1834年10月29日写给皮埃尔的信中,欧文称打算以“阿斯托里亚”为计划中的作品命名,原因在于这个主题不仅关乎阿斯特的殖民和商业事业,以及他的殖民地的命运,而且涉及落基山脉以外、哥伦比亚河边界的整个区域的大量信息,包括海上与陆地探险(26)Pierre Munroe Irving,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Washington Irving, Vol. Ⅲ, 1863, pp.62-64.。 在欧文看来,阿斯托里亚具有商业与政治双重价值,其一是“作为一个庞大商业的市场”,其二是“作为一个能形成广泛文明之芽的殖民地”(27)Washington Irving, Astoria, Vol. I , 1836, p.39.。 在通篇行文中,他使用了许多华丽词汇来形容阿斯托里亚,认为它会极大地促进商业发展,并从国家角度为这项事业的夭折惋惜,甚至假设了西北海岸落入美国手中的情形:“除了四处游荡的捕猎者和贸易商之外,那片区域可能已经被勤劳的农夫开发和定居了;同时,那些与河流接壤的、夹在群山之间的肥沃山谷,可能早已盛产出农业珍宝来为国家的总体财富贡献力量”(28)Washington Irving, Astoria, Vol. II, p.261.。
欧文关于阿斯托里亚的认知,显示出他对远西部殖民形势的洞悉,以及对皮毛贸易战略价值的了解。事实上,欧洲人早已将皮毛作为闯入美洲的利器,商人和捕猎者为求取财富而足迹遍布山区、森林、草原和滩涂,帝国的统治者则借此将新的“被发现地”据为己有,皮毛贸易、地理探险和军事占领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17世纪初,由于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对金银更感兴趣,皮毛贸易最先成为法国人的事业;18世纪后,英俄等欧洲国家也陆续加入这场由皮毛引发的殖民地争夺战(29)Hiram Martin Chittenden, The American Fur Trade of the Far West, pp.1-70.。 美国独立后,制定了相关政策和法律推进皮毛贸易,以吸引商人、猎手和投机者前往西部。托马斯·杰斐逊在19世纪初发起“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30)杰斐逊就任总统后,于1802年派遣梅里韦瑟·刘易斯和威廉·克拉克率领一支队伍远征北美西部,该探险队被任命为“发现军团”,其行程覆盖了密苏里河至哥伦比亚河的沿途地区,从1804年5月持续至1806年9月,是美国人首次进入远西部的大规模探索,被称之为“发现之旅”。,并下达指令考察印第安人的文化和生活,调查他们参与皮毛贸易的情况,并说服对方与美国人交易,达到以贸易而非战争方式吞并西部的目的(31)Donald Jackson, ed., Letters of the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with Related Documents, 1783-1854,Vol.1, Urbana, Chicago and London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8, p.61; James P. Ronda, Lewis and Clark among the Indians,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4, p.3.。 詹姆斯·P·龙达(James P. Ronda)据此指出:“历代帝国建造者都利用皮毛贸易来稳固印第安盟友、防范潜在的帝国敌人、扩张领土。皮毛贸易不仅是成堆的皮草和一时兴起的男性时尚,帝国之路与贸易紧密相连”(32)James P. Ronda,"'A Knowledge of Distant Parts': The Shaping of the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The Magazine of Western History,Vol.41,No.4(Autumn 1991), pp.4-19.。
事实上,从18世纪末持续到19世纪40年代的“俄勒冈之争”(33)历史上俄勒冈地区的面积不限于当今美国的俄勒冈州,其大致范围指北美落基山脉以西、加利福尼亚以北至阿拉斯加以南的大片区域,即北纬42°至54°40′之间的地区。,就是远西部贸易竞争的重要背景之一。其中,俄国皮毛商长期活跃在白令海峡附近,于1799年创建了俄美公司来扩大殖民利益;西班牙在西北海岸建立了据点,曾与英国争夺努特卡湾;英国作为最早发掘西北海岸皮毛商机的国家,通过哈德逊湾公司和西北公司掌控哥伦比亚河口(34)Clarence A. Vandiveer, The Fur Trade and Early Western Exploration, Cleveland: 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1929, pp.141-148.。 欧洲多国竞争的态势限制了美国的扩张,而当时美国在该地区尚未拥有贸易站或公司,因而阿斯特组织海陆探险和修建贸易堡垒的意义就非同寻常。1819年后,西俄两国先后退出竞争,剩下英美商业集团以哥伦比亚河为界限分别占据了南部和北部的皮毛资源,直到1846年《俄勒冈条约》签订之前,两国都力图通过一系列事件来证明各自的“合法”权益,这些事件基本都与18、19世纪的探险、商贸和殖民活动有关(35)美国摆出的证据包括:1792年格雷在探险中发现哥伦比亚河并为其命名,1803年美国从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1805年刘易斯与克拉克在哥伦在比亚河地区探险并建立“克拉特索普堡”等。同时,英国也出示了相应的理由,如1778年库克的太平洋航海探险和西北公司在该区域的贸易活动等。参见Eric Jay Dolin, Fur, Fortune, and Empire, pp.284-285.。 而阿斯托里亚因两次易主成为英美分歧的焦点:1813年战争之际,阿斯特为避免损失将它卖给西北公司(36)1813年1月,阿斯特的合伙人得知英国战舰已启航准备夺取阿斯托里亚,自知无力抵抗,便以5.8万美元将其卖给了西北公司,被更名为“乔治堡”。参见雷·艾伦·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下册),韩维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2页。;1815年《根特条约》生效后,美国声称阿斯托里亚属于英国人强占的美国领土而将其夺回,英国则以它曾是西北公司的财产为由强调对俄勒冈的所有权。
彼得·斯塔克(Peter Stark)把“阿斯托里亚”视为北美西海岸的第一个美国殖民地,正像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作为东海岸的第一个英国殖民地一样,并指出商人和政党的不同期许:“对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来说,西海岸殖民地将成为一个全球商业帝国中心,北美西部几乎所有财富都将经他之手纳入一个巨大的贸易网络。对于曾热切地鼓励阿斯特建立殖民地的托马斯·杰斐逊来说,它将开启西海岸的一块独立区域——一个面向太平洋的美国的姊妹民主政体”(37)Peter Stark, Astoria: John Jacob Astor and Thomas Jefferson's Lost Pacific Empir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14, p.2.。 尽管二人存在理念分歧,但并不影响帝国的目标与商人的利益在一致时达成共谋。在欧文创作《阿斯托里亚》的1836年,英国商人虽然掌控了俄勒冈地区大部分皮毛资源,但大英帝国却聚焦于亚洲和非洲的殖民事业而无瑕他顾,一波波美国移民则乘势涌入远西部。欧文对这一情势了然于胸:“我们的定居点已经延伸到落基山脉,我们的拓荒者们渴望的眼神将探向远方,他们视为帝国宏伟出路上的任何障碍或阻隔都会令人感到不耐烦。”而一旦将来英美两国再次爆发战争,“阿斯托里亚就会成为争夺太平洋沿岸主权的口号”(38)Washington Irving, Astoria, Vol. II, p.262.。
以创作西部小说著称的库柏对欧文表现出的爱国主义表示怀疑,认为他长期迎合英美上层社会,与艺术家、政客和富商等美国贵族保持密切交往,这样的“爱国”可能只是他赢得美国读者好感的一个伎俩(39)电子文献:Brian Jay Jones, Washington Irving: The Definitive Biography of America's First Bestselling Author,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11. Web.12 October 2021.访问日期:2021年10月12日。。 库柏甚至将欧文视为“阿斯特的寄生虫”“一个没有什么主见的人”(40)范怀克·布鲁克斯:《华盛顿·欧文的世界》,林晓帆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页。。 如此评判也许一部分出于作家间的私人恩怨,但欧文早期创作的确呈现出商业色彩和亲英痕迹,这与他出身于纽约富商之家、有从商经历且热衷于投资不无关系。然而欧文叙事中的国家意识显然不止是迎合美国文学市场这么简单。虽然旅居欧洲数年使欧文相对疏远美国的现实纷争,但到1829年,美国的社会变革激发了他对政治的兴趣,使他回国后转向杰克逊民主。小阿瑟·施莱辛格认为,杰克逊时代的政治斗争引起了整个美国在思想上的震动,不少作家都转变为杰克逊主义者,在他开出的一张名单中,欧文与班克罗夫特、惠特曼、霍桑、布莱恩和库柏等都在其列(41)Arthur M. Schlesinger, The Age of Jacksonia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5, p.369.。 随着政治权利的西移和民主基础的扩大,杰克逊政府制定了有利于西部定居者的土地政策,新的经济政治秩序将美国向西推进,移民势力进一步点燃了1830年代的“俄勒冈热”,那种从独立之初就存在的“美国将扩张至太平洋沿岸”的帝国设想被充分激活了。在欧洲殖民者意欲瓜分远西部及英美争夺俄勒冈的形势下,美国皮毛商的贸易和探险直接关涉国家未来的疆域。
在这样一种社会意识的笼罩下,欧文将文学嗅觉投向西部,开始重新打量美国,且敏锐地抓住了皮毛贸易与帝国政治联姻的主题,《阿斯托里亚》就是时代变革引起作家思想震荡的产物。而一封写于1838年的信更像是回应了《阿斯托里亚》末尾所表达的遗憾,即美国政府的不作为导致英国皮毛公司长期占据哥伦比亚河地区,从而造成英美对抗的局面。欧文就此写下了关于帝国出路的思考:
至于遭到强烈谴责的过度的商业扩张和无节制的土地投机,我把它们看作是一个正在迅速繁荣壮大的年轻国家所拥有的天然进取精神的产物;这种精神,虽然偶尔过激,却给予了我们国家向前的巨大动力,并保证引领它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近来的土地投机活动,遭到如此多的抨击,尽管对于许多参与者来说是毁灭性的,但却使得农业和文明进入荒野深处;开辟了原始森林的隐秘地带;使我们熟知广阔内陆的可利用之地;把未来城镇和繁忙商业区的种子撒在蛮荒孤独的中心;在浩瀚的江河和内海布下港口,这些港口将会很快激活巨大的国内贸易。(42)Pierre Munroe Irving,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Washington Irving, Vol. Ⅲ, 1863,p.122.
这段看似为商业扩张和土地投机申辩的文字,流露出与美国早期国家主义理念的共通性。美国的国家主义最初产生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对美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思考,他们主张形成统一的联邦国家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应对重商主义主导下充满竞争的国际环境。但国家主义并不等同于联邦主义、或仅代表资本家和上层精英的态度,在美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环节中,那些不属于联邦党阵营的政治家,如杰斐逊、麦迪逊、杰克逊等,在其治国实践中都推动了联邦体制和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中央政府的力量和权威。尤其在第二次英美战争后,以亨利·克莱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抛弃了杰斐逊式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共和宪政思想,代之以‘美国体制’(American System)的经济发展思想”,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正是当年联邦党人的国家构想(43)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页。。 19世纪头30年间,面对内外困局、商业冲突、领土扩张的强烈愿望和扩展经济的迫切要求,民主共和党在变化的形势面前一次次倒向国家主义、放弃州权传统和共和主义追求(44)J·布鲁姆等:《美国的历程》(上册),杨国标、张儒林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4-349页。。
尽管不同时期的政治诉求和社会经济状况造成了19世纪上半叶美国国家主义的复杂化,加上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党派纷争、南北冲突和1819年经济危机等,使这一思想充斥着各种争论和矛盾,但不同倾向的国家主义在维护其政治共同体、谋求财富和自由、追求资本主义等方面形成了相对的共识,并作为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的强大精神动力,为美国大陆扩张和南北统一提供了思想基础。当国家主义在文化领域掀起波澜时,集体性的国家认同感进一步削弱了其中的对立和冲突。查尔斯·A·彼尔德夫妇认为,国家主义在19世纪前期的美国文学中占据“高音调”位置:它发声于共和国时代,强化于第二次对英战争时,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和杰克逊民主又加深了其影响,因而,“这个时代的所有美国作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音调的现实意义和它的号召力——甚至那些企图把欧洲文化工具应用于他们的文化活动的作家也不例外”(45)查尔斯·A·彼尔德、玛丽·R·彼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上卷),许亚芬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801-802页。。这句话恰巧可概括欧文在1830年代的思想转变及其在《阿斯托里亚》中的投射。
三、全球化视阈下的叙事悖论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新航路的开辟使各大陆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变得频繁,帝国资本和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传播,近代世界贸易体系也逐渐形成。18世纪末19世纪初,太平洋西海岸的皮毛贸易联通了北美、西欧和东亚之间的航线,使包括欧裔美国人、英属加拿大人、北美印第安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在内的参与者都卷入了一个全球性的交易网络。但与此同时,欧洲对非欧洲世界的控制与支配也愈加严重,帝国之间的竞争导致激烈的土地争端和资源掠夺,给美洲生态及原住民制造了极大的灾难,因而关于民族国家的话语建构在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视域中被消解了。而欧文试图把美国人在远西部的“拓殖”转化成吻合读者期待的“民族事业”,这种嫁接和转化虽然在当时的西部书写中并不鲜见,但如果考虑到美国同欧洲一样是出于吞并美洲的目的而进入西部,那么《阿斯托里亚》中的一系列“美国化”操作就值得探究。
独立战争使美国失去了原宗主国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提供的优惠条件和军事保护,英国的禁运很大程度上中断了美国的国际贸易(46)1775年,英国议会对北美采取贸易禁令,封锁了美国的沿海港口,抢夺西印度群岛的美国船只,导致美国商人跨大西洋贸易的风险和成本都显著增加。参见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巫云仙、邱竞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7页。,战后,美国陷入与欧洲交往的困局,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被各项政策法令削弱,这就促使保护美国国内市场的呼声越发强烈,经济独立成为第一代建国者面临的艰巨任务。在对外贸易受阻的情形下,跨太平洋皮毛贸易使美国突破了英国在亚洲的贸易垄断,据英国的档案记载,1804-1819年间美国商船输出广州的货物中,动物皮毛占比极大,美国商船数量在广州的增加对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构成威胁(47)松浦章:《19世纪初期美国商船的广州贸易》,《海洋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80-91页。。 阿斯特计划形成一个覆盖北美西部、面向海外贸易市场、且具有排他性的商业帝国。这一梦想一开始就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支持(48)1808-1809年间,阿斯特先后给纽约市长德维特·克林顿和总统杰斐逊去信,声称计划中的太平洋皮毛公司是一项具有公益精神的事业,会使北美大陆的皮毛贸易落入美国手中,帝国扩张也将在不损耗国库的前提下实现,因而太平洋皮毛公司在成立之初便获取了认可。,又被欧文提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恰恰反映了1812年英美战争以来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在美国社会的兴起,而这种情绪又是新生共和国在面临恶劣外部环境时的必然选择。
根据《阿斯托里亚》可知,阿斯特并未像承诺的那样维护美国利益而打击外国势力,相反,他创建的太平洋皮毛公司在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上具有明显的合资企业特点,其中,加拿大人的投资占了很大比重,许多雇佣船夫是法裔加拿大人,一些领头人物还是西北公司的前雇员。此前,英国为了压制美国而扶持加拿大皮毛商,造成后者在大湖区的贸易活动远超前者。按照1794年英美《杰伊条约》,英属加拿大人可以穿越五大湖及远西部的国界从事皮毛交易,使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量资源被掠走。假如这是一份所谓的“民族事业”,那么无论加拿大人或是英国人都没有理由被招纳进来。事实上,“阿斯特曾希望这是一项国际事业,不仅能激发美国的皮毛公司(只有美国公民才能控股的美国企业)的投资,而且成为国际合作的典范,吸引更多的英国甚至俄国的资本”(49)Stephanie LeMenager,"Trading Stories: Washington Irving and the Global West",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Vol.15, No.4(Winter, 2003),pp.683-708.。 欧文关于阿斯特事业的民族性建构与它实际上的跨国性之间显然构成了错位。
面对唾手可得的贸易利润,各国皮毛商都想从中分一杯羹,大大小小的公司活跃在远西部。当欧文声称欧洲商人在这片疆域内进行交易的“非法性”时,文中不少细节却显示欧美争霸发生在非美国土地上。在陆路探险中,亨特的队伍遭到来自他国探险队的阻碍和跟踪,许多重要的贸易区几乎都被“外国人”把控:法国人建立了麦基诺公司作为休伦湖与密歇根湖的主要站点;在靠近密苏里河口的边境地带,法国殖民者、新英格兰商人、偏远山区猎手、印第安人、印白混血儿及水上船工等形形色色的人组成了密苏里河皮毛公司;而哥伦比亚地区的皮毛交易被西北公司操纵;西北太平洋沿岸至密西西比河谷之间的皮毛资源则被哈德逊湾公司占据。在斯蒂芬妮·莱梅纳格(Stephanie LeMenager)看来,远西部贸易中掺杂着许多非理性因素,使商业帝国主义催生出一种野蛮复杂的经济形式,而这种非理性是欧文和许多非知名作家在西部书写中的明显特征(50)Stephanie LeMenager,"Trading Stories",pp.683-708.。
如果说多国合作的企业形式和帝国间的非理性竞争构成了国家主义叙事中的不和谐声调,那么无处不在的“印第安威胁”则直接表明了这片土地的归属权。在《阿斯托里亚》中,无论海上还是陆地远征,探险队途经之处大都是印第安人的栖息地,始终伴随着被“野蛮人”袭击的恐慌。例如在穿越落基山脉地区时,白人随时都面临被克劳族(Crows)和黑脚族(Blackfeet)偷走马匹或嗜杀的危险。欧文写道:“如果他们足够幸运地穿过苏族的区域而没被骚扰,那么前方等待他们的将是另一个更加野蛮好战的部落,是白人的死敌。”(51)Washington Irving, Astoria, Vol. I , 1836, p.139.虽然欧文没有完全丑化印第安人,但他的态度相比二十年前发生了微妙变化。1814年,他在《印第安人的性格特点》中谈到英属殖民地时期印第安人所遭受的不公对待:“他们被唯利是图且常常肆无忌惮的战争夺去了世袭财产;他们的性格遭到心胸狭隘又带有偏见的作家们的诋毁。殖民者常常把他们当作森林里的野兽对待;而作家则竭力为自己的暴行辩护。”(52)此文最早刊发于《大西洋月刊》,后收录进《见闻札记》。Washington Irving, 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New York: A.L.Burt Company, Publishers,1990,p.247.假如欧文早已意识到白人的暴力是导致印第安人“滥杀无辜”的根源,那么为何在《阿斯托里亚》中又对此颇有微词?
不难发现,文中横行的“野蛮人”实际上主要是在皮毛贸易中投靠英国的印第安部落,比如与西北公司建立了往来的苏族提顿人(Sioux Tetons),他们“把美国贸易商装备良好的平底舟视为可攻击的猎物”,欧文称其为“密苏里海盗”,并推测他们的暴行是“受英国商人怂恿”(53)Washington Irving, Astoria, Vol. I , 1836, pp.177-178.。事实上,庞蒂亚克起义(54)英法七年战争后,英国代替了法国在五大湖地区的殖民统治,长期以来与法国结盟的渥太华印第安人不满英国的高压政策,以庞蒂亚克为首的部落酋长发起了对英国殖民者的反抗和袭击,战争从1763年持续至1766年,最终以谈判和妥协结束。之后,英国对印第安人的态度由驱逐和镇压转向笼络和收买,企图通过皮毛贸易来维持北美的政治稳定,并在独立战争中拉拢一些部落参战。即便在战败后,英国依然牢牢控制着大湖区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重要贸易堡垒,而那些与英国长期合作的部落也将美国人视为敌方。与英国不同的是,杰斐逊政府鼓励与印第安人贸易的动机是在西部建立一个农业共和国,通过在印第安人居住区修筑贸易站、提供贷款,诱使他们断开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而进入美国贸易体系,并廉价出让土地来还债,从而兵不血刃地夺占其土地。但这一策略最终未能奏效,美国非但没能以“和平”方式把西部纳入联邦,也没能以“文明”手段同化印第安人。
土地是引起印白种族冲突的根由。到杰克逊时代,工业革命和移民潮加剧了种族主义的仇恨和种族间的对立,人口膨胀刺激着白人对土地更强烈的要求,推动了美国的成长,也催生了基于共同生存空间的国家意识。在争夺领土的过程中,美国的州和白种人口成倍增长,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印第安部落和人口数量的锐减(55)1829年,杰克逊就任总统时,美国人口从19世纪初的大约500万增加到1500万,州的数量也增长到24个,杰克逊退位前又添加了2个州,与之相反,印第安部落的数量却迅速缩减。参见Robert V. Remini, Andrew Jackson and His Indian Wars, New York: Viking Penguin,2001, pp.279.。1830年,杰克逊政府制定出《印第安人迁移法》来掩盖一场清洗运动的实质,将印第安人从原来的土地上驱逐并隔离,五大文明部落被迫踏上“血泪之路”,所建立的短暂繁荣也毁于一旦。相比而言,欧洲殖民者虽然在19世纪之前已经改变了印第安社会的原初状态(56)白人到来美洲之前,印第安人保持着朴素的生态观、土地观和宇宙观,宰杀猎物是根据家庭或部落需求而定,但当他们卷入白人的交易之后,便抛下古老的信仰滥杀动物、使之变成全球市场上的商品;与此同时,对枪支和酒精等欧洲商品的依赖,使印第安人放弃原有的生存技能、与白人达成“合作”关系。过度掠夺造成的生态灾难加重了印第安社会的脆弱性,导致其衰落。参见付成双:《试论毛皮贸易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态影响》,《世界历史》,2006年第3期,第4-11页。,但尚未撬动印第安人的生存根基,且交易者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固的网络,加固了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同盟关系,使皮毛贸易有了一定的外交意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制衡着北美大陆的各种力量(57)Eric Jay Dolin, Fur,Fortune,and Empire,p.31.。 而随着皮毛资源的枯竭,美国的农业边疆不断逼退皮毛边疆,工商业生产占用了大量土地,印第安人生活的自然空间和物质条件被彻底摧毁了。
西部土地的不确定性引发的文化焦虑贯穿在欧文写作的始终,为强调美国人拥有土地的所属权,欧文多次瓦解欧洲商人在美洲从事皮毛交易的所谓“正当性”,并刻意矮化卷入贸易纷争的敌对印第安部落,但又在不经意间展示了与之矛盾的细节。也许正是这种“不经意”暗含他对国家身份认同的迟疑,以及对美国侵蚀印第安人土地的事实在国家叙事中如何被表述的困扰。在皮毛贸易全球化视角的观照下,商人借维护国家利益之名瓜分美洲的资源和财富,利用原住民或将其赶杀殆尽,殖民帝国则操控利益集团来扩张本国势力。这些事实在美国的民族国家话语中虽然被削弱,但并不意味着被湮没,而是作为一种解构中心的力量涌动在作家书写的暗角,抵消着他们建构民族诗学的努力。
四、结语
欧文的“西部浪漫主义”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其西部叙事的主角往往是探险家、富商和官员,通过把帝国冲突作为核心,他将读者引入一个多种文化与政治因素杂糅的空间。19世纪初,美墨战争尚未爆发,淘金者还没有涌向加利福尼亚,铁路时代要在半个世纪后才到来,这一时期的北美西部充满了复杂的帝国欲望,它在地理上被认为是未经开发的“荒蛮地带”,在政治上是欧美列强图谋瓜分的殖民地,这样的西部在文化上是边缘性的,不会自动归化美国。欧文像同时代的浪漫主义作家一样,被围绕在这片区域内外的暴力与冲突所吸引,他将欧美争夺远西部的历史浓缩进一个皮毛贸易故事中,并对美国的殖民扩张进行文化编码。但在疆土界限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当美国以非文明手段对西部土地强取豪夺之时,文学很难表达纯粹符合道义的爱国主义。对美国而言,向西部扩张意味着在远离欧洲的土地上形成一个新的大陆帝国,以传播民主和自由、发展独特的美国文明,这种“例外论”构成了塑造美国国家身份的观念基础,而18世纪末以来的美国国家主义其实已包含了“大陆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思想因素。《阿斯托里亚》中的叙事悖论折射出国家主义话语实践与帝国扩张政治之间的复杂张力,也透露了早期美国国家认同的危机及其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