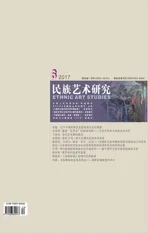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研究
2022-01-14李刚存
宗 蔚,肖 洋,李刚存
世界遗产是自然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我们保留下来的自然景观和独特资源,以及人类以其聪明才智创造出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结晶,是最具价值的自然和人类历史文化遗存。①陈兴中、郑柳青:《论世界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从德国与四川世界遗产业的比较分析谈起》,《西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则是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或个人视为他们文化财富重要构成部分的各种实践、表现、表达、知识、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物品、文物和文化空间。②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Convention for thesafeguarding of the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Paris:UNESCO,October 17,2003.
近年来,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具有前沿性技术特点的数字技术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方式、传播途径。在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进行传播的过程中,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不仅加快了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海外传播速度,而且还为海外受众更好地接受此类信息提供了便捷的 “窗口” 。与此同时,随之而来的数字鸿沟问题也对云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工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在数字化时代来临的当下,如何在有效弥合数字鸿沟的同时,更好地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向海外进行传播便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数字鸿沟形成的机理
早期研究认为,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现象意指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个人、家庭、企业地区之间在获得数据信息和通信技术机会等方面所存在着的差距。①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Divide,Paris:OECD Publications,2001,p.5.在此之后,伴随数字技术的逐渐普及,人们开始意识到:造成数字鸿沟现象产生所涉及的行为体应该扩展至在数字化时代来临的背景下一切受益于数据化技术红利的所有行为体及没有受益于此项技术的所有行为体。②Martin Hilbert, “The End Justifies the Definition:The Manifold Outlooks on the Digital Divide and Their Practical Usefulness for Policy-Making”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Vol.35,No.8,2011,pp.715—736.
综合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是造成数字鸿沟产生的关键性 “症结” 。一是与数字化技术推广和普及相关的基础设施配套的问题。马丁·希尔伯特(Martin Hilbert)所做的研究就曾发现受众接入因特网的带宽不一样容易造成受众之间获取数据信息的不对等。③Martin Hilbert, “The Bad News is that the Digital Access Divide is Here to Stay:Domestically Installed Bandwidths Among172 Countries for 1986—2014”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Vol 40,No.6,2016,pp.567—581.Martin Hilbert,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Inequality as an Incessantly Moving Target:The Redistribu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apacities Between 1986 and 201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64,No.4,pp.821—835.二是受众自身所具备的文化水平、技术技能和数字化素养问题。即身处于数字化时代之下的各类行为主体是否具备操作和使用终端设备的知识,以此来获取所需信息的技能是导致数字鸿沟出现的另一大诱因。④Mun-Cho Kim&Jong-Kil Kim, “Digital Divide:Conceptual Discussions and Prospect” ,in Won KimTok-Wang LingYoon-Joon LeeSeung-Soo Park ed.,The Human Society and the Internet Internet-Related Socio-Economic Issues,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eoul:Springer,2001,pp.78—91.三是地理位置不同的地区(如城市主城区和郊区、农村)在数据信息的接入联通性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别。⑤Gretchen Livingston,Latinos and Digital Technology,2010,Washington,D.C.:Pew Hispanic Center,February 9,2011.此外,年龄差距也成了数字鸿沟现象在21世纪初期较为突出的第四个原因。有研究发现,年龄越大的群体获得数字化信息的比例越低。⑥Elizabeth Vidal, “Digital Literacy Program:Reducing the Digital Gap of the Elderly: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in Mónica Adriana Carreño León,Jesús Andrés Sandoval Bringas,Mario Chacón Rivas and Francisco JavierÁlvarez Rodríguez ed.,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clusive Technologies and Education,Piscataway: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nc,2019,pp.117—120.而且,这一个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同地区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对安全性的担忧、记忆下降、缺乏必要经济条件支持等具体性的原因往往成为老龄群体获得数字化数据信息比例较低的根源性诱因。⑦Thomas N Friemel, “The Digital Divide has Grown Old:Determinants of a Digital Divide Among Seniors” ,New Media&Society,Vol.18,No.2,pp.313—331.最后,经济收入水平差异、意识观念差别等客观因素也是致使数字鸿沟问题在世界各地区均不同程度存在的主要原因。
有研究人员从其问题、现象形成的过程入手,经过研究后发现,关联性程度较高的过程性原因亦是当代社会诱发数字鸿沟问题出现的主要 “幕后推手” ,即 “传播—接受—运用—占有” 是当代社会数字鸿沟问题形成的过程性原因。⑧See Van Dijk,The Deepening Divide:Inequal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2005.海量的数字化信息通过不同类型的网络从一个位置向世界各地进行传播,由于传播过程中普遍会存在数据信息的通达性问题,因此,传播过程其实就是数字鸿沟问题所形成的前端环节。当数字化信息的传播过程完成以后,不同受众接受数字化信息的过程就会随即启动,但是受制于文化传统、受教育程度等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受众群体对于数字信息的接受程度又会存在着量度范围层次上的差异,于是第二阶段性(后端环节)数字鸿沟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总体而言,那些思想意识较为开放、勇于尝试接受前沿信息技术的受众群体,往往能够在接受这类前沿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将其进行内化性的 “运用” 乃至 “占有” 。而那些思想观念保守、缺乏探索精神的受众,不但不会接受这些前沿性的信息技术,而且他们往往还会以各种方式对其进行抵制。所以,后端的数字鸿沟问题形成也就成了必然之事。①See Van Dijk,The Deepening Divide:Inequal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2005.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数字化技术日益 “渗入” 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等多个领域的当下,导致数字鸿沟问题出现和存在的机理是多方面的。具体而言,具有复杂性特质的层面性原因及前后环节有密切联系的过程性原因均是诱发数字鸿沟问题形成的主要机理。
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数字鸿沟形成的原因
在参考数字鸿沟形成机理的基础上,笔者以田野调查、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后发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化的传播过程中出现和形成鸿沟性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数字化弱势群体的存在
数字鸿沟问题形成的一个重要机理就是在已经具备数字信息终端的前提条件下,受众由于自身观念、知识、技能水平的限制,不能将所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数字化信息终端设备向外界进行传播及展示。笔者在实地田野调查中发现,代际之间对于掌握和使用数字化传播终端的差距是造成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播过程中形成鸿沟问题的主要内源性原因。例如,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勐拉乡、广南县坝美镇,能够展示傣族三弦叮琴弹拨、壮族铜鼓舞技艺的实际传承表演者,其平均年龄均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通过在勐拉乡、坝美镇的实地访谈,笔者了解到,上述两地约80%的实际传承人都认为他们的表演应该借助数字传播终端平台更好地向更多的受众进行展示。但令人遗憾的是,实际掌握这些艺术技艺的传承人又基本上属于不会使用诸如抖音、快手等数字化传播终端平台的人群。此外,笔者在调研过程中还发现,年纪在18—35岁之间的青年人群体,虽然大多都能熟练掌握和运用抖音、快手等数字化传播终端平台,但是,他们对于传承好本民族父辈们的艺术技艺却显得不是那么感兴趣。特别是在面对就业、升学等诸多现实问题时,几乎没有当地的青年人会主动地利用他们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数字化传播终端平台的技能来帮助他们的父辈们更好地传承和传播此类民族特色艺术。
于是,实际掌握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传承技能的中老年群体沦为了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的弱势群体,而那些能够熟练掌握、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的青年一代却是 “非遗” 传承的边缘群体。在此状况之下, “非遗” 传承的数字鸿沟不仅不会消弭,而且 “鸿沟的宽度” 会随着实际传播者年龄的继续增大而继续变 “宽” , “鸿沟的深度” 也会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提升和运用场景的加强而继续变 “深”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
近年来,受 “原生态” 思想观念意识的影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及保护工作普遍强调 “原生态性” 保护和 “原生态性” 传播,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播过程中原封不动地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属性及原生性形态。笔者在宜良县匡远镇、石屏县坝心镇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民间的彝族烟盒舞表演队、彝族舞龙表演队因为一味地追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的表演形式,而出现了青年表演者成批退出表演队的现象。据悉,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青年表演者普遍认为,艺术表演应该在遵循传统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融入一些数字网络世界中较为流行的诸如R&B、RAP等时尚性的元素,而在表演队中人数占大多数的中老年表演者却始终坚持认为少数民族艺术文化的展现、传播必须坚持原生性及复古性原则。在受众群体日趋年轻化的当下,由于占表演队总人数较多的中老年表演者始终不肯改变整个队伍的表演风格,因此,越来越多的青年退出表演队伍,而年轻受众不再关注这些表演队的表演也成了一个相应的既成事实。
相同的,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表演团体会以集体出资、或向当地文化宣传主管部门申请经费补助等方式筹资聘请专业化的传媒公司为其拍摄和制作数字宣传材料。但是,这些由传媒公司所拍摄、制作并上传至网络空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由于太过于强调所谓的古朴性 “原生态” 气息,因而在网络空间中并不会引起数字化传播的主力受众——青年群体的问津。从诱发数字鸿沟问题的机理角度来讲,承载着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视频经互联网渠道传播之后,其必然会在 “传播—接受—运用—占有” 环节中的 “接受” 环节遭遇在艺术文化审美中日渐追求时尚和与时俱进的受众的抵制,即形成第二阶段性数字鸿沟现象。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数字化传播技术的融合性程度较低
相较于依靠传统的静态性传播方式而言,数字化技术具有能够从面部表情、声道传感、体态语言表达、可视化成像等多个维度全面综合向外界尽可能地传播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面貌特点。①Marilena Alivizatou-Barakou,Alexandros Kitsikidis,Filareti Tsalakanidou,Kosmas Dimitropoulos,Chantas Giannis,et 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New Technologies: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ultural Preservation&Development” ,in Marinos Ioannides,Nadia Magnenat Thalmann&George Papagiannakis eds.,Mixed Reality and Gamification for Cultural Heritage,Gewerbestrasse: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7,pp.129—158.因此,从国内外在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取得的示范性经验来看,数字化技术的全面介入确实在其传播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方面发挥着事半功倍的作用。前沿性的数字化传播技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之间的紧密结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对外传播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条件。
截至2021年9月15日,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所收录的云南项目共计145项,②数据详情信息参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数据库,http://www.ihchina.cn/project#target1,数据检索时间2021年9月15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01项③数据详情信息参见:中国民族文化中心资源库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据库,http://www.minzunet.cn/eportal/ui?pageId=765195,数据检索时间2021年9月15日。该数据包含了云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47项;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增补名录21项;云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4项;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9项;云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0项;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36项;云南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37项,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扩展名录37项。。在这些已经被确定为国家级、省级的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里,绝大部分属于独具云南少数民族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及开源性情报数据研究法进行分析后发现,数字化科技手段运用比例较低是制约当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展示取得新突破的根本性瓶颈之一。云南省除了在省级层面建设了 “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 (www.ynich.cn)之外,大量分布在地州、县一级具有本地方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没有搭建好专门性的数字化对外传播展示平台。这些分布着大量具有地方性少数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所在地借助数据化技术向外进行传播和展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当地文化及宣传主管部门的官方网站以 “图片+文字” 的简略方式来开展和进行的。此外,受社会大众所喜爱且接受度较高的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数字化的传播平台至今很少出现专门展示和宣传云南基层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专业性账号。
综上所述可知,基于诱发鸿沟性问题的层面性原因来看,宣传文化意识淡薄、地理位置偏僻,是阻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数据化前沿传播技术结合进而在网络空间进行高效传播的又一主要原因。此外,从过程性原因的角度来分析,思想意识陈旧、缺乏开拓意识,亦是造成数字化传播技术很难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互融合的重要因素,继而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程度较低、数字化表达信息载量无法满足海内外受众需求,并最终诱发鸿沟效应扩大化的主要根源性原因之一。
三、消弭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数字鸿沟的策略
作为一个拥有26个民族共居的西南边疆省份,云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绚丽多彩,这不仅是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在 “一带一路” 倡议及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不断深入实施的背景下,云南对外展示文化风貌、促进人文交流的一张靓丽 “名片” 。为了更好地将云南本地特有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成为海内外各界进一步认识中国、了解云南的新 “窗口” ,在数字化传播技术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相互紧密结合的当下,笔者认为,云南可以从以下几个具体方面入手,以尽早消弭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和保护的数字鸿沟问题。
(一)不断提高和增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运用数字技术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能力
从文化传播的过程视角来讲,经过数字化技术处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电子化代码的方式在网络空间领域进行传播。由于此类上载至网络空间平台的电子化代码是以向外界传播和展示所属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信息内涵为目标的,因此,这些经过数字化编码技术处理的信息代码具有反映文化属地特色的自然属性。依据数字鸿沟问题形成的机理可知,所属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数字化编码技术上载至网络空间进行展示、传播的质量往往是形成数字鸿沟问题的开端。所以,在数字化传播技术全面来临的时代,有效地提高和增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运用数字技术传播技术的能力,是从源头减小及消弭其与外界数字鸿沟问题最为有效的方法策略之一。
1.着力建设及完善覆盖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数字化通信网络基础设施
云南目前被列为国家级和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五百余项。在这些被列入国家级、省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有半数以上的项目都来自社会经济欠发达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例如,地处边地的绿春县、金平县的哈尼族同胞在山区村寨表演和传唱表现本民族稻作文化的长诗《浩伙腊伙》时,因受制于数字通信网络上传速率较低的影响,无法通过便捷性的数字编码终端设备如智能手机、数码摄像机等将实时性的表演和传唱现场画面进行展示、传播,因而造成了编码端上传电子化编码信息总量与解码段解码破译电子化编码能力不相对等,即编码信息上传量无法满足破译代码信息实际需求的数字鸿沟问题。因此,通过着力建设及完善高质量的数字化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成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逐步缩小甚至是消弭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所形成数字鸿沟的主要策略。特别是在5G技术已经开始全面推广的当下,尽快地在云南的边疆少数民族集聚区建设相应完善的通信基础设施,不仅有利于这些地区向外更好地展示和宣传其独具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风貌,而且能够从技术层面环节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数字鸿沟问题。
2.着力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的数字化技术运用能力
传承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向外界传播的主体,同时亦是其传播过程中的主要施动者。因此,着力提升传承者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有助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原意性意义进行编码,从源头上提高其编码质量,继而减小因第三方编码造成的编码信息不能准确表达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原生性意义的现象,力求使作为解码者的受众所获原意性解码信息大致上等同于原意性编码。就具体的实施方案而言,建构多方参与的混合培训模式能够在最大限度上使各类资源要素发挥相应作用的同时,逐步提高传承人运用数字化技术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能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地的相关政府部门而言,可以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通过支付公共文化财政专项经费购买服务的方式,向那些资质较好、社会信誉度较高的培训企业购买技术培训课程,以供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承人学习,提高他们的数字化传播能力。从发挥好公益性资源所具有的社会服务职能角度而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地的地方政府亦可通过出台政策性文件的方式,鼓励引导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科研院所及高校志愿者基层服务团等有序地参与到提升少数民族传承人数字化编码传播水平的培训服务工作中。
3.建立健全多样化的数字性传播平台
长期以来,受缺乏传播意识、不掌握数字编码表达技术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向外传播展示的途径、手段主要是依靠政府部门不定期搭建的外宣展示平台来完成的。在数字化传播方面,除了有少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得以在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上进行宣传之外,云南省内其他被列为省级、国家级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是其名称目录在该网站上得以出现。在数字化传播技术日趋普及、受众解码文化信息日益便捷的今天,传播渠道单一的瓶颈问题不仅制约了云南境内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外传播工作,而且还是造成并引发数字鸿沟问题不断扩大的主要问题之一。为了有效破解传播平台单一的问题,笔者认为尽快建立、健全多样化的数字传播平台,是促进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取得突破、消弭数字鸿沟的一项可行方法。在政府层面,除了既有的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需要尽快扩容,以便让更多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会 “搭乘” 数字化传播技术的 “快车” 在海内外传播之外,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需要在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下,尽可能多地与海内外专业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专业化数字网络平台建立相互访问、浏览链接的协议,以便更好地提升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的对外传播力。从传承者参与传播的过程来讲,其在掌握了相关数字化编码传播技能的同时,需要积极适应现在受众群体接收文化信息便捷化、个性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自媒体平台已经成为现今大部分受众者接收编码性文化信息的背景下,云南境内的传承人更是应该抓住抖音、快手、视频号、哔哩哔哩、微博等自媒体数字平台覆盖受众范围广、深得海内外受众喜爱的优势,积极创建和打造高品质的自媒体宣传账号,从而不断地扩大其在海内外受众中的覆盖范围。
(二)转变思想积极顺应当代文化传播需求
在全球受众文化信息品味不断更迭的前提下,其对文化信息所蕴含的时代性气息的需求也在不断地提升。从当下文化传播的实际情况来看,赋予文化内容以更多的时代气息元素是传播行为主体有效缩小乃至消弭其与受众间数字鸿沟的一种有效手段。
数字化技术嵌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过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将那些具有悠久历史且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信息更为生动、更为形象地在更广阔的受众群体中传播和扩散。目前,青年群体在世界各国的数字化传播受众中明显扮演着 “绝对主力” 的角色。而青年群体在欣赏文化方面所共有的一大特征,便是他们喜欢追求文化场景或氛围之中的时尚元素、流行元素。因此,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在数字化 “洪流” 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不断地提高其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及影响力,就必须在继承本地区民族传统文化基本内涵的同时,巧妙且适时地将当今的流行及时尚元素融入传承和传播过程之中,做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前文中笔者所提及的原属于彝族烟盒舞表演队、彝族舞龙表演队的青年人在退出原来的表演队伍后,重新组建了完全由青年人所构成的烟盒表演队、舞龙表演队。他们在进行对外传播展示的过程中,将青年所乐于接受和喜爱的摇滚音乐、R&B音乐及说唱、喊麦元素融入传统的烟盒舞及舞龙表演,不仅在抖音、快手等数字化的自媒体平台上收获了大量的点击量及 “粉丝” ,而且一些原创短视频还被海外传播度极高的照片墙(Instagram)、脸书(Facebook)等自媒体社交网络平台大量转载。基于以上的客观分析及案例分析可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只有在找准受众需求、切实转变思想,并积极打破其刻板印象的前提下,才能够在融入流行时尚元素化解受众群体 “对抗性解码模式” 的同时,有效地消弭横亘在传播者与解码者之间的数字鸿沟。
(三)进一步探索及延展数字化传播技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融合程度
形式单一的数字化传播手段及方式在受众群体不断追求多样化需求的背景下,不但制约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外传播,而且不断诱发数字鸿沟的出现和扩大。有鉴于此,进一步探索及延展数字化传播技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融合程度,不断增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手段,在现如今文化传播手段层出不穷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在进行综合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今后的传播过程中应该结合本身所具有的艺术特质,采取分类式、有针对性的深度融合方法,不断加深及延展数字化传播技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融合程度。
例如,针对红河县的哈尼族多声部民歌、沧源县的佤族木鼓舞、景谷县的傣族章哈等这一类观赏性较强的音乐、舞蹈、曲艺节目,传承表演者完全可以依托数字化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更好地将表演者的肢体动作、语言神态等有关细节突出展示在受众面前,进而让受众能够通过交互式体验的方式更好地享受和品味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文化内涵。又如,针对像澜沧县拉祜族同胞经常哼诵的史诗《根古》、盈江县傈僳族在重要时节必须传唱的《阔时目刮》等这一类极具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其传承人可有效依托数字可视化技术,在将声音、文字等表达本民族独特文化特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性要素向受众进行展示的同时,借助3D影像的有效嵌入,使表演传承者向受众展示此类文学艺术历史背景的同时,更好地帮助受众认识和理解其所要向外界传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层意义。
结 语
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在使得全人类不同族群能够更为快速、便捷地认识和了解彼此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次生性问题。特别是在数字化技术已经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播领域相互高度融合的今天,受制于配套性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不具备数字化编码能力、数字化传播意识欠缺、受众群体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等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向外界进行传播、展示的过程中出现了数字鸿沟不断加剧的问题。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所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总体上具有种类多样、品目齐全的特质。在当今全球化 “浪潮” 不断席卷世界各国从而使得各国文化出现高度同质化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向外进行传播及展示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可以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影响力,而且还能够有效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力。但是,在数字化技术已经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高度融合的当下,客观存在着的数字鸿沟问题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工作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因此,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工作要想取得进步和突破,一方面必须在不断适应社会变革发展、受众需求日益多元化的新形势下,切实地提高传承者运用数字化传播技术的能力、努力消除受众群体中可能会时隐时现的 “对抗性解码模式” ;另一方面,包括传承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内的多个传播行为体要不断深挖数字化技术在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潜力,着力探索缩小及消弭数字鸿沟问题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