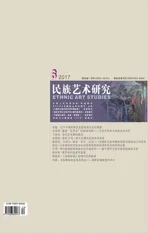文化重构与声景变迁
——以瑶族 “还家愿” 与 “盘王节” 仪式音声为例
2022-01-14赵书峰
赵书峰
近些年来,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领域针对民俗节庆仪式音声景观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民族音乐学关于音声景观的研究主要强调其文化属性、构成要素、音声形态、仪式象征等诸问题的考察。尤其关注到音乐表演文本与文化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音乐的艺术形态与文化表征、文化隐喻之间的指涉关系的思考。关于 “音声景观” 这一概念的思考更多地将音乐艺术形态结构与文化隐喻的勾连关系置于特定的民俗、历史、社会、国家、政治、区域等综合语境中进行立体多维地分析考察,而不是只关注音乐的艺术形态与物理学意义上的声音形态,同时还特别重视民俗仪式音声景观的文化空间立体构成,声音景观或者文化空间中诸多政治、社会与权力关系之间互动关系的思考,或者关注民俗仪式表演场域中的 “场域” “资本” “惯习” 三者互动关系背景下的音乐表演文本的身份变迁与声景重建问题的思考。特别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现代化以及 “非遗” 语境的影响与渗透下,传统乐舞文化的表演语境与音声景观的变迁问题值得民族音乐学界深刻关注。
通过文献梳理看出,《中国音乐》(2020年第1期、第6期)设 “中国少数民族节庆仪式音乐的建构与认同”①《中国音乐》2020年第1期刊登的文章主要有:杨民康《少数民族当代节庆仪式音乐与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以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实践为例》、杨曦帆《建构与认同理论的音乐人类学反思——以嘉绒藏族为例的少数民族节庆仪式与传统音乐发展研究》、赵书峰《传统的延续与身份的再造——瑶族 “盘王节” 音乐文化身份研究》、张应华《地方全球化——黔东南苗族民俗节庆音乐文化的守望与 “发明” 》、魏琳琳《蒙汉杂居区节庆仪式音乐中的地方性与族群认同》。《中国音乐》2020年第6期刊登的文章主要有:胡晓东《族群·区域·国家——彝、哈、傣、苗杂居区节庆仪式音乐中的三重文化认同》、李延红《 “地方制造” 与节庆表演——当下 “侗族大歌” 的地方建构与认同》、路菊芳《彝族诺苏人的现代火把节仪式音乐与国族文化认同》、张林《新宾满族节日音乐文化建构的认同差序特征》、李纬霖《云南与周边国家傣仂赞哈表演前的模式与族性特征研究》、王旭,孙云《佛教供养与礼乐文化传统的双重建构——以五台山南山寺焰口仪式为例的考辨》。专栏,是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界比较集中地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民俗节庆仪式音乐的发展与变迁问题展开的分析与思考,集中刊载了杨民康、杨曦帆、张应华等学者的文章,其中笔者的研究主要针对 “盘王节” 音乐的传统与当代音乐的互文性、 “盘王节” 的 “去民俗化” 问题、 “盘王节” 表演空间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等问题给予的思考。另外,笔者的文章《原生民俗性与舞台审美性—— “云南省第十届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 观后感》①赵书峰:《原生民俗性与舞台审美性—— “云南省第十届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 观后感》,《人民音乐》2019年第1期,第42—45页。,是针对传统音乐的表演语境的变迁问题展开的初步思考。目前,关于瑶族 “盘王节” 研究多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的成果,民族音乐学界甚少关注瑶族 “还家愿” 与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的重建问题的思考。为此,本文选取民俗仪式象征性的瑶族 “还家愿” 与舞蹈审美娱乐特征的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的重构与变迁问题展开初步地分析研究。
一、民俗仪式象征语境中的 “还家愿” 音声景观构成
笔者的博士论文《湖南瑶传道教音乐与梅山文化——以瑶族还家愿与梅山信仰仪式音乐的比较为例》②赵书峰:《湖南瑶传道教音乐与梅山文化——以瑶族还家愿与梅山信仰仪式音乐的比较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针对过山瑶民间自发的以家庭或姓氏为单位的 “还家愿” 仪式音声景观的宗教与音乐属性有比较深入的分析与解读。结合本人对湖南蓝山县汇源瑶族乡 “还家愿” 仪式音乐进行的多年(2008年至2020年)跟踪考察与再研究发现,其仪式音声景观与 “盘王节” 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具有鲜明的瑶传道教仪式音乐的特点,是瑶族传统文化信仰与汉族天师道文化互融后的文化产物。这部分的道教仪式音乐的主要旋律音阶构成多以do、mi、sol和do、re、mi、sol音阶构成为主。伴奏乐器多来自汉族地区,以锣、鼓、镲为主,以及仪式舞蹈中伴随 “请圣” “还愿” 诸仪式环节用的法器铜铃。如湖南《蓝山图志·瑶俗》记载的瑶族 “还家愿” 仪式场景,即: “岁以冬月建醮,曰盘王醮,入坛齐戒,然必先宰一猪供坛前,以猪头心肝肚肺等件,堆列猪背,戒妄动。瑶巫三五成群,摇铃撞钲,诵咒跳舞,咒词甚俚。”③雷飞鹏纂修:《蓝山县图志·礼俗·瑶俗》(卷十四),中国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057页。除了瑶族 “还家愿” 仪式乐舞具有的道教文化属性之外,瑶族 “度戒” “丧葬” 等等民俗仪式中也具有上述典型的宗教特点。同时从过山瑶 “还家愿” 仪式空间的布局(坛场中的神像图)、仪式音声景观特性(仪式乐舞特点)、仪式象征隐喻符号(仪式所指)等内容来看,均属于非常典型的瑶传道教文化。
其二,以祭祀盘王(诵唱《盘王大歌》)(18段、24段、36段)为主的瑶族传统仪式音声景观构建。 “还家愿” 仪式景观的第二部分主要以祭祀瑶族祖先盘王为仪式主题,从仪式诵唱与仪式话语的交流、仪式结构、仪式内容到仪式表征等等内容带有鲜明的封闭性与强烈的瑶族文化认同特征。其中师公与歌娘诵唱的《盘王大歌》从唱词结构、唱词内容、音乐结构、文化隐喻等等都有诸多差异,构成了《盘王大歌》祭祀音声空间的 “对话性表述” (即复调表述)④参见米歇尔·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另外,在祭祀盘王仪式中,不但有诵唱长篇《盘王大歌》(其中还包括 “七任曲” )歌本,而且也有祭祀师公在乐器伴奏下跳长鼓舞祭祀盘王仪式。总之,从仪式内容、诵唱文本结构、仪式音乐与仪式表征等内容分析看出,瑶族 “还家愿” 音声景观具有典型的二部结构特征,即瑶传道教仪式音乐(汉族天师道)与瑶族传统音乐认同的二维特性。如《蓝山图志》(卷十四)记载的瑶族 “还家愿” 仪式音乐,即 “瑶祭槃瓠……用乐……按瑶歌词调不一,其音节,有瑶音,有五朝音,又皆有本音,有唱音,唱声靡曼动人。”⑤雷飞鹏纂修:《蓝山县图志·瑶俗》(卷十四),中国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040页。
二、全球化、现代化与 “非遗” 语境中的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构成
首先,由政府打造的 “盘王节” 活动,其目的主要分为以下方面:其一,祭祀祖先盘王,强化瑶族的族群文化认同,提升瑶族群众的国家、政治与社会认同感;其二,受 “非遗” 活动的影响,借助这种大型民俗节庆活动来保护与传承瑶族传统乐舞文化;其三,通过举办 “盘王节” 活动来打造地方文化名片,为拉动地方旅游文化经济服务;其四,通过举办 “盘王节” 活动借以宣传地方政府的文化政绩。尤其湘南每年举办的瑶族 “盘王节” 暨 “坐歌堂” 仪式活动,通常放在地方政府打造的民俗文化新村,或者由政府修建的安置新村中进行,其目的就是要展示与呈现地方政府的文化政绩。
其次,与民间传统的 “还家愿” 相比,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具有以下特征:其一,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构成属性的多元一体,即主要由盘王祭祀仪式音乐与 “坐歌堂” 仪式、瑶族唢呐展演、传统与现代流行乐舞表演组成。与 “还家愿” 仪式音声具有的典型道教文化属性相比,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则更多呈现出神圣性、世俗性与现代性的三维并置的文化空间特征。因为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是由神圣性的盘王祭祀仪式与世俗性的 “坐歌堂” 竞赛活动(或者瑶族 “哭嫁” 仪式展演与长鼓舞沿街巡演),以及现代流行乐舞为主体的舞台化展演构成。这种立体多元化的音声景观属性特征已经远远超出了瑶族民间 “还家愿” 仪式音声景观独有的道教文化属性特征。其二, “盘王节” 仪式参与者族性的多元化。参与节庆活动的主体除了瑶族(过山瑶、平地瑶、蓝靛瑶等支系),还有参加演出的大部分演员与观众以及部分外地游客,他们也成了 “盘王节” 节庆仪式参与互动的又一主体。通过笔者实地考察得知,在湖南衡阳常宁瑶族乡举办的2019年湘南三市 “盘王节” 的瑶族长鼓舞表演中,有42位小学生参加,其中只有一位学生是瑶族身份,所以与 “还家愿” 仪式参与者的封闭性特征相比, “盘王节” 民俗节庆活动则更鲜明地表达出其仪式参与者族性的多元开放性特征。其三,与 “还家愿” 相比,为了扩大瑶族文化传播效应与打造瑶族地区旅游文化名片,如今的 “盘王节” 仪式音乐展演开始充分运用现代新媒体技术(如微信、网络直播等)打造瑶族民俗节庆活动的社会影响力。比如2019年湘南三市举办的瑶族 “盘王节” 活动中,参与 “坐歌堂” 的歌手们在活动之余还拍摄了快闪《我和我的祖国》,之后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所以与 “还家愿” 仪式音声的封闭性与单一属性相比较,被全球化、现代化重构之后的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则体现出多元开放性的文化特征。
三、 “还家愿” 与 “盘王节” 民俗活动展演中仪式神圣性的衰减
首先,过山瑶以酬神为主的 “还家愿” 仪式具有鲜明的神圣性与程式性特征,即 “还家愿” 仪式需要经历从头年的 “许愿” 到来年的 “还愿” 仪式过程,且具有非常典型的民间自发性、仪式神圣性、仪式文化参与者主体性的综合特征。经过仪式重建之后的大型 “盘王节” 活动,则是以祭祀祖先盘王为主,包括舞台展演、 “坐歌堂” 仪式、商业项目推广、学术研讨等为辅的,在 “还家愿” 基础上的被建构而成的、周期性的,且由政府主导和民间参与的一种大型的现代民俗节庆活动。
其次,由政府打造的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与民间 “还家愿” 相比,其仪式神圣性特征走向衰减。因为别具原生性与民俗性特点的瑶族 “还家愿” 仪式音声景观,从仪式场域(如悬挂道教神像图)、仪式构成、仪式音声、仪式象征隐喻都呈现出多层次立体丰富性特征。尤其神圣性特征贯穿整个仪式场域,虽然在祭祀盘王中有某些比较搞笑、诙谐的仪式表演环节,其实际上是一种娱神活动。如跳长鼓舞环节也是为了祭祀盘王的目的。如《蓝山图志》记载的盘王祭祀仪式中的 “跳长鼓舞” 环节,即嘉庆时 “瑶祭槃瓠……用乐,以木为腰鼓二,长者四尺,短二尺,击鼓鸣铙,吹角,或吹横笛,一人持长鼓,绕身而舞,二人短鼓相向舞。”①雷飞鹏纂修:《蓝山县图志·谭震瑶俗记》(卷十四),中国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041页。而由政府主导打造的 “盘王节” 活动中的仪式音声景观不但呈现出鲜明的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而且也具有仪式音声景观的舞台审美与娱乐性特征。比如 “盘王节” 舞台展演的节目多是与歌颂祖国政策与美好生活的内容有关,甚至盘王大型公祭仪式中的舞蹈也是经过了地方文化馆或者高校专业舞蹈教师精心排练而成的。所以与 “还家愿” 仪式相比,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的神圣性环节渐趋递减,而其娱乐性与政治性属性在逐渐增强。同时也看出,不但是现代节庆仪式音乐具有上述特征,而且中国古老的节庆仪式音乐 “在由民间仪式向官方仪式演变的过程中,种种古老的特征逐渐被抛弃了。”②[法]葛兰言(Marcel Granet):《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四、 “还家愿” 与 “盘王节” 中仪式乐舞与表演语境的变迁
当下,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以及 “非遗” 语境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民俗节庆仪式音声景观特征呈现出民俗仪式象征性与舞台审美娱乐性的二维并置特征。这同时说明传统民俗仪式音乐在民间语境与官方语境的双重维度中其表演语境正在悄然发生变迁。正如有学者认为,语境不是名词性的 “context” ,而是一个建构过程——语境化。这个过程不仅建构了民众生活的情境与世界,也建构了他们即时的身份。③胥志强:《语境方法的解释学向度》,《民俗研究》2015年第5期,第34页。因此从 “还家愿” 到 “盘王节” 活动,前者多是基于神圣性语境中的一种民间祭祀活动,后者则更多地带有舞台审美性质的现代民俗节庆展演。这种表演空间、表演文本、音声景观、仪式象征与文化功能的显著变化,鲜明地彰显出多方文化权力与瑶族 “地方性知识” 、学者、民间艺人互动背景下的,一种带有国家政治与文化认同的音乐话语实践。作为地方传统音乐在多方话语与艺术实践权力的 “共谋” 互动作用下的一种 “媒介化” 的艺术展演,它不但是瑶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创新性表达,而且是操演音乐话语实践背后多种表演权力的博弈语境下的产物。④赵书峰:《传统的延续与身份的再造——瑶族 “盘王节” 音乐文化身份研究》,《中国音乐》2020年第1期,第30页。因此,从 “还家愿” 到 “盘王节” ,实际上经历了从民俗仪式象征性到舞台审美娱乐性仪式音声景观的发展变迁。因为传统的 “还家愿” 仪式场景更强调 “还愿” 仪式的有效性目的,而 “盘王节” 活动不但是一种公众参与的 “公祭盘王” 活动,而且非常重视瑶族传统乐舞文化的集体呈现与舞台审美语境下的文化展演。在整个仪式活动中表演者与观众(游客)的全面参与互动表演也是 “盘王节” 互动中的重要环节,比如集体性地跳 “竹竿舞” ,以及 “坐歌堂” 仪式结束后 “送客” 环节的 “对歌” 场景也是集体互动参与表演的一种音声景观表述。其次, “还家愿” 中跳的长鼓舞主要用在祭祀盘王(或娱神)的仪式中,通常是一人表演或两人对跳的形式,且舞蹈语汇与象征意义与瑶族的族群发展历史、日常生活劳作、宗教祭祀仪式等等密切联系,其伴奏乐器主要以锣、鼓、镲打击乐为主(偶时也会加入唢呐),而 “盘王节” 中的长鼓舞是经过删减改编过的一种集体性舞蹈,且常用创作版《瑶族舞曲》作为伴奏音乐。因此与民俗仪式性较强的 “还家愿” 仪式活动相比, “盘王节” 音声景观更多呈现全球化、地方化、现代化、流行化等多元立体构成特征,这种音声景观属性的变化同时也折射出其乐舞结构与仪式表演语境的变迁。
五、 “还家愿” 民俗祭祀活动的封闭性与 “盘王节” 仪式节庆展演的开放性
首先, “还家愿” 多是瑶人自己参与的一种以祭祀祖先为主的具有封闭性特点的民俗祭祀仪式,而由政府建构而成的大型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是一种带有舞台化性质的节日仪式狂欢。因为 “盘王节” 仪式既有传统的盘王祭祀环节,又有具有世俗性特点的瑶族 “坐歌堂” 竞赛表演,同时还带有现代性与流行性特征的舞台展演(如流行乐舞文化),上述三种音声景观构成了瑶族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的主体,因此从音声特点的象征性来看就是:神圣性—世俗性—表演性特征。尤其湘、粤、桂区域的 “盘王节” 仪式,如今成了地方政府周期性的重要的大型现代民俗活动,这不但是一种民俗节日文化展演,同时也是一种包括瑶族与汉族共同参与的节日狂欢。在整个仪式展演中,从由政府参与的大型盘王祭祀活动到具有传统与现代的舞台展演,以及 “坐歌堂” 仪式展演活动,都是公众集体性参与的一种仪式狂欢活动。整个仪式活动中表演者、观众、游客、仪式主办方(包括地方政府官员等等)的族群身份、文化信仰、社会身份等等边界走向模糊与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成了整个 “盘王节” 仪式狂欢的主体。正如俄国评论家米歇尔·巴赫金认为,在中世纪的狂欢中没有表演者和观赏者之分,说表演者是根本不确切的。狂欢不是供人们驻足观赏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甚至不是供人们表演的;它的参与者们置身其中,根据有效的规则来狂欢;即,他们过着一种狂欢式的生活。在狂欢节中,决定日常生活结构和生活秩序的法规条文以及各种清规戒律等非狂欢式的东西都被抛在了一边:被抛在一边的首先是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恐惧、敬畏、虔诚和礼节——即,由社会等级制度的不平等或人与人之间的其他任何形式的不平等(包括年龄)所带来的一切。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抛在了一边,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特殊的狂欢节的关系:人与人之间自由自在、亲切随意的接触。①[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杨竹山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176页。
其次,瑶族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不全是以祭祀盘王为主的仪式展演,同时带有传统与现代性质的舞台表演,以及呈现瑶族传统民俗特征的街头巡演仪式。比如江华瑶族自治县每年的 “盘王节” 活动中不但有大型的街头婚俗表演(如长鼓舞巡演),而且还有舞台上的过山瑶与平地瑶的 “哭嫁” 仪式展演。因此瑶族祭祀盘王仪式语境的文化变迁与音声景观重建,不但是仪式表演语境的变迁,而且也是其仪式文化象征隐喻的变迁。因为传统的瑶族 “还家愿” 仪式不但具有神圣性的仪式空间,而且仪式参与人全是瑶族(祭祀盘王仪式音声中必须说瑶语,不能说官话),而由政府参与主导构建的带有舞台化展演性质的大型 “盘王节” 活动不但是一种开放性的全民参与(瑶族、汉族等)集体性民俗节庆活动,而且整个仪式音声景观的构成是开放与多元化的。尤其仪式象征隐喻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文化变迁现象,因为虽然是以祭祀盘王为主的活动,但是围绕祭祀仪式分层次、分时间段,甚至并行发展的各种文化展演活动与商业文化推广活动都是 “盘王节” 活动中的亮点,这就是所谓的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的构成从仪式展演、仪式属性、族群参与构成、音声景观的属性等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共存与并行发展的节日仪式特点,同时也隐喻出瑶族民俗节庆仪式音声景观从神圣性的封闭式仪式场域向集体性的仪式狂欢发展。
六、从 “还家愿” 到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的变迁隐喻了瑶族文化参与主体性的转换
(一)仪式音声表述与参与主体性变迁。 “还家愿” 多是以家庭或姓氏为单位的祀神还愿仪式活动,是瑶族祭祀祖先盘王的一种神圣仪式,而且仪式主办与参与者主体均是瑶族人,从仪式构成、仪式音声景观属性、仪式象征隐喻等方面都带有鲜明的瑶族传统文化属性。同时这也是瑶族 “地方性知识” 的一种文化表达,因为操持与共享仪式的主体均是瑶族人,不管是仪式执行者的师公,还是诵唱《盘王大歌》的歌娘均是瑶族。而由政府操持构建的大型 “盘王节” 活动中,其仪式主办者、仪式展演者、参与活动者,甚至仪式审美受众的主体都是多元开放的,尤其 “国家在场” 成了 “盘王节” 仪式音声表述的主体构建者,即 “盘王节” 仪式音声表述的权力与社会关系构成,以及舞台文化展演与互动者的族群身份与文化身份构成是立体多元的,不是完全由过山瑶民间艺人决定,也就是说其仪式音声表述主体性发生了显著的变迁。比如,2020年湘南桂阳 “盘王节” 参加盘王祭祀仪式音乐环节的瑶族民间艺人甚至被替换成当地汉族专业湘剧团的唢呐乐手。这种情况虽然是田野个案,但是它鲜明地呈现出由官方参与建构的 “盘王节” 仪式音乐的参与以及音声表述的主体性正在基于全球化、汉族传统文化等主流文化影响下发生重建现象。
(二)仪式音声表述的文化象征意义的主体性变迁。传统的过山瑶 “还家愿” 仪式文化象征隐喻是对瑶族祖先认同的一种神圣性的仪式音声表述,而政府构建的 “盘王节” 仪式音声表述更多呈现出一种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的文化象征隐喻。民间自发举办的 “还家愿” 音声象征意义不但隐喻了与瑶族传统有关的族群、宗教、语言等多重文化表征,而且具有封闭性特征的过山瑶核心信仰仪式是其族群认同、宗教认同的一个典型载体。基于官方色彩打造的具有复合型音乐表演文本的 “盘王节” 仪式活动,既彰显其鲜明的 “国家在场” 的音声表述特性,同时从仪式的节目程序与表演内容来看又带有文化旅游名片推广作用的应用民族音乐学学术思维。比如2020年11月湘南桂阳瑶族 “盘王节” 活动不仅仅是为了举办每年一届的瑶族传统节日,更多的目的是推广当地的旅游文化景点。又如湘南瑶族 “盘王节” 暨 “坐歌堂” 仪式,不单单是为了传承与发展瑶族传统音乐文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举办瑶族民俗节庆活动来呈现国家城镇化政策给瑶族日常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因为 “坐歌堂” 活动通常会选址在移民新村安置点进行,这些地方大多是政府修建的两层小楼,生活环境和住宿条件都较之前的瑶族民居有较大改善,在此举办活动是为了更好地宣传国家与地方政府民族政策。然而,城镇化进程也给传统文化的生存语境带来诸多问题,即仪式中依附的歌舞乐随生活环境的变迁而渐趋消失,日常的对歌仪式逐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广场舞表演。因为搬迁到移民安置点的瑶民由于其原初的生活语境消失了,伴随的某些日常民俗活动也缺少了举办的场景,造成某些传统仪式乐舞的生存语境逐渐消亡,进而被现代化的自媒体艺术所取代(如瑶族对歌微信群)。最后,从 “还家愿” 到 “盘王节” ,折射出瑶族传统仪式展演(演)到文化展演(观)的主体性变迁。因为原生语境中的过山瑶 “还家愿” 是一种仪式性、程式性特征较强的民俗仪式展演活动,而由政府、民间艺人、瑶族文化学者共同构建而成的 “盘王节” 是一种周期性较强的大型的民俗节庆文化展演活动。前者更强调以家庭或村寨为主参与主体的仪式展演,虽然是仪式展演实际上其 “表演” 成分较少,更多带有神圣性、仪式性、象征性特性,后者则是在祭祀瑶族盘王仪式的基础上融合了舞台审美特点的传统与流行乐舞表演,是一种典型的民俗节庆文化展演。因此从 “还家愿” 到 “盘王节” 的身份变迁与文化重建,预示着瑶族传统民俗仪式与文化展演的主体性的变迁。因为民间语境中的 “还家愿” 是一种封闭性较强的民间仪式,仪式展演与参与互动主体更多是作为局内人的仪式主办者——过山瑶,甚至是其传统信仰中作为一种比较日常的礼俗仪式展演活动,这里主要是 “演” 的因素,因为不管有没有 “观众” ,其仪式是要按程序、定时举办的。因此, “还家愿” 仪式展演更多强调仪式表演的神圣性与仪式象征有效性的目的,而被观看与欣赏并不是其仪式展演的主要目的;而被政府构建的 “盘王节” 活动则是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平台,通过向外界和观众展示瑶族传统与现代乐舞文化,为地方政府推广瑶族传统文化与发展旅游经济以及展示文化政绩提供宣传平台。比如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每年一届的 “盘王节” 活动,其舞台展演与沿街巡游展演成了当地百姓与外地旅游者观看的主体,所以 “盘王节” 民俗活动成了一种被观看、被欣赏的民俗节庆文化展演活动。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米尔顿认为, “文化展演” (Cultural Performance)一词常常被用于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语境中,指当地人在特定场合向外来者以及本地人表演其文化结构中的特别事项,如婚礼、庙会、诗歌、戏剧、舞蹈、音乐剧等。①Milton Singer(eds.),Traditional India:Structure and Change.Philadelphia: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1959,pp.xii-xiii.所以从 “还家愿” 到 “盘王节” 仪式表演语境与身份的重建过程看出,瑶族传统的民俗活动正在经历从 “仪式展演” (演—主体)到 “文化展演” (观—主体)的变迁过程,即瑶族民俗节庆仪式音声景观互动中 “演—观” 主体的变迁,即从局内人的主体性互动参与走向跨族群间的开放性文化共享。
七、 “盘王节” 仪式表演场域族性的重建(置换)
传统的 “还家愿” 仪式表演场域都是在瑶族生活的传统村落或聚集区进行的,而由政府打造的 “盘王节” 仪式甚至发生了表演场域族性的主体性变迁。即,它不完全是在传统的瑶族原始村落中进行,有时候也会在汉族村落中举行展演,这就是瑶族 “盘王节” 仪式表演场域族性与仪式表演空间主体性的置换。或者说就是 “盘王节” 仪式音乐族性构建与仪式表演场域的一种文化互文。因为具有瑶族族性特征的 “盘王节” 仪式音乐被人为放置在具有汉族传统文化特性的村落中进行文化展演,导致这种瑶族传统节日表演场域或者表演空间的主体性置换,实际也是其仪式表演空间的一种文化重建现象。比如2020年11月在湘南郴州桂阳县举办的瑶族 “盘王节” 暨 “坐歌堂” 仪式活动,实际上其表演场地是放在两个汉族村落中进行的,当地政府为了构建其具有瑶族族性特征的仪式表演空间场域,主办方临时修建了盘王祭祀神像与仪式表演广场。甚至 “盘王节” 仪式表演场域的主体性变迁同时包含执仪者身份的人为置换。据笔者2020年12月在湘南江华县某村考察得知,该村 “盘王节” 仪式展演如今发展成为一个被旅游经济 “干预” 下的由地方政府、民间艺人、资本利益等 “共谋” 与拼贴(盘王祭祀、度戒)的现代节日。因为这里的 “盘王节” 仪式展演为了迎合旅游的目的,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拼贴仪式,真正的盘王祭祀仪式与音乐环节成为了一个简单的过场,尤其执仪者是由当地道教协会派出的一位汉族身份的道士来主持整个仪式,其中的 “度戒” 则是运用上刀梯仪式作为吸引游客的一种文化展演。所以从民间传统的 “还家愿” 到由政府参与打造的国家级 “非遗” 项目—— “盘王节” 仪式表演空间与场域族性的转换,不但是其音乐表演文本的重建,而且也包含其音乐表演场域族性主体性的置换。
结 语
“非遗” 语境中的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的重建现象是一种基于瑶族传统的盘王祭祀仪式信仰基础上,受到多方行政权力与音乐话语实践基础上的互为建构。 “盘王节” 是集全球化与地方化、现代化、新媒体艺术、商业与旅游文化开发背景下的一种仪式景观的再造与文化重建产物,尤其是基于瑶族文化传承与保护为目的的地方旅游文化经济的综合推广。换言之, “还家愿” 重视的是过山瑶族群传统民俗仪式文化的传承与接续, “盘王节” 更加关注的是政府参与互动下的一种政治学实践。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的重建现象是在保持与过往的历史连续性的 “传承母体” ( “传承链” ——盘王祭祀仪式)的基础上,作为瑶族师公的传承人在特定的 “非遗” 语境中,受到全球化与现代化以及主流文化(汉族传统)涵化影响下的一种文化再造与重建的产物,而且这种创造与发明是持续不断的。所以从民俗仪式语境中的 “还家愿” 到 “非遗” 语境中的舞台化展演性质的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的构成看出,它鲜明地表征出过山瑶支系民俗仪式音声景观的仪式重建与声景变迁过程。因为民俗语境中的 “还家愿” 仪式呈现与 “非遗” 语境中的 “盘王节” 舞台化展演有较大差异,前者更强调民俗性与仪式象征性,后者更强调舞台性与审美娱乐性。从 “还家愿” 到 “盘王节” ,不但是祭祀瑶族祖先盘王仪式的身份重建,而且也是其音声景观与象征隐喻、文化认同的变迁过程。因为 “非遗” 语境中的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不但是全球化与地方化语境中的流行与现代乐舞的立体呈现,而且也是族群认同、区域认同、国家认同、政治认同背景下的瑶族 “盘王节” 仪式音声景观的多维表达。当前,民间语境中的 “还家愿” 仪式活动逐渐减少,而由政府打造的 “盘王节” 活动每年都会周期性地隆重举办。比如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与湘南三市六县八瑶族乡举办的 “盘王节” 暨 “坐歌堂” 仪式活动,如今成为地方政府每年一次的重要工作。这种在 “非遗” 语境下建构的带有传统性的现代民俗活动,既传承与发展了瑶族传统文化,又促进了地方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为推广政府政绩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宣传平台。同时看出,上述做法也正是迎合了政府提出的 “非遗” 项目产业化或者应用人类学思维,因此从 “还家愿” 到 “盘王节” 仪式音乐的文化身份重建也是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