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不变的“无能为力”
2021-12-11乒乓台
乒乓台
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趴在长毛绒毯上,慢慢抬起的头遮住远景里的臀,蓬松的金发下露出一张无忧无喜的脸,倔强的厚唇抵制笑意。这是性感女神的第三十一个银幕角色,第一次出现在法国新浪潮电影里。有八卦说片头的裸体是导演找裸替完成的,确实,加上标志性的红蓝滤镜、标志性的身体局部问答题,如此突显的并非芭铎的美,而是导演的任性—还有挑衅。
这是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第六部剧情长片:一九六三年的《蔑视》,也是他第一次拥有大成本的跨国制作,换句话说,也是他第一次惨遭资方束缚手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戈达尔的反抗由内到外,后劲强大,时隔五十三年,这部名叫《蔑视》的电影重回大众视野,经典大全景出现在二○一六年戛纳电影节的官方海报上。

《蔑视》中的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
戈达尔既是导演,又是编剧,这部影片改编自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一九五四年出版的第四部长篇小说《鄙视》。莫拉维亚晚年曾说这是他最好的小说之一,既有深刻的感受,又有完全的创造。从二十二岁出版处女作《冷漠的人》开始,莫拉维亚始终精于塑造具有现代性特质的中产阶级男性,他们大都自我意识过剩,经济条件尚可,或者说有不错的赚钱能力,但他们并不能够得到幸福。这些中产阶级及其以上阶层的人物都显示出一种很适宜被归纳到“现代性”的无能为力。然而,那终究是半个世纪前的创作,在无意识呈现的男性视角下,即便是莫拉维亚这样洞悉人性的大作家也难免在刻画女性形象时落入大男子主义的窠臼,因而在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当代读者看来,这个故事并不只是男性因为女性的不可捉摸而苦恼,倒有点像“普信男”自命清高、自毁幸福的反面教材。好在婚姻、两性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得到根本性的改良,所以这个有关忠诚、背叛的故事依然能让人深思:相爱的人为何互相鄙视?妙就妙在戈达尔对莫拉维亚的改编恰恰弱化了这一点,无论是资本的介入还是戈达尔骨子里的新浪潮意识,都让他避开了这个雷区。在莫拉维亚的书中,鄙视的起源被描述成一个缓慢的、背情弃义的过程,小说的某些段落不乏挖苦,甚至愤怒和暴力,影片中,这些负面情绪都不存在了,爱情转变成鄙视的过程既是转瞬即逝的、又是整体性的,没有渐变,也没有层次,而且不可逆转,极富隐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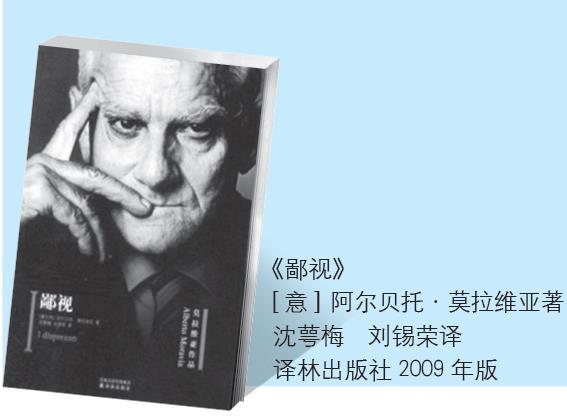
吸引戈達尔的是笼罩在夫妻关系之上的另一层关系:电影和创作。小说的男主角是意大利编剧里卡尔多·莫尔泰尼,理想是创作舞台剧,但为了还房贷,给新婚两年的爱妻埃米丽亚一个家,不得不靠写电影剧本赚钱。制片人巴蒂斯塔请来德国导演赖因戈尔德,要拍一部以奥德赛为主题的大片,还邀请他们一起去卡普里岛写剧本。莫尔泰尼夫妇的感情本来就处于动荡之中,美丽但愤懑的埃米丽亚最终弃他而去,跟巴蒂斯塔一起驱车回罗马,途中因车祸丧生,里卡尔多哀伤不已。这是一个沟通无效的主人公,意大利文坛把里卡尔多视为第一个文学作品中面临危机的知识分子形象,类似的人物将会充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意大利小说和电影,尤其是安东尼奥尼的《奇遇》(1960)和《蚀》(1962),这类人物创作灵感的枯竭总是通过情感破灭来展现的。莫拉维亚也不是无中生有写电影界故事的,他担任过很多部意大利电影的编剧,当过记者,还创办了文学刊物《新主题》,因此和名导皮耶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成了至交。莫拉维亚是在跟进马里奥·卡梅里尼(Mario Camerini)的电影《奥德修斯》的拍摄准备工作之后写出了《鄙视》。
戈达尔当导演前写过影评和剧本,对这个人物想必很能感同身受,对史诗电影要不要拍成好莱坞式的声光电大片这类问题也一定有自己的思考,和安娜·卡丽娜的关系也走上了下坡路……诡异的是,书中的里卡尔多和真实世界里的一位编剧高度相似,他叫维达里亚诺·庞加蒂,是个西西里的小说家,后来为一九五四年罗贝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导演的电影《游览意大利》担任编剧。据说,庞加蒂亲口对莫拉维亚说他在《鄙视》中看到了自己的故事:他也想做戏剧,开始写剧本就是因为妻子想要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但就在他能成功地为她买房的那一天,她把他甩了。莫拉维亚开始写作《鄙视》的时候,正值罗西里尼的这部电影在意大利上映。两个故事的情节也很雷同,讲的都是一对处在情感危机中的夫妇去意大利南部,但罗西里尼的电影里的夫妇最终达成了和解。更诡异的是,《游览意大利》这部电影的海报就出现在戈达尔的《蔑视》中,在那座即将荒废的意大利电影厂的墙上。还有影评家指出,戈达尔这次拍摄奥德赛主题的神话人物时所采用的手法俨如在向罗西里尼致敬:罗西里尼用长时间的全景拍摄那不勒斯美术馆中的古希腊雕像,戈达尔也让雕像长时间地出现在蓝天白云的背景中。
所以,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是“电影”这个主题把戈达尔和莫拉维亚乃至罗西里尼联系在了一起,而非“感情”—无论是鄙视、忠诚、背叛还是深陷在任何历史时期的窠臼中的任何人性元素。莫拉维亚以笔力刺穿了现代男性知识分子的痛处,窥到了细微的深处;而戈达尔从那刺穿的洞口往外看,跨在两性间永恒的裂缝上,将现代化的弊端加以拆解和跳接,将更宏大的矛头指向电影界和文化界。莫拉维亚的文本封闭在里卡尔多的内心,是内向的剖析和倾诉;戈达尔的电影从头到尾充满指涉,满屏隐喻,话不多说,都是言外之意,全留给观众去解读。为此,戈达尔搬出了新浪潮历史上最强大的明星阵容—
最厉害的明星:弗里茨·朗
戈达尔彻底取消了叙事者的视点和内心独白,转而侧重对电影艺术的表态,担纲这个重任的是电影里看似配角的老导演,由弗里茨·朗(Fritz Lang)饰演的弗里茨·朗—但也不能说这位鼎鼎大名的老导演饰演的就是自己,确切地说是化身为理想、经由戈达尔认证的符号化形象,他诠释了电影艺术的精神内核、坦诚而坚忍的创作实践,他是这部电影里唯一得到戈达尔袒护的人物,除了他之外的另外四个人物都是被观察、被评判的对象。
那一年,朗已有三年没拍电影了,一只眼睛已近失明。这位德国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和演员曾在一九二七年导演《大都会》,一九三一年执导《M就是杀手》,堪称影史上的绝对经典。朗在一九三三年逃离了纳粹主义下的德国,因而要在好莱坞找到折中的办法。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好莱坞电影工业兴起,和欧洲电影之间产生了鸿沟,像朗、罗西里尼这样的老导演被好莱坞资本压制着,被逼到无片可拍的困境。
戈达尔是朗的崇拜者。他曾说过,新浪潮导演的前几部作品都是“影迷”拍出来的,所以,他一直很喜欢让他心目中的哲学、政治、诗歌和电影界的杰出人物客串他的电影。比如在处女作《筋疲力尽》中,他让著名的黑帮片导演让-皮埃尔·梅尔维尔(Jean-Pierre Melville)演了一位时髦的小说家,在《狂人皮埃罗》中,男主人公在码头堤坝上遇到了戏剧表演艺术家雷蒙德·德沃斯(Raymond Devos);但这次不一样,朗不是单纯的客串,而是被强烈赋予了精神内蕴,甚至和原著小说中的人物截然不同,毋宁说这是戈达尔在电影中创造的人物。就在拍摄《蔑视》的这一年,吕克·穆莱(Luc Moullet)在《今日导演》系列中论述了朗的成就。碧姬·芭鐸饰演的卡米耶穿着浴袍读的就是这本书。这种明显的指涉是戈达尔的标志性手法之一,但时过境迁,当代观众需要注脚才能领悟个中深意。
在莫拉维亚的小说里,德国导演赖因戈尔德是个年轻人,对于二战后的欧洲思想有着自己的反思(诸如“文明对于所有不开化的人来说,常常意味着贪污腐化”等),还善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史诗中的人物,正是在他解释奥德赛拖延了十年才回到妻子身边的缘由时,害得里卡尔多自行代入,摆脱不了自己被妻子鄙视的困惑和耻辱。在小说中,这个人物的重要性在于:他承担了“史诗—创作—传统的精神世界”和“战后意大利中产知识分子的日常世界”之间的纽带。

电影《蔑视》剧照,左二为弗里茨·朗(Fritz Lang)
戈达尔改变了这一点,完全颠覆了导演和精神世界的关系:朗不仅忠于荷马史诗,更要以尊重古典文本的方式来拍这部电影,他的言谈间会引用但丁、高乃依、荷尔德林和布莱希特。朗不要拍好莱坞大场面的《奥德赛》,也不想拍被精神分析理论修订过的版本。电影开始时,一行人在放映厅里,朗在画面的中央,被身后的放映机的光束照亮,他伸出手,众神的画面就出现了。这种镜头语言宛如在暗示:朗,这位导演,是《奥德赛》的创造者,俨如造物主。众神和凡人的关系就是命运,鄙视的故事也由此上升为悲剧。
电影中的导演和编剧不再是对立关系,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就要做出适当调整,戈达尔就将小说中的意大利制片人改成了美国制片人,通过改变国籍,戈达尔把小说中的两层矛盾(文化的和情感的)扩大到整个电影史,直面新好莱坞与欧洲作者电影间的冲突关系。为此,戈达尔又选了一位恰到好处的明星—
最可怜的明星:杰克·帕兰斯
杰克·帕兰斯(Jack Palance)一九一九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是煤矿工人之子,前职业拳击手,二战期间是飞行员,因在一场飞机火灾中毁容,做了整容术,因而有一张很独特的面孔,似乎总带着笑意,还有点土气。这张脸,加上魁梧的身材,让他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电影中的招牌坏人,或是野蛮人。到了九十年代,他凭借《城市乡巴佬》中的表演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但吸引戈达尔选用他的并非演技,纯粹是形象—在此之前,帕兰斯演出的多半是恶徒、杀手。据说,帕兰斯刚到剧组时曾真心实意地和导演交流,但提出的各种建议都被否决了,后来他只能和布景师闲聊,可怜那个法国人只会十几个英语单词。
在《蔑视》中,他是好莱坞电影的面具化人物,直指戈达尔铁了心要批判的那种坏蛋:来自好莱坞的制片人,还有了不同于小说人物的新名字—普罗科施。他开一辆红色的阿尔法-罗密欧,他的电影品位可谓粗野,在观看半裸女演员在水中扑腾的镜头时露出粗俗的大笑,生气时又像掷铁饼那样粗暴地扔出碟盘,听到“文化”一词就会掏出支票本,签支票时让女助手俯下腰,就像古罗马暴君在奴隶的背上用蜡板写字。他送给编剧一本关于古罗马绘画的书,说是要帮助他的改编工作,但编剧的回应是:“《奥德赛》是用希腊文写的。”任何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极端漫画化的人物,只用英语,不尊重翻译,喜欢用专横的“Yes or no?”来结束句子,没有文化,还是个暴发户式的自大狂。帕兰斯的指涉太过明显,简直没资格被称为“隐喻”,而是明明白白的明喻—俨如一切鄙视的根源和对象—戈达尔这样做实在很任性,简直有点孩子气。
他也没有照搬书里的结尾,索性毫不留情地让美国制片人和女主角一起死于车祸。既然如此改编了,留着他何用?既然他指涉的是独霸强权的美国文化,那么在车祸之后出现的场景是不是就更容易理解了?弗里茨·朗面对纯净的蓝色地中海、开阔的天空,泰然自若地要把《奥德赛》拍完,一切宛如回到电影的原点,不再有干扰。
最容易被忽视的明星:皮科利,以及戈达尔
近似透明的演技让一位好演员在片中显得有点暗淡,他不像艳星那样吸睛,不像老导演那样让人仰望,也不像美国暴发户那样招摇又可笑。但戈达尔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选择了他,在这部电影里的五个人物里,他必须是最稳妥、最靠谱的。他是男主角啊!
一九六三年,米歇尔·皮科利(Michel Piccoli)饰演保罗这个难度很高的角色时已经出演过三十部长片了。戈达尔是在皮埃尔·谢纳尔(Pierre Chenal)的影片《城市大搜捕》(1958)中注意到他的,拍完《蔑视》后,戈达尔还说过:“我选皮科利是因为我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他的角色很难,但他演得很好。没有人注意到他很出色,因为他的角色重在细节。”
改编后的里卡尔多成了保罗,里卡尔多的内心戏只能从保罗的神态、动作、言谈中尽量地渗透出来,但这依然是个无法理解妻子的不安的丈夫,保罗不用太痴情,笨拙些更好。这份笨拙就是皮科利精心塑造的结果,他不断改变说话和姿态的节奏,和芭铎、帕兰斯形成对比,让彼此都有施展空间。这个男主角一点儿也不抢戏。
这和戈达尔的改编是分不开的。制片和导演被改写后,编剧也得到了新的对位:他首先不再是纠缠于夫妻关系的苦恼的丈夫,其次,他对应了史诗中的奥德赛,犹如导演对应了造物主(荷马),制片对应了恶魔(独眼巨人)。对现代的奥德赛来说,家是要还贷,还需要牺牲理想的商品,爱人的忠贞是可疑的,他完全不知道该不该或怎样回到珀涅罗珀的身边;他不仅意志薄弱,缺乏奥德赛的巧舌如簧(甚至里卡尔多的愤怒反驳)和其他生存能力,还总有种歪戴帽子、手指勾着外套的浪荡儿的气质。书中的里卡尔多听赖因戈尔德解释了奥德赛的心理动因后是很不悦的,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和被现代理论解构、重释的史诗英雄一样,都已在现代生活中沦落不堪。电影中的保罗却是有这种意识的,举止的犹疑、拖沓似乎都在暗示这一点,当他在卡普里岛别墅的客厅里成为众人略带嘲笑、冷眼关注的对象时,就连彼此的站位都在暗示他有这份自知之明。
一九六三年对戈达尔来说是个大起大落的年份。前一年拍摄的《卡宾枪手》和《蔑视》的剧组几乎是同一班人马,也都由法国电影人乔治·德·博勒加尔(Georges de Beauregard)和意大利电影人卡洛·庞蒂(Carlo Ponti)联合制片,但前者是戈达尔的第一次巨大失败,也是新浪潮中引人注目的一次滑铁卢:在巴黎首轮放映的两星期里只有两千八百人次观影;后者却有了美国制片人兼发行商约瑟夫·E.莱文(Joseph E. Levine)加盟—他纯粹是被碧姬·芭铎吸引来的。庞蒂是意大利电影界的老牌制片人,拥有莫拉维亚小说的电影改编权。莫拉维亚的小说里的意大利制片人巴蒂斯塔的职业生涯和庞蒂有不少相似之处。庞蒂一九五七年开始在派拉蒙公司的美国制片人生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和博勒加尔联手,致力于革新意大利和法国电影,制作了戈达尔、梅尔维尔、费雷里和罗西里尼的影片,包括戈达尔的《女人就是女人》和《卡宾枪手》。《蔑视》是三国制片人联手,投资金额达到五亿法郎(《筋疲力尽》的成本仅为四千多万)。意大利制片人与美国制片人都想牢牢把控改编和剪辑权,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部由法美两国明星联袂出演的“国际大片”。戈达尔按照小说的叙事主线写了几个不同版本、内容详尽的剧本—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他与制片人的冲突主要在于“性爱场景”,资方坚持认为这是大众商业电影必备的条件。结果,影片为此推迟了数月才完工,直到一九六三年底,戈达尔才同意加拍几个镜头。
不难理解,戈达尔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关于莫拉维亚和庞蒂,IMDB的八卦一栏只提到戈达尔说莫拉维亚的小说是“火车小说”,这句话的出处应该是《电影手册》(1963年8月刊),“莫拉维亚的小说是庸俗、漂亮的车站小说,充斥着古典的过时的感情,尽管场景带着现代性。但是人们就是经常用这样的小说来拍出美好的影片”。IMDB的资讯提供者们也没有引用戈达尔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我读过这本书很久了。我非常喜欢它的主题。既然我要为卡洛·庞蒂拍一部影片,我就向他建议改编《鄙视》,一个章节接一个章节地遵照着拍。他先是答应了,然后又因为害怕而反悔了。我建议他启用金·诺瓦克(Kim Novak)和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但他们拒绝了;他更想用索菲亚·罗兰和马切洛·马斯特罗亚尼,但我不想。我们一直僵持在那里,直到我得知碧姬·芭鐸对这件事感兴趣,愿意和我一起工作。多亏了她,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所有人都很高兴,包括那些美国人,或更确切地说乔·莱文,他为这桩事投资了一部分,庞蒂向他保证影片会‘很商业化。接下去,我们就在意大利自由地拍摄了六周。”
他曾说过自己有个梦想:在好莱坞式的片场里,导演一部美国式的大制作。但在拍完《蔑视》的十五年后,他在蒙特利尔的讲演会上是这样说的:“这是一部我感兴趣的定制影片。这是唯一一次,我能够用大预算拍摄一部伟大的影片。事实上,对影片来说预算很小,因为所有的钱都给了芭铎、弗里茨·朗和杰克·帕兰斯。然后还剩下我一般拍电影要用到的钱的两倍多一点。还剩下二十万美元,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已经很多了,但对一部伟大的影片来说并不算巨额。”

戈达尔(Jean-Luc Godard)
里卡尔多/保罗是创作者,也是现代文明世界里一个普通的计件工人:完成订单并收取酬劳。这样的知识分子在电影/文化生产链中发挥的功能恰恰是《电影手册》学派猛烈攻击的对象。这一次,戈达尔自己也难逃此运,附身于保罗之身:他也是不得不出卖天赋的一个合同工。我们不难发现保罗和戈达尔的相似之处—戈达尔的自我指涉—相当明显:穿着打扮,两人几乎一模一样,尤其是帽子,片中的助理导演也戴了差不多的一顶;再说品位,两人引用的文学、电影片段如出一辙,也都对弗里茨·朗崇敬有加。
戈达尔不仅在角色身上进行自我指涉,还索性客串了一把。他饰演了朗的副手。小说讲述的是写剧本阶段的故事,而电影讲述的是拍摄接近尾声,制片人强令创作团队修改补拍部分镜头时的故事,所以,电影中就需要出现拍摄现场,戈达尔就创造了“朗的第一助理导演”这个角色,亲自出演。一开始他只有声音出现,很快,他的身影就活跃起来,在船上忙碌,还时不时地遮住朗的镜头,继而在拍摄独眼巨人的片段中变得更清晰,最后,他出现在最后一幕中,俨如老导演的代言人,担负着把电影创作进行到底的重任。
赚得最多的明星:碧姬·芭铎
巨额投资的一半,都花在了她身上。我们的文章也将一半篇幅献给她吧。
一九六三年是碧姬·芭铎的翻身之年,甚至可以说是这位性感女星演员生涯的至高点。虽然在她之前,戈达尔至少看中了两位女明星,但最终愿意冒这个风险—在新浪潮名导的影片中饰演女主角—并且没有沦为花瓶的人是她。甚至不是被誉为“新浪潮的标签”的安娜·卡丽娜,那时候,她和戈达尔的婚姻已岌岌可危。
换个角度想,安娜·卡丽娜可能并不适合这个角色,对卡米耶而言,她看上去好像太聪明、太镇定了。根据莫拉维亚的里卡尔多的描述:“她真的并不出众,但不知为什么,她总显得那么美,也许是她那婀娜多姿的、柔软的腰部衬托出了她胯部和胸部的线条;也许是因为她腰直胸挺,仪态庄重;也许是因为她的自信和气度,以及那两条挺直结实的长腿所显示的青春活力。总之,她身上有那种无意流露的、天生的秀美庄重的气质,所以才本能地显得更为神秘和难以捉摸。”更重要的是,埃米丽亚应该是缺乏知性美的,“我没有能跟一个与我志同道合、兴趣爱好相同又能理解我的女人结婚,却娶了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素养的普通打字员,她身上有着她所属阶层的一切偏见和奢望,只是因为她貌美我才娶了她。若是跟前一类女人结婚,我就可以应付贫困潦倒的拮据生活,在一间书房或一间配有家具的房间里凑合,豪情满怀地期盼着能在戏剧创作上获得成就;可是跟后一类女人结了婚,我就不得不设法弄到她梦寐以求的房子。我绝望地想道,也许我必须以永远放弃文学创作这一远大的抱负作为代价。”细究起来,在埃米丽亚鄙视里卡尔多之前—更早之前乃至之后—他始终都在鄙视她粗鄙的出身。她只有“美”是值得投资的,比如房子和婚姻。这种男性态度在当今语境下无异于一只大靶子,但凡有点女性意识的读者都能批判男主角在物化女性。更糟糕的是,这是一个男性知识分子的自我剖白,过于清醒,过于坦白,因而更让人深思。他彻头彻尾地相信自己真诚地爱着妻子,对此深信不疑,甚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如何伤害了妻子。他无法相信妻子不再爱自己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自己让她坐制片人的跑车、答应制片人的邀请,但事实上,鄙视的肇端并不需要他的批准、解释或配合,只需妻子本人的感知即可成立。鄙视链永远存在,不仅在两性间,还在资本与创作之间。

电影《蔑视》海报,1963
戈达尔用电影主题置换了情感主题后,完全放弃了男女关系的这一条线,根本没有兴趣去讨论莫拉维亚在小说中细密描摹的那种心理状态。埃米丽亚就摇身一变,变成了卡米耶。卡米耶会让人想到他电影中的别的女主吗?那是当然—《筋疲力尽》的女主角帕特里夏有一段经典的台词,阐释她和通缉犯相处、帮他逃亡又向警方告发他的逻辑:我和你在一起不是因为爱你,而是要做出判断,既然我对你不好,说明最终是不爱你的。这个过程充满矛盾,但颠覆了女性被动处于男性追猎、凝视下的刻板形象。在戈达尔的电影里充斥了这种现代男女关系,充满了动荡、不可靠。我们应该承认,戈达尔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反罗曼蒂克的,他的电影里的性不是两情相悦,不是情色交易,也不是性解放……说起来,帕特里夏还有一段黑色幽默的对话讽刺了电影界、时尚文化界的潜规则。当男主问她是不是一直在做电影?她回答:“哦,没有,这得和太多人睡觉。”男主又建议她去当摄影模特,她又回答:“哦,这不行!这得和所有人睡觉。”从帕特里夏到埃米丽亚/卡米耶,她们都分明意识到了这个男权世界里司空见惯的性剥削,鄙视正是来自于这种本能的警惕。虽然埃米丽亚没什么文化,但她非常清楚,丈夫把事业不得志归咎于自己,潜意识里确实有可能放任制片人贪慕自己,假如因为她不喜欢这样而拒绝这份剧本的差事,他早晚會怪罪她。这种认知不需要“文化”,不过是现代男女之间很基础的博弈本能。
戈达尔在剧本中是这样描绘卡米耶的—
卡米耶非常漂亮。她有点像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绘画中的夏娃。她的头发必须是褐色的,或者深棕色,像卡门那样。她总体上是严肃、认真、矜持的,有时候谦逊,带点孩子气的天真的冲动。电影并不应该满足于隐喻,但它知道卡米耶应该被再现为一朵简单的巨大花朵,长着合在一起的阴郁的花瓣,在它们中间,在这宁静而清晰的总体之中,一片浅色而鲜活的小花瓣以其攻击性而发起反抗。……大部分时间如风平浪静的海,甚至心不在焉,卡米耶会突然发怒,紧张而又无法解释地一阵阵诉说着。我们在影片中不断思考卡米耶在想什么,当她放弃被动麻木的境地时,她主动出击,这种行动也总是无法预期和无法解释的,就像一辆沿着直线行驶的汽车,突然离开路面撞毁在一棵树上。这是激起影片中三四次真正高潮的原因,同时也构成了首要动力元素。和她的丈夫相反,后者总是在一系列复杂的理性思考之后才采取行动;卡米耶凭冲动行事,一种生命冲动,就像是一棵需要水才能存活的植物,而不是依靠心理。卡米耶和保罗之间的冲突,是由于她是纯粹植物性的存在,而保罗是动物性的存在。
碧姬·芭铎刚好可以展现卡米耶的这种反罗曼蒂克的存在、主动的出击。
她一出场就是主动发问。问题非常戈达尔,因为类似的问题在《筋疲力尽》中就有过了。在红色、蓝色的滤镜下,卡米耶趴在床上,第一时间就用美臀锁定了观众—这部电影的观众远远、远远不止两千八百人次了。她把自己拆分成很多个局部,一个一个地问丈夫是否喜欢:“你在镜子中能看到我的脚吗?你喜欢吗?脚踝呢?膝盖?屁股?胸部?乳房和乳头?肩膀?手臂?脸?全部吗?嘴?眼睛?鼻子?耳朵?”在得到肯定回答后,她用越来越严肃的语气说道:“那么,你爱我的全部!”而保罗的语调更加强烈、更加低沉:“是的,我全部地、温柔地、悲剧性地爱着你。”众所周知,这段开头是后来应资方要求补的,戈达尔一不做二不休,不仅贡献了本片中最近距离的写真照,还尽可能地贴上了自己的电影语言标签。
戈达尔仔细研究了莫拉维亚的文本,原著共有二十三个章节,时间轴长及数月,由两段同样长度的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在罗马,持续了九个月,包括新婚两年的回忆,充满了主人公的推论、揣测和心理剖白。第二部分在卡普里岛,持续三天两夜,多了一些幻想色彩,以及富有精神性的对白。戈达尔根据电影拍摄的需求,首先浓缩了人物,仅保留了五人,但颠覆了两人的国籍和文化属性;其次精选了地点:意大利电影城里的走道、普罗科施的古罗马别墅、卡普里岛的别墅、加油站、事故发生时的高速公路,几乎全是貌似废墟的处所;还压缩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就在两天内,第一天在罗马,第二天在卡普里岛。但是,在拍摄保罗和卡米耶在家里对峙时,现场发生了美妙的化学反应,出来了一段日后被奉为经典的将近半小时的室内戏。因而,电影的最终形态有三个部分:经典电影之死(约29分钟),夫妻关系之死(约34分钟),在神的凝视下的悲剧命运(约26分钟)。
虽然碧姬·芭铎在三个部分中都有引人注目的存在感,但让观众(或至少是影评家们)看到她从性感女星转变为演员的段落主要就是那段室内戏。剧情大致符合原著中夫妻吵架的段落,演员的动线覆盖了客厅、卧室和浴室,大家都注意到了芭铎懒洋洋的、不疾不徐的说话节奏,她不需要丈夫的注视就能对镜更换形象,形成自足的存在感。比如,点着烟的她坐在马桶盖上,反问追问她的保罗:“也许是我在思考一些事情,这让你吃惊了吗?”又比如,她躺在浴缸里读一段弗里茨·朗对电影的观点。诸如此类的表现让卡米耶脱胎于埃米丽亚,又生发自戈达尔的电影观念,最终稳固地驻扎在碧姬·芭铎的肉身上。
为什么说这生发于戈达尔呢?戈达尔已在《筋疲力尽》《狂人皮埃罗》中拍过类似的长时间的室内戏,男女主人公在极狭小的卧室、浴室里不断交换位置、动作、事件、对白。这是最能体现戈达尔场面调度的空间,也是芭铎能够自如演绎自我的时段。他让她在金发上戴上黑色假发,穿蓝色海军上衣,穿有淡绿色花朵的连衣裙,穿黄色浴袍,用红色的浴巾……这是一种让性感女星的身体变得更引人注目的策略,也是戈达尔输出海量隐喻的战术。但戈达尔发现了这个卡米耶的自我存在感,她没有笑容、自然而然噘起的饱满双唇似乎特别适宜传达鄙视、漠视、冷眼和嘲讽的情绪。不需要五官卖力地表演,她就可以演好卡米耶。当保罗说她和粗话不搭时,她用低沉沙哑的嗓音、没有起伏地念出一连串粗话,能指和所指产生剧烈的分裂,粗话好像突然变成了悲剧里的台词。相比而言,小说里的埃米丽亚似乎自始至终都是里卡尔多眼里的局部式的女人,晦暗不明,而芭铎的卡米耶格外鲜明、立体,彻底脱离了原著的男性心理分析叙述局限。
戈达尔还用蒙太奇的手法让卡米耶的主动性更明显。书中,里卡尔多在卡普里岛上目睹了制片人对妻子求好,吻了她的手臂,还把衣裙从她肩头撕扯下来,但里卡尔多只是在黑暗的阳台上站着看,全程无所作为。后来,埃米丽亚告诉他,她知道他在看。电影中,保罗在长长的别墅台阶上往上走,走到了平台,从那个角度往下看,看到制片人和卡米耶双双侧坐在窗沿上,她好像先往上看了看,再回过头去刻意地亲吻了美国制片人。这两种“看”,顺序不同,意义大不一样:卡米耶显然比埃米丽亚更敢挑衅丈夫—那个她已因鄙视而不再爱的男人。
更进一步说,戈达尔的卡米耶是被设定为神一样的女人,对位珀涅罗珀,是被欲望争夺的对象,是“被爱”的原型人物,是悲剧命运的主人公,也是女性主义者重述经典时绕不过去的一个形象—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珀涅罗珀记》中是如何颠覆这个形象的!所以,在半小时的室内戏中,保罗和卡米耶轮流泡澡后,包裹浴巾的方式俨如古希腊、古罗马人,让浴袍垂下自然的褶皱,这让他们在现代风格的小公寓里对位了戈达尔用以象征纯粹电影理念的古典精神—在这个谱系里,卡米耶和朗是同一阵营的,都安然从属自然的秩序,不受现代文明的恶劣影响。
让我们退回到《蔑视》的开场镜头:大全景,画面当中的路上铺着轨道,轨道车上坐着摄影师,持着一台笨重的摄影机,他的身边站着录音师,举着高高的收音杆,對准女演员,然后镜头移动,轨道车慢慢地朝观众推进。画外音开始念诵主创人员名单。戈达尔通过这样的方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我在把整个影片的生产机制呈现给你们看。等到摄影机走到镜头前面,大约切到中景的时候,摄影师突然把那台摄影机的镜头调转九十度,对准了观众,也就是另一个镜头所代表的观众的视角。第四面墙被打破了,影片这才算正式开始。惯常的电影,或者说好莱坞的主流电影总是在强调电影的幻觉性,让观众沉浸在电影里,最好什么都相信。和小说《鄙视》沉浸式的独白小说截然不同的是,《蔑视》从一开始就强调了电影本身的存在,这些明星的出演并不是要模拟逼真的现实故事,而是一起投身于电影的魅力,拍出一部让人有所思考、有所批判、有所感受的艺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