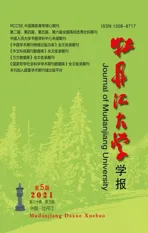亚裔美国女性的创伤体验与自我追寻
——以《中国娃娃》为例
2021-12-05丰芸
丰 芸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外语系,广东 广州 510303)
一、引言
继《雪花与秘密的扇子》《恋爱中的牡丹》《上海女孩》《乔伊的梦想》这几部纽约时报畅销书之后,当代著名华裔美国作家邝丽莎在她的又一力作《中国娃娃》(China Dolls, 2014) 中延续了女性情谊的书写。《中国娃娃》讲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亚裔美国歌舞俱乐部表演者的生活,小说中的三位女主人公都曾有过难以言说的创伤体验:格蕾丝聪明乖巧,却自幼遭受父亲的家暴;海伦在逃亡途中惨遭侵华日军的欺凌,而在抵美后又深受唐人街父权社会的禁锢;露比只身离家,在美国隐藏自己的日裔身份,珍珠港事件后,她和其他无罪的日裔美国人一样,被遣送至沙漠中的集中营拘禁长达14个月。三位 “中国娃娃” 身陷双重边缘境地,艰难地生活在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面对创伤记忆,她们饱受折磨,在重建与他人和世界的联系中,通过见证与倾听的交流方式完成了创伤叙事,逐渐走出创伤领域。
二、《排华法案》的历史伤痛
小说中的第一位 “中国娃娃” 格蕾丝生长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城,她天资聪颖,颇有舞蹈天赋,幼年便荣获舞蹈冠军。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她说着地道的英语,接受全盘西化的教育,希望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电影明星梦。然而,聪明伶俐的格蕾丝并不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相反,她长期遭受父亲的家暴。这一事实是她难以启齿的伤痛,对于多年来父亲的谩骂和暴打,母亲的不作为,除了默默忍受,格蕾丝甚至陷入了自我检讨,而这一切与父母设法隐藏的身世秘密有着莫大关联。
格蕾丝的父亲出生在美国,他自小跟随其父在矿区做工,是一个在美国社会底层辛苦挣扎了一辈子的华人男子。1882年《排华法案》颁布之后,美国国会开始明确禁止华人进入美国,这使得华人社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以至于产生了畸形的华人 “单身汉社会” 。彼时格蕾丝的父亲正启程回中国娶妻,经人介绍与格蕾丝的母亲相识,她身世凄惨,五岁被卖到美国,十二岁流落妓院,所幸后来得到唐纳蒂娜·卡梅伦①的营救,得以从良,嫁做人妇。格蕾丝的母亲在临盆之际被医院拒之门外,理由是他们拒绝为华人接生,在路边生下女儿后,夫妻俩决心离开旧金山,来到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定居,希望开始新生活。事实上,不管他们怎样努力融入美国社会,依然无法改变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身份。格蕾丝从小在学校遭受排挤,白人同学从未停止对她的嘲笑和讥讽,小小的她未曾气馁,仍然梦想有一天能成为电影明星。邝丽莎以其细腻的女性视角呈现出格蕾丝一家的创伤之痛,巧妙地批判了美国种族歧视与排斥造成的华人悲惨命运和屈辱历史; 揭露了美国华裔祖辈所经历的历史创伤及其引起的集体心理创伤。
1882年的《排华法案》是美国移民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成功 “将排华行为推向了顶峰” 。这项法案 “是由美国最高权力机关——国会,通过实行的。它带有强烈的歧视性色彩,在美国移民史上影响深远” 。[1]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在美国只是一个笑柄,他经营一家洗衣店来维持生计,从事的是白人所不齿的 “女人干的活儿” 。他对妻子早年的卖身经历耿耿于怀,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令他羞愤不堪,自己的无能和妻子的失贞彻底地摧毁了这个男人的自尊,他常年对妻女施暴,借以发泄心中的怨气。
正如蒲若茜所说: “不仅是在美国主流文学和大众文化中,在屡屡获得大奖的华裔美国女作家汤亭亭、谭恩美等人的小说文本中,华裔父亲形象要么是‘缺席’,要么是‘沉默’或‘失声’的……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裔父亲在美国土地上被去势、被‘女性化’的生活现实。”[2]十七岁那年,在父亲置之死地的一番毒打之后,格蕾丝终于忍无可忍,痛下决心离家出走。那晚,母亲第一次向她讲述了自己的苦难身世,母亲非但没有阻止她,反而鼓励她逃去旧金山,勇敢开启新生活,并把多年辛苦积攒的积蓄悉数交给女儿。在日后的艰难岁月里,母亲的勇气给予了她极大的力量,成为了她的精神支柱。
长年累月的受虐不仅使格蕾丝遍体鳞伤,遭受父亲毒打的记忆仿佛挥之不去的梦魇,给她成年后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阴影。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在她的著作《沉默的经验》(Unclaimed Experience, 1996)中首次提出了 “创伤” 的定义,她认为 “创伤” 是指某些人 “对某一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 ,并且 “人们对灾难事件的反应通常会推迟出现,并反复出现幻觉,无法控制。”[3]即使逃离了父亲的桎梏,格蕾丝时常从噩梦中惊醒,大汗淋漓,久久难以平复。她无法原谅父亲, “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怜悯父亲,但那改变不了多年来那间房里所发生的一切。父亲带给我的一切伤痛:肋骨、手指和脊椎的疼痛、僵硬感会永远留存在我的身体里。一旦当我感到身受威胁,我内心的恐惧感愈加深刻。”[4]289
六年后当她重返故里,提心吊胆回到家中,却发现父亲离世,母亲终于向她坦白了隐藏多年的秘密。她从来不知道那个专横、暴戾的父亲也有温情、柔软的一面:在她离家后,父亲一直在默默关注着女儿,他搜集了格蕾丝每一次演出的海报,将它们拼贴起来,制作成剪贴簿。因为她是父亲的骄傲,是父亲所有的希望,正如母亲所说: “你爸爸确信小镇上的每个人都知道你离开了这儿,实现了梦想。”[4]285尽管格蕾丝永远都不会理解父亲——他的生活、他的选择和他的耻辱,她无法忘记过去,但她可以选择如何面对未来:在和母亲的沟通交流中,她慢慢放下对母亲的怨恨。当代创伤研究的先驱朱迪丝·刘易斯·赫尔曼认为, “理解心理创伤始于重新发现历史” 。[5]当母亲向她讲述了过去的一切,格蕾丝终于明白父母也是种族主义的牺牲品,他们饱尝了美国华裔祖辈所经历的历史创伤及其引起的集体心理创伤。伊·安·卡普兰教授坚信,文学叙事是转化并愈合创伤的有效途径, “创伤的痛楚如果呈开放式,那么苦痛可以通过艺术转化而愈合”[6]。一味地逃避和隐忍并不能化解格蕾丝心中的伤痛,只有直面创伤,积极地对话交流,她才能慢慢地打开心结。在母亲的往事追忆中二人的情感关系得到了修复,这样的沟通叙事对于格蕾丝的创伤复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日军侵华的梦魇
小说中的第二位 “中国娃娃” 海伦是典型的唐人街女孩,她出生于传统的父权制家庭,父亲是一名成功商人,不但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对家族事务更是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在这个大家族里,海伦被动地接受男尊女卑 “这个事实” ,家庭地位低下。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她深信 “妇道人家应当守身如玉”[4]29“女子无才便是德”[4]32。哥哥们可以上大学,而她不能抛头露面,只能在家学做饭、女红。十六岁那年,海伦在父亲的安排下回中国与苏州富商之子订婚,她听从父母之命,十八岁时回国完婚。婚姻生活和谐美满,海伦颇有经商头脑,她在丈夫的鼓励下参与到其事业中,二人琴瑟和鸣。可惜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的爆发打乱了她宁静的生活,她在战火中失去了丈夫和儿子。
死里逃生的海伦在美国领事馆的协助下回到了美国,唐人街并不是她的避风港,除了哥哥门罗,家人们排斥她,不给她丝毫的安慰和温暖。她只能把伤痛深埋在心里,麻木度日,逆来顺受。后来她借由父亲的关系在唐人街的电话交换中心上班,这份差事安稳、乏味,她无法忍受这种一眼望到底的牢笼般的生活,每天 “听其他女同事在接电话的间隙谈论要给丈夫做什么晚饭,孩子多聪明,维持收支平衡多么艰难。”[4]17
然而,格蕾丝和露比的出现将她从灰暗的守寡生活中解放出来,她慢慢敞开心扉,在两位亚裔姐妹的教导下学习跳舞,同她们一起去 “紫禁城” 工作,开始与外部世界重新建立联系。这份工作使她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她对人生有了新的期待,在好姐妹的支持下女性意识逐渐被唤醒,用实际行动奋力挣脱父权制的枷锁。著名创伤理论专家和治疗专家德瑞·劳和朱迪斯·赫尔曼都认为,创伤不能独自面对,只有 “在关系中” 才有康复的可能。因此,帮助幸存者与他人和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对于创伤幸存者的复原至关重要。
模糊的血肉终会结痂,肉体的伤痛可以愈合,但创伤记忆好比肉中刺,它深埋于心中,午夜梦回时仍会隐隐作痛。海伦无法消除对日军的仇恨和对战争的恐惧,胸口的伤疤也时刻提醒着她间接害死了儿子的事实。长期的隐忍为日后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一旦触发了创伤的原始场景,个体就会唤起创伤记忆,从而频繁地受到幻觉或梦境的侵扰。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唤醒了海伦的创伤记忆,她声泪俱下,向格蕾丝和露比倾吐内心深处的伤痛。在这次的创伤叙述中,她表达了对侵华日军的深恶痛绝,对于自己的创伤经历依然有所保留。格蕾丝和露比由此得知:日军侵华战争期间,海伦亲眼目睹了日军烧杀掳掠、惨无人道的暴行,看着丈夫和所有亲人被杀,她历尽浩劫得以幸存。重回美国后,她被视作家中尴尬的存在。海伦长期被家人忽视,在父亲眼中,她只是个一文不值的女儿。父亲的 “厌女症” 给海伦带来了极大的自卑感,正是因为她的出世,父亲生育八子的希望落空了。她不仅是个女儿,还是个寡妇,父亲多年的轻视让她明白她就是家族的耻辱。
“创伤性历史事件的强迫性闯入带来的痛苦使人难以忘怀,走出创伤并不是指完全地忘却或是创伤完整地愈合,而是指对创伤的认识和自我身份和主体意识的修复与形成。”[7]多年之后,当格蕾丝、海伦和露比三人之间再次出现争执,海伦才将日军侵华的创伤经历和盘托出。当年她和丈夫育有一子,家破人亡之后,海伦独自带着幼子逃亡却没能躲过一劫,三个月大的儿子被刺刀穿透了胸膛,海伦在被轮奸之后坚强地活了下来。听到这里,格蕾丝率先把手放在海伦的肩上, “你太勇敢了,海伦” “你所经受的一切,换做是我,我认为我没法活下去”[4]356。露比看见海伦胸前的伤疤,不禁为她心疼。创伤的讲述意味着他人的参与,在海伦的创伤叙事中,格蕾丝和露比作为聆听者也是创伤事件重要的参与者和拥有者。通过倾听,她们也部分地经历了创伤。师彦灵认为, “倾听者在倾听的过程中可以帮助幸存者将创伤事件重新外化、对创伤经历进行重新评价,帮助幸存者对自己做出公正阐释,重建正面的自我观念。”[8]在两位好姐妹的倾听和见证下,海伦勇敢地克服了自身的耻辱感,将自己的创伤经历表达出来,只有直面撕心裂肺的创伤记忆,她才能一点点解开心结,从而走上创伤治愈之路。她意识到自己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她的不幸经历并不是人生中的污点,她更不应该如父亲所说,带着耻辱和自责等死,作为一个独立女性,她应该为自己而活,也值得拥有新生。犹如浴火重生的凤凰,她终将展翅高飞,飞出唐人街的牢笼。多年之后,海伦因其出色的商业头脑成为了地产大亨,凭借个人努力开创了一番新天地。
四、珍珠港事件的身份危机
最后一位登场的 “中国娃娃” 则是来自夏威夷的日本人露比,她美艳动人、精明世故。通过改名伪装成中国人,露比隐藏了自己真正的族裔身份,她不愿做传统的日本女性,反对男尊女卑的日本文化,试图挣脱父辈的束缚。于是她背离父母,来到唐人街的 “紫禁城” 歌舞俱乐部,结识了一同来试演舞女的格蕾丝和海伦。意外落选之后,迫于生活压力,她甚至去做人体艺术模特。她坚持自己的美国人身份,希望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
小说中的 “紫禁城” 俱乐部弥漫着浓厚的东方气息,在此供职的亚裔歌舞表演者才华横溢,辛勤工作,试图以自身的努力打破在白人眼中的刻板印象。豪放不羁的露比更是因一档露骨的表演节目迎来事业的巅峰,成为 “紫禁城” 的顶梁柱。在这里,亚裔美国女性为绝大多数白人观众表演,她们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美国主流社会在思想观念上和实际行动中的歧视和排挤。她们是土生土长的亚裔美国人,努力打拼维持生计,她们热爱舞台,在表演中获得自由和乐趣。但无论她们怎样竭力融入美国社会,她们始终是白人眼中的异乡人——扮演着固定的 “异国情调的东方” 女性角色。这也印证了亚裔妇女学者周颜玲的观点,她认为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亚裔妇女的模式化看法和亚裔社会中的父权制的家庭结构仍然是当代亚裔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根源。[9]
在这部小说中,邝丽莎运用以小见大的手法,通过对露比一家的命运刻画,有力地将日裔美国人的困境戏剧化地呈现出来。露比有两个哥哥,其中一个在珍珠港事件中被一架美军飞机击中,当场身亡。她的父母涉嫌通敌卖国,被关押在一个戒备森严的特别集中营。她的另一个哥哥被船运到天使岛,在那里被拍照、按手印,检查是否患有传染性疾病。接着,他被关押在犹他州的托佩兹集中营。邝丽莎在她的另一部小说《上海女孩》中阐述了珍珠和梅两姐妹在天使岛的经历,这是一个犹如监狱一般的拘留所, “四周有铁丝网围着,有荷枪的警卫看守,住在木屋的中国人,每天只有一次放出到围墙内的空地散步。”[10]在这座 “永恒之岛” 中, “时间慢得让人感觉如同在阴间一样” , “每件事都是规定好的。外面对何时吃饭,吃什么东西,何时开灯关灯,何时睡觉起床都毫无选择的余地”[11]。除了糟糕的居住环境和难以下咽的食物,她们还要随时接受长达数小时的非人的审讯和盘查。这样的种族歧视虐待和长期的稽留关押无疑给亚裔移民造成了永久的集体心理创伤。
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露比遭受了一连串的家庭变故。同时,美国政府公开宣称要驱逐所有日本人。露比表面上故作镇定,实际上害怕自己的日裔身份被拆穿,终日活在恐慌之中。作为幸存者,她成功隐瞒自己的身份长达14个月,后因海伦的背叛,露比的真实身份被揭发,从此她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的电影角色被人取代,男友发现她的真实身份后愤然离开。她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接受数日的连续审问,之后被送往犹他州的托佩兹集中营。恶劣的居住环境和非人的待遇让她几近崩溃, “这个地方如此荒凉,我们的家庭支离破碎,我的生活毁于一旦”[4]221。
在集中营的艰难生活中,她并没有颓废,而是苦中作乐,坚强地撑了下来。邝丽莎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将个人遭遇与民族命运交织在一起,在族裔创伤书写的同时,露比坚毅、顽强的女性形象也跃然纸上。一方面她坚持和海伦书信交流,在描述集中营的凄惨遭遇时和好友分享内心的感受,以此获得鼓舞和支持,在积极沟通中进行创伤疗治。另一方面,她慢慢融入这个集体,在日常生活中恢复了和族裔群体的联系。 “不到十分钟,我看到的日本人可能比我这辈子见到的还要多。”[4]219更令人欣喜的是,她在集中营意外地和哥哥重逢,兄妹俩在短暂的相聚中聊天、散步,又在午饭时遇到了叔叔一家。在这特殊的时间和场合,一家人的团聚显得格外珍贵,露比也因此获得了些许的慰藉。
在亲历了集中营生活之后, “中国娃娃” 露比坦然接受了自己的日裔身份,开始欣赏母亲所崇尚的日本文化,她完成了身份创伤的自我治愈。邝丽莎借助这个鲜活的女性角色,向我们展现了认同自身的文化之根对于自我身份建构的重要性。族裔群体的情感维系和好友的倾听与见证都是帮助露比摆脱心理创伤、建构自我身份的重要前提,正是这种深埋于文化传统中的同胞之爱、手足之情帮助露比治愈了文化夹缝中的心理创伤,使她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身份建构。
《中国娃娃》以文学叙事的形式再现了亚裔个体和种族的创伤记忆。在故事叙述中,邝丽莎把个人心理创伤和集体心理创伤结合起来,在回顾个人经历的同时也重新构建了族裔历史。通过给予三位女主人公自我言说的机会,邝丽莎为我们展示了叙事的力量。 “正是对自身创伤记忆的叙述,使得那些被压抑进潜意识里的创伤体验重新浮现,她们能够在痛处哀痛,以此释放那些影响着自己当下生命的过往感受,重新获得生命的自由。”[12]107
五、结语
《中国娃娃》重构了亚裔女性在美国真实的生活现状,从多维度呈现了亚裔群体遭受的心理创伤,同时也致力于思考亚裔群体重生和创伤疗治的可能。从《中国娃娃》中格蕾丝、海伦和露比的人生际遇,我们不仅看到了亚裔女性在异乡谋生的悲哀与艰难,还有父权制、种族主义俯视下保持独立主体性的不易。邝丽莎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三位敢做敢为的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寄予了她对亚裔美国女性双重边缘处境下生存状态的关怀,以及她对亚裔美国女性实现种族与性别双重平等的美好愿景。在她笔下,身处美国的三位 “中国娃娃” 恢复了与他人和世界的联系,逐渐打破沉默,正视创伤体验,在创伤叙事中完成了对自我和他人的创伤疗愈,构建起和谐而完善的自我,从而走向新生。
注释:
①唐纳蒂娜·卡梅伦被称为 “唐人街上的愤怒天使” (the angry angel of Chinatown),一生营救、庇护了华人妇女约3000人,并教会她们英文和生活技能,帮助她们在美国成家,自己却终身未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