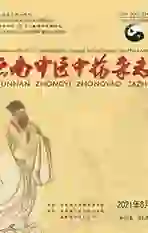基于疡科心得集外科三焦辨证的理论探讨及临证发挥
2021-08-09黄南车朝敏邹纯燕张艳菊李梦琪邓洋张成丹欧阳晓勇
黄南 车朝敏 邹纯燕 张艳菊 李梦琪 邓洋 张成丹 欧阳晓勇
摘要:清代高秉钧著《疡科心得集》,取源《黄帝内经》,旁达温病,创“外科三焦辨证”,首倡“外科三焦辨证”理论和“按部求因”的辨证方法,对中医外科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通过跟随导师欧阳晓勇教授临证,在上部者,除风温、风热外需察虚火;在中部者,除气郁、火郁外需审湿郁;在下部者,除湿火、湿热外需辨寒湿,导师动态的运用“外科三焦辨证”理论,重视病机在上、中、下三部的演变及传化,对“外科三焦辨证”多有发挥,临证常获良效。
关键词:《疡科心得集》;外科三焦辨证;按部求因;理论探讨;临证发挥
中图分类号:R24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21)06-0034-03
“外科三焦辨证”出自“心得派”代表人物、清代医家高秉钧所著《疡科心得集》,其“按部求因”的辨证方法对外科疾病,尤其在皮肤病辨治中起到纲举目张的指导作用。笔者跟随导师欧阳晓勇教授临证,拟从该理论的内涵、对外科临证的指导作用及其在皮肤病治疗等方面进行探讨,在传承应用该理论方面有所发挥。
1 “外科三焦辨证”理论内涵
高秉钧[1](下称高氏)在其著《疡科心得集》例言中指出:“盖以疡科之证,在上部者,俱属风温风热,风性上行故也;在下部者,俱属湿火湿热,水性下趋故也;在中部者,多属气郁火郁,以气火俱发于中也。”这是他根据多年临证经验,对头颈、胸胁、下肢不同部位的疮疡的发病原因进行了分类,创造性地提出“外科三焦辨证”理论,是方便后学者的精辟总结。
《灵枢·百病始生》曰:“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黄帝内经》的理论是高氏提出“外科三焦辨证”的理论源泉和科学依据。风性轻扬,湿性重浊;怒伤肝,喜伤心,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肝失疏泄,气机升降不利则郁,气有余便是火。“外科三焦辨证”取源内经,引入温病时邪伤人的理论,如高氏在该书“申明外疡实从内出论”中提到:“夫风温客热,首先犯肺,化火循经,上逆入络,结聚咽喉,肿如蚕峨,故名喉蛾”。
“外科三焦辨证”是高氏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高氏熟读《黄帝内经》,旁达温病,深明内科,擅于外科,临证强调“外疡實从内出”、“虽曰外科,实从内治”[2]。上部头面风热、颈项痰毒、托腮、口糜生疮等疾,常治以疏风清热之法,方用牛蒡解肌汤、升麻葛根汤、导赤散等;中部疮毒结于胸乳、乳癖、乳痈等疾,常治以清气化火之法,方选柴胡清肝汤、疏肝导滞汤等;下部臁疮、漏蹄、肝胆湿热致小便赤涩等疾,常治以清热利湿之法,方用龙胆泻肝汤、萆薢渗湿汤等。
2 “外科三焦辨证”在外科临证中的指导作用
笔者研读文献发现,对高氏学术思想进行探讨研究者颇多,但将其运用于临床的报道者较少,谌癸酉等[3]、张庚扬等[4]曾将其运用于外科疾患辨治。高氏在《疡科心得集》中提到:“其间即有互变,十证不过一二。集内所论,颇已详括,余证悉可参悟而得,毋俟再为拈示也。”“夫外疡之发也,不外乎阴阳、寒热、表里、虚实、气血、标本,与内证异流而同源也。”提示后学:“外科三焦辨证”中会有些不遵循此规律的证候,但可借鉴此理论参悟施治;其次,外科疾病实发于内,在辨证上与内科同源。欧阳晓勇教授在临证时常将该理论灵活运用于皮肤病的辨治中,并有所发挥。“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他认为无论头面、胸胁还是下肢疮疡都应该先辨别阴阳、虚实,注意常证中的“变证、异证”,随证治之;不能刻板的把三部疾患均归为风温风热、气郁火郁、湿火湿热,“外科三焦辨证”以八纲、气血、标本为基础,临证可灵活变通。现就欧阳晓勇教授运用“外科三焦辨证”理论辨治头面部、胸胁、下肢的皮肤病及对该理论的运用发挥做以下探讨。
2.1 头颈部疾病 《素问·太阴阳明论》曰:“伤于风者,上先受之。”风为阳邪,性轻扬,易袭阳位,上部为阳位,且火性炎上,故头面部多为风温风热侵袭致病,如:痤疮、面部皮炎、头面部湿疹等疾病,症见发热重恶寒轻,面红目赤,口干思冷饮,皮疹红艳,舌红,苔薄黄,脉浮数等,病势较迅猛,病性属实。欧阳晓勇根据上部多为风温风热特点,常治以清热凉血祛风之法,方用荆芩汤加减,由荆芥、黄芩、生地、赤芍、牡丹皮、紫草组成,方以清热凉血为主,佐以祛风,取“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意。
2.2 胸胁部疾病 中部者,内含五脏六腑,为人体气化之所,气机升降出入枢纽所在。“喜怒不节则伤脏”,七情五志亏极皆可导致脏腑功能失调,气机失畅,如《素问·举痛论》言:“余知百病皆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5]气机失畅与皮肤疾患的发生有直接联系,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言:“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朱丹溪言:“气有余便是火。”气机失畅久可化火,因此,气郁火郁是中部疮疡病的常见病因。如:发于胸胁部的带状疱疹、银屑病、湿疹等疾病;症见胸闷、胸胁不适、呕逆、腹满、皮损红艳、大便干结、小便黄赤、舌红或红降、苔黄、脉弦数等,病势较迅猛,病性属实。欧阳晓勇教授常以柴胡类方、化斑汤、白虎类方加减治之,气火两清。
2.3 下肢部疾病 《素问·太阴阳明论》曰:“伤于湿者,下先受之。”“清湿则伤下”,湿为阴邪,易袭阴位。下为阴位,湿性趋下、黏滞,易与热邪相合,故下部多湿火、湿热致患,如:下肢丹毒、慢性溃疡、下肢静脉曲张、湿疹等疾病,症见身热不扬、脘腹痞闷、纳呆、肢体困重、患处肿胀流滋、或漫肿如绵、或腐烂破溃,大便黏腻、小便黄或不利、口干不思饮,舌红,苔黄腻,脉弦滑或滑数等。病势缠绵,病性属实。欧阳晓勇教授常以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复兴教授自拟龙胆汤治之,清热利湿。龙胆汤[5]为《医方集解》载龙胆泻肝汤化裁而来,由龙胆草、车前子、通草、黄芩、苦参、土茯苓组成,去肝胆经引使柴胡,去辛温、滋腻之当归、生地,防利湿太过去泽泻,苦参易栀子,清热燥湿,经刘老化裁后的龙胆汤不专为清肝胆湿热而设,能清一切湿热,应用范围更广,疗效更捷。
3 “外科三焦辨证”应用发挥
高氏强调:“凡治痈肿,先辨虚实阴阳”;经言:“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一切疾病都有阴阳两面,因此临证时不可拘泥于“外科三焦辨证”,而是师其经旨,以阴阳虚实為本,结合风邪、火邪易伤人上部,中部乃气升降出入的场所、亦是运化水湿的通道,水性趋下。因此上部亦有虚火致病,中部也有湿郁之机,下部可有寒湿为患,笔者认为高氏的“外科三焦辨证”理论旨在为后学者诊治外科疾病示法,其字外之义,需后学者参悟而得。
3.1 临证多参悟,可得“三焦”机 高氏治疗头面部疮疡常用辛凉疏散之剂,如:牛蒡解肌汤;治疗胸胁部疮疡常用散火解郁之品,如逍遥散;治疗下肢疮疡常用化湿清热之剂,如:萆薢渗湿汤[6],但这不能完全涵盖契合三部疮疡病的表现和辨治。
欧阳晓勇教授认为头面部疮疡若症见恶寒重而发热轻或不发热,面青目黯,口干或口干反思热饮,或口中和,皮疹色暗,舌青、舌淡,苔薄白或水滑,脉沉细或细数,此病性属虚,乃虚火或阳虚寒凝所致,虚火之证方用潜阳封髓丹,以潜阳降火,阳虚寒凝方选阳和汤、当归四逆汤之类。中部五脏六腑化水谷精微,布散津液,若中部疮疡症见胸闷、腹满、皮损色暗伴有渗出、纳差、大便黏、舌红、苔白厚腻、脉滑等,此为湿郁所致,治以运脾化湿之法,常用平胃散、三仁汤等。下肢部疮疡若症见恶寒不怕热、无汗、口中和,患处色淡、久不愈合,小便清长,舌淡,苔白或水滑,为阳虚寒凝之证,清热利湿之法不中与之,欧阳晓勇常用麻黄细辛附子汤、阳和汤、茯苓四逆汤等扶阳温阳之剂扶阳抑阴,以破阴霾。
张庚扬[4]教授也指出“外科三焦辨证”虽然对辨治外科疾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仍需以阴阳、脏腑辨证为本,欧阳晓勇教授不拘泥于高氏的“外科三焦辨证”,取其临床象思维:在上部者,察其虚火;在中部者,审其湿郁;在下部者,辨其寒湿,动态的察析邪气在部位之间的演变与传化,对疮疡病的发病过程及时把控,趋利避害,随证治之。
3.2 利湿后当清其热,审疮疡进退,定部位病因 基于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叶天士“湿去热孤”的治疗思想,欧阳晓勇教授认为治疗因湿热引起的疮疡,清热利湿为首要治法,方药以祛湿为主,湿去则热亦去;热过之处,其阴必伤,火性炎上,湿去后余热升腾,故利湿后当清其热以收功;在临证中,湿疹患者全身泛发皮疹,经治疗后下肢皮疹逐渐消退,上部皮疹仍存或还在发展,根据在上部者,属风温风热,亦有虚火等特点,此时常以清热为治法。欧阳晓勇的“利湿后当清其热”、“审疮疡进退,定部位病因”等观点扩大了“外科三焦辨证”内涵,是对“外科三焦辨证”临床应用的发挥。
3.3 验案撷英 患者,郑某,男,65岁,2020年6月11日初诊。主 诉:头面、四肢、躯干皮疹伴瘙痒半年,加重20 d。患者于半年前无明显诱因头面、四肢、躯干出现红斑、丘疹伴瘙痒,遂至“云南某医院”就诊,诊断为“湿疹”,予口服中药及外用药物治疗,症状缓解不明显,后皮疹逐渐增多,左下肢皮疹加重伴渗出,肿胀明显,为求进一步治疗来本科门诊就诊,以“湿疹”收入院。入院症见:头面、四肢、躯干红斑、丘疹,部分皮疹浸润肥厚,左小腿肿胀,皮损融合成大片,可见糜烂、渗出、结痂,尤以前胸、头面、左小腿为重,伴瘙痒,对称分布,压之褪色;无发热恶寒,无口干口苦,无胸闷心慌,纳食可,眠差易醒,仅能入睡3~4 h,尿赤,大便畅。舌红,苔黄腻,脉弦滑。诊断:湿疮。辨证:湿热内蕴证。方药:龙胆草10 g,黄芩15 g,苦参15 g,川木通10 g,土茯苓50 g,车前子30 g,青蒿30 g,连翘30 g,秦艽30 g,徐长卿15 g,五加皮15 g,乌梢蛇15 g。2剂,内服,2次/日。外治:院内紫连膏4盒,外搽,2次/日,火针1次/日。嘱患者忌食辛香、辛辣、腥臭刺激等,避风寒,慎起居。
2020年6月15日查房:经上述治疗,患者下肢皮疹、左小腿肿胀消退明显,瘙痒缓解,左小腿已无明显糜烂、渗出,局部结痂,黄腻苔消退,背部有少量新发皮疹,无发热恶寒,无口干口苦,无胸闷心慌,纳食可,眠差易醒,大便干结,小便调,舌红,苔薄黄,脉弦数。患者下肢皮疹有所消退,瘙痒减轻,黄腻苔消退,但上身仍有皮疹,患者大便干结,脉弦数,湿邪渐退,余热升腾,治以清热凉血、祛风止痒,更方为荆芩汤加减:荆芥15 g,黄芩15 g,生地黄30 g,牡丹皮15 g,赤芍30 g,紫草30 g,大黄10 g,千里光15 g,五加皮15 g,徐长卿15 g,乌梢蛇15 g,全蝎5 g。服法同前。外治:继予院内紫连膏外搽。
2020年6月18日查房:经治疗,患者皮疹消退,无明显瘙痒,遂予出院,院外继服上方5剂巩固治疗。
4 体会
高氏“外科三焦辨证”取源《黄帝内经》,以八纲、气血为本,旁达温病,重视时邪伤人,“按部求因”,对外科疮疡疾病的辨治有指导意义;后学者不可拘泥于简单的部位辨证,应重视取其象思维,随证治之,与八纲、气血、脏腑辨证相结合,察析邪气在人体三部的转归,精确施治,临证可取得较好的效果,以此扩大“外科三焦辨证”的内涵和应用。
参考文献:
[1]清·高秉钧.疡科心得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15.
[2]贾忠武.从《疡科心得集》分析高秉钧的学术思想[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8,33(9):3849-3851.
[3]谌癸酉,梁宏涛,王若琳,等.《疡科心得集》对脓症认识及和营法运用的探讨[J],2020,41(6):786-789.
[4]李云平,矫浩然,马晓辉.张庚扬教授“外科三焦辨证”发挥[J].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32(3):132-134.
[5]欧阳晓勇.刘复兴——当代中医皮肤科临床家丛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5:34-35.
[6]范新六,赵唯贤.《疡科心得集》 “外科三焦辨证” 学术思想探讨[J].四川中医,2008,26(12):53-54.
(收稿日期:2021-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