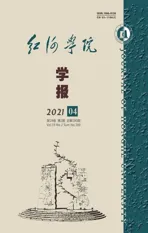变迁与凝聚:大理洱海流域水信仰与传说及其社会功能
2021-04-11吴宇航李富伦
吴宇航,李富伦
(1.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 541001;2.云南大学文学院,昆明 650091)
本主,意为本境之主,是大理地区各村的保护神,亦是大理白族的民族神。在大理,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白族居住,并都有一个本主神。这些本主神,来源丰富,各司其职,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在众多的本主神中,与水利有关的本主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大理地区现存的文献资料、碑刻、壁画、塑像进行考察且分析后不难发现,大理白族与水利有关的本主信仰与本主传说在发展中既有变迁,也有整合,明清时期经历变迁和整合后渐趋稳定。“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1],社会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同时,社会意识能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影响着社会的变迁与整合。这些水信仰与水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理的地方社会、文化风貌和民众的精神生活,并作为一种强大的信仰力量影响着当地民众,推动着地方社会的稳定和大理白族水利共同体的形成。因此,对大理白族水信仰与水传说的研究既有历史价值又具现实意义。
一 明清时期洱海流域水信仰与水传说的变迁
“社会的变迁会推动民间信仰、观念的变迁,同时,民间信仰对社会变迁具有极强的适应性。”[2]因此,民间信仰、观念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历史的发展过程。
洱海流域水信仰的变迁,一方面是从鱼螺崇拜到龙王信仰的变迁,体现了大理白族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从自然物崇拜到人格化神的信仰,是本主信仰建立和发展的过程。水传说的变迁经历了注重治水到注重分水的过程,这是大理白族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其核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究其原因,与大理白族农业的发展和农业化、水利化的发展密不可分。
(一)水信仰的变迁:从鱼螺崇拜到龙王信仰
一般认为,“白族的本主信仰起源于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等多种原始宗教观念。”[3]大理白族原始居民主要居住在苍洱地区,由于原始农耕和渔猎活动及对自然环境的极大依赖,日月、雨雪、云雾、河湖等都是其主要崇拜对象。洱海地区白族先民以渔猎经济为主,在洱海地区原始居民自然力量崇拜的意识中,众多的自然物被先民加以崇拜,大到山川河流,小到草木石头动物都可能被奉为神灵。因此,水信仰的变迁与大理白族先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从鱼螺崇拜到龙王信仰的变迁。
1.鱼螺崇拜的变迁及边缘化。基于“大理地区本主信仰具有的功利性和实用性的特点”[4],洱海湖畔白族最初的本主信仰对象应取材于与他们先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物。“从洱海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陶器上刻有的颇似鱼网形状的符号来推测,网罟形符号可能是以捕鱼捞虾为主要生活来源之一的生产方式的一种表现,也可能是后期以鱼或螺为图腾的氏族的一种标志”。[5]故而,金鱼与海螺最初可能是白族先民日常食物。如今巍山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细奴逻是彝族祖先,与白族祖先罗刹交战。因罗刹王一天吃3对人眼睛,细奴逻请观音来制服罗刹。观音请罗刹吃面条,面条变成了绳索拴住罗刹后,把他拴在大石头内。后来祖先罗刹白族不吃人的眼睛,改吃螺蛳了。”[6]
张锡禄,通过对史料和白族沿袭下来习俗的研究分析,认为金鱼和海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当作崇拜对象,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孑遗。[7]
唐《南诏中兴图传》中也描绘有西洱河金鱼、金螺的情景。其中有一洱海图,画面作两蛇相交之状,中有鱼和螺蛳各一,洱海周围有河相通,各有题记。图上端另有小字题记六行:“西洱河者,西河如耳,即大海之耳也。河神有金螺、金鱼也。金鱼白头,头上有轮爰,毒蛇绕鱼之,居之左右,分为二河也。”[8][10]426在此明确指出:金螺和金鱼是洱海的海神。由此可见,南诏时期洱海周围的居民西洱河蛮(即白蛮)是崇拜鱼和海螺,并把它们作为神物来描绘。
喜洲河涘城下面有座洱海海神祠——金圭寺,寺内有尊石头浮雕的六手神像,神像前面一只手托着绕着线的鱼,胸前挂着一只海螺,号曰“归源寺镇圀灵天神”。虽没有标明年代,但从里面的唐武则天时流行的“圀”字来看,疑是建造于南诏大理国或稍后些时代。
北元宣光六年(1375年)的《重建阳派兴宝寺续置常住记》载:“梵贝铃螺,祝赞国家康泰,虽干戈扰攘之际,诸郡寺院摧毁过半,而兹寺赖侯(高实)之笃信得以安全。”[9]由此可知,唐元时金鱼和海螺已从最初的崇拜对象逐渐成为宗教法器或本主神装饰。至明清时,随着龙王信仰达到兴盛,鱼螺崇拜逐渐被边缘化。
大理白族甲马纸大约产生于明清时期,按照如今流传的版本来看,金鱼和海螺的形象已不多见,人格化水神的形象则较多,主要包括龙王、龙本主、洱海海神等,现今金鱼和海螺的形象多出现在地方庙会的中。
2.龙王信仰的出现及兴盛。大理白族对龙王的信仰源于何时,到今仍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有学者认为龙王信仰中包含着诸多原始宗教的因素,龙是白族图腾。徐嘉瑞从文化交流与延续的角度说:“九隆神话中之龙,乃夏民族之徽帜,亦羌族之图腾”。[10]30并明确提出龙既是华夏图腾,也是白族图腾,大理白族与中原华夏龙文化是一个整体。赵橹则认为“龙不是白族图腾”[11]2,一方面肯定“龙”意识在大理白族地区普遍而深入,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根源;另一方面,认为大理白族龙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白族原始文化中只有“水神”崇拜的意识,白族龙文化和龙信仰是积极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它自始至终都以传统的‘水神’意识与外来的龙文化相互交流。”[11]4此说不无道理。大理白族龙信仰应当有其独特的发展脉络,是白族先民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主动融合外来龙文化所形成的。
唐南诏时,大理白族龙信仰受印度教和佛教的影响较大,天龙八部中的龙,其实并非中国古代所信仰的龙,而是一种长身无角无足有剧毒、单头或者多头的眼镜蛇神,此时的龙与后来大理信奉的龙王无论从外形还是宗教内涵都相去甚远。
宋大理国《张胜温画卷》中(见图1),龙王作为护法神出现,仍是多头眼镜蛇神的形象,不过已专司兴云降雨,在承继了唐南诏时龙神的基础上开始了本土化的转变,如在《张胜温画卷》中出现的白难陀龙王后来成为了大理市下关大展屯村、荷花村、阳平村等八村的本主。而龙王作为白族信仰,并当地广泛信仰则是在明清时期。

图1 《张胜温画卷》中的“龙王”
明清时期,大理白族对龙王信仰非常兴盛。龙分善恶,与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相关,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李元阳撰并书的《大观堂修造记》中记载当地父老曰:“吾郡古泽国也,蛟龙是患,没人田庐。昔有异人令多所建塔,水患用弭。今千有余年,塔圮什七,而水患荐至。”[12]666-667同时,在明清时,龙王信仰对象及范围不断扩大,其中包括生前为当地民众开沟修渠、挖井筑坝、治理水患、乐善好施的普通人,甚至投水自尽的著名官员将领,这些事皆与“水”关系密切,因此包含着英雄崇拜与祖先崇拜的诸多因素。明正德二年(1507年)年赵仪撰文的《重修龙王庙记》中说:“粤稽,龙王姓李,起自大唐。将军领命南巡,至此而终,遂□□贞感,而威灵主庙。享祀与古者句龙后稷之类,有功于世而人祀之者,一道也。”[12]567-569由此可知,本主神崇拜由自然之神向人物之神过渡,同时龙王作为水信仰对象的代表,宗教内涵更加丰富,崇拜对象更加广泛。
概言之,第一,大理白族水信仰首先经历了从鱼螺崇拜到龙王信仰的过程,既是大理白族农业发展的反映,也是龙文化本土化发展的结果。第二,水信仰对象从自然物崇拜到人格化神的发展过程,是本主信仰建立和发展的过程。第三,则是鱼螺崇拜退居次要地位,龙王信仰居于主导地位。喜州一带海舌上有个村叫“河矣城”,村中有座洱河神祠,建于明清时期,其中供奉的是“九隆圣母”“洱河灵帝”。洱河灵帝帝位右侧立一神人,头戴状元帽,帽上有条鱼,称之为“鱼神”,其上悬一匾额书“金鱼现身”四字。帝位左侧立一神人,双手捧一托盘,内盛一个大“吐庆”即海螺,当地白族称其为海螺之神。其上悬一匾额书“玉螺现彩”四字。可见,大理白族水信仰在“人格化”变迁的过程中金鱼、海螺的崇拜退居次要地位,“洱河灵帝”(即龙王)的信仰地位提升,取代鱼神、螺神而成为主神。
(二)水传说的变迁:从治水传说为主到分水传说为主
大理白族地区流传着大量的水传说,这些传说大多形成于明清前后,有的已被收集汇编成册,存于《大理丛书·本主篇上卷》《大理海东风物志续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白族卷》等中,有的至今被当地口耳相传。这些丰富的水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理白族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总体来看经历了从治水传说到分水传说的变迁。这些水传说以人与自然为核心,从最初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到逐渐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同时伴随着人们对水资源与水利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过程。在变迁过程中,水的地位不断被提高。
1.治水:唐宋及其以前水传说的核心。从现存的文献史料和相关传说来看,大量治水传说出现在唐宋及其以前,到元明时,治水传说已明显趋于对水的来源、水利建设的描写。大理市处于坝区,关于这一地貌的形成,龙怯村有一传说:“相传大理原为泽国,洱海出口被黑龙所阻。黄龙为了拯救人民、降低洱海水位,因而与黑龙交战,逐走了黑龙,洱河北水大大降低,现出坝子,人民得以从山林移居平坝。”[13]3
大理市下关镇葭蓬村供奉着黄牛本主,号“护国安邦信神景帝”:
相传有一年,连日的暴雨引发了凶猛的山洪,洪水肆虐,冲垮河堤,直逼村庄,人们拼命往外逃。等洪水退去,百姓返村看时,发现村子安然无恙,房屋没有倒塌。有人说正当洪水冲向村庄的时候,一头大黄牛跑到洪水决口处,用身体堵住了决口,为保住村子而牺牲了自己。后来村里的百姓才知道这黄牛是村中姓字家儿子变的,全村百姓都非常感谢它,把他奉为本主。[14]5
这则传说体现了大理白族先民与自然力量抗争时的悲壮与伟大,在治理水患的同时,也难免有人牺牲的事实,大多治水传说都具有壮阔的英雄情怀。
大理市下关镇登龙村和凤仪镇凤翥村的本主是大理国王段思平的长子,他不以父亲当国王为荣,长大后不进朝廷做官,反而深入民间为民众做善事。
当年大理国都城周围登龙村一带,一到雨季,登龙河洪水成灾,淹没庄稼农舍,百姓深受水患之苦。段思平关心百姓疾苦,派大儿子前往帮助百姓治水患,大儿子到登龙村后一心治理水患,是的百姓安居乐业,五谷丰登。他与世长辞后,被尊为登龙村本主,享受百姓祭祀。[14]21
诸如此类的传说数不胜数。段赤诚斩蟒的故事,在大理白族地区也广为流传。大理古时常遭山洪水患之灾,因而,产生了不少龙神话传说。其中不少是降龙治蟒的传说。这些降龙治蟒的人物多是白族先民与自然抗争、建设和利用自然中涌现出来的英雄。
此外,大禹、李宓部属七将军、邓姓官员、李定国等历史人物被奉为本主或雨神,皆与其在当地治理水患、建设水利有关,相关的传说多集中在唐南诏国、宋大理国及其以前。
2.分水:明清时水传说的核心。明清时,与分水相关的传说大量出现,相较之前的治水传说,其内容更加丰富有趣,同时更具现实意义。
如腾龙村的本主为“大圣东海龙王玉璧天帝”(共有5子):
相传东海龙王不喜欢大儿子,因此也就不给用水。大儿子向他的母亲哀求,母亲给了他绣花针大的一股水,所以现在头村水利缺乏。但东海龙王爱自己的三儿子,就给了他一瓢水。老三很高兴地回家时,路上遇到四脚地神,四脚地神认为东海龙王太不公平,所以就踢了老三一脚,水洒在地上。老三再向东海龙王要水时,东海龙王不愿意再给。老三只得哭告母亲,于是也向大哥一样得了细至针般大的一股水,因此现在井塝村也水利缺乏。[13]6
又如栗木庄村的传说:
相传明朝初年,征南军队进攻大理时,傅友德在战斗中腿部受伤,多亏庆安里村的一个白族女子救了他,落脚在当地,他在沙栗木庄村子里,为本村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受到老幼的爱戴。后来,本村百姓听到傅友德与世长辞后,为他在村里建庙塑金身,尊奉为本村本主。傅友德做了本主后,有一次沙栗木庄村百姓要栽种而缺水,要到庆安村里去求本主借水,傅友德一看,才认出当初救他的正是这位白族本主杨高珍,因而庆安里村的本主杨高珍把水借给傅友德,也给了雨水。[14]133
通过对水资源的分配,沙栗木庄村与庆安村两村共用一井水,感情更加深厚。
大理喜洲附近的九坛神是附近上下各村的本主,各自都很维护本村的利益。在栽秧用水季节,本主们都为水资源使用和分配争执不休,有时还会大动干戈。后来大家为了不伤和气,共同聚在一起商定分水事宜,避免了村与村之间的争执和械斗,九个本主至今被供奉在喜洲。[14]80大理市周城镇流传着“下关水浇上关花”的本主传说,这也与水资源的分配有关,这些水传说与现实中当地分水规则相印证。从治水传说到分水传说的转变是大理白族水传说变迁的基本脉络。
(三)水信仰与水传说变迁的原因
大理白族水信仰与水传说的变迁与大理农业发展密切相关,是大理白族农业化与水利化的表现。
白族本主信仰的源头何在,无稽可考,但从广泛流传着的本主传说和口碑材料中,能够推断,“关于白族本主起源,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15]远古时代,白族先民主要以原始的采集和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当时人们从大自然中获取鱼虾、野果等初级产品,是纯粹的“靠天吃饭”,因此原始宗教的产生大多伴随着从自然中获得恩赐之后的感恩之情,金鱼、螺蛳等自然物成为当地白族最初的崇拜对象。
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大理坝区主要的经济方式,白族先民在认识自然规律的过程中,如旱涝的季节变化,认识到了水利工程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兴风降雨的龙神,有治水之功和建设水利设施的人被奉为当地本主并加以崇拜,龙王崇拜不断兴盛起来,其中一部分龙王成为当地本主。这种从鱼螺崇拜到龙王信仰的转变中也体现了大理从求生存到谋发展的变化。
在大理白族龙王信仰兴盛以后,“龙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水神”的代名词,供奉龙王的目的就是祈风调雨顺、民众安居乐业。值得注意的是,白族信仰中的龙不全都是本主,龙本主和龙王是两个概念,但是都具有“水神”的性质。从性质上看,“龙王崇拜有较多的自然崇拜特征,龙本主崇拜却有更高的层次,它是龙崇拜的发展,具有人为宗教的特点。”[16]从在信仰中的地位来看,龙本主的地位高于龙王的地位,龙本主已经成为本村之主或是本境之主,塑像一般在庙宇正殿正中,而龙王塑像不在庙宇正殿正中而在偏殿。龙王信仰在向龙本主信仰转变的过程中,是水神信仰在大理白族信仰地位的提升,体现了当地白族对农业、水利的重视。
大理白族龙王和龙本主信仰的核心就是祈求风调雨顺,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明清是洱海流域重要的土地开发时期和水利建设时期。明朝大理地区“改土归流”中,众多卫所建立,中原农耕开发模式打破了当地传统的生产方式,大理地区的土地被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并兴修了大量水利灌溉设施。
清代大理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有资料显示: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云贵两省各地册载耕地数量及其所占比例中,大理府田地山塘共1089678亩,占全省比例11.5%,位居云贵两省第一;道光十年(1872年)田地山塘共1088520亩,占全省11.8%,光绪十年(1884年)田地山塘1009932亩,占全省14.5%,均是全省第一。[17]
明清大理地区开发力度之大,耕地数目之多,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与农业相关的本主信仰对象不断出现,如大理市湾桥镇大宁邑村、小宁邑村尊奉的育物景帝赤子大爷,钊邑村尊奉的育物景帝赤子二爷,由上甸村、北甸村、南甸村、中甸村尊奉的育物景帝赤子爷和杨家登村尊奉的长子,都因治蝗有功被当地人奉为本主。[14]58因此,水信仰从鱼螺崇拜到龙王信仰的发展与大理白族农业化联系紧密,是信仰在农业发展条件下的具体表现。
水传说经历了从治水传说到分水传说的变迁,体现大理白族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从与自然抗争、到改造自然,再到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从而与自然达到和谐状态。同时伴随着人们对水资源与水利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过程,从对治水英雄的歌颂,到对开荒创业、兴修水利的本主进行赞扬,再到对分水本主尊奉的过程,也是大理白族水利化的发展过程,对水利秩序的认可直接推动着农田水利化和农业的发展。
二 水信仰与水传说的社会功能
民间传说和信仰具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整合社会价值、推动地方文化认同感的建立和文化传承的社会功能,是地方社会的重要精神纽带。[18]
大理白族水信仰与水传说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长期、持续地影响着当地社会。共同的水神信仰有利于增强大理白族文化认同、推动地方社会的整合。水传说是对现实分水秩序的反映,是水源使用和分配的解说,是当地社会的稳定剂,推动着大理白族农业的水利化发展。
(一)地方水利共同体的形成及维系基础
洱海地区域存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水利共同体,这些水利共同体以共同的水神信仰对象,各村遵守着共同的用水规则,是构成洱海地区水利共同体的基础。大理地区水利共同体的维系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龙王信仰向龙本主信仰的转变,龙本主信仰更加强调对区域水利共同体的维系;二是小区域间共同的水信仰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的整合作用。
不同的水利共同体具有不同的水信仰对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龙本主信仰。龙本主信仰经历了从龙王信仰到本主信仰的发展过程,是大理地水神意识与外来龙文化结合并逐渐本土化的过程,也是大理白族水神信仰地位提高的表现。龙本主信仰有利于村社之间构建起一个以龙本主为中心的小的水利共同体。如大理茫涌溪山谷出口处,有一座本主庙,庙内供奉着一尊山神和一尊水神,庙里的龙本主是溪水所灌溉村庄共同的水神,上下几个村共同用水,合理分水,和平相处,由此便在各村之间构建起了一个稳定的、小范围的水利共同体,成为大理白族地区水利共同体的一个基础部分。
此外,小区域间共同的水神信仰对当地文化和社会具有整合作用。
苏吉本是唐天宝十三年征南诏军队李宓将军部下高级官员,征南军来到凤仪,在云浪村扎营。在和南诏军队的大战中,苏吉率领的征南军在凤仪和宾川之间山上倒刮水处全军覆灭,苏吉的尸首安埋在塘房下干塘边,后来在他墓旁出了一井水,使干塘变成了水塘,给八村百姓永受益。[14]22
“同饮一井水”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的凝聚力和区域认同感。明朝时八村百姓在水塘边为苏吉本建庙塑金身,敕封他为“南面婆苏吉大龙王”,尊奉为八村的本主。
时至今日,每年农历正月初三、初九,大理市凤仪镇云浪村、洗马塘村、麻地村、洞壁村、许长村、青罗村、高仓村、长发村都会过庙会,共同祭祀本主。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大理下关大展屯村、荷花村、阳平村、四脚村、宝林村、单家村等八村都会共同祭祀为他们疏浚河道、降雨供水、消灾解难的本主白难陀龙王。
又如海东一带10村共同信奉的金銮圣母本主,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和五月二十都有盛大的祭祀活动。诸如此类几村共祀一本主的情况也很多并虽封号仍是“龙王”,实则已是当地白族本主,是以村社和地缘为纽带的水信仰表现,对地方社会的文化与社会整合具有推动作用。从宏观角度上看,水信仰作为白族意识的粘合剂,以洱海为中心构建起一个稳固的水利共同体,共同的信仰文化、宗教活动推动着白族共同心理素质方面的整体性,水信仰作为白族社会中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熔铸了白族各个时期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二)维持乡村水利秩序
大理白族地区流传的水传说一定程度上是对现实分水秩序的解说。水资源是公共资源,不可能个人占有,也无法完全平均分配,且地区间存在差异的现实无法避免。因此,明清时大量出现的水传说中反映出维护乡村秩序稳定的样貌,对于当地树立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具有积极作用。大致而言,这些水传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解释水的来源;二是对村与村之间水量分配情况的说明。
第一,解释水来源的相关传说利于促使当地民众在利用水的过程中树立珍惜水、保护水的意识。在大理市下关镇向阳村流传着这样的传说:
向阳村的水府龙王本主是大理苍山脚下阳乡村人,有一年大理坝子旱情严重,村里有一个青年人叫慧生,为了给百姓解除旱情,走遍苍山十九峰都未找到水源,他的忠诚感动了苍山神,苍生神赐他羽扇和隐身衣到天上偷了王母的瑶池水,洒向苍山,变成十八溪,使得大理人享受永久的灌溉之水。[14]23
虽然向阳村水源并没有其他村庄丰富,但是他们仍然感念本主为他们求得的一眼终年不断的井水,他们顺应现实,知足常乐,这则传说也解释了向阳村水的来源。
第二,与水量分配相关的传说可以推动村与村之间对现有用水秩序的认可与维护。
洱源河头龙王一家妻子儿女都是本主,是牛街附近村寨的本主。相传河头龙王本主的小女儿嫁到了云南驿,夫妇很和睦,公婆也疼爱她,但那里缺水,生活贫困。小女儿回娘家把此境况告诉河头龙王,河头龙王心疼女儿,便给了女儿一股水,水量可以灌溉云南驿龙王辖境的田地,从此那里五谷丰登。人们为此感谢三公主为之建了龙女庙,奉为本主,四时致祭。[13]17
此传说与当地水资源分配也有很大关系,是对当地水量分配的解说。
还有本主传说直接与水资源分配有关。大理市喜洲各村信仰九坛神,分别是灵镇五峰建国皇帝、鹤阳摩诃金钵伽罗大黑天神、宾阳三崇建国鸡足名山皇帝、囊聪独秀应化景帝、凤岗阖辟乾坤懿慈圣帝、河矣城龙王妙感玄机洱河灵帝、白姐阿妹神武阿利帝、桑霖元祖镇子福灵景帝、狮子国王—德天中央皇帝,会期在每年农历四月。
相传各村的本主非常维护本村的利益,在栽秧用水的季节,本主们都为水源的使用和分配争执不休,有时候还大动干戈。有一回,大家为了不伤和气,各村本主相互约定,共聚在一起商议,制定出一个好的分水办法,免得经常争吵。于是九位本主来到喜洲本主庙议事,一直争吵到鸡叫了第二遍,因为公鸡一叫他们就回不去了,九个本主只好留在了喜洲做当地本主,被叫做九坛神。[14]80
另一则传说:
相传福爱圣母是凤凰女神慈爱圣母的妹妹,她们两姊妹原先是凤阳邑村本主,后来妹妹也跟随姐姐到了大井盘村做了本主。由于大井盘和凤阳共用水源,慈爱圣母做了大井盘村本主后,掌管了分水权,她就对凤阳邑村有所忌恨,凤阳邑需要水时,她就少分给他们,是凤阳邑村人畜饮水庄稼用水带来困难。[14]163
此传说具有解释现实的作用,并以上这两则传说说明在洱海地区存在着明显的水利纠纷,而这些水传说起到了维持用水秩序消弭水利纠纷的作用。
三 结语
大理白族地区水信仰与水传说有其独特的发展脉络,伴随着大理白族农业的发展,水信仰经历了从鱼螺崇拜到龙王崇拜的变迁,同时经历了从自然物到人格化神的转变。水传说经历了从治水传说为主到分水传说为主的变迁。大理白族水信仰与水传说,一方面维系着大理白族水共同体,推动地方社会与文化的整合;另一方面维持着乡村水利秩序,通过对现实分水秩序的解说,促进着地方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共同发展。水信仰与水传说的构建通过民间信仰的方式认识和认可地区间水资源与水利建设的差异性,使得存在差异的区域间水利分配与合作成为可能,推动着大理白族地区共同经济基础的建立。水信仰与水传说作为白族意识的粘合剂,以洱海为中心构建起一个稳固的水利共同体,推动着民族团结和地方稳定的发展。
综观所述,笔者认为,大理地区洱海流域的水信仰与水传说体系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水信仰体系。这个体系,是以洱海为中心,人与自然为核心,以白族原始宗教信仰为基础,以汉文化和佛教文化为重要元素,以地方社会为依托的综合体,是一个具有云南地方特色的水信仰与水传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