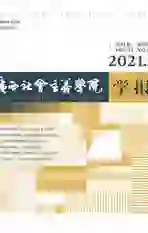新时代中小学“多元共教”预防犯罪教育体系的建构
2021-02-03肖姗姗
摘 要:预防犯罪教育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举措,中小学是预防犯罪教育的黄金阶段。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的新时代背景下,应当结合犯罪预防理论,将传统的犯罪控制转向罪前预防。在此基础上,明确预防犯罪教育对象,规范教育行政部门、家庭、学校和社会在预防犯罪教育中的责任,丰富预防犯罪教育形式,建构“多元共教”的中小学预防犯罪教育体系。
关键词:预防犯罪教育;多元共教;罪错分级;罪前预防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5.017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5-0099-07
犯罪学研究表明,教育与犯罪二者之间紧密相连,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实施违法犯罪的概率相对较低[1]。“与其将经费用来改造罪犯,不如将经费投入到预防犯罪教育中”[2]“与其将研究视角置于犯罪后的法律规范,不如研究犯罪前的预防教育”[3],预防教育在犯罪预防中的地位与作用已然获得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可。预防犯罪教育在一般预防、临界预防与特殊预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警戒作用。
纵观各国未成年人专门性立法,我国预防犯罪教育为国际先河。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便已将此专章规定,2021年修订实施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从未然犯罪出发,以罪前防范为目标,尝试从预防犯罪教育的主体、形式和内容等方面探索该制度的体系性建设,力图使未成年人尽可能少违法、尽可能少犯罪,在“罪错分级”的基础上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现代化与法治化建设。然而,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我国的预防犯罪教育主要还停留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数个条文之中,教育的内容、主体、方式等仍存在诸多留白之处。如何从未然犯罪出发,构建中小学预防犯罪教育学科体系,成了新时代法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中小学预防犯罪教育的规范特征为基础,采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力图从以下四个层面探讨如何理解并构建“多元共教”的新时代中小学预防犯罪教育大格局。
一、現行规范的整体性省思
从现有法律规范来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治理的理念为“提前预防,以教代刑”,并试求从多元教育主体、丰富教育内容与多样化教育方式等领域探索预防犯罪教育的开展与实施。但是,结合实际情况来看,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法律规范内容单薄
从当前世界主导的未成年人立法模式来看,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刑事司法一元化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儿童福利法、少年法二元模式,也有以瑞士、挪威等国家为代表的福利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断探索未成年人立法模式,民法与刑法均将年龄视为责任能力的重要考量因素,对未成年人民事、刑事责任能力予以规定。20世纪末《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两部专门法的制定实施,打破了由刑民笼统规定的传统做法,我国未成年人立法开始走向“福利法+司法法”二元模式。在司法法的这一分支体系中,以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为主要内容。在当前对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予以分级化处理的新时代背景下,2020年我国较为系统全面地修订了《刑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由此我国已形成了以刑法为基础,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一专门法为支撑的罪错未成年人二元立法模式。
预防犯罪教育作为未成年人司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主要作原则性规定,除涉及较为多元的预防犯罪教育主体规定外,预防犯罪教育的内容、对象、方式等具体内容未有明确规定。在其他相关法律规范中,仅有2021年最新修订实施的《教育法》第40条明确规定“国家、社会、家庭、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为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接受教育创造条件”。立法内容单薄与立法形式单一,使得我国预防犯罪教育的开展与实施面临困难。应当如何从立法层面为预防犯罪教育提供法治保障与规范性指引,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各教育主体之间缺乏衔接
虽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了较为多元丰富的教育主体,但从具体的条文规定与实际操作来看,还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研究表明,未成年人的预防犯罪教育往往容易被忽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各教育主体之间职能分工不明确,缺乏有效的衔接联动机制[4]。
从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预防教育规定内容来看,多将两者混为一谈,各自的分工与职能并不明确。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7条规定,两者均应将预防犯罪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计划;第22条规定,两者均应当通过举办讲座、座谈、培训等活动,介绍科学合理的教育方法,指导教职员工、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监护人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然而,这些规定并未能彰显出教育行政部门的组织、领导与管理职能,学校应当在此过程中充当实施预防犯罪教育的直接主体,而分工的不明确将导致预防犯罪教育工作难以开展。
从家庭预防犯罪教育与学校预防犯罪教育来看,两者之间的衔接机制有待加强。结合我国家校合作的历程来看,家庭的作用已然由传统的“辅助配合”转向“与校协同”,家庭教育也由私人领域转向公共事务,家庭教育走向制度化发展[5]。对于家庭教育,既要充分尊重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自主性,也要有效发挥政府、学校和社会的促进作用,必要时进行国家干预,从而加强家庭教育的价值引领和教育功能,促进未成年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6]。预防犯罪教育既是家庭教育的新领域,也是家校合作的新领域。但从现有规定来看,家庭在这一特殊教育中并未实现角色转化,而是仍停留在辅助配合学校预防犯罪教育的层面。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6条虽然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监护人规定为预防犯罪教育的直接责任人,但第19条第2款、第22条第2款均强调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预防犯罪教育的配合作用。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既是家庭预防犯罪教育的特殊主体,也是直接责任人,但其在预防犯罪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并未得以彰显。
预防犯罪教育离不开学校与家庭,两者的有效协同能进一步加大预防犯罪的效果。如何有效发挥家庭教育在预防犯罪教育中的作用,进而强化家校之间的预防犯罪教育协作亦成为这一领域的一项新议题。
(三)对象范围不明确
新修订实施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是在未成年人罪错分级处遇的背景下提出的,通过预防犯罪教育,对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予以提前干预和介入,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基本要求。预防犯罪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之一即为教育对象。结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行为分级来看,教育对象可以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结合特殊预防理论,这三大主体理所应当为预防犯罪教育的对象。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应当结合一般预防的犯罪理论,将并未涉罪涉错的未成年人纳入预防犯罪教育的对象范围。
以何种标准确定预防犯罪教育的范围,也是构建预防犯罪教育体系的重点与难点之一。结合当前的规定来看,预防犯罪教育并未明确是应当以教育场域为主界定对象范围,还是以教育对象的年龄范围为界限确定范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主要规定的是各预防犯罪教育主体的职责,教育主体依据场域的不同开展预防犯罪教育,教育场域主要包括家庭、学校、社区及其他社会活动场所。作为专门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预防犯罪教育的对象范围当为所有的未成年人,即未满18周岁的我国公民。但是,从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实际情况来看,年龄范围不同致其所接受预防犯罪教育的场域也不同,如学前低龄儿童,接受预防犯罪教育的场域当为家庭;未成年中小学学生,接受预防犯罪教育的主要场域当为学校;18周岁以下辍学、失学的未成年人,或已就业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接受预防犯罪教育的场域当为家庭、社区或其工作所在的单位。
由于教育对象不明确影响了各教育主体之间的分工与有效衔接。如何结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及生活学习场域的不同,明确核心的预防犯罪教育对象,也成为预防犯罪教育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
二、新时代预防犯罪教育的目的转向
从犯罪基礎理论来看,犯罪控制与犯罪预防紧密相连。虽然犯罪学中通常将两者融合为“犯罪预防”这一概括性术语使用,但两者是不同的具体研究范畴,且在概念、术语和应用对策上存在严格区别。犯罪控制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后或者过程中采取的不使犯罪行为继续发生或再次发生,并防止犯罪现象的数量与质量超出正常范围(或称为社会所能容忍的范围)的硬性抑制手段。犯罪预防是指对犯罪的事先防范活动,具体是指消除犯罪原因,避免犯罪发生的各种社会组织与管理、建设与发展的活动[7]。由此可见,犯罪控制的运行特征更具主动性,整体上是一种积极的治理措施,是对犯罪的积极避免和主动出击,而犯罪预防的运行特征在整体上具有一定的消极被动性,是对犯罪的被动防守和事后处置[8]。
从现有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来看,我国刑法第17条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实体法规定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程序法规定,均聚焦于未成年人已然犯罪,强调犯罪控制。针对这一情况,《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结合罪错分级的方式,重点关注未然犯罪,强调一般预防与临界预防的重要性。从现行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建构来看,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倡导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二元论。但需要强调的是,预防犯罪教育作为犯罪预防的重要手段,它属于罪错前预防,即在罪错发生之前,采取积极措施对罪错行为进行预防。与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临界预防(或称罪错中的预防)不同的是,预防犯罪教育的重点在于强调犯罪一般预防的作用,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视野提前,不再将预防对象局限于已然罪错的未成年人。
预防犯罪教育属于犯罪预防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实现预防犯罪的重要工具,旨在防止和减少犯罪的发生,针对犯罪形成的原因及其作用于犯罪心理的外化过程,选择和设置防治犯罪的工具及其措施。具体而言,在预防犯罪模式下,预防犯罪教育应当以预防犯罪为目的,并应当具有以下功能:其一,教育功能,即通过对中小学生开展人生理想教育、道德情操教育、法治观念教育和文化知识、劳动技能教育与培训,通过塑造人们的心灵,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其二,排除功能,即排除可能产生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社会因素及其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以防止未成年人形成犯罪意识;其三,疏导功能,即对罪错前的征兆,既不能消极地堵塞漏洞,更不能只着眼于事后的承办,而是将未成年人的反社会情绪扭转或引导到维护社会安宁上,避免、减轻某些消极因素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以防止犯罪意识形成或被强化。
预防犯罪教育应当以犯罪预防为目的导向,其具有保护性预防的性质,应当调动和组织一切社会力量,采取有效措施,为中小学开展预防犯罪教育提供保障。
三、分级化处理教育对象范围
预防犯罪教育体系构建,应结合未成年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及行为特征,对教育对象范围予以分级化、明确化规定。
(一)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特征
未成年时期的罪错行为依不同年龄而有不同特点,其发展规律大致如下:第一是劣迹的程度逐渐加深,一般分为萌芽阶段、试探阶段、发展阶段、加剧阶段与下水阶段;第二是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高发期为10周岁至16周岁;第三是罪错行为的年龄分布即综合性罪错发展顺序规律,如同样是以非法侵占他人财产为目的违法犯罪行为,小年龄的未成年人在体能上处于弱势而采取秘密的方式窃取,大年龄的未成年人则倚仗体能上的优势采取公开抢夺的方式攫取。整体而言,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特点主要体现为突发性、凶狠性、腐蚀性、复杂性、二重性、隐蔽性及反复性[9]。近年来,未成年人罪错行为也呈现出了低龄化、暴力化及团伙化等特征。
(二)从年龄入手限定预防犯罪教育范围
结合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发展规律,不宜设置中小学预防犯罪教育的年龄上下限,应当有针对性地合理调整预防犯罪教育的适用范围。具体而言,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将18周岁以下的中小学生均纳入预防犯罪教育的对象范围。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来看,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但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看,16周岁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其可塑性极强。从犯罪预防的角度而言,不应当将这一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排除在中小学预防犯罪教育的对象范畴之外。
二是不设置年龄下限,将所有中小学适龄未成年人均纳入预防犯罪教育的对象范畴。虽然我国刑法规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12周岁,但结合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低龄化趋势及犯罪预防的需要,小学阶段的未成年学生亦需纳入预防犯罪教育的对象范畴。
(三)从行为入手设置教育对象范围
预防犯罪教育应当结合中学生与小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与预防犯罪教育的内容,为满足中小学生差异性的需求,结合犯罪预防理论,予以层次化处理。
一是对于已经实施犯罪行为,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若未接受专门教育矫治,仍在中小学接受教育的未成年学生,应当以特殊预防教育为重点,旨在防止其再犯。
二是对于已经实施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在接受惩戒矫治的同时,中小学应当加大临界预防教育,预防中小学生的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恶化升级为犯罪行为。
三是对于尚未实施罪错行为的中小学生,应当加大预防犯罪教育中的法治教育,通过典型案例等阐释罪错行为后的严重后果,强调一般预防的重要性。
四、“多元共教”预防犯罪教育大格局建构
从现有的预防犯罪教育规范来看,政府、学校、家庭、社区及各社会团体组织均已被纳入“多元共教”预防犯罪教育主体。因此,应在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家庭为基础、学校为重要媒介、社区及其他社会组织为重要补充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共教”的预防犯罪教育大格局。
(一)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
“亲权”始于直系血亲关系。“国家亲权”则意味着超越传统的血缘关系,“国家”取代传统“父母”的角色,基于未成年人利益保护考量,对与未成年人相关的监护、教育、继承等事宜予以干预。国家亲权理论虽源于英美法系,但从我国最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来看,这一理念已成为我国未成年人立法的重要理论支撑之一[10]。对此,作为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公权力化身,教育行政部门需要结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在犯罪预防教育体系中发挥统筹与指导作用。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积极承担国家责任,充分发挥主导机能。其一,将预防犯罪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即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预防犯罪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计划,指导教职员工结合未成年人的特点,采取多种方式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犯罪教育。其二,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其三,积极引导社会工作者参与犯罪预防教育工作,鼓励和支持学校聘请社会工作者长期或者定期进驻学校,协助开展道德教育、法治教育、生命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参与预防和处理学生欺凌等行为。其四,教育行政部门通过举办讲座、座谈、培训等活动,介绍科学合理的教育方法,指导教职员工、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其五,充分发挥考核职能。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预防犯罪教育的工作效果纳入学校年度考核内容。
此外,教育行政部门还应当建立健全政策法规。政策法规是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督导学校,使各主体积极参与预防犯罪教育的重要保障,是多元共教协同机制民主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重要前提。关于预防犯罪教育的立法完善,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法律上明确各教育主体的地位、具体的职责;二是明确预防犯罪教育的主管部门、机构及其职责,完善预防犯罪教育的工作机制与管理机制[11];三是明确学校预防犯罪教育与家庭预防犯罪教育的界限,促使监护人积极参与学校预防犯罪教育,学校积极引导家庭预防犯罪教育;四是明确各预防犯罪教育主体的指导服务提供者;五是明确预防犯罪教育的评估机制及具体的法律后果;六是明确预防犯罪教育的经费保障制度。
(二)父母及其他监护人作为第一责任人
与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密切相关的一般控制理论与社会控制理论均提及了对父母教养的要求。一般控制理论的提出者戈特弗里德森和赫希认为,有效的父母教养是未成年人得以有效自我控制的主要原因[12]。父母主要通过对子女行为监督,对子女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认知和惩处来有效预防未成年人实施罪错行为。社会控制理论从依恋、奉献、参与、信仰四个社会控制键入手,分析人为什么不会犯罪。其中,赫希在《少年犯罪的原因》中明确提出,未成年人之所以不犯罪,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了上述四种社会控制机制的结果。通过研究发现,对父母高度依恋的未成年子女,实施违法犯罪的行为要低很多[13]。由此可见,父母通过对未成年人的行为引导、监督和管教,可有效预防未成年人实施罪错行为。
基于父母角色在预防犯罪中的重要性,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积极履行监护职责的同时,应当积极履行多重预防犯罪教育职责。其一,积极引导职责,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良好家风,培养未成年人的良好品行。其二,监督职责,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心理异常或行为异常的情形予以及时了解、教育、引导和劝解。其三,充分配合学校的预防犯罪教育工作。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作为连接学校与未成年人的重要媒介,在预防教育工作中要求其积极与学校沟通,积极配合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犯罪教育,从而进一步提升家校联合的效果。
为充分发挥家庭在预防犯罪教育中的作用,对家庭预防犯罪教育的专业化指导与服务能有效提高家庭的预防犯罪教育能力与水平,这是预防犯罪教育现代化、法治化的实质性要求。对此,应当整合现有资源,加大预防犯罪教育家庭指导与服务专业化建设,主要从专业化队伍建设入手,建立专门的预防犯罪教育指导队伍,通过资格认证、岗前培训、监管评估等制度,规范专业队伍建设。同时,应当制定预防犯罪教育家庭指导与服务的标准,包括指导与服务的时间、地点、评价机制等,为家庭预防犯罪教育提供专业化高素质的指导与服务。当然,父母与监护人作为第一责任人,预防犯罪教育的权利与义务不能“让渡”给他人,应当在承担具体法律责任的同时,激发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学习和吸收预防犯罪教育知识,摒弃传统的“唯成绩论”观念,更加关注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的罪錯行为。
(三)学校作为重要媒介
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克拉克从研究视角集中于被害人所处环境与犯罪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情境犯罪预防理论。该理论强调犯罪受情境因素的影响,通过环境设计和管理遏制潜在犯罪人的犯罪之决断来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
学校作为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具体实施单位,除传统的理论知识教育外,应当结合预防犯罪教育的需要,通过营造良好的学校环境,落实预防犯罪教育工作。一是丰富教学计划与教学队伍,如通过聘任从事法治教育的专职或者兼职教师,可以从司法和执法机关、法学教育和法律服务机构等单位聘请法治副校长、校外法治辅导员,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等措施,将道德教育、法治教育、生命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落到实处。二是结合情境犯罪预防理论,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作为预防未成年犯罪的重要防线,学校应当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完善学生欺凌发现和处置的工作流程,严格排查并及时消除可能导致学生欺凌行为的各种隐患。三是对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指导职能,学校可通过举办讲座、座谈、培训等活动,向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介绍科学合理的教育方法,指导他们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四是积极履行告知职能。学校应当将预防犯罪教育的计划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从而有效地推動家庭协助配合预防教育工作的开展。
创新预防犯罪教育形式,培养孩子树立远离犯罪的健康心理,掌握预防犯罪的技能技巧,学以致用,是预防犯罪教育的终极目标。学校教育应当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规范指引之下,整合学校资源与社会资源,将多种社会力量运用至中小学预防犯罪教育中。如将法治副校长的职责履行到实处,邀请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办理未成年人罪错案件的专门机关委派办案人员定时定点进行法律法规解读、以案说法等;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举办家长读书会或家长学习会,定期为家长提供专业的课程培训与指导,就未成年中小学生的在校学习情况与身心健康发展情况及时沟通,在发现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之际及时反馈以共商解决方案。
(四)整合社会预防犯罪教育资源
作为我国社会预防犯罪的总方针,综合治理要求国家、社会、家庭、社区等多元组织参与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中。预防犯罪教育工作并非仅将责任归于国家、家庭与学校。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未成年人学习、生活所在的村(居)委会、社区,及与他们活动密切相关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等组织或场所也应当充分发挥其在预防犯罪教育工作中的辅助性职责。
学校预防犯罪教育、家庭预防犯罪教育与社会预防犯罪教育为“交叠关系”,三者根据场域的不同,所承担的预防犯罪教育职责具有差异性,但三者在共教中又存在着诸多相互协同合作的关系[14]。对此,在厘清三者边际的基础上加大三者的合作机制,如社会团体组织应当定期联合学校开展公益活动,将分散的、自发的社会预防犯罪教育资源充分运用起来。同时,也应当重视社会力量的参与,教育行政部门可设置专门经费款项购买社工服务,为未成年中小学生提供专业化的预防犯罪教育。
(五)预防犯罪教育内容多元化设置
预防犯罪教育,是指以培养未成年人守法意识和对犯罪的防范意识为目的的教育。它是法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基础工作。法治教育在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同时,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也应从内容、主体、形式等方面予以具体落实,对预防犯罪教育的内容形式等加以规范和指导。
预防犯罪教育的目的具有法治与教育双重性质。通过教育使未成年人懂得违法和犯罪行为对个人和家庭、他人和集体、社会造成的危害,懂得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抑制和消除犯罪冲动,减少犯罪的发生。
中宣部、司法部印发的《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明确指出,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制定青少年法治教育新格局目标,要求政府、司法机关、学校、社会、家庭共同参与到这一目标中来,通过法治教育培育中小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观念,使未成年人树立遵纪守法和防范违法犯罪的意识,提高自我管控能力。
预防犯罪教育不仅以法治教育为内容,还应当充分结合其他教育内容,开展预防犯罪教育。道德教育是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2017年教育部出台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指出,应当将中小学德育内容细化落实到各学科课程的教学目标之中,融入渗透到教育教学全过程,通过道德教育提高中小学生的道德觉悟和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树立道德信念,培养道德品质,养成道德习惯,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成长为有助于社会的新时代公民。心理健康教育是指导未成年人健康发展的必备教育内容之一,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向中小学生传授培育心理健康的知识和方法;它强调教育主体从良好的氛围出发,与教育对象产生有效的互动,从而了解其心理现状,分析所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对应的心理治疗方案。此外,未成年学生的自我控制教育、伦理教育、生命健康教育也是预防犯罪教育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Katayoon Majd. Students of the Mass Incarceration Nation[J]. Howard Law Journal, 2011(54).
[2]Eric Blumenson & Eva S. Nilsen.How to Construct and Underclass,or How the War on Drugs Became a War on Education[J]. Journal of Gender Race and Just,2002(61).
[3]Smith,Michael.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PLE[J].Resource News,1982(3).
[4]Denise C. Herz,Joseph P. Ryan,Shay Bilchik.Challenges Facin Crossover Youth:An Examination oJuvenile-Justice Decision Making and Recidivsm[J]. Family Court Review,2010(6).
[5]边玉芳,周欣然.我国 70 年家校合作:政策视角下的发展历程与未来展望[J].中国教育学刊,2021(3).
[6]赵祯棋.家庭教育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J].中国人大,2021(2).
[7]许章润.犯罪学: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87.
[8]张小虎.中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综述[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272—273.
[9]许肇荣.犯罪预防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181—187.
[10]王广聪.以公益诉讼促进实现未成年人保护国家责任[N].检察日报,2020-11-16(03).
[11]李明舜,党日红.家庭教育的立法进程[M]//孙云晓.中国家庭教育蓝皮书(2017-2018).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9:49.
[12][美]迈克尔·哥特弗里德森,特拉维斯·赫希.犯罪的一般理论[M].吴宗宪,苏明月,译.北京: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92.
[13]Travis Hirschi.Causes of Delinquency[M].Routledge,1969:132.
[14]谭轹纱,简天凤.劳动教育的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J].中国教育学刊,2021(5).
责任编辑:吴红博
收稿日期:2021-09-01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CFX037);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XSP20YBC160)。
作者简介:肖姗姗,女,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盟刑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刑法学、犯罪学、少年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