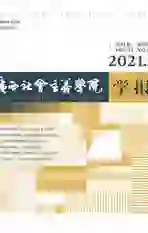瑶族“漂洋过海”:从浙江绍兴到广东潮汕
2021-02-03莫金山
摘 要:通过运用历史文献与民族文献互勘互证方法,对瑶族“漂洋过海”的原因、时间、地点、过程进行考证,可以得出结论:东晋义熙八年(412年)前后,因自然灾害、朝政动荡和战火洗劫,特别是受孙恩、卢循起义的影响,居于绍兴的瑶族一千多人,乘坐十几只大船,从浙江绍兴出发,经杭州湾、宁波、舟山、台湾海峡,用七天七夜的时间,到达广东的潮州、汕头,行程1 200多公里。此后,广东才开始有瑶族的居住和分布。
关键词:瑶族;漂洋过海;绍兴;潮州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5.012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5-0068-08
一、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
中国古代的航海业始于何时,现难稽考。1973年,在浙江余姚发掘的距今7 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木桨[1]。 《周易》记载:“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这说明先秦时期人们已知造船航行。另外,相传秦代秦始皇也派徐福率童男童女三千人东渡日本。
西汉时期,中国古代的航海业已很发达,从会稽郡至广东,已不鲜见。公元前334年,楚国打败越国,并杀越王无疆,越地被楚国所占,瑶族和越国公族向浙东温州迁徙,建立“东越国”。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政权的吕嘉反叛,汉武帝出兵讨伐。“东越王”余善带八千兵卒助汉军平叛,率兵卒从海路来到广东潮州揭阳。
汉武帝平定吕嘉叛乱后,废除南越政权,在其地设置了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九郡。汉朝最南端的交趾等郡的贡赋,如走陆路则太难,只能走海路,于是从今越南北部到中国东部沿海和长江的水上交通便繁荣起来。
《汉书·地理志下》记载了当时中国东南沿海至印度半岛的海上丝绸之路:“自日南(越南)、障塞、徐闻(广东)、合浦(广西)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苏门答腊);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缅甸);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印度)……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國’(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2]1671
《后汉书·郑弘传》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治泛海而至,时属会稽郡。汛海而至,风波险阻,沉溺相系。”[3]“东冶”,即今福建福州。“交趾”即越南北部地区。可知,从会稽郡到这些地方是当时“贡献转运”的要道。
《汉书·地理志》记:“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2]1669“东鳀”,即今日本。
《三国志·许靖传》:“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漂薄风波。”[4]
三国时期,印度人康僧会从海路来到东吴国都建业,创建寺院,传播佛教[5]。
东晋时期,法显(约337-422年)从山西出发,经敦煌,越葱岭到天竺国取经,其后走海路回国,经苏门答腊到广州,最后到建康。其著《佛国记》,记录了他的行程及见闻。
可知,两汉、三国、东晋时期,中国沿海的航海造船能力和经验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人们驾舟船劈波斩浪,东到日本,南到东南亚和印度,已不是新鲜事。
二、“漂洋过海”背景和原因
瑶族“漂洋过海”与“盘瓠故事”“千家峒传说”,共同构成瑶族传统文化三个核心内容。它应是历史的真实记忆,故事应当发生在汉立之后。因为汉代以后才有远行航海的记载,且在东汉应劭撰的《风俗通义》中仅记“盘瓠故事”,而无“漂洋过海”的记述。
然而,关于“漂洋过海”具体的历史时间,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相比较而言,主张南宋理宗年间和元朝大德年间的“漂洋过海”之说,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影响较大。关于“漂洋过海”的地点,学术界也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如“漂游长江”“漂游洞庭湖”“漂游渤海”“漂游台湾海峡”“漂游琼州海峡”等。其中,“漂游长江”和“漂游洞庭湖”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影响较大。
本文将在叙述“漂洋过海”内容时,就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因、时间、地点、过程等问题,提出笔者的看法。
据笔者研究,瑶族起源于“东夷九黎族”,中心地点在山东泰安泰山。其后经武昌、南京、扬州,迁到浙江绍兴会稽山[6]。瑶族在会稽山生活的时间很长,从尧舜时期一直延至东晋晚期。在“漂洋过海”之后,绍兴大地才找不到瑶族活动的影子。
“漂洋过海”发生在东晋晚期的依据,主要是东晋后期所发生的一系列天灾人祸,符合或接近瑶族、畲族文献对“漂洋过海”的追述。
一是旱灾饥荒。瑶族对“漂洋过海”原因的追忆:天气干旱无雨,农作物生长受损,农事歉收,饮食难济,于是迁徙。瑶族文献《盘王大歌·天大旱歌》记:“寅卯二年,天大旱七岁,官仓无粮,深塘无鱼,蕉木出火烟,瑶人吃尽万物,无得投靠。十二姓瑶人姐妹商量要出家园。”又说:“天日出火,大旱,树木焦枯,到处官仓无粒米……小冲大河无水流,深潭水干无鱼游……海中无水龙洗澡,旱得龙王飞上天。”[7]
这符合东晋时期会稽郡的历史。晋安帝元兴年间(402—404年)桓玄掌权。会稽郡遇旱灾和火灾,造成饥荒,饿死者众。《晋书·桓玄传》记载,“会稽饥荒……百姓散在江湖采稆”“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三吴大饥,户口减半,会稽减十三四,临海永嘉殆尽”。可知,瑶族的传说与会稽历史记载相符。会稽郡的旱灾饥荒使居于此地的瑶族,产生远离此地的想法。
二是火灾罹祸。瑶族在“海岸捕鱼,失落火种,烧去房屋”“上司旨下回文,拘十二姓瑶民盘王子孙”,于是瑶族才“奏(凑)本(钱)开船,漂洋过海”[8]440。
《十二姓瑶分基来路总图》记:“始祖大公赵朝三,自后开辟年间,原住武昌,下湖(海)南海岸,出会稽山白云之地安居。十二姓瑶人,为大旱三年,妻子寻找无食,放火烧南海万里江山,百姓(汉人)奏报上司,主上倒本回拘十姓瑶民。十二姓盘古子孙计议到广西投生。”[8]457
這两条材料说出如下信息:其一,这场大火发生在会稽郡;其二,火灾的面积很大,“火烧南海万里江山”;其三,官府认为是瑶民纵火,于是要拘拿瑶民问罪;其四,瑶民恐惧,举族迁走,漂洋过海。
这“南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泛指是“中国南方”,狭义专指浙江宁绍平原和广东省。夏后帝少康封其庶子无余于会稽以奉禹祠,使无余成了越国的始祖,始都于会稽。《史记·太史公自序》则有:“少康之子,实滨南海,文身断发,鼋鲜与处,既守封禺,奉禹之祀。”[9]此处的“海南”明显是指越地的会稽山和宁绍平原。
这场火灾在东晋后期越地的历史上得到印证。《晋书·五行志》记:“太和二年(367年),郄愔为会稽内史。六月大旱灾,郡治火烧数千家,延及山阴(绍兴)仓米数百万斛,炎烟蔽天,不可扑灭。”[10]806这场大火灾与瑶族文献所记相符。
三是社会动荡。晋武帝死后,西晋王室争权夺利,发生“八王之乱”,国力衰弱,北方少数民族乘机南下。永嘉五年(311年),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十万晋军,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旋攻入京师洛阳,俘获晋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造成“永嘉之乱”。
瑶族文献《辛巳岁立歌传》记:“瑶人落难年多久,漂洋过海各分枝……五羊反尽无人知,五羊吵闹中华国,有日千里无人烟。”[11]这就告诉我们,瑶族“漂洋过海”与“五羊反尽”“五羊吵闹中华国”的历史事件有联系。
什么是“五羊反尽”?笔者认为是“五胡反晋”。所谓“五羊吵闹中华国”,就是人们常说的“五胡乱华”。
“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游牧部落。西晋后期,原居于北方的“五胡”,趁西晋王朝衰弱空虚之际,大规模南下,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百余年间,他们先后建立十几个割据政权,中国历史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这时期中原地区战争不断,北方人民为逃避战乱,纷纷举族南迁。大量人口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南渡持续两个世纪之久,人数多达近百万,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
北民南渡,一方面促进了宁绍平原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重了这一地区人地之间的矛盾,人们的生产资源和生活空间受到极大的挤压。
瑶族文献经常说“山猪马鹿野耗反乱”,造成瑶族迁徙离散[12]。对这现象人们长期也弄不清楚其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寅卯”,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纪年,它很可能是“壬寅”“癸卯”的合并简称,即是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二年(癸卯),即公元402年、403年。这是孙恩投水自尽,卢循继举帅旗,坚持反晋斗争的特殊岁月。
什么是“马鹿(驴)之乱”?这是隐语。所谓“马”,是指东晋皇族司马集团,他们内部争权夺利,以及司马氏与王导为首的琅玡“王氏”之间的争权夺利,时称“王与马,共天下”。所谓“鹿”,即“卢”,指“卢循”。
淝水之战后,东晋朝廷虽然暂时消除外部威胁,但内部却危机四伏,司马道子专权,朝政腐败、政刑谬乱,朝中党派林立、互相矛盾、互相倾轧,不断爆发流血斗争。浙东地区赋役苛重,民不聊生。《晋书·桓玄传》记:“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10]2597《晋书·孙恩传》记,当时掌握会稽郡实权的是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元显纵暴吴、会,百姓不安骚动”[10]2633。新安太守孙泰是五斗米道教主,企图利用传道聚集民众反抗东晋朝廷,但被司马道子诱杀。其侄孙恩带领众人逃入海岛翁州(今浙江舟山群岛),举旗造反,“旬日之中,众数十万”[10]2632。即言之,是东晋王朝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和卢循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造成的社会混乱,促成瑶族“漂洋过海”。
四是广东经济富庶,社会相对平静。广东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一向是岭南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的中心,自秦始皇征服岭南设南海郡以治其地后,经两汉三国时期的开发,社会经济贸易,特别是造船和航海业,空前繁荣,广州番禺成为航海中心。《汉书·地理志》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2]1670《水经注》卷三十七,记东汉建安中,孙吴交州刺史步鹭到南海(今广州),所见情况是“负山带海,博敞渺目……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13]。《晋书·吴隐之传》记:“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10]2341《南齐书·王琨传》记:“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14]《南史·萧劢传》记:“广州边海,旧饶。”[15]此“旧饶’,应包括东晋时期的社会经济景象。
这时期广东经济富庶,贸易繁荣,相对平静,社会稳定,还可以从广州地区出土的晋墓砖块“永嘉铭文”得到证实:
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
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
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16]。
永嘉之乱时,江南和广州仍然处于相对“康平”的生活环境,不受战乱、荒灾的影响。广州还出现“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的良好局面,居民可以开设集市,自由进行商品贸易。这件铭文反映了西晋时期中国北方动荡,南方稳定,人民安居的史事。卢循领导的起义军为什么南下广东,一因广东官兵势弱,二因广东富庶。
五是孙恩、卢循起义的战火波及瑶族。隆安三年(399年)十一月,孙恩自海上起兵攻会稽。《晋书·孙恩传》记:“吴会承平日久,人不习战,又无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诸贼皆烧仓廪,焚邑屋,刊木堙井,掳掠财货。”[10]2633元兴元年(402年)三月,起义军在进攻临海作战中,严重受挫,孙恩投水自尽。余众数千人推举其妹夫卢循为首领,继续坚持抗晋斗争。
元兴二年(403年)七月,卢循因连战失利,无法在浙东立足,遂率军登船向广州方向转移。十月,占据番禺,自称“平南将军”,摄广州事。卢循命姐夫徐道覆守始兴(今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义熙六年(410年),卢循与徐道覆合兵北伐,打到长江边,曾攻下九江、荆州等地。后因受刘裕反击,兵败退守番禺,最后死于交州,起义失败。
孙恩、卢循起义队伍中,大量是“免奴为客”,即“奴婢佃客”身份人员。这些人员是“北民南渡”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东晋官府“征兵”不满而参加起义,目的是获得土地和生存空间。
孙恩、卢循起义队伍中,也有一些瑶族。《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载,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卢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始兴溪子,拳捷善斗”[17]。胡三省注:“始兴溪子,谓徐道覆所统之始兴兵也。”陈寅恪先生撰《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及推论》一文,谓“溪子”为瑶族先民。这些瑶民应是随卢循起义从浙东南下到广州和始兴。
孙恩、卢循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坚持战斗了12年,先后四次从舟山群岛出发登陆进攻掳掠宁绍平原诸郡县,最多的一次“掳去男女20余万口,逃入海”[10]2633,杀戮亦重。《晋书·孙恩传》记:“自恩初入海,所虏男女之口,其后战死及自溺并流离被传卖者,至恩死时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没谢琰、袁山松,陷广陵,前后数十战,亦杀百姓数万人。”[10]2634可见,当时宁绍平原战火浩劫之严重,可用“白骨蔽野”“满目疮痍”来形容。这期间的瑶族就生活在宁绍平原大地上,瑶族也遭受战火洗劫,这是可以肯定的。瑶族在此地已无生存发展的基础和优势。
三、“漂洋过海”的时间
卢循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在广州建立了政权,前后有五六年。这场战火对广东的经济社会也产生负面影响。别的不说,卢循攻广州时,当时广州刺史吴隐之,率军民抵抗了一百多天,粮尽援绝,死伤无数。卢循攻占广州城后,焚烧官府屋舍,百姓房屋,将几万具尸体放在一起进行集体焚烧。卢循占据广州后,征役拉夫,战事不断,不少人死于兵戈,更多的人携带妻儿,举族迁走,庐舍焚毁,土地荒芜。
此时正是旧的社会秩序被打乱,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之际,也是当时瑶族迁入广东富庶地区的最佳时机。同时,卢循义军从浙东海路杀到广州,对瑶族“漂洋过海”思想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为瑶族“漂洋过海”提供路径和经验。在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的条件下,瑶族于是决定举族南迁。因此,在卢循失败的第二年(412年),南方战乱刚平息,社会刚刚恢复平静,瑶族就举族南迁了。当然,瞅准此机会的绝不仅仅是瑶族,应当说更多是浙东人士,瑶族仅是南迁队伍中的一部分人而已。
由于这些人是在卢循败后才大量迁移到闽南和粤东,于是晋朝在此设立新郡县来安置。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晋廷分广州东官郡,在粤东北和闽南新立“义安郡”,辖海阳、绥安、海宁、潮阳、义招等5县。今漳州南境属义安郡绥安县(县治在今云霄县境内),北境仍属晋安郡晋安县管。
《晋书·桓玄传》记:“会孙恩败走,玄奉诏……招集流人,立绥安郡。”[10]2590
《宋书·州郡志四》载:“义安太守,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分东官立。领县五,户一千一百一十九,口五千五百二十二。”[18]1199又载:“义招令,晋安帝义熙九年,以东官五营立。”[18]1200
清道光二年阮元主编的《广东通志》卷九十二,“舆地略”记:“古称鴂舌者,蛮猺岐诸种是也……东晋、南宋,衣冠望族,向南而趋,占籍各郡,于是语言不同。”可知,在阮元等人眼中,瑶族也是从东晋时期开始迁到广东的。
众多的流民南下福建、广东,晋朝不得不设新县衙府来加强管理。我们从这些新设郡县中,亦可寻得瑶族迁来福建、广东的时间,应在公元413年前后。
在瑶畲文献中,关于“漂洋过海”发生在东晋晚期,也有近似的记录。广西苍梧县沙头镇瑶族收藏的《过山文》记载:“壬子年,无下反乱,逼着漂洋过海,到南海八万乡登岸。”[8]383所谓“壬子年”,即晋安帝义熙八年(412年),这与上文所说“公元413年前后瑶民南迁广东”,基本相符。
广东连南瑶族房氏保留的《房氏年命书》(《房氏族谱》)记,房氏祖先原居淮南,迁到广东的第一世祖先,名叫“房法成九郎”,他出世是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19]。这个时间与我们所说“晋安帝义熙八年(412年),瑶族漂洋过海到广东”,相差仅4年。
瑶族与畲族是同源的民族。《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记:“从文献记载、传说和族谱来看,畲族的祖先,早在2-5世纪就已居住长江中游一带,其后向南迁徙。”[20]即是说,五世纪之后瑶族才“向南迁徙”,这与我们所说东晋晚期瑶族“漂洋过海”,大致也相符。
关于瑶族乘船下海的时日,瑶族文献中有不同的记录。有的说是“四月初八日”[8]493,有的说“八月十五日”[8]475。有的说“七月初八日”[8]512,更多的说是“十月十六日”。湘南江华瑶族流传的文献《十月十六调盘王》记述:相传在远古时代,瑶胞乘船漂洋过海,途遇狂风大浪,眼看船毁人亡。这时,有人在船头祈求始祖盘王保佑子孙平安,并许下大愿。许愿过后,立即风平浪静,船很快靠岸,瑶胞得救了。上岸瑶民砍树挖成木碓,把糯米蒸熟舂成糍粑,尔后唱歌跳舞,庆祝瑶族新生和盘王生日。从此,瑶族就把这一天定为“盘王节”。
在这几种时间记录中,以哪种为是呢?笔者认为应以十月十六日为是。古代行船要靠风力,所谓“一帆风顺”“乘风破浪”,依靠风力的推动比人力划桨更省力省时。中国古代的航海者已经非常准确地掌握了季风规律,并利用季风的更换规律进行航海。宋代地理学家朱彧在《萍洲可谈》卷二中记:从中国东南的杭州、泉州、广州到东南亚的航线“船舶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21]。宋代泉州太守王十朋(1112-1171年)《提舶生日诗》的“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描写了利用季风进行航海贸易的情景。瑶族是从会稽郡到广州的,应是借北风向南吹拂的推力。十月十六日,正是北风兴起之时。其他的“四月初八良日”“八月十五日”,都是南风吹向北方,不符合航船南下的要求,故摈弃不用。
四、“漂洋过海”的过程
迁徙频繁是瑶族文化的重要特点。瑶族、畲族迁徙并非莽撞,毫无目标地“周游天下”。他们迁徙总是有目标、有计划的。按《浙江省少数民族志》记,这次迁徙是在“盘瓠后期王国”的最后一个国王主持下进行的,这国王名叫“盘王碧”。在迁徙之前,盘王碧就先派出瑶族勇士赵法章、盘林二郎、邓养一郎等,乘船过海,前往广东,实地勘察。在确定有迁徙的意义后,盘王碧和族众共同商量迁徙的具体事项。瑶族文献《祖先根牒》记,瑶族原先居住在南京七宝山,“人丁不旺,买卖不顺,求人不得,求鬼(神)不安,十二姓瑶人又商量移居。十二姓赵法章、盘林二郎、邓养一郎,乘船过海,经往广东察看,得见土地丰富,耕种也熟,求人也得,求神也安,买卖兴旺。回高州告知众瑶族子孙。在戍寅七月初八日,三更半夜,带着一十二姓子孙承(乘)船过海”[8]512。
这条材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瑶族先派人员到广东实地考察,感觉那里有很好的生存发展条件,广东土地丰富,耕种易熟,求人也得,求神也安,买卖兴旺,于是决定南迁。这与前文所言“广东经济富庶,社会相对安定”相符。其二,瑶族是“三更半夜,乘船过海”。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瑶族原居住地绍兴离海边不远,他们“三更半夜,乘船过海”是可能的。如远离海边,拖兒带女,将老扶幼,举家搬迁,是很难“三更半夜,乘船过海”的。这与我们说瑶族原居住在绍兴七贤洞,距杭州湾不远,也相吻合。
瑶族文献记“漂洋过海”的有下列具体情况:
瑶族文献 《过山版》记:“备齐十二面大船,十二姓瑶人分船坐渡。”[8]493
郑德宏等根据清乾隆年间抄本整理译释的《盘王大歌》一书中的《放猎狗》篇说:“船成了,疍家师傅来试船,又请大哥来指点,踏上船头船行走。船成了,三百船夫来试船,三百船夫齐喝号,驾船到州号声高。”[22]《十月十六调盘王》篇记:“寅卯二年天大旱,瑶人坐船游各方。划船过海受苦寒,过了七朝又七夜。念经拜神船开航,漂洋过海各分飞。”
广东乳源瑶族文献记:“瑶民子孙下广东,进南海岸八万山,瑶水洞。随山耕种地水塘,养瑶儿孙性命”“行过海中风打散,重留六姓在河边。十二姓瑶人平平上,踏上船头水面游。行过海中罗经定,罗经定转广南东。”[23]
所谓“罗经”,即罗经仪,是指南针的一种,它主要用于航海,判定方向,以保证航线的正确性。所谓“广南东”,就是广南东路,简称“广东”。
这些材料,提供了如下信息。
其一,瑶族“漂洋过海”,乘坐的是“十二只船”还是“十七船”?我们认为这两个数据都正确,但又不全对。因为他们从杭州湾出发时是17只船,但到了温州、潮州时有12船人上岸,其余5只船继续前行到广州,故有两处说法。其二,由疍民来撑舵开船,并使用了“罗经仪”。所谓“疍民”是我国沿海地区水上居民的一个统称。他们以水为家,熟悉水性,是在近海内河从事渔业或水上运输的人。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记:“以舟为家,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疍也。”[24]其三,船大人多。宁绍平原水乡泽国,乘舟行船是当地人的擅长。早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里,越人就有造船行舟的遗迹。到了春秋时期,吴、越争霸,水战时常发生。他们能够造出大中小各类的战船,称为“大翼”“中翼”“小翼”。据清钱培名《越绝书札记·逸文》引《水战兵法内经》记载:“伍子胥水战法,大翼船宽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中翼宽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宽一丈二尺,长九丈。”这“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共79人。1974年底,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市文化局建筑工地上,发现了一处秦汉时期的造船工场遗址。从工场规模看,可造出宽8米、长30米、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25]。因为瑶族乘坐的是“大船”,每只船我们以乘坐79人计,则这次瑶族“漂洋过海”人数在948—1343人之间,谓之“一千余人”,可也。其四,海上航行“七朝又七夜”。古代人们用帆船航海,以点香柱来计时间,一支香柱燃尽为半更,约今一个小时,两支香柱为一更,每更约2个小时。明清时期福建沿海渔船民手中有一本名叫《针簿》的航海指路书,记录古代航海情形。据学者研究,从厦门港金门岛外的北椗礁(北碇)开船,驶往惠安崇武外海中的乌丘岛,约120公里,要用七更,14个小时[26]。从会稽郡(绍兴)到广东潮州、汕头,约1 200多公里。按此推算,应需要140多小时,约六天六夜。若再航行到陆丰、揭阳,这更接近“七朝又七夜”的传说了。
路程遥远,耗时又多,这事不应发生在长江和洞庭湖。有人说,瑶族不识湖海的区别,看到洞庭湖宽阔水面,就将“漂游洞庭湖”误写为“漂洋过海”。这解释实在太勉强了,是典型的“强解材料以就我”。长江、洞庭湖水面并不宽阔,人坐船中两岸景物历历在目,怎能用“七天七夜”的时间呢?又怎能“不得靠岸”呢?瑶族不识湖海的区别,但水工船夫总该知道吧?瑶族上船之前,总要打听清楚才上船吧?所谓“漂游渤海”“漂游台湾海峡”也不对,因为朝鲜半岛和台湾岛,没有瑶族或很少有瑶族居住。至于瑶族移居“琼州”,那是明清时期的事情了。
五、关于登岸的地点
瑶族“漂洋过海”是按照不同批次,不同时间来进行的,因此登岸的地点也有多处,其中主要是潮汕地区以及陆丰、揭阳。
关于登岸地点主要在潮州,有文献可证。2018年8月,笔者在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考察时,在瑶族盘艳明家看到一份祖先流传下来的族谱,其中《瑶族迁徙歌》记:
瑶族本住在海边,好山好水好家园。只因那年蒙大难,十二兄妹离家园。离家瑶族要过海,游到海中浪又高。当天许下盘王愿,才保瑶族命周全。娣妹上岸洒泪别,分路游荡各州县。游到广东南海岸,潮州落脚安下身。珠玑巷中起瑶寨,开山耕种又多年。抛落潮州各自去,各自投身不共园。
有学者将上述内容注释为:“十二姓瑶族长房盘姓四兄弟在‘漂洋过海’时,遇大风浪,经奋力拼搏,到达福建马尾港。本想上岸,但却被当地官府拒绝,无奈继续航行,到达广东潮州。这里的官府收留并安置了十二姓瑶族。”[27]
《平地瑶歌选》一书中有“盘王子孙留记”篇记:“当初流落广东省,潮州县里忆愁忧……十二姓瑶人渡到岸,三江岸上各奔波。江华永明聚瑶众,道州兰山亦有人。富川县里多瑶姓,金秀荔浦多瑶亲。再渡广西田西县,泗城府里得安居。百色县城瑶多众,汪甸乡里亲戚多,又有去到贵州省,分散源头各自居,前渡去到云南省,富宁县里好安居。”[28]
按此文所记,湖南的江华、永明、道州、兰山,广西的富川、金秀、荔浦、田西、泗城、百色、汪甸以及贵州、云南富宁等地的瑶族,都由潮州扩散出去的。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白水村《邓氏墓碑》记:“吾高祖原籍南京道到南海八万乡。”[29]
《瑶人来路经文》记:“瑶人子孙流下广东道潮州府、乐昌县、朱基巷(珠玑巷)。在八万里,治有田塘广阔居住。”[8]400
这“八万乡”“八万里”,何义?在何处?人们长期弄不清。笔者认为就是今广东陆丰市的八万镇。八万镇地处陆丰市东北部,东邻陂洋镇,西连城东、河东镇,南接博美镇,北靠陆河县,这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农业山区镇。此地汉晋时属南海郡管辖,故曰“南海八万”。这群瑶族登岸后,有一部分人的落脚点就选在此地,他们在那里“治有田塘广阔居住”。
另有一部分人则在“南海佛(浮)桥头”上岸。广东连山《过山榜》记:“盘王政(正)在南京十宝洞下到紫金山住居落业,又到南海佛(浮)桥头。”[8]393
这“南海佛(浮)桥头”,在瑶族文献中多次言及,是瑶族在广东很重要的一个居住地,有“祖地”之称。《十二姓瑶分基来路总图》记,“南海佛桥头住居为祖地”[8]454。《景板瑶人来路总图》也有此语[8]501。
“佛(浮)桥头”在何处呢?人们长期也不知晓。笔者认为就是今揭阳市惠来县隆江镇浮桥头巷。隆江镇自古商贸发达,交通方便,地理条件优越,资源丰富,素有“三百六十乡墟”之美称,是惠来县商贸业和轻工业的经济中心之一。浮桥头是隆江镇传统的治所,这里距潮州市很近,地图上直线距离不足40公里。
在瑶族“漂洋过海”之前,广东大地没有瑶族活动记录的痕迹。瑶族见于广东的活动,始于《述异记》。任昉(460-508年)撰《述异记》记:“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30]。这“南海”当指广东,盘姓是瑶族的一大姓,盘瑶时常被称为“盘古瑶”。可知,在任昉之前(5世纪末6世纪初),瑶族已迁到南海郡(郡治在今广州市)居住了,而且人口众多,分布广泛,“亘三百余里”。这样广泛的分布,应当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由此溯推“东晋晚期瑶族漂洋过海到广东”,也是合理的。
最后,还得作一些交代:我们所说的东晋末年瑶族“漂洋过海”,大家不要理解为“唯此一次,别无来者”。瑶族的迁徙是分批、分时段进行的,我们所说的应是最早或最主要的那次漂游,其他的批次只好略而不论。瑶族是因多批次的漂游,才出现“分散各地”的历史情状。
[参考文献]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374.
[2][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156
[4][西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964.
[5]释慧皎.高僧传:卷第一[M].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42.
[6] 莫金山,李大庆.会稽山齐贤洞:瑶族文化发祥地[J],广西民族研究,2019(4).
[7]盘承乾,等.盘王大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62.
[8]黄钰,辑注.评皇券牒集编[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9][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2020:2865.
[10][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99.
[12]李本高.瑶族漂洋过海析[J].广西民族研究,1988(3).
[13][北魏]郦道元.水经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5:548.
[14][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578.
[15][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62.
[16]陈鸿钧.广东出土西晋“永嘉”铭文砖考[J].广州文博(辑刊),2015(00).
[17][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629.
[18][南朝·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9]李默,等.八排瑶古籍汇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1995:904.
[20]福建省编辑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M].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9:228.
[21][宋]朱彧.萍洲可谈[M].李伟国,点校.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87.
[22]郑德宏.盘王大歌[M].长沙:岳麓书社1987:243.
[23]盘才万,等.乳源瑶族古籍汇编: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1187、867.
[24][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M].北京:中华书局,2006:86.
[25]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J].文物,1977(4).
[26]陳雅群.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G]//泉州文史委员会.泉州文史资料:第26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215.
[27]盘艳明,邱明.盘瑶祖居地位置及南迁情况[M]//中国瑶族文化传承研究中心组.瑶学论丛:第二辑,沈阳:沈阳出版社,2019:70.
[28]奉大春,等.平地瑶歌选[M].长沙:岳麓书社1998:7.
[29]黄钰.瑶族石刻录[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404.
[30][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上[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潘宏纹
收稿日期:2021-09-10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XMZ012)。
作者简介:莫金山,男,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广西瑶学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瑶族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