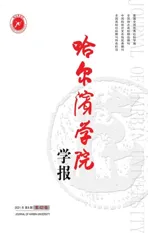寓意解读:《边城》三题
2021-01-16黄志军
黄志军
(泉州师范学院 应用科技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沈从文曾说,他创作《边城》是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遂“借重”20世纪初叶湘西边远的小地方茶峒,几个“愚夫俗子”——老船夫一家与船总顺顺一家四五人,被一件普通人事——儿女情事——因缘际会牵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一份体认和反应,从而“为人类的‘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45)沈从文以小见大,以“一”观“天”,其所推崇和表现的“人生形式”是一种人生与人心的存在状态,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阶段,它跟人、人性、人事以及这三者所处的环境——大自然/“天”紧相关联。正是在“天”的影响与控制下,人在其一生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其“人生形式”因受人性与人事的直接影响而呈现出不同形态。而沈从文在构建和表现它们的过程中的手法及寓意,值得通过文本细读来作一解析。
一、《边城》的大小虚实
沈从文的写作用意,在《边城》中可谓开篇显志——小说第一自然段,字数不多,意蕴却颇为丰富。沈从文采用俯视视角,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小”见“大”,由实至虚,虚实交互,廖廖数笔便将故事发生的自然环境及相应人物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为全篇定下了田园诗化的民间叙事格调。其以“一”观“天”的用意彰显了作品主旨寓意指涉,也为全篇呈现了解构的目标与意义,值得细究。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在这一段里,沈从文以“一条官路”“一个地方”“一小溪”“一户人家”“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一系列的“一”,还有“小山城”“小溪”“小塔”——这一系列的“小”——来呈现其在全篇中“以‘一’观‘天’”、“以‘小’见‘大’”(广大而普泛的整个人类社会)而反映普遍的人生状态的立意用意,即以边城的这一个小家庭因一件儿女情事而牵连出来的人事悲欢,来书写和呈现美好的人性、美好的人事及其遭遇的挫折与不幸,展示人因美好存在状态的渐渐消失而困窘进而渐渐呈现并占据人的现在与未来,在这一叙事过程中沈从文深深的叹惋则萦绕其间。
上述一系列的“小”与大自然的“大”相映衬,呈现出“人事”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在“天”及“天意”面前的卑微无力。然而“人事”虽小,当其落在人类任何个体(与大自然相较个体显然卑微弱小)身上。大自然即“天”所施加的力量与影响,却非任何个体所能轻易承受的,往往需要他们承受长久的痛苦与忧伤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不仅于此,四川湖南边境、官路边城、溪水白塔等现实风物,这些是实景,是现实与客观的描述。而老人、女孩儿和黄狗,则是虚拟的存在,诚如小说在后文中所述——“大自然长养”他们、他们在“风日里长养着”,他们依托前述现实风物——四川湖南边境、官路边城、溪水白塔等而存在,但他们早晚终将从这个大自然中消失不见,亦如小说中所写——“老的已作完了自己分上的工作,安安静静躺到土坑里去了”“老年人是必需死的”“人死了哭不回来的”,并永不再重返这个由大自然所掌控的存在世界里。而前述客观存在的现实风物中有个特别的存在物,即白塔,它不是大自然造就的,而是人们建造的,经年之后塔虽然会坍塌,亦如人的病殁,但正如小说后文中所写——白塔在大雷雨之夜圮坍之后,人们又重建了这座白塔。然而诚如与白塔在同一时间里死去的老船夫的生命却永不能重还一样——重建的白塔虽是白塔,却物是人非,因为此塔非彼塔,甚至人们心里所赋予新塔的意义同旧塔相比都是有所区别的。新塔不过是“有比没有好”而已,所以塔的重建仅仅是人们聊以寄托一种美好的愿望,旧塔所代表的一切终究是不存在了。沈从文如此建构,这就意味着,小说后文正是将上述由传统民间风物(白塔)所象征的美好的人、人性和人事,以及由这一切所构建的人的诗意与美好的存在世界解构开来,喻指这美好的一切将不再重还,即使人们主观意愿重建,也仅如白塔的重建一样,只能是新的一座对已消失的美好的人生形态的祭奠与纪念,一种徒然的心愿而已,只能令人扼腕长叹。
二、《边城》的四季人生
人是大自然的产物,生养在大自然中,受春夏秋冬季节更替的时令变化和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所影响和控制,因而懵懂无知、天真纯朴的儿童,其生理和心理都得逐渐发育成长为青年,在荷尔蒙的作用下思慕和爱恋异性,积极寻觅婚配,在身心条件都成熟后结为夫妻并生儿育女,侍奉老人,且等待人生终结的到来。这一过程恰如四季时令变迁的易理——在大自然即“天”的推力作用下,明净温婉的春必然升温进入高温湿热、万物疯长的夏;但物极必反,夏盛而衰,降温降水,遂进入温凉而万物成熟的秋;大自然进一步降温,万物凋敝,进入寒寂的冬天,植物保存种子,动物保守机体,蛰伏静守以待下一个轮回之春的到来。
正是因为在大自然之力——“天力”的推动下人必须“成长”,必然走向生理和心理的成熟,而生理的成熟是能生儿育女,心理的成熟则是能面对和承担人生中一应繁琐与烦苦的人事,承担“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因而“成长”的过程就是走向人的困境——“长受苦”的存在状态的过程,是一种出离人在娇嫩质朴、纯真无忧的儿童时期所拥有的美好身心状态、美好人生阶段即“春天”的过程,是一种日渐走向人事烦苦的过程,是从“春天”出发,经过“夏天”的狂热,“秋天”的凄凉,最终走向“冬天”的沉寂与终结的过程。
而《边城》的故事情节正是被沈从文精心设置从而“先后经历”了三个绵长的夏天、一个短暂的秋天,而终结在寒寂的冬天的。春(在《边城》中以象征的方式存在)夏秋冬这四个时令季节明明白白地与情节及人物命运的发展同步推进,亦步亦趋,沈从文正是在此过程中实现他所要突出表现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换言之,在《边城》中,季节这一时令环境与沈从文所表现的“人生形式”之间存在明确对应的象征关系。沈从文按人的一生自出生至死亡的存在过程的先后形态差异,将之与大自然的四季相对应,在“天人合一”的象征过程中,先后书写人的四个不同存在阶段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一)人之初
在《边城》中,按故事时间、环境的先后及人的成长过程,首先书写的显然是沈从文最为推赏的“人生形式”——人最美好的性灵的呈现状态——即人生的早期阶段。“人之初”的孩童时期,在作品中正是13岁以前的翠翠所呈现出来的“一只小兽物”的性灵状态——俨然就是大自然的精灵!其呈现的是一种纯净、朴野、良善、美好的性灵状态,是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即天人合一的存在状态,在人的一生中唯有在“人之初”阶段才能与之相若。有如“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为,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於造化之外”。[2](52)作为被沈从文“安置”在荒僻之地“边城”的女孩翠翠,“在大自然的长养与教育下”,她人生的前十二三年,即她“天真活泼,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的童年,因未解人事,尚未沾染人事的污浊、惹上人事的烦苦,所以“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这是典型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状态。倘与她在后文中走向“成熟”的成长过程中的烦苦人生相比较,“人之初”阶段的翠翠尚无她后来渐渐长大后伴随而来的夏天里她的恋爱的苦闷、无助、忧伤和误解,更无秋天里爷爷死后她的孤寂与痛苦,以及冬天里她的寒寂、忧虑与长受苦。因而现阶段仿佛是她人生的春天,所以在沈从文笔下她的性情、精神品格等皆与春天和谐一致。这一段“人之初”的岁月,也就是翠翠人生的春天阶段,也是小说所构筑的人物成长的“春季”。
(二)青春期
在大自然力量的推动下时令进入“夏”这个“宽假万物使生长”的高温湿热季节,[3](P78)“天力”促使翠翠走向生理与心理的成熟,以便承担作为女性应担的那一分哀乐、那一分人事——在小说中表现为“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于是——
“时间在成长她,似乎正催促她,使她在另外一件事情上负点儿责。……这女孩子身体既发育得很完全,在本身上因年龄自然而来的一件‘奇事’,到月就来,也使她多了些思索。”
翠翠同大自然上升的温度与季节的更替同步发展至“夏天”——青春期。翠翠身体成熟,具备了生儿育女的生理条件,然而翠翠心理却远未成熟,尚不完全具备做茶峒人家媳妇的基本条件。所以沈从文安排大老天保这个爱慕翠翠的年轻小伙直率地对老船夫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照料家务的媳妇。”
换言之,翠翠必须身心都成熟,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才能面对成年人所应面对的一应人事,但这一点仍得由“天”来推动翠翠去完成。所以沈从文写道:“不过一切皆得在一份时间中变化。这一家安静平凡的生活,也因了一堆接连而来的日子,在人事上把那安静空气完全打破了。”
显然,沈从文认为人的生理成熟靠大自然,而心理的成熟则靠“天”管控之下的“人事”。这里,“时间”与“日子”即指时令,指大自然,指“天”,“天”之力也将实实在在地落实在“人事”上。这段文字也暗示“好景”不常在——大自然所长养出来的人的美好的存在状态总要变迁,“安静平凡”的美好生活终将因来临的“人事”而遭“打破”,是“人事”破坏了安宁、祥和、纯净的人心存在状态。换言之,“人之初”这一人生最美好的状态是被“人事”所破坏的,且影响人心的存在状态。
对此,小说是集中以三个“端午节”所处的季节时令——夏天——来重点和集中演绎主人公翠翠及人们围绕她而进行的儿女情事的:倾慕、求婚、相思及因之而来的误会与愤懑等。然而这种基本上只因生理成熟而来的儿女情事,其力量显然还不足以促使人的心理成熟,还需“天之力”来进一步推动,因而故事不可逆转地进入了“秋”——“緧迫品物使时成”的季节。[3](78)
(三)緧使成
从夏进入秋,其间的转折就是夏末秋初的那场大雷雨。为什么是大雷雨?因为大自然推动有生命的万物的发展,靠的就是水与温度:春要进入夏,需要升温加丰沛的雨水;夏要进入秋,需要降温加雨水。此外,大雷雨还在沈从文笔下承载“天意”这一任务,也就是担任大自然的“推手”这一角色。“緧迫”一词,显见采取的是外在的力量来“迫使”女主人公心理成熟,那么,似乎在“天意”看来——当然实质是在沈从文看来——仅靠一场大雷雨来“打破人事”显得力度不够,“天”因此再加之以象征边城风水(“风水”即是“天”,即大自然的力量)的白塔的圮坍,再加之象征摆渡边城人们的精神灵魂至其终极追求的“彼岸”的渡船被大洪水冲走,又再加上一个于故事情节极为重要的、亲和纯朴的老人的死去,四者之力叠加,方才撼动主人公翠翠封闭自守、自幻自恋的心扉开启一线缝隙。所以,那个大雷雨之夜老船夫死了、白塔圮坍之后,故事陡转直下,饱染凄凉的气氛,而亦步亦趋紧跟情节的时令也陡然急转入秋天。爷爷死后前来陪护孤女翠翠的杨马兵告知了翠翠她所不知道的一切——
“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时所不提及的许多事。……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全明白了。翠翠把事情弄明白后,哭了一个夜晚。”
所谓“明白”,就是“懂得”,并且承担。在“秋”的“緧迫”之下,翠翠似乎自此心理“成熟”了——具备了做茶峒人儿媳的心理条件,已“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可随时嫁到船总家去做媳妇,生儿育女。现在,翠翠就只等那个远在辰州的心上人二老傩送的归来。
(四)物终灭
很快,情节发展到了最后,时令也同步到了冬天。沈从文仅以一段话来为全文、也为翠翠的爱情和人生画上一个句号——“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冬天,大自然的推手已进一步降温,进入了万物枯候或终结的时令;而已被允诺做船总顺顺家儿媳的“成熟”的翠翠,现在则进入了寒冷而长受苦的渐趋寂灭的人生阶段——“冬天”。这是万物的循环,也是人生的必然。但是人在身心上是没有循环轮回的机会的,诚如《边城》中所写“老年人是必需死的”“人死了哭不回来的”。所以在此“冬天”,人除了等待不日将至的死亡,余下的就只有回忆和怀念——回忆和怀念人们在“人之初”的春天阶段大自然所赋予人们的那些因本能而来的“小兽物”般的性灵与快乐,以及夏天/青春阶段充满激情和幻想的略带忧伤的儿女情事,它们是人生中最美好阶段的内容,且永远不能重现了。
因此,沈从文在小说结尾将故事永远定格在冬天里——碧溪岨山崖下女主人公苦候远在辰州的心上人(返回茶峒来迎娶她)的场景,这是在寒寂的长受苦的“冬天”里所展开的绵绵无绝期的枯守,等待那个远在“夏天”的心上人的回来。因为那个在第一个夏天里邂逅并在第三个夏天里爱上翠翠的小伙儿傩送,也是在第三个夏天里因误会和其他不幸的“人事”的扰攘下负气出走的,所以,翠翠的爱情实际上是在夏天遭遇并开始,却也是在夏天里被终结的。在小说结尾,几乎失去灵性与生机、失去主动与幻想的“成熟的翠翠”鱼肉一般被“天力”或“天命”搁置在命运的几案上,枯候她那几无悬念的已被天命与“人事”所裁定的人生结局,虽然她才十五岁!因而小说中这个在“冬天”里——人生的困境里——枯守的意象,其所暗指的即是那个有如“人之初”的美好的存在状态的人生阶段已在“天力”的作用下永远地结束了。
人们难以想像,无论傩送回不回来,无论翠翠最终嫁给了谁,当有一天人们看见二十岁左右头挽发髻的翠翠背上背着一个婴儿,左手提一桶衣服,右手挎一竹篮菜蔬,从吊脚楼走下青石阶来,到茶峒河边浣衣洗菜,显然,这就是大老天保心目中的那个能“照料家务的媳妇”和能做“一切正经事”的茶峒媳妇,这就是一个身心都已成熟的普遍的广大家庭主妇的形象与命运归宿,是千百个“翠翠”的形象与命运归宿。那么,这时,那个作为大自然的精灵、大自然的化身的名叫翠翠的女孩子,那个“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的“小兽物”又在哪里呢?所以,什么叫美好的事物一去不复返?什么叫“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或许才是沈从文对美好人性消失不再的讴歌与叹惋。所以不难理解《边城》故事为什么终结在冬季。当一个人的身心经历过人生的夏与秋并完全成熟后,他的人生,剩下的就是置身并面对万物终灭的冬天了——那就是“长受苦”。
三、《边城》的天命大鱼
其实这就是让人们发现,《边城》故事的悲剧,或者说造成小说中几个愚夫俗子因儿女情事而起的伤心与不幸的,乃是大自然本身——在小说中常称之为“天”:“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船总顺顺也说:“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显然,无论是老船夫还是顺顺,都如是看待自家的悲剧,都归因于“天”,而在他们的语境里,也就是“天命”。
“天”是一种力,一种神秘而无形的力,但它通过转承在人们身上而呈现为具体的力量。在《边城》中,它可以作“一物双面”解:一方面“天”是大自然,另一方面“天”是命运(命运常常是大自然之力与人事之力的合力作用与结果),二者或可合称为“天命”。“天命”在一定层面和程度上表现为大自然的时令(季节与节气)、温度、雨水、雷电、植物等,以及与之紧相关联的其他物、人、事等。在《边城》中具体表现为春夏秋冬和端午节等,表现为温度、雨水、雷电、篁竹、虎耳草等,还表现为圮坍的白塔(因大自然之大雨冲击、雷声震撼、重力作用,再加之属于人为的年久失修,这些皆为“天命”的作用与表现)、老人的死去(人体的生老病死)、少男少女生理与心理的成熟(大自然与人事的合力作用)、人们内心的忧伤、美好人事的消失以及人们因之而起的怀念(人事之力作用的表现与结果,这些皆为命运的作用),等等。
“天”这种力,在《边城》中还突出表现为沈从文用心构建的“水里大鱼”意象,其象征一种命运的力量。沈从文早在小说第四节就颇为用心地设置情节,安排翠翠与傩送这对年轻人邂逅,借傩送之口说出“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从而把导致翠翠爱情悲剧的力量——“水里大鱼”引了出来,且一语成谶!事实上,翠翠爱情悲剧性的转折正是天保为翠翠的事赌气出走而意外淹死。换言之,翠翠的爱情的遭际正是“水里大鱼”作祟的结果。老船夫和船总顺顺虽然都并不在意那句“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的话,但二者都不约而同地感叹儿女婚事的不合乃为“天意”。
沈从文的侄子、著名画家黄永玉为小说《边城》画过两幅插图,其一即《大鱼》,形象地表明他读懂了《边城》。因为同样在湘西边城风日里长养大并走出来的黄永玉,他对沈从文的亲近、了解与理解非一般人所能及。在这幅逆时针构图的《大鱼》画作中,黄永玉在构图方面有意将鱼最大化,以体现出“大鱼”之“大”,此即“天”之“大”,正是命运之不可违逆。此外,图中大鱼的位置恰好介入在一对男女之间(他们分别代表傩送和翠翠),巨大的鱼头张开大口凶恶地咬向女孩,而女孩虽侧身走避,却是低眉垂目回首顾盼,显见其情愿而却又无知地面对人事以及她的爱情命运;而男子的头被黄永玉画成与画中“大鱼”一样的鱼头状。显然,黄永玉也认为,女孩爱情的悲剧也是由这一“鱼头男子”所造成的,是由她的爱情所对应的异性一方因爱而起的人事所摧折的!换言之,翠翠爱情的悲剧是傩送所代表的男方对翠翠的爱造成的,是因为傩送兄弟二人为争夺翠翠,兄长负气出走而意外溺亡,而傩送及父亲顺顺都认为自家亲人的死是由老船夫一家造成的,自此以冷脸对待老船夫,导致老船夫绝望地死去。可见,在黄永玉看来,“水里大鱼”就是傩送的化身,它承载翠翠的爱情,也吞噬了翠翠的爱情,同时也是翠翠所面临的命运的象征。所以沈从文安排二人在第一个端午节的傍晚的水边邂逅时,特意让傩送对翠翠说“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这个“回头”,就是一种时间的顺承。
总而言之,“天”所指代的命运的力量,在《边城》中是颇为引人注目的。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有意将《边城》里的主要人物及他们的命运,与一些特定的动物联系起来,并寄寓了特别的意蕴。诚如傩送同翠翠的婚事,终因“水里大鱼”而牵连延搁下来,悬而未绝。这些,总还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