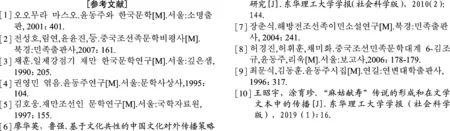异域体验,文致内融
——在华朝语文学对中国文化的接受问题研究
2020-12-10夏艳
夏 艳
(吉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这里有朝鲜文学任何角落都无法找到的大陆文学开拓者的文学特征和新气象,不能不说这是全朝鲜文学的一个巨大收获,值得作家和编者骄傲……”[1]从廉想涉为《发芽的大地》所做的序中,不难看出其对在华朝鲜文学最初收获的肯定。20世纪初,日本的殖民侵入造成朝鲜半岛农村经济的崩溃,无以维持生计的大量流民涌向北部与半岛仅一江之隔的中国东北。寄居于此的朝鲜人受到中国自然生态、城市生活、语言习惯、宗教民俗等多方面影响,日渐形成“朝汉并蓄”的文化心态。有关这一时期朝语文学的国内外研究,大多集中于朝鲜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事实上由“中国形象”亦可推知他们正接受着“中国影响”。从外族文化吸收视角探究在华朝语文学,有助于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精髓。
1 作家心态——乡愁中憧憬
这一时期在华活动的朝鲜移民作家群体生存于两国的夹缝间,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缺失使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混乱。徘徊于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始终未逃离日本殖民侵略的阴影。在华朝语作家存在着普遍的文化身份焦虑,他们身上带有不同程度的“他者”怀乡病,属于一群漂泊而执着的“缪斯”。一方面对故乡依恋不舍,通过思乡主题进行倾诉吐露;另一方面又将中国视为延续民族生存的沃土,经由“北乡”主题显形于外。乡愁中苦闷、焦灼中筹谋,不仅伴随着作家的创作过程,而且浸入到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中。
这一时期朝语文学作品或寄情自然、或回忆儿时美好、或浓缩生活片段,都从不同方面流露出对故土和家乡的思念。20世纪初的那场大规模移居,是大部分朝鲜人无以为继、迫不得已的选择。移居过程的颠沛流离和凄楚无助,触动了他们思乡的神经。李民求认为:“‘乡愁和忧郁’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移民文学理所当然要描写乡愁和忧郁。”[2]二十世纪上半期,在华朝语文学的中枢就是表现移居民对故乡深切的缅怀和眷念。无论是自然景物的描绘,还是对往昔生活片段的怀念,都映射出离乡和失乡的苦涩和无奈。
“在战胜现实困苦和实现异域梦想的行程中,我们含泪吟唱”[3]。这一时期表现思乡情绪的诗歌作品众多,如宋铁利的《五月》《故乡》,尹东柱的《故乡的故居》《数星星的晚上》,千青松的《先驱民系列》等都通过现实意象表达着对故乡的不舍和追忆,这其中尹东柱的思乡作品最具代表意义。“郑翰武认为,在中、韩、日三国的辗转中尹东柱切肤体会到失乡情,北间岛的生活感受浇灌了其作品母题的失落感”[4]。迥异于其他生于朝鲜半岛的一代移民作家,尹东柱的出生地就在中国东北。承袭朝鲜血脉、出生于中国,他的诗情始终徘徊于“故乡”与“他乡”之间。无论是《故乡的故居》中儿时回忆留下的心灵慰藉和故土追忆,还是《数星星的晚上》中仰望星空勾起的孤寂和憧憬,都寄托了尹东柱内心的故乡情。乡愁基调外,他的诗歌还常常透出一份源自痛失过往的悲凉。“虔敬中思乡,自省中抗争”的创作特质使其成为东北的朝鲜文人中“在韩国人气最高、最受尊敬的诗人”[1]435。
然而,沉浸于过往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在移居完成后,朝鲜人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定居下来。鉴于日本殖民的强势,他们深知无权抉择自己未来的去留。为维持民族的永续发展,将“间岛”(1)“间岛”为1877年咸镜北道流民私自越江开垦之地,指图们江北岸中国所辖的光霁峪前的一块面积不大的江中滩地(位于今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井境内),被称为“垦岛”,音译为“间岛”。视作未来的寄居所和生存地,是移居民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他们全部希望所在。在与自然抗衡中付出的血泪和艰辛,常人无法想象和体会,但正是这种落差和苦难,培养了移民作家对民族未来生存沃土的情愫。倡导“北乡精神”和专注农业发展,成为朝鲜人意在实现永久扎根的明证。
“北乡会”成立后,安寿吉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北原》、第一部长篇小说《北乡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代表作《北间岛》均以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和安居为主题展开。作为在华朝语文学的代表作家,安寿吉的主要作品名称均携“北”字,不难看出他对“北上”和定居的属意和珍视。这种源自北乡挚爱的“北乡精神”正是建立在农民对土地和农业的热爱基础上,同时渗透出朝鲜人顽强不屈的生存意志。在《牧畜记》中,安寿吉常表露出朝鲜人对第二故乡的深爱。小说中赞浩之所以放弃教师职位而投身于牧畜业,原因有两点:“第一,自己没有为学校立下功劳,也不似亡命于间岛的志士一样拥有演讲家的口才;第二,拥有一百五十万同胞的农村在热切地期待学习者的出现。”[5]对农业和畜牧业的热忱回归,正是源于赞浩对新故乡的深挚情感。
伴随着追忆过往和憧憬未来,流落异乡的朝鲜移民开始试图在新环境中寻找自己的定位。但在身份认同的徘徊中,他们始终难以改变自身的漂泊状态。“对于李旭和金昌杰,韩国和中国分别认为他们属于韩国文学和中国朝鲜族文学;韩国将安寿吉、姜敬爱和金昌杰归于东北韩国文学者,而中国则将安寿吉和姜敬爱视为外国文学者……”[1]401从颇具争议的文学归属不难看出,他们始终区别于朝鲜半岛的朝鲜人和作为汉族的中国人,文化隶属的二重性成为在华朝鲜人最显著的身份特征。
2 生活方式——素常中自适
“朝鲜族文学融合了中国文学和朝鲜文学,它既使两者有了碰撞的机会,又开辟了了解两者的通道。”[1]445这个特殊的文坛并受朝鲜和中国双重文化的影响,朝鲜作家笔下呈现出双文化融合的意象。安寿吉、金昌杰等作家的作品中的“二汉人”从语言、形象到思维方式,都和中国人相差无几。移居初期,朝鲜人对中国的生活环境和方式习惯保持抵制和抗拒的姿态,他们更多的是站在朝鲜人的视角,将中国人作为异族审视。这一时期朝鲜作家的自我身份意识十分强烈,在对本民族肯定意识基础上形成对其他民族的全盘否定,但这层自我封闭和消极排外的盔甲并非牢不可破。“自从人类进入群居社会, 不管是处于东方, 还是在西方, 不论生活于古代, 还是现代, 时空、地域、习俗和民族的差异, 乃至文化上的差异, 都不能掩盖人类的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及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的共通性。这众多的一致性和共通性构成了超越时空、地域和民族等界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6]在无法回避的日常交往中,朝鲜人开始对中国人的饮食、服饰、居住、节日等生活文化有所接触,并表现出期待了解和探寻的倾向。
及至后期,朝鲜作家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开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转化。对于不同阶级的中国人,作家在刻画上的差别体现在贫苦阶层的中国人表现出勤劳、真诚、温顺的本性。“移居民此时受限于半岛的理念活动,开始在东北探索新的出路……”[4]78姜敬爱的《菜田》中出现了中朝民族互助的情节。“作家已经将移民的生活融入身份认同的共同体,与中国人和谐互助、共生共存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7]。
从最初搬迁对汉族人的排斥和反感,到逐渐了解和共处,再到后来的模仿和融合,这一变化轨迹勾勒出了朝鲜人从移居到定居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从排斥到接受的过程。同时也伴随着对移居民从朝鲜人到朝鲜族的称谓变化而完成的。这种变化在文学作品中,是以被内化的“中国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即建立在“北乡情结”基础上的中国元素渗透。从朝鲜半岛到中国东北,不仅意味着生活场所的转换,而且在新身份认同基础上形成的“非朝鲜人”心理定位,也突然让自己深感彷徨和忐忑。
身份转换的阵痛虽不可避免,但仍无法阻隔人们接受新事物的趋势,金昌杰在《第二故乡》中表现出的强烈生存意识已成为新身份认同的宣言。“虽为朝鲜人,却与朝鲜半岛的朝鲜人不同,他们带着对自身新国民的身份认同,或称其为作为移居民的生存欲求,并站在移民作家的立场上将其表现出来”[12]243。安寿吉被视为移民文学的代表,不仅在于其作品展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容纳,更源自其将在朝鲜人中广泛存在、融合中国元素的“二汉人”(2)“二汉人”为移居至中国较早的朝鲜人,其在语言、穿着和思维方式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他们利用其作为文化中介的身份,充分享受文化同化带来的红利,而这一惠泽获得的前提却是建立在剥削、抢夺和压榨本族人血汗基础上的。形象的成功提取和塑造。“二汉人”因搬迁至中国时间较早,主动或被动的中国文化接受给他们带来了物质和名利上的丰厚收益。受益后,他们自然更乐于吸纳中式文化和思维方式。虽其目的只是通过融入上层阶层来维持和扩大既得利益,并不存在文化传播的初衷,但客观上他们却被置于民族沟通媒介的地位。在当时,这一现象的发生已非个例和偶然,随着带有混杂民族特征的朝鲜人群体的扩大,“中国化”已渐入移居民生活的常态并不断被扩散开来。
3 自然风俗——守望中内化
“这些作品集蕴含着当地的真实气息和面貌,它将半世纪的移民体验融入了浸透泥土气息的文学”[4]205。可以看出,崔其正认为东北朝鲜文学不但展现了中国的生活风貌与自然民俗,也投射出朝鲜作家的处世态度和社会体验。作品中的自然风俗,主要通过特定景致、特殊物品和田园生活的描绘表现出来。“沉浸于长白遗韵和龙江竹篱,倾情于松花杏村,尽享海兰沙场的掌故……目睹渤海遗址的基石”[1]421。作为《金达莱》吟咏的先驱者,朴八阳已将长白山、黑龙江、海兰江等东北风情收纳其中。
尹海荣在诗歌《海兰江》中,依托见证朝鲜人移居历程的海兰江来歌颂朝鲜民族坚韧乐观、独立自强的不屈精神。无论是“繁星点点”的天上,还是“人烟阜盛”的地上,海兰江都汇聚了朝鲜移居民为开创生活栖息地付出的汗水和泪水。诗中引入年轻勇士战胜邪恶势力的故事,喻指人们为守护家园和实现民族独立而做出的牺牲。“倾心于龙井瑰异的景色,沉溺于深沉的乡愁,诗人将其鲜明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融汇于此”[8]83。 诗中将特定景物作为媒介把朝鲜民族的特质与中华民族的壮举结合在一起,奔流不息的海兰江水不但寄托了朝鲜人的民族爱,同时也饱含了他们真挚的东北情。
诗人李旭出生于中国,因此对“间岛”怀有不同于其他朝鲜作家的特殊情感,这种挚爱源自对生养故乡的依恋和憧憬。在作品《帽儿山》中,“诗人不但借用西方的创世神话,而且把朝鲜民族‘太白山和神坛树下’的檀君神话也引用来,将帽儿山形象化为创造生命的‘伟大古人’”[8]178。透过帽儿山这一意象,李旭对“间岛”及其自然景观的热爱不言而喻,一贯的乡土情和自然爱投射出作者长久以来积蕴的东北挚爱和中国情结。《镜泊湖》《罗子沟》《埋葬在豆满江》等诗作,单从题目上便不难看出令作家长久萦怀的东北景致魅力。
此外,通过特定物品来体现民俗风情的作品也不在少数。金朝奎在作品《胡弓》的开头部分,就以黄昏下的地平线作为背景,传达出演奏胡弓时的哀怨和踌躇。“日暮渐浓……到了夜晚,灯盏也必须去适应风俗”[8]。作为移居民族,朝鲜人在陌生环境中遭遇的种种困境,会使他们自然地流露出思乡之情。然而,在移居现实无法改变的前提下,他们必须学会接受和适应,这其中既包括习惯和心态,也包括民俗和思想。“胡弓”的演奏,虽以悲怨的曲调透露出人们的移居苦,却也展现和表征了饱含异域情致的生活取向和民俗文化的渗透渐融。
在日本殖民侵略十分猖獗之时,部分朝鲜作家在作品中却刻意避开残酷的战争景象。这种重归自然的追求,是人们期待远离世事纷扰、寻找内心平和理想的映现。相对于充满邪恶与杀戮的环境,作品对田园宁静平和的描绘与追求就显得十分可贵。在众多在华朝语作家中,尹东柱可以说是最接近自然描写的作家。尹东柱出生于龙井明东村,儿时优美的自然环境经常在其诗歌作品中再现。但这种再现并非止于追忆美好,作家意在通过自然的纯澈无暇反衬出现实的罪恶血腥。其弟尹一柱在回忆录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有时,他坐在树林里仰望升起在夜空的星星,或是遥望远处的河水。他默默地坐着,我虽然少不更事,却也能感觉到他心潮澎湃在憧憬着什么”[9]。《春天》的金达莱和云雀、《少年》人与自然的融合、《山林》的博爱思想、《花园花开》的内心平静都在微观世界的审视中歌颂着朴实的信念,映射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命哲学。尹东柱的田园守望,既包含了对硝烟和侵略的抵制,亦蕴含了对现地风土人情的守护和挚爱。在从朝鲜人向东北人的过渡中,自然景致和民俗风情的热爱和吸纳一方面排解和消散了离乡后的苦闷和孤寂,另一方面也引导和加速了人们对新环境的熟悉和接纳。
4 传统文化精神——浸润中萦怀
在华朝鲜人身上表现出的东北特性,可以看作是朝鲜人向中国人过渡过程中的渐变媒介,它使由朝向中的身份转换避免了急转、得到了缓冲。20世纪上半期的在华朝语文学作为存在于中国的异族文学和朝鲜族文学的前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十分全面而深刻。之所以如此,与移民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民族了解的不断加深密不可分。在华朝语文坛与韩国文坛在作家身份和创作语言上是一致的,但就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来说,二者却差异巨大。在有别于朝鲜半岛的异国环境中,在华朝语文坛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吸收和储备。这种吸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中式意境的自然生成和中国语汇的大量介入。
中国化元素对在华朝语作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在研读中国古典文学过程中开始对“中式”创作产生兴趣,进而在创作中尝试摸索“中式意境”,这其中李旭十分具有代表性。作为出生和成长在中国的朝鲜作家,李旭受到祖父和父亲的影响,自幼对汉学有着深厚的挚爱和钟情。正是由于对中国古代汉文诗歌创作特点及创作手法的谙熟和承袭,在他的诗作构图上经常呈现出主题豁然和对比强烈的意蕴。他回忆道:“我自儿时起读过大量汉诗,谙熟诸多含蓄和对仗等格律诗写法,关注汉诗后创作了数百篇绝句和律诗。”[8]190-191得益于汉文诗歌方面的前期积累,李旭的创作形式和技巧都流露出中国古典浪漫派的倾向。从他的作品中,既能体会到李白清新飘逸的诗风,又能感受到苏轼婉约旷达的理想。总体上来看,作品情感深挚、意境强弱分明,体现了对传统象征性手法的继承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旭可以称作是中国朝鲜族诗坛的中流砥柱——既是伪满洲国时期朝鲜人文坛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鲜族文坛最初的诗人。”[8]192
在传统文化精神的接受方面,文本语言的体现十分直接和显著。“明清时期是俗文学发展的兴盛时期。”[10]封建王朝末期,由于受到中国语言和文学影响,在文字产生之前朝鲜人使用汉字书写,但在读音上使用朝鲜语,这种记录方式被称为“吏读”。而二十世纪以后在华朝语小说中出现的中国语汇则与此相反,他们在作品中使用朝鲜语书写,但在读音上传达出的却是汉语意义。由于这些词语在朝鲜语中不存在,所以作家不得不使用汉语在其后进行标注,这样可使读者直观地理解词语的含意。作为执着于“北乡情结”的作家,安寿吉在其作品中进行的汉语标注最具代表性。如《土城》中66处、《稻子》中65处、《黎明》中58处,而在长篇小说《北乡谱》中则高达四百余处。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朝鲜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汉语词汇使用已十分普遍。及至目前,国内朝鲜族使用的语言中有近60%的汉语词汇,而且比例还在不断升高,这种语言杂糅状态的形成正是始于百余年前。
5 结语
20世纪前半期的在华朝语文学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形于无声、成于无形,它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下生根、发芽,并不断结出具有跨族异色的文化果实。可以说,具有强大感化力和渗透力的中国文化,从异族深度吸收的侧面更彰显出其博大深厚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