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论归义军建立初期与唐中央的宗教交往
2020-12-06胡可先虞越溪
胡可先 虞越溪
(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浙江 杭州 310058)
悟真的创作与生平,敦煌遗书中留存了不少材料,加以他在晚唐归义军时期突出的政治地位与卓越的文学成就,就成为敦煌学者着重研究的对象。陈祚龙《悟真的生平与著作》(1)陈祚龙《悟真的生平与著作:关于敦煌文化的研究》,巴黎:法国远东学院,1966年。,续华《悟真事迹初探》(2)续华《悟真事迹初探》,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0年。,伏俊琏《唐代敦煌高僧悟真入长安事考略》(3)伏俊琏《唐代敦煌高僧悟真入长安事考略》,《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第70-77页。,集中于悟真事迹的研究;齐陈骏、寒沁《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徐志斌《〈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补四则》(4)齐陈骏、寒沁《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第5-15页;徐志斌《〈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补四则》,《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第65-68页。,集中于悟真作品的研究;张先堂《敦煌写本〈悟真与京僧、朝官酬赠诗〉新校》(5)张先堂《敦煌写本〈悟真与京僧、朝官酬赠诗〉新校》,《社科纵横》1996年第1期,第43-49页。,集中于赠答诗的文本整理;杨宝玉、吴丽娱《悟真于大中五年的奉使入奏及其对长安佛寺的巡礼》(6)杨宝玉、吴丽娱《悟真于大中五年的奉使入奏及其对长安佛寺的巡礼》,《吐鲁番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67-76页。,颜延亮《归义军设立前夕敦煌和长安僧界的一次文学交往——悟真和长安两街高僧酬答》(7)颜延亮《归义军设立前夕敦煌和长安僧界的一次文学交往——悟真和长安两街高僧酬答》,《丝绸之路》2012年第22期,第35-45页。,王庆卫《新出唐代张淮澄墓志所见归义军史事考》(8)王庆卫《新出唐代张淮澄墓志所见归义军史事考》,《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第12-21页。,钟书林《敦煌遗书S.4654〈赠悟真等法师诗抄〉探赜——兼论光复后的敦煌与大唐中央政权的微妙关系》(9)钟书林《敦煌遗书S.4654〈赠悟真等法师诗抄〉探赜——兼论光复后的敦煌与大唐中央政权的微妙关系》,《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3期,第50-56页。,关注到归义军张氏政权与唐朝的佛教交流。但是,关于他在大中五年(851)率领宗教使团出使京师一事,以及与京师大德所作之赠答诗合钞,都还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悟真所率宗教使团上贡图籍与奏疏,展示了敦煌的风采,为其后张议潭使团在政治诉求、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处理做了良好铺垫。悟真出使是臻于极盛的敦煌佛教对世俗政权干预的结果,同时也打开了唐归双方宗教往来的局面。宗教交往既使唐归双方在佛教典籍注疏上可以互通有无,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双方矛盾的润滑作用。
一、《阙题四首》所见张氏政权的三次遣使入京
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所录《悟真受牒及两街大德赠答诗合钞》中收有《阙题四首》,原抄写于S.4654V,又见于P.3645V,因第一首诗与悟真回赠京师大德的答诗《悟真辄成韵句》前四句相同,故被认为同属悟真所作,四诗如下:
敦煌昔日旧时人,虏丑隔绝不复亲。明王感化四夷浄,不动干戈万里新。
重云缭绕拱丹霄,圣上临轩问百寮。龙沙没落问年岁,笺疏犹言忆本朝。
表奏明君入紫微,便交西使诏书进。初霑圣泽愁肠散,不对天颜誓不归。
龙沙西尽隔恩波,太保奉诏出京华。英才堂堂六尺貌,口如江海决悬河。(10)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6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7-218页。录文参见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40页。
这四首阙题诗的背景和内容,学术界众说纷纭。徐俊认为“内容均涉及奉诏入朝,面谒龙须,与大中五年悟真赴长安献款有关”。颜延亮抓住“太保奉诏出京华”一句认为“张氏归义军时期称‘太保’者仅张议潮一人,其称‘太保’的时间在872年以后”(11)颜延亮《归义军设立前夕敦煌和长安僧界的一次文学交往——悟真和长安两街高僧酬答》,第39页。。黄征、张涌泉认为“张议潮归阙不返后,张淮深皆袭其叔父之职称,亦可称太保”(12)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87页。。然而我们考察张议潮与张淮深行迹,与诸说并不相合。张议潮咸通八年(867)应召入朝留居京师,直至咸通十三年(872)去世,没有“奉诏出京华”之举。而且张议潮是卒于长安而非归阙不返之时被诏赐“太保”,故张淮深“袭其叔父之职称”一说不妥。因此“太保”既非张议潮亦非张淮深。我们认为,诗中“太保”当指张议潭。一方面,张议潭确有“奉诏出京华”的经历,大中五年五月悟真入朝后,七月张议潮又遣兄议潭入京,并获封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和检校吏部尚书等职。而由《张淮深碑》所载大中七年(853)张议潭入长安为质不归可知,这一次张议潭应顺利回到了敦煌,故“太保奉诏出京华”应指张议潭带着诏书离开京师一事。另一方面,虽然张议潭从未曾获封“太保”一职,但一直以来归义军统治阶层内部对唐朝的分封职衔并不严格遵从。比如由《张议潮变文》可知,在大中十二年(858)或此后不久,张议潮未获朝廷分封便自称仆射,还在辖境内自称河西节度使(13)张议潮所修莫高窟第156窟供养人题记云:“(1)窟主□(河)西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尚书、……(2)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统军□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行图。”可知其在境内自称河西节度使。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73-74页。。悟真在《五更转兼十二时序》中也称张议潮为“尚书河西节度”,且自称“京城临坛供奉大德”,而“供奉”二字很可能是其为了提高名望而妄加的(14)参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7页。,故而此诗中悟真以“太保”称张议潭也是符合情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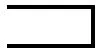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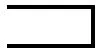
二、赠答诗与悟真使团进贡行为的考察
悟真的《阙题四首》描述了张氏政权三次遣使入京的情况,其中悟真使团与其他两批使团相比,究竟扮演着何种政治角色,又发挥着怎样的政治作用呢?答案应该从其进贡行为中寻找。而令人遗憾的是,传世史书中鲜有对悟真此次出使情况的记载,我们只能从悟真与京僧的这些赠答诗中考察其进贡行为。
首先,针对杨宝玉、吴丽娱提出的悟真向朝廷奉献佛教经论的观点(21)参杨宝玉、吴丽娱《悟真于大中五年的奉使入奏及其对长安佛寺的巡礼》,第73页。,我们略有质疑。两位先生根据建初《感圣皇之化有燉煌都法师悟真上人持疏来朝因成四韵》诗题以及诗中“鼓舞千年圣,车书万里同。褐衣持献疏,不战四夷空”(22)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9册,第9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份)》第6卷,第212页。录文参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335页。的诗句,认为悟真进献的是敦煌保存的佛经注疏,而我们认为此诗中的“疏”应该是奏疏。悟真出使京师之时,正值会昌法难之后唐宣宗大力恢复佛法之际,如果他持佛经来献,应在当时造成较大的轰动影响,但是除了建初一诗提及献疏之外,别的大德赠诗都只字未提此事,有些不合情理。再据《大宋僧史略》卷下“赐僧紫衣”条记载悟真入奏之事并未提及其进献佛经注疏,而对比同条关于咸通四年(863)西凉僧法信进《百法论疏》一事就有明确的记载。(23)[宋]赞宁撰,富世平点校《大宋僧史略校注》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60页。《旧唐书·懿宗纪》中也有咸通七年(866)沙州僧昙延进《大乘百法门明论》的记载。(2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60页。可见当时朝廷及后世史书对沙州僧向唐廷进献佛经注疏都是极为重视的,这也说明悟真所进者并非经疏。在唐代,向朝廷所进之“疏”大多是“奏疏”,属于奏议类文体的一种,其特点是围绕中心、分条陈事。P.3770V《僧悟真改补充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牒》记载此事道:“入京奏事,为国赤心。面对龙颜,申论展效。”(25)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第364页。P.4660《河西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也有类似的表述:“入京奏事,履践丹墀。升阶进策,献烈宏规。”(26)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3册,第26页。研究参见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80-414页。这些都说明悟真在上朝面君时为了沙州张氏政权能获得朝廷的接纳和支持曾侃侃而谈、建言献策。因此,我们认为建初诗中的“疏”指的是悟真对未来双方关系出谋划策的奏疏。除了奏疏之外,悟真使团还进献了何物呢?宗茝《七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二首·其一》云:“沙漠关河路几程,师能献土远输诚。”在古代,“献土”很有可能指的便是献上地图,因为地图是非常重要的军事资料,献地图就相当于将疆土拱手让人,所以悟真使团为表忠诚很可能进献了河西地图。此外,可道《又同赠真法师》云:“远国观光来佛使,边庭贡籍入王宫。”(27)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以外部份)》第6卷,第212页;录文参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338页。诗中所言“边庭贡籍”应当指的就是贡献沙州等地的户籍,献户籍相当于献百姓,同样表达了诚心归顺之意。上贡地图、户籍是一个有着很强政治属性的行为,足以证明悟真一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交流使团,而是承担着重要的政治任务。
将悟真使团的上贡之物与其前后两批使团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悟真使团进贡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很大,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张氏政权循序渐进的政治诉求。关于高进达使团所献之物,《新唐书·吐蕃传下》记载:“沙州首领张义潮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2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4,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07页。在大中二年(848)张议潮派遣高进达等人赴京报捷之时,仅收复了瓜、沙二州,但第一批使团为表归顺却奉十一州地图以献唐廷,这一方面说明张议潮献图的象征意义远高于其实际意义,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在未来经略河西的意图。不过,此次出使仅为张议潮取得了沙州防御使的头衔。第二批悟真使团在进献地图的基础上还加上了户籍与奏疏。此时张议潮已收复瓜、沙、甘、肃、伊五州,以户籍来献可见张议潮对河西地区已掌控日深。而将地图、户籍一并上贡则可视为一种更加正式的投诚行为,且上献奏疏可知张议潮对未来的河西经营有着较为长远的规划。此次遣使入京张议潮在展示自己实力的同时也向唐廷表达了十足的诚意。第三批张议潭使团进献之物大部分史书都笼统地记载为十一州户口,唯《唐会要》记载有所不同:“大中五年七月,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潭将天宝陇西道图经、户籍来献,举州归顺。”(29)[宋]王溥《唐会要》卷71,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269页。天宝年间的陇西道含陇右、河西二道,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下辖共21州(30)[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39、4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79-1045页。,新旧《唐书》虽略有出入,但所载下辖范围均远大于十一州。比之前两批使团,张议潭使团规格更高,图谋也更大,进献之物也应有所不同。悟真使团已经上贡了十一州图籍,张议潭使团似乎不应与之相重合,而以天宝陇西旧图上献,则可见其收复河陇失地、重现天宝辉煌的抱负决心,以及谋求河西节度使一职的愿望。不过,分官进爵显然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张议潭使团最终争取到的也只是“归义军节度使”的旌节,以及将张议潮从沙州防御使升格为十一州观察使。但是在瓜沙境内,张议潮显然并未严格遵守朝廷的分封,而是更多地使用“河西节度使”的称号。三批使团,规格渐高,收获渐丰,悟真使团于其中则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既向朝廷进一步展现了张氏政权的实力与诚意,又为其后张议潭使团表达更大的政治诉求打下铺垫。
悟真的此次上贡图籍、奏疏之举可谓非常成功,不仅获封京城临坛大德并赐紫,在长安佛教界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总览京师高僧的赠诗不难发现他们不仅对悟真本人的博学多识、兼通儒释赞誉有加,对悟真的进贡行为也报以很高的评价。比如宗茝所作《七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二首·其一》:“沙漠关河路几程,师能献土远输诚。因兹却笑宾獒旅,史籍徒彰贡赋名。”(31)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第114页;录文参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333页。“宾獒旅”典出《尚书·旅獒》,指的是古时西戎远国进贡大犬一事,诗中将其与悟真不远万里进献河西图籍相比较,反衬出悟真此举的意义非凡,真正值得彪炳史册。又如栖白《奉赠河西真法师》云:“知师远自燉煌至,艺行兼通释与儒。还似法兰趋上国,仍论博望献新图。已闻关陇春长在,更说河湟草不枯。郡去五天多少地,西瞻得见雪山无。”(32)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9册,第9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以外部份)》第6卷,第212页;录文参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337页。“法兰趋上国”用东汉天竺高僧法兰来到洛阳传授佛法的典故,“博望献新图”指的是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后向汉武帝汇报西域诸国的情况。栖白将悟真出使与法兰传法、张骞献图相提并论,是因为悟真此次入京兼具僧人与使者的双重身份,他既与京师高僧探讨佛法,也向唐廷进献河西图籍,可见栖白所取的类比对象是极为精切的,表现了他对悟真的高度赞扬。
三、悟真使团及其后的唐归宗教交往
从悟真创作的这些赠答诗中可见其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高超的政治素养,在与京师大德诗歌唱和之时不卑不亢,进退有据,又时刻牢记以张氏政权的利益为先,确实是一名优秀的使者。除此之外,张氏政权又因何要派遣悟真率领的宗教使团入京奏事呢?首先,敦煌是一座受佛教影响极大的城市,张议潮青少年时期就曾在寺院中跟随高僧法成学习(33)参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69页。。可能因此机缘,在其率众起义、驱逐吐蕃的过程中敦煌佛教界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悟真本人在张议潮的逐蕃斗争中就曾随军出征,立下过汗马功劳。起义成功后,敦煌佛教界势力趋于顶峰,并进一步参与世俗政权的管理。张议潮确立了以都僧统为首的僧官制度,并任悟真老师洪辩为第一任河西都僧统,此时僧人在敦煌拥有较为独立的政治地位。悟真的此次出使便是奉洪辩之命,代表的是敦煌的僧官系统,而朝廷对洪辩、悟真二人也给予单独的分封:“洪辩可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悟真可京城临坛大德,仍并赐紫,余各如故。”(34)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330页。故派遣悟真为首的佛教使团出使京师是敦煌佛教界势力干预世俗政权的结果,不过他们在出使目的上与高进达、张议潭使团还是大致相同的,都是为了给沙州地区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其次,张议潮派遣的第一批使团可能带来了许多关于唐朝的情报,使其得以知晓唐朝正处于会昌法难后的佛教复苏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议潮为了能够顺利求取旌节而派遣悟真使团进京,可能也有着投好唐廷的意味,而悟真也确实在长安为第三批使团的来访打开了局面。
悟真的这次出使可谓开创了归义军与唐王朝之间宗教交往的先例,其后在张氏政权统治时期双方宗教往来颇为频繁,比如上文提到的西凉僧法信、沙州僧昙延向唐廷进献佛经注疏,再如P.4962V记载:“准数分析奏文,陷蕃多年,经本缺落,伏乞宣赐,兼降宣命,诏当道在朝。”(35)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3册,第312页。可知张议潮也曾向唐廷求取沙州缺落的经本。除了这些史籍或遗书中有明确记载的宗教往来外,与悟真《阙题四首》以及杨庭贯《谨上沙州专使持表从化诗一首》同抄于P.3645的《莫高窟巡礼题咏诗钞》似乎也是一起双方宗教往来的例证。《莫高窟巡礼题咏诗钞》含诗五首,前两首并序无作者署名,录文如下:
巡礼仙岩,经宿届此。况宕泉圣地,昔僔公之旧游;月窟神踪,倣中天之鹫岭。三危峭峻,映宝阁以当轩;碧水流泉,绕金池而泛艳。中春景气,犹希彤云,偶有所思,裁成短句。
三危极目耸丹霄,万里[□]家去且遥。满眼彤云添塞色,报恩终不恨征辽。
今日同游上碧天,手执香积蹈红莲。灵山初会应相见,分明收取买花钱。(36)该组诗歌原卷前本无题,此处暂从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之拟题。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以外部份)》第6卷,第207、218页;录文参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622-624页。
从“巡礼仙岩”之举以及诗中所用“香积”“灵山”“买花钱”等佛教语汇、典故,可以推测作者很可能是一位僧人,“万里[□]家去且遥”说明来自于中原地区,“报恩终不恨征辽”说明他可能与悟真出使京师一样,肩负着一定的政治任务,是为了报答君恩而来到敦煌的。诗钞第三、四首题名《延锷奉和》,“延锷”即张延锷,是张议潭之子张淮深的第四子,大顺元年(890)与其父兄同卒于沙州政变。最后一首题名为《又瑭彦不揆荒无(芜)聊申长句五言口号》,“瑭彦”之名在敦煌文书中多有出现,其全名为氾瑭彦,是敦煌当地的官吏文士。由此二人作陪,可见这位僧人地位较高。而根据张延锷所写的“南阳一张应天恩,石壁题名感圣君”一联,也可从一侧面说明中原僧人可能是奉君命而来,瑭彦所写“诸公燃圣烛,荐福益三台”则体现出他的这次陪客游览实是为了公家之事,故这次宗教交往很可能具有一定的官方性质。这组诗钞创作于张淮深执政时期,此时唐军忙于镇压中原地区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而无暇西顾,在河西地区的势力逐渐减弱,张淮深则在抗击外族的军事战争中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此消彼长之下,归义军在河西的势力进一步扩大。从《张淮深变文》中唐廷使臣亲临敦煌加以封赏的行为,以及《张淮深造窟功德碑》中“五稔三迁,增封万户。宠遇祖先之上,威加大漠之中”(37)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85页。的叙述来看,这一时期自顾不暇的唐朝对归义军颇为优待,这位派往敦煌的高僧可能就是为了表达朝廷的善意而来。另一方面,张淮深屡请旌节不得,在归义军内部所受质疑与日俱增,也急需唐朝封授以稳定自己在河西地区名正言顺的统治地位,故张延锷对中原高僧也是礼遇有加。虽然出使方式不同,但这一时代背景与大中五年悟真出使京师时十分相似,均为双方各有所求的制衡时期。
那么又是为何在悟真使团之后,唐归双方的宗教往来一直如此频繁呢?首先,悟真的此次出使可谓大获成功,为唐归双方的宗教交往打开了良好的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唐王朝与沙州地区又都十分信仰佛教,特别是敦煌本就是一座传统的佛教都市,即使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教也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还因此非常幸运地避过了唐武宗的会昌法难,故留存有中原地区散佚的佛经注疏。而唐王朝此时正值法难之后的佛教复兴时期,大量早期的佛学经典毁于法难,故此期唐归双方对佛经注疏的频繁交流正好补充了唐朝佛教的不足。其次,在“当时唐朝中央政府和藩镇间对立的基本历史背景”(38)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64页。下,归义军与唐王朝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但面对外敌环伺、虎视眈眈的现状,双方又需要同仇敌忾,戮力合作,故而宗教在这一时期就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一方面,归义军随着势力东扩渴望摆脱唐朝的控制,而唐王朝随着国力衰退对归义军的发展愈发忌惮,这就决定了双方明争暗斗的关系实质。而另一方面,唐王朝需要借助归义军掌控河西,归义军又要扯唐朝的大旗维护统治。所以当双方互有所求,关系趋于和缓之时,双方对佛教的共同信仰就使得宗教交往成为了一种很好的润滑手段,避免双方陷入剑拔弩张的局面。而从悟真出使的成果来看,这种宗教交往也起到了不错的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