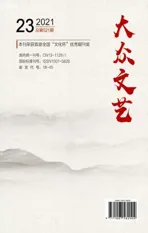从《再袭面包店》的夫妻关系中分析“我”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的考察
2020-07-12
(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23)
一、引言
1.先行研究
村上春树是举世闻名的作家,他的不少作品都是文学研究的对象。他的短篇小说——《再袭面包店》便是其中之一。在这部作品中,他描写了一对寻常人无法理解的夫妻。为了解读这对夫妻的“荒唐行为”,学界关于《再袭面包店》的研究从未停止。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聚焦于讨论小说的主题以及解释和分析小说的荒诞之处。 例如,森本隆子在《〈再袭面包店〉——朝着非存在的名义》(「『パン屋再襲撃』——非在の名ヘ向けて」)一文中提出,小说所反映的是一个 “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①,并指出“以欲望的自我繁殖和大规模消费为座右铭的消费社会,无非是通过虚构徒有其表的差异来标榜个性,但实际上只是自缚于平均和统一化内的系统而已”。②总而言之,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下,个人必须接受主体性消散和灭亡的命运。同时,也有学者根据森本提出的主题,进行了对主人公“我 ”的分析。例如,关冰冰和杨炳菁在《从〈象的消失 〉到 〈再袭面包店〉--谈两篇小说中的 “我”》中提出:“‘我’在经过第一次袭击面包店后失去了主体性,但是躯体仍在同现实负隅顽抗,期待重拾主体性。而第二次袭击则是为了重拾主体性,由妻子主导的行动。”③
2.本论文的视角
针对上述观点,石仓美智子提出了 “夫妻关系 ”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 她在《夫妻的命运I——村上春树〈再袭面包店〉》中提出:“‘我’看似通过婚姻接受了他人,但却避开了可能由这段关系萌生的自我改造的机会。不仅如此,在知道‘妻子’寻求的不过是举行一场仪式后,‘我’因为这个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法,甚感欣慰。”④
如上所述,在此前的研究中,针对与小说主题密切相关的“我”的分析和对 “夫妻关系 ”的讨论是分开进行的。在探讨《再袭面包店》的主题时,自然应把重点放在对主人公“我”的分析上,但同时 “我 ”也和贯穿全文的“妻子”构成了“夫妻关系”,剥离“我”讨论这段“夫妻关系”是不合理的。
此外,关于“夫妻关系”先行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文本分析,缺乏系统的科学定义。 鉴于此,本论文将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对《再袭面包店》中的“夫妻关系”中的“我”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力图阐明村上春树为什么要设定这样一个人物。
本论文将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从“夫妻关系”的角度出发,聚焦于人际关系中的夫妻关系。在讨论夫妻关系时,不可避免地要用到亲密关系的理论。“亲密关系中有一个共同点:相互依赖。社会心理学中的相互依赖是指两个人长期相互影响,全身心地密切关注对方,并尽可能地进行合作。”⑤
在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中,根据关系双方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对对方持何种态度,如何对待对方,会产生不同类型的亲密关系。 其中一种是“依恋型”。根据Horowitz(1991)的研究,可以将“依恋型”进一步分为四种类型,即:安全型、专注型、超脱型和恐惧型。下面,本论文将运用“依恋型”的理论和分类模型,对《再袭面包店》中处于“夫妻关系”中的“我”进行分析。
二、夫妻关系中的“我”和“妻子”
1.“我”的依恋类型
“我仍然不确定告诉妻子我袭击了面包店这件事情是否正确。 (中略)事情已经发生,覆水难收,还未发生的事情则未曾出现。”(原文:「パン屋を襲ったときの話を妻に聞かせたことが正しい選択だったかどうか、いまもって確信が持てない。(中略)起ったことはもう起ったことだし、起っていないことはまだ起っていないことのだ。⑥」)
如上所述,“我”开始用回忆的形式说话。当时,再次袭击面包店的事情已经发生。 但是,“我”却描述得很含糊,没有任何结论。“我”不是想让人倾听自己的故事,也不是企图评判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而是想传递自己的迷茫。 这是因为“我”“已经没有了判断能力”⑦,没有了主体性。所以,“我”认为 “不管我怎么想,都无法改变任何事情。”⑧由此可见,“我”与对自我保持积极态度的“安全型”和“超脱型”这两种类型相差甚远,分为“专注型”和“恐惧型”更为合适。
然而,当强烈的饥饿感袭来时,没有主见的“我”却和“妻子”抱有些许期待。“移步厨房,在冰箱里寻找食物的行为象征着‘我’和‘妻子’都努力在‘夫妻关系’中寻找应对‘饥饿感’的办法”。⑨此时“我”在与“饥饿感”的斗争中主动出击。但矛盾的是,“我”一直保持着悲观的态度,坚信自己不可能会成功,却仍然在努力。
“如果人在幼年期就形成了依恋类型,会形成定型。但是,这种定型并非从此一成不变。当失去家人或开始新的依赖关系时,依恋类型或许也会发生改变。”⑩因此,可以认为“我”与“妻子”结婚后,依恋类型也发生了变化。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当时,我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妻子在一所设计学校做文职工作。(中略)两人都顾不上冰箱里有什么东西。”(原文:「その頃僕は法律事務室に勤めており、妻はデザイン·スクールで事務の仕事をしていた。(中略)冷蔵庫の中身までにはとても気がまわらなかった。」(11))
虽然“我”记不住结婚纪念日,“妻子”的工作和年龄却记深谙于心。而且,“妻子”的意见对“我”而言就像某种谏言,振聋发聩。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妻子”,“我”才能像有主体性一样表达自己的意见。“我”并不是依赖于“夫妻关系”,而是依赖于“妻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依赖“妻子”,“我”的依恋类型并不是“恐惧型”,而是“专注型”。 那么,“妻子”又属于哪种依恋类型呢?
2.“妻子”的依恋类型
“在我喝啤酒的时候,(中略),我们都小心翼翼地吃了两块。(原文:僕がビールを飲んでいる間、(中略)、我々はそれを大事に二枚ずつかじった。(12))
以上只是“我”的叙述,不一定是事实。但至少可以推断,“我”所看到的生活现状与“妻子”看到的不同。另外,在对待“饥饿感”这一问题上,“妻子”采取的行动也与“我”不同。这是因为“我”和“妻子”两人的依恋类型不同。
在“我们”把三个员工被绑在柱子上后,妻子询问了他们:“疼不疼?” “你要不要上厕所?”虽然“把他们绑在柱子上”是不得已的事情,但“妻子”主动地选择了向他们表示关心。“妻子”对于为了让自己免于“饥饿感”而给他人带来灾难这件事情,感到内疚。因此,想要尽力对他们作出弥补,关心他们。这就是“妻子”对他人的关心和爱。“妻子”既爱自己,又爱他人,积极地看待事物,即使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也会积极地采取行动。这些便与“我”不同。可以判断“妻子”属于“安全型”。
那么,在“夫妻关系”中,依恋类型不同的两个人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呢?
三、针对“夫妻关系”中“我”的分析
1.“我”产生“饥饿感”的必然性
“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年。(中略)袭击面包店也是那个时候的事情。”(原文:もう十年前のことだけど。(中略)パン屋を襲ったのもうちのひとつで――(13))
渐渐失去主体性的“我”和“搭档”两人“向面包店发起了袭击,试图拒绝现状,重获自主”(「現状を拒否し、主体性を回復しようと、パン屋を襲撃した」(14))。 这是“我”第一次袭击面包店。 然而,第一次的袭击以失败告终。“我”和“搭档”也被“诅咒”,被社会同化,彻底失去了主体性,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后来,“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并结婚。“从此再也没有袭击过面包店”。(「二度とパン屋を襲ったりはしなくなった。」(15))
第一次袭击面包店后,“我”被“文明”所席卷,成为“文明”的一员。可为什么一向沉稳的“我”会再次被“饥饿感”侵袭呢?“饥饿感”,是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状态。此外,“饥饿感”发生的时机,是在“我”与“妻子”结婚两周后。换句话说,“我 ”在第一次袭击面包店时已经失去了主体性。因为“夫妻关系”的建立,“我”和有主体性的“妻子”之间产生了冲突,“饥饿感”也油然而生。
“三十个巨无霸,打包带走。”。妻子说道。(中略)“除了面包之外,我不会抢任何其他的东西。”妻子向女人解释道。(原文:「ビッグマックを三十個、テイクアウトで」と妻は言った。(中略)「パン以外には何も盗る気はないよ」と妻は女の子に説明した。(16))
在第一次袭击面包店时,“我”和“搭档”也“只想要足够填饱肚子的面包,并不是想抢钱。”(「自分たちの飢えを充たすだけの糧秣であるパンを求めるだけであり、何もお金を盗ろうとするわけではない」(17))“妻子”主导的第二次袭击也是如此。 那么,“妻子”为什么会做出夺回主体性的行为呢? 原因是“安全型”依恋类型的人有更强的同理心,他们在与人交往时,不仅能够从自己的角度,也能从对方的角度理解“关系”。(18)换句话说,不仅“我”受到了“安全型”依恋类型的“妻子”的影响,“妻子”也受到了“专注型”依恋类型的“我”的影响,做出了与“安全型”相矛盾的行为。
2.“我”参加“再袭面包店”行动的目的
“我”在失去主体性后,服从于已有的社会规则,和“妻子”结婚了。由此,缔结了“夫妻关系”的两个人便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专注型”的“我”不假思索地寄托依赖于“妻子”。然而,在这段“夫妻关系”中,已被社会规则同化的“我”和拥有主体性的“妻子”之间产生了冲突,“饥饿感”也随之袭来。
因为“我”曾经体验过“饥饿感”,所以知道其产生的原因,也知道解决的办法。但“我”已经失去了主体权,无能为力。 于是,“我”寄希望于“妻子”,希望她能够把自己从“饥饿感”中解救出来。“再袭面包店”便是由“妻子”主导的反抗行动,这是对既定规则的反抗。将目标锁定麦当劳,准备袭击工具,制定计划,抢劫汉堡的个数等等,全部都是“妻子”决定的。对于“我”而言,参加这场“再袭面包店”的行动,是加入“妻子”反抗性的胜利,同时也是为了获得救赎。
四、总结
村上春树试图通过描写“专注型”的“我”和“安全型”的“妻子”,来描绘当时的社会现状。 在一个社会管理体制柔和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一个以欲望的自我繁殖和大规模消费为座右铭的消费主义社会中,毫无疑问,不仅是“我”,还有更多失去主体性的人们,都希望能有人来拯救自己。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尽管悲观,认为自己已无能为力,但依旧会对他们抱有希望。
注释:
①森本隆子『パン屋再襲撃』——非在の名ヘ向けて[J].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95,(4):92.
②森本隆子『パン屋再襲撃』——非在の名ヘ向けて[J].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95,(4):92.
③关冰冰,杨炳菁.论《再袭面包店》作品中的“夫妻关系”[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7,(05):73.
④石倉美智子.夫婦の運命I——村上春樹『パン屋再襲撃』論[J].文研論集,1992,(9):205.
⑤R·A巴伦,D·伯恩.社会心理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131.
⑥村上春樹.パン屋を襲う[M].新潮社,2013:26.
⑦关冰冰,杨炳菁.从《象的失踪》到《再袭面包店》——谈两篇小说中的“我”[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03):109.
⑧村上春樹.パン屋を襲う[M].新潮社,2013:27.
⑨关冰冰,杨炳菁.论《再袭面包店》作品中的“夫妻关系”[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7,(05):112.
⑩杨吟秋.成人依恋风格和婚姻质量的关系[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05):02(参照).
(11)村上春樹.パン屋を襲う[M].新潮社,2013:29.
(12)村上春樹.パン屋を襲う[M].新潮社,2013: 33-34.
(13)村上春樹.パン屋を襲う[M].新潮社,2013: 37.
(14)石倉美智子.夫婦の運命I——村上春樹『パン屋再襲撃』論[J].文研論集,1992,(9):196.
(15)村上春樹.パン屋を襲う[M].新潮社,2013:44.
(16)村上春樹.パン屋を襲う[M].新潮社,2013:64-68.
(17)劉潔,大橋真,「パン屋再襲撃」のなぞ[J].言語文化研究,2011,(12):114.
(18)R·A巴伦,D·伯恩.社会心理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