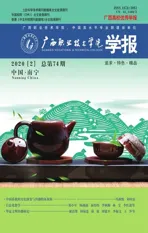作为“海丝”文化的媒介:中国外销瓷的历史特点与现实启示*
2020-03-15李海文
李海文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福建 福州,350002)
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主要有东海、南海和西洋等三条航线。一般认为,它肇始于秦汉,兴于隋唐,繁荣于宋元,明清之后由盛转衰。何为“海丝”文化?“海丝文化”即指因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发展而来的文化,它向海而生,包括一切相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其特点是蕴含丝路精神,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1]“海丝”常见的输出货物有丝绸、茶叶、瓷器、铜铁器等,输入的则是香料和各种各样的奢侈品等。而瓷器分为三大体系,即官窑、民窑和外销,为何外销瓷是展示和传播“海丝”文化的极佳媒介?媒介是“在特定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象征传递和流通的手段的集合。”[2]外销瓷何以成为“海丝”文化的媒介,如何存储和传播文化信息,表达丝路精神?在新时代下,外销瓷能否继续发挥效用?又何以可为?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1 历史特点:中国外销瓷的“三维性”
中国外销瓷是对出口海外市场瓷器的统称,包括唐宋元瓷器、明清专供出口瓷等。它基于时间、空间和器物的三重维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海丝”文化的中外交互性,生动传递了丝路精神,成为“海丝”文化的极佳媒介。
1.1 时间维度:大宗货物延续千年,极具代表性
瓷器是千年“海丝”的大宗货物,深受海外市场的青睐,极具代表性。唐朝中后期,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主通道。中国瓷器外销的历史始于隋唐,瓷器成规模外销不晚于9 世纪下半期,即唐代后期。也就是说,“海丝”兴起的时间,正是外销瓷兴起销售的时间,两者基本同步。在唐代,邢窑、越窑和长沙窑是外销瓷的三大中心。五代十国时期,对外输出的主要货物是纺织品和瓷器。进了宋元时期,海上贸易进入繁荣阶段,瓷器成为最理想的压舱货物,地位日益显要,因此又称作“海上陶瓷之路”。明朝建立伊始,一度实行海禁,但没有杜绝瓷器出口。郑和下西洋的“贡赐贸易”和民间贸易也有大量的瓷器出口。明朝中晚期到清初,瓷器外销进入黄金时期,数量不计其数,产品多为外国定制。据T·佛尔克(Volker)编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记载,公元1602 至1682 年,即明末清初的八十年间,仅荷兰人贩运中国瓷器就达1600 万件以上。[3]
外销瓷的大量输出,除了文献资料记载外,也可从海捞瓷中获得有力辅证。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从“海丝”水域考古打捞上来的沉船甚多,著名的有唐代的“黑石号”海船(在印尼发现),10 世纪的“井里汶号”海船(在印尼发现),南宋的“南海一号”海船(在中国广东发现),元代的新安沉船(在韩国发现),明代的“平顺号”海船(在越南发现)和“南澳一号”海船(在中国广东发现),清代的“头顿号”海船(在越南发现)、“金瓯号”海船(在越南发现)、“哥德马尔森号”(Geldermalsen,又称南京号)海船(在中国南海发现)、“泰兴号”海船(在印尼发现)和“碗礁一号”沉船(在中国福建发现)等。这些沉船均装有数以万计的各类瓷器,成为外销瓷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物证,成为永不消逝的丝路符号。
清朝中期“海丝”由盛转衰,而中国瓷器的海外市场此时开始走弱,两者衰弱的时间几乎一致。瓷器易碎,相比较陆路海路平稳安全,单次运载量大,运费低廉,因此“海丝”发达会促进外销瓷出口,两者共生传播。“海丝”诸国人民对中国瓷器颇为青睐,瓷器外销又会繁荣海运。外销瓷输出时期之长,规模之大,几乎与“海丝”同命运共呼吸。一部外销瓷史可谓就是一部“海丝”史。
在上千年的外销史上,中国瓷器不管是民间贸易还是“贡赐贸易”皆是在和平友好中进行,并无政治、军事冲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心相通在于常联系。作为主流的持续的民间瓷器贸易,更是促进了中国与“海丝”诸国的友好往来。外销瓷的长期化、规模化,大大超越了官窑瓷器的馈赠赏赐,成为走进千家万户的大众媒介。
1.2 空间维度:器成天下走,极具影响性
中国瓷器烧造之后,器成天下走,“行于九域,施及外洋”,横跨欧亚美非四大洲,与“海丝”人民共享。在今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巴林、约旦、叙利亚、苏丹、埃及、坦桑尼亚等国都出土了中国唐、五代时期的陶瓷标本,品种有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瓷器、广东梅州市梅县区窑瓷器等。[4]外销瓷的位移,打破了中外方的语言与地域隔阂,交流增多。随着出口越来越多,外销瓷不仅仅是海外上流社会的奢侈品,还逐渐大众化,与民同享。正如荷兰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庞塔拉( Johannes Pontanus)所言,中国外销瓷“几乎成为普通人的日常使用之物”[5]。
外销瓷影响“海丝”诸国,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也促进了当地陶瓷业的发展。就瓷器自身而言,外销瓷有大量的日用瓷,造成了东南亚、欧洲等一些地方的“饮食革命”,改变了树叶、木质、陶器、金属等餐具的使用习惯。清代创烧的广彩瓷就是典型的外销瓷,“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6]。青花瓷中的啤酒杯、咖啡壶、剃须盘、奶杯、汤盆、军持以及圣诞老人瓷塑等陈设品,也是景德镇迎合西方市场所制产品。日本“伊万里”瓷器纹样来自中国,一度畅销欧洲,成为日本重要的外汇源。在东南亚某些地区,中国瓷器和当地的社会生活以及风俗习惯发生了奇特的联系。在菲律宾,当地人珍视中国瓷器,平时将瓷器埋在地下,节日才取出一用,用后又再深埋地下[7]。《东西洋考·文郎马神》说:“文郎马神(婆罗洲东岸的Bahbjermasln)……初,盛食以蕉叶为盘,及通中国,乃渐用磁器,又好市华人磁器,画龙其外,人死贮瓮中以葬。”[8]明清瓷器到了欧洲后,可谓是惊艳登场,促发了追求中国瓷器的风尚,上流社会人士纷纷购买、收藏和陈设。他们把瓷器视为珍宝,用以婚礼、赏赐和交换等。他们对外销瓷进行研究仿制,借鉴中国瓷器的造型与装饰,成功烧造了欧洲版的陶瓷,如荷兰德尔费特(Delft)陶、德国迈森(Meissen)的硬质瓷等。外销瓷刮起的“中国风”(Chinoiserie)还对西方文化艺术产生了影响,推动西方艺术史从巴洛克艺术风格向洛可可艺术的转变。外销瓷成为西方文艺绘画、园林建筑、文学作品等中的常见元素。借用著名海上瓷路研究学者叶文程的话,外销瓷“极大地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其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刻的”[9]。
外销瓷不仅影响“海丝”诸国,也反作用于中国。瓷器生产加工、转口贸易等都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例如,景德镇与瓷器关系不用赘言,泉州、广州的兴盛还分别与德化瓷器、广彩瓷密切相关。宋元时期,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最大出口商品便是德化瓷。《马可波罗行纪》载:“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Tiunguy)(指德化)。制造碗及磁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购价甚贱。”[10]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说:“中国瓷器,只在刺桐和隋尼克兰城(指广州)制造……是瓷器种类中最美好的。”[11]德化白瓷流传欧洲后,外国人又称之为“鹅绒白”“雪瓷”等。直到现在,法国人还以“中国白”(Blanc de Chine)直呼德化窑白瓷。在长年累月的发展中,德化白瓷形成了“世界白瓷看中国,中国白瓷看德化”的美誉,至今还促进泉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彩瓷指广州烧制的织金彩瓷,其白瓷来自于景德镇,在广州仿造西洋画法或按来样绘图加彩二次烧成。它是专门为外销而生的,成为清代三大出口外销瓷之一。广彩瓷的生产、外销不仅促进了广州制瓷业的发展,而且繁荣了广州市场,利国富民。其它著名港口如扬州、杭州、宁波、福州等也长期受惠于外销瓷的转口贸易。海丝诸国也有陶瓷及其原料流入中国,中国并不排斥域外优秀产品的输入。中国不少地区出土了它国陶瓷,如“广西合浦出土的汉代青绿釉带把陶壶、江苏扬州发现的唐代双耳绿釉陶壶、福建福州刘华墓出土的三件唐代孔雀蓝釉陶壶,经研究都是从西亚地区输入,与中国陶瓷器相映成辉”[12],生动阐释了丝路精神开放包容的特质。元代及明初青花瓷关键原料——钴料就是从中东进口而来,汉译名称为“苏麻离青”。这段时期烧制的青花瓷色青浓艳,富有特色,不可复制,价值高昂。
同为“海丝”的大宗货物,丝绸、茶叶都是从中国走向海外,属于单向旅程,而瓷器却是你来我往,不断互动。外销瓷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正如日本著名陶瓷研究专家三上次男(Mikami Tsugio)所言:“海上陶瓷之路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13]外销瓷不仅让中外陶瓷抑或是其它产品甚至其它领域,不断谱写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和谐篇章。
1.3 器物维度:文化融合古今中外,极具媒介性
常言道:百代消亡,惟瓷永存。瓷器是土与火的艺术,经过高温烧造,变得坚固耐磨,存载或附带的信息就不易失去。按照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论,瓷器是兼具时空偏向的一种较为平衡的媒介。中国出口的大宗货物丝绸、茶叶和中国进口的大宗货物香料,都属消耗品,且不易保存,缺乏时间偏向。铜铁器虽可运输、可保存,然而不像瓷器具有较大的图画观赏性。正如学者甘雪莉(Shirley Ganse)所言:“累世以来,茶和丝绸虽然是东西贸易的主体,但谈到推动跨文化对话,促进意念、纹饰、设计和技术创新的交流,则非瓷器贸易莫属。”[14]学者芬雷(Robert Finlay)甚至说“在中国与遥远的欧亚大陆另一端之间,瓷器扮演了极为独特的交流角色,这是其他任何货物在内涵或本质上都无法达成的任务。”[15]瓷器静默,但非无言,不管是形式各异的造型,还是丰富多彩的纹饰,抑或是精致唯美的釉色纹理,无不透露着各种信息。尤其是瓷器具有一定的表面,不管是平面还是曲面,皆可充当符号的载体[16]。许多外销瓷在这些表面上打造了丰富的图文装饰,传达了中外风土人情等信息,因此外销瓷具有较强的信息传递功能。例如,近代欧洲人“通过瓷器上所描绘的图案而模仿中国人的生活,使用中国瓷器、喝中国茶、穿中国服装、坐中国轿子、建中国园林等等”[17]。
3)直流侧单极故障时高接地阻值有利于故障穿越及系统恢复,直流电压不平衡保护作为该类故障的主保护并动作于报警,系统可带故障运行;由故障选线定位策略实现该故障类型的隔离。
外销瓷融合古今中外文化,成为文化交流互鉴的印证。在唐代,长沙窑作为中华第一彩瓷,受到域外文化的影响而兼收并蓄,形成丰富多彩的造型和纹饰,受到海外市场的广泛喜爱,外销数量惊人。据不完全统计,在亚非13 个国家、73 个地区都曾出土长沙窑瓷器,器身还出现了胡人、椰枣、棕榈纹饰及阿拉伯文字。[18]在宋代,创烧的一系列长颈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9-11 世纪伊斯兰玻璃器的启发。[19]在明清,外销瓷大户福建德化窑不仅融合了各个窑口的长处,还吸收了其它工艺品和外来文化的元素。它吸收了宋代定窑和耀州窑的刻印之法,吸收了哥窑的“开片釉”装饰工艺,采用开片釉使器物表面富于变化,易于观赏。德化白瓷生产吸收了泥塑、木雕和石刻等民间工艺美术的技艺,综合形成了由瓷塑工匠主导的瓷塑生产工艺,并逐步发展成德化窑以生产、经营佛教文化产品为主。产品中的陈设供器就借鉴了商周青铜器的式样;雕塑人物就有不少外来宗教中人物的角色(如佛教的如来、观音、弥勒、罗汉、达摩等)。明朝科学家宋应星说:“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20]其中著名工匠何朝宗就吸收了中国泥塑、木雕、石刻等佛像技艺风格,融汇于瓷雕。[21]他所制作的白瓷瓷塑,例如“达摩渡江”“渡海观音”等作品融百工之长,汇中外文化,以致线条深秀洗练,人物形神兼备。佛教文化为白瓷生产提供了文化素材,而白瓷瓷雕生产之多、销售之广又让白瓷成为佛教传播的一大媒介。正如新华社报道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电讯所言:
历代德化瓷制造都特别重视研究海外文化,结合销区民众生活习惯、传统民俗、宗教信仰、审美偏好等,德化瓷工匠们代代相传,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元素对产品的造型、瓷色、釉色、图案、工艺、装饰等加以设计,不仅推动了德化陶瓷的蓬勃发展,也形成了融汇中外的特有艺术风格,创造了新的中华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22]
瓷都景德镇四大瓷器之一的青花瓷,“正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瓷器新品类。”[23]元末明初,青花瓷大量融入域外文化元素,造型、装饰等尽显外销瓷风采。清代广彩瓷,其所用素白瓷主要来自景德镇,与内销瓷相比,造型更丰富,装饰方面更华丽,题材有西方的风景、人物、城堡、帆船等。除了德化、景德镇等著名窑口,其它小窑口也吸收外来元素。即使到了近代外销瓷衰弱时期,也是不忘美美与共的传统。如1904 年在台湾金门创办的“华宝制瓷公司,改进式样,仿照西洋款式,使用机器生产”。[24]该公司聘请了国内江西和国外日本工匠等前来制造,各施所长,谋求发展。
与现代社会相比,古代通讯技术并不发达,大部分中国人与大部分外国人的交流往往通过商品来传递信息,获取对域外的印象。明朝外销瓷对于欧洲人而言,不仅仅是物体,还是对中国的一种文化镜像。[25]器以载道,物以传情,器物具有一定的媒介功能。外销瓷搭载了不少文化信息,成为重要媒介。学者王炳文曾说:“瓷器是古典时期另一个重要的物质交流媒介,它甚至成为西方对于中国的一种固有印象。”[26]2017 年6 月学者王鲁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设《瓷行天下》讲座,谢小铨副馆长开幕辞中说道:“肯定地说,世界上可能找不出哪样东西,能够像中国外销瓷一样,成为多民族、多宗教、多习俗、多文化共同参与创造的载体。”[27]
中国外销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遗产,也是世界多元文化的遗产。它融合了古今中外的元素,因材质坚硬长期保存,器物本身有力地展现和传播了“海丝”文化,成为“海丝”文化的极佳媒介。
2 现实启示:中国外销瓷何以可为
由上可见,外销瓷与“海丝”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生动传达了“海丝”文化,可谓是其传播中的极佳媒介。今时并非往日,外销瓷是否还可以继续发挥传播“海丝”文化的效用?答案是创造条件,依然可以。一是外销瓷本身凝结了千年“海丝”文化的精髓,历史地位不可撼动,传统影响继续发挥作用;二是在媒介日益丰富的今天,外销瓷因兼具实用功能和艺术功能,市场广阔,依旧是世界上传播文化的重要使者;三是外销瓷并非一成不变,可以创造条件,为其增添新的传播力。那如何创造条件,以何可为?笔者认为需要处理好以下三大关系,即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内容与传播。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大关系并非彼此独立,互不相干,只是看待问题时所采取的一种主要角度。
2.1 正确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中国瓷器源远流长,在商代就有了原始瓷器,在东汉发展成熟,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外销瓷亦有上千年的历史,曾经拥有令人骄傲的辉煌,也有近代一段衰败的时光。对待过去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坚持辩证统一,树立信心。以史为鉴,扬长避短,把握现在,面向未来。
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与时俱进,推动外销瓷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首先,要不忘本来。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加以传承,如外销瓷蕴含的思想观念(天人合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崇德向善等)、传统制作技艺(好料好工、手工制作、传统柴烧等)、产销方式(市场定位、中西合璧等)、传统优秀产品(青花瓷、釉下五彩瓷等)。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外销瓷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8]丰厚的历史本就是一笔丰厚的资源,不能弃而不用,而要继续利用。
其次,创新是文化发展和进步的灵魂与动力。纵观人类文明史,无论东方或者西方,文化创新对于文化的历久弥新和繁荣昌盛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历史上的外销瓷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富有时代性,不断吸收各种元素,逐渐走向明清之巅峰。目前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要复古到古代丝绸之路,而是要复兴。正如其名“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当下的“海丝”有着21 世纪的时代使命与特征,是对古代“海丝”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历史上的外销瓷技术先进、独有,价格高昂,“一箱金银一箱瓷”,而如今的外销瓷出口价格较低,有待创新发展,打造独特风格,方能在新的外贸形势中占据优势。
今非昔比,海外市场对外销瓷的消费需求,逐渐从实用功能转向实用与艺术相结合。在这注意力稀缺时代,中外之间的交流多样化,外销瓷要在众多媒介中再起明显的传播作用,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保持外销瓷的媒介性,不变的是魅力,变的是魅力的表现形式。因此,目前发展外销瓷必须走文化艺术产业之路,“产业陶瓷艺术化,艺术陶瓷产业化”,加深全球分工与国内主要产区合作,实行品牌化、规模化经营。另外,除了日用陶瓷、陈列陶瓷,建筑陶瓷、工业陶瓷和卫生陶瓷等瓷器产品出口的增加,亦不可忽视。中国陶瓷企业要在技术和产品方面转型升级,推动非艺术陶瓷的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加深文化内涵。瞄准未来,才有未来。高技术陶瓷和特种陶瓷是未来陶瓷行业的发展趋势之一,必须加强研发高新产品。重视技术并不排斥文化,技术与文化好比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海丝”文化是历史的珍贵遗产,在现实中依然富有魅力。因此,外销瓷要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运用“海丝”文化元素加强设计,促进外销瓷整体的升级换代,再造辉煌。
2.2 正确处理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
中国虽然是瓷器的故乡,长期以来一枝独秀,独立风骚,但如今并非特产,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是趋势。闭关锁国和盲目排外早已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悖逆全球化浪潮。回顾历史,外销瓷就是向海而生,交流互鉴,如同植物生长一样,吸收阳光雨露才能生生不息。中国影响世界,世界作用于中国,彼此互联互通互动。美国传播学者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网络构成了各种各样的基本生活模式。”[29]如果说“海丝”是网络中的通道的话,那么外销瓷便是网络中的流动物,人们借此与远方发生联系。因此,中国发展外销瓷,传播“海丝”文化,要树立正确的大局观。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还要着重吸收外来,正确处理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
如今“海丝”国家和地区比以往要更多,影响范围更广,外销瓷更要吸收外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30]中华民族历来尚和合、求大同,以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为价值追求。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在与其它文明不断交流互鉴的过程中逐渐丰富、成熟、壮大的文明。吸收外来,不仅要善于融通国外各种有益的思想文化资源,大胆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不断为外销瓷提供养料和活力,而且还要瞄准海外市场,有的放矢,进行供给侧改革,继续提供适销对路的优美瓷器。当然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也会迷失自我和失去方向。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文化平等的原则,以开放的精神,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吸纳各民族之优长,采百家之智慧,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与世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吸收外来只是一种手段,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最终目标。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时代主题,但形势风云变幻,“四大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是最大的世界性问题。国际关系的冲突与矛盾根本在于人的思想观念的不同,器物是构建交流桥梁的良好媒介。作为全球化第一商品,外销瓷本来就是中外合璧,是超越“文明冲突论”的典范。在新时代下,外销瓷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契机走出有形或无形的围墙,通过这一器物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中国陶瓷坚持提升开放水平,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在“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加工制造型、资源利用型及商贸物流型境外陶瓷产业园区,各取所长,优势互补。不管是“中国设计+联合制造”,还是“外国设计+中国制造”,抑或是“联合设计+联合制造”,都将有利于外销瓷的复兴。发挥好外销瓷的双重功能,即经济和文化功能,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必将有利于“海丝”文化的传播。
2.3 正确处理好内容与传播的关系
内容与传播的关系在这里首先要理清传播什么内容。外销瓷在千年的发展之中,内容丰富多样,绝大部分是优秀的,但也有些许糟粕。必须去粗取精,扬长避短,与时俱进。尤其是在彩绘装饰方面,不再使用如“满大人”“一夫多妻”等落后题材,坚决拒绝使用殖民、淫秽色情、邪教等腐朽的题材。外销瓷虽然是迎合海外市场,但在中国生产,必须坚守中国正能量的底色。同时,兼顾“海丝”沿线国家的陶瓷文化,吸纳其中的优秀文化,从而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符号距离,提高受众的认可度。
其次是怎么传播的问题。传播“海丝”文化是目的,如何实现传播是手段。要想有效传播“海丝”文化,需要手段的高效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外销瓷作为“海丝”文化的极佳媒介,首先要注重外销瓷本身的发展。不管是在造型还是装饰,抑或是烧造技术、产品包装、市场营销等方面,都要与时俱进,走在时代前列,满足市场需求。就属性而言,外销瓷首先是海外贸易产品,其次是文化载体。文化交流通过商业手段其传播效果更为成功、更为持久,也就是人们常言的“卖出去”强于“送出去”。“海丝”文化因“海丝”贸易而生,那么通过贸易手段更能发展。文化通过器物间接隐性传播,“可见可听可触,对人更有直接可感性,受众更容易认知”[31]。瓷器是日常生活中常见器物,通过它可以把抽象的“海丝”文化具体化、落地化,跨越文化传播障碍,造就受众对“海丝”文化的认同。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社会媒介化已成明显趋势。[32]在传播力决定影响力的今天,围绕外销瓷直接讨论如何传播“海丝”文化也是一大重要课题。这就需要有关各方加强合作,构建协同机制,共同传播。例如,政府要注重政策引导,搭建交流平台,如陶瓷国际博览会、“海丝”学术研讨会、大型政治会议的“瓷器国礼”展等。各级政府加强对外销瓷的保护开发,打造相关线下线上场所,提供展示外销瓷的实体和虚拟空间。对于“海丝”文化的传播,沿线诸国出于国情在认知上或有差异,这就离不开政府之间的外交斡旋。“文化是最大的经济,经济是最大的文化,经济与文化彼此在对方的领域实现自己。”[33]“海丝”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政府重在引导,市场主体才是主角。陶瓷企业也要有文化自觉,要有传播“海丝”文化的主体意识。生产外销瓷,不仅仅是制造加工一件普通商品,而是打造一件文化艺术品。把中外文化元素有机融为一体,互利共赢,“海丝”文化才能得到更有效的传播。陶瓷企业要力推外销瓷的复兴,重新焕发昔日的勃勃生机,展现“海丝”文化的新风采。传播机构要不断更新传播理念,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利用VR、AR、区块链、5G、超高清等最新技术围绕外销瓷做文章,打造融媒体产品体系,提高信息在场率,加强对“海丝”文化的传播。公众人物或意见领袖,发挥好自媒体的作用,合理运用传播影响力,为“海丝”文化的传播添砖加瓦。如果说传统媒体具有授权性,是官方大使的话,那么自媒体就具有草根性,是民间大使。在传播渠道与受众需求日渐多元化的今天,再小的自媒体都有它的传播空间与粉丝,民间大使的作用不可小觑。自媒体要有责任感,上微博、发朋友圈等都要以正能量为导向,响应主旋律。爱好外销瓷的用户,不局限于做欣赏者,要做参与者,甚至可以UGC(用户生产内容),合力传播“海丝”文化。
一言以蔽之,内容为王,传播为要。
3 余论
外销瓷是“海丝”的宝贵遗产,可谓是丝路上最重要的活化石,浓缩了“海丝”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成为体现和传播“海丝”文化的极佳媒介。在新的时代下,外销瓷能否发挥如同昔日的传播作用,有待以史为鉴,创造条件,再创辉煌。因此,我们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断推动外销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要重视、把握传播之道,发挥传播之长,共同构建和传播“海丝”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