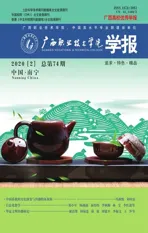我与华夏传播学体系的建构(下)(之二)*
——“三大体系”之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探索之路
2020-03-15谢清果
谢清果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
(续上篇,上篇发表于本刊2020 年第1 期第6—14 页)
上一篇我介绍了“华夏传播学”学科体系建构的点滴心得,主要侧重教材建构方面。本篇作为全部专题文章的第四篇即最后一篇,就与读者一起畅谈下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构方面的一些思考与做法,盼望能起抛砖引玉之效,诚挚邀请同行结合自己的经验一起把这个话题引向深入,共同为了传播学“中华学派”的早日实现而不懈奋斗!
3 搭建学术平台:以学术共同体为核心打造“华夏传播学”学术体系
华夏传播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其构建之路才刚刚开始。参照季为民构建中国新闻学学术体系的思考,“学术体系主要包括学术思想、代表学者、学术流派、专业论著、研究方法、道德规范、评价标准等要素和学术活动平台等辅助系统。”[1]华夏传播学的构建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开展研究,通过打造华夏传播研究会等形式的学术共同体和以《华夏传播研究》《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等专业刊物为代表的学术成果展示平台以及学术成果评价体系、学术社团组织、学术伦理规范等学术辅助系统,持续探索,精心建设,不断完善,世代传承,不断汇聚各方面的人才,发展和完善研究方法,形塑华夏传播学的学术范式,增强学术共同体意识,推进学术创新,传承学术精品,推出学术新锐,提升华夏传播在中国传播学界的学术地位与学术话语权。
3.1 学术刊物提升了华夏传播学的显示度
2013 年是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成立20 周年,为了纪念前辈的丰功伟绩,进一步推动华夏传播研究再上新台阶,研究所决定创办一份学术期刊——《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著名学者孙旭培教授亲自题签了刊名。我在题为《责无旁贷地推进华夏传播研究》的发刊词中深情地写到:“我们将在许多海内外学者的关心指导下,继承华夏传播研究的传统,高扬华夏传播研究的主体意识,争取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我们将以刊物为平台来集聚研究队伍,一起切磋琢磨,共同促进中华文化传播与创新,以无愧于这个多彩的时代。”[2]这份集刊前5 期为年刊,2017 年与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后,转型为半年刊,由九州出版社出版,著名学者詹石窗教授题签了刊名,至2019 年共出版6 辑。该刊共开设10 个栏目,每辑都策划有一个主题,并将之设置为该辑主打栏目。10 个栏目中“盐文化研究与传播”“贤文化与组织传播研究”“国学新知”由中盐金坛公司文化部主持,其它7 个专栏由我邀请海内外学者主持。这6 辑主打栏目分别是“乡村传播与文化空间”“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中国礼文化传播研究”“老子传播思想研究”“华夏文明传播研究”“认识传播学探索”(以上各辑中国知网均有收录)。
2018 年,在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庆祝建所25周年之际,在新闻传播学院领导的支持下,我决定创办《华夏传播研究》集刊(半年刊)。郑学檬教授题签了刊名,郑学檬、孙旭培、陈培爱、邵培仁、戴元光、李彬、吴予敏、赵振祥、陈国明(美国)、黄鸣奋等一批学者发来创刊贺辞。这本集刊与《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相呼应,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列入“传媒集刊方阵”出版。《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的办刊宗旨是“华夏传播·文明传承·文化自觉·民族复兴”,定位为以华夏文明传播研究与贤文化传播研究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新闻传播类集刊,论文字数通常在1 万字以内;而《华夏传播研究》则以“中华文化立场·全球传播视野”为办刊宗旨,以建构“华夏传播学”、打造传播学“中华学派”为己任,力争成为华夏传播研究领域专业性高端学术集刊,论文字数通常在1.5 万字左右,亦可长达3-4 万字。该刊目前已出版2 辑,第3、4辑正在出版中。
3.2 开辟专栏,进一步拓展学科展示平台
黄星民教授看到我们创办了两份集刊,高兴地说,余也鲁那个时代还没有设想过创办期刊,现在办出两份集刊,这是新的进展。邵培仁教授也多次勉励我们,说这几年经过一批青年学者的努力,把本来冷清的研域搞得红红火火。吴予敏教授也肯定华夏传播研究会这几年办会办刊颇有起色。《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集刊在其公众号上将《华夏传播研究》与《中国网络传播研究》《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符号与传媒》一起列为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代表性集刊。暨南大学刘涛在《理论谱系与本土探索:新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70 年(1949—2019)》一文中专列“本土思想的理论推演”部分,指出李敬一、邵培仁、谢清果、潘祥辉、李红、姚锦云等学者“比较系统地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或思想遗产中所蕴含的传播观念,努力以‘华夏传播学的名义’与西方对话,追寻和确认中国传播的本土身份。”[3]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我认为很有必要跟一些学术性期刊合作。2016 年,邵培仁老师在其主编的《中国传媒报告》总第60 期上邀请我担任“华夏传播研究”专栏主持人,并刊发了由我组织的一组文章;2019年,《西北师大学报》第2 期首次刊出“华夏传播研究”专栏3 篇文章;同年,《郑州大学学报》第3 期刊载了两篇礼文化传播的文章;2020 年,《山西大学学报》通过专栏刊发华夏传播研究方面的论文。最为难得的是,《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邀请我从2019 年第4 期开始开设并主持“华夏文明传播研究”专栏,逢双期刊出,一年三期,每期5-6篇论文。此外,《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四大刊也是发表本领域研究文章的重要期刊。可见,华夏传播研究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认可与关注。
3.3 成立专业研究会增强“华夏传播学”学术共同体意识
进入21 世纪以来,我深切感到20 世纪90 年代盛极一时的华夏传播研究由于后续缺乏组织领导等原因,日渐有边缘化之势。于是,我发愿要重新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形成学术共同体。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奔走联络,华夏传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逐渐成形,其构建之路经历了若干阶段和步骤。第一步,2016 年3 月25 日晚,在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委员会筹备成立的会议上,我申请在该会下成立华夏传播研究工作组并得到了批准。第二步,2017 年11 月18 日,借助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委员会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召开年会之际,我发起承办了年会上的华夏传播研究分论坛,并于19 日上午召开了华夏传播研究会成立筹备会,来自华东师大、西南政法大学、深圳大学、广州大学、郑州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的十余位代表畅谈了推动华夏传播研究的思路,共商筹建研究事宜。第三步,同年12 月19 日,我应邀参加了全球修辞学会在越秀外国语学院召开的学术年会,会长陈汝东代表该会批准“华夏传播研究会”加盟的申请,期望共同推动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第四步,2018 年9 月16 日,在江苏金坛召开的首届“华夏文明传播与企业家精神培育研讨会”闭幕式上,在全国一级学会——“华夏文化促进会”的支持下,“华夏文化促进会传播专业委员会”(简称“华夏传播研究会”,下称“研究会”)正式挂牌成立。研究会礼聘吴予敏为荣誉会长,郑学檬为首席顾问,孙旭培、邵培仁、李彬、戴元光、陈国明、黄星民等一批学者为学术顾问,由我担任会长。从此,华夏传播研究有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有了推动相关学术活动的稳定组织。
为了彰显华夏传播研究影响力,不断提升学术显示度,我积极联合各方力量持续举办了专业学术会议与工作坊。早在研究会正式成立之前,我就以传播研究所为推动机构,举办专业性学术研讨会。如2016 年5 月14 日,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厦门筼筜书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及厦门伟纳机电技术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中华文化与大众传播研讨会”。2018 年5 月18-19 日,西南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联合主办了“传统文化与传播学术研讨会”。2018年9 月15-16 日,华夏传播研究会与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共同主办了首届“华夏文明传播与企业家精神培育”研讨会。研究会成立之后,举办了更多的学术研讨会,如2019 年4 月12-13 日,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研究会联合举办了首届“礼文化与华夏文明传播研究”工作坊。在2019 年5 月11-12 日举办的第一届“媒介中国研究百人会”上,研究会副会长潘祥辉教授主持了其中的“传统文化中的传播考古”研讨组圆桌会议与“传统文化与华夏传播”论文发表组圆桌会议。2019 年7 月5-6 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办了首届“贤文化与华夏传播研究”工作坊。2019 年9 月21 日,我受邀请在首届“传播与认同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华夏传播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历程”的主旨演讲。2019 年11 月22-24 日,研究会与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合办“‘一带一路’倡议与华夏文明传播研究学术研讨会”。此外,研究会还以协办机构的名义,参与举办了重庆大学主办的“第十一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华南理工大学主办的“跨学科视域下传统族群文化的现代传承与文化认同”学术研讨会。我还牵头在2019 亚太传播学会联盟年会上举行了一个“本土传播学”方向的讨论组。2020 年,研究会还将与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扬州大学、深圳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多场学术研讨会。正是因为有了多场研讨会、工作坊的举办,华夏传播学以崭新的姿态重现于中国传播学界,并占据了一席之地。
3.4 主编专业丛书,彰显“华夏传播学”学术生产力
通过丛书集中展现某个领域或某个学科的学术成果,已成为许多学科发展的标配。为了打造华夏传播研究的学术体系,夯实华夏传播研究的学理基础,开启新时代“华夏传播学”研究新高度。我主编了以下几套丛书:
其一,主编《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丛书》。刊物与丛书互相配合,学科的显示度就会增强。在举办《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集刊的时候,我同时筹划主编《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丛书》,2014 年,我利用手头结余的科研课题经费出版了《华夏传播学读本》《道教养生哲学与生活传播》《道德经与当代传媒文化》等三部著作。
其二,主编《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文库》。2015年厦门大学社科处资助著作出版,我提交了《生活中的老子——〈道德经〉与大众传播学》这部书稿。当时心想如果将来能出版一套丛书,就以这本作为丛书的第一本著作。受这个念头启发,我开始主编《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文库》,进而首次提出“华夏文明传播”这个观念,因为当时认为“文明传播”是“华夏传播学”的理论特质。《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文库》从2016 至2019 年已出齐10 卷,上面提到的那本是第1 卷,其余9 卷分别是《大道上的老子——〈道德经〉与人际沟通》《华夏文明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张湛、卢重玄〈列子〉诠释研究》(林俊雄著)《甲骨文四重证据研究法》(巫称喜主编)《华夏传播学的想象力》《中庸的传播思想》《华夏文明与舆论学中国化研究》《光荣与梦想:传播学中国化研究四十年(1978-2018)》《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研究举隅》(吉峰著)。这当中有三本是同行所著,其余均为我编著。
其三,主编《华夏传播学文丛》。2019 年,我开始主编第三套丛书——《华夏传播学文丛》。这套丛书我直接使用了“华夏传播学”这个提法,希望能够比“华夏传播研究”更为简洁明了。现已出版《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九州出版社,2019),后续还将有《华夏礼乐传播论》《华夏文明传播论》等著作出版。
其四,主编《华夏传播研究论丛》。为了庚续2001年郑学檬主编的《华夏传播研究丛书》(三卷本)的传统,我也主编了三卷本的《华夏传播研究论丛》,这三卷分别是:《华夏传播研究在中国(谢清果卷)》,主要收录我和我的团队近年发表的论文;《华夏传播研究在海外(陈国明卷)》主要收录陈国明在海外发表的论文。经他授权,我组织团队对论文进行了翻译,因此书中许多文章是第一次用中文形式推出;《华夏传播学年鉴(2019)》,主要是为今后出版专业年鉴试水。丛书将于年内正式出版。
其五,主编《经典与传播研究丛书》。主编出版这套丛书是为了呈现同名读书会的成果。该丛书已于2019 年出版了《庄子的传播思想》,《〈论语〉的传播思想》即将面世,年内还将推出《〈周易〉的传播思想》《经典新探:王充〈论衡〉的传播学释读》(吉峰著)等,未来计划推出《〈礼记〉的传播思想》《〈尚书〉的传播思想》《〈孙子兵法〉的传播思想》等,出版总数至少达10 部。
其六,主编《华夏传播学读本丛书》。我认为既然中国传播学有政治传播学、经济传播学、文化传播学、艺术传播学、时尚传播学,华夏传播学同样也可以有华夏身体传播学、华夏情感传播学、华夏文明传播学等垂直细分领域,我现在已在指导博士生去开拓这些领域,为了与研究相配合,我就规划了这套丛书,计划于2020 年陆续推出,主要包括《华夏传播学新读本》《华夏文明传播学读本》《华夏身体传播学读本》《华夏情感传播学读本》等。
4 提炼学术概念:构建华夏传播学的话语体系
季为民指出:“话语体系反映人类交往活动中交往主体通过语言符号建立起来的表达与接受、解释与理解、评价与认同等多重关系,包括术语、概念、范畴、命题、判断、语言、思想等要素。”[1]华夏传播学应以本学科核心概念为基础,以中华文化自身的话语系统为表达架构,总结我国五千年来传播实践的话语逻辑,形成华夏传播学的表达系统和话语体系。其基本要素包括:术语和概念(核心概念、扩充概念、边缘概念、交叉概念)、基本观点和思想原则、专业知识和表达逻辑等。习近平同志在“5·17 讲话”中也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4]对于华夏传播学而言,在离真正建立学科还很遥远的当下,可以从打造核心和标识性概念和有代表性的理论体系着手,由点突破,再到面,再到体,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4]“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4]华夏传播学要积极因应时代的呼唤,回应传播学中国化过程中提出的时代命题,以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深厚积淀为基础,以自主、开放、包容、对话的原则,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传播学的文化资本,让五千年的实践成为构建华夏传播理论体系最为可靠的基础,进而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形成适合时代发展和国际合作潮流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从而改变中国的话语权在世界上处于劣势的被动局面。只有打造出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富有时代新气息的思想理论体系,才能在话语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正如习近平所说的,“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4]华夏传播学只有能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思想资源与动力支持,才有生命力,也才能有底气与世界传播学对话。例如,面对西方文明的宗教传播本质,中国可以彰显中华文明的礼乐传播本质。宗教文化传统可以开出民主政治与自由平等之花,礼乐文化传统也可以结出贤能政治与协商民主之果。发展路径是多元的,条条道理通罗马,不同的思想文化,可以在共生交往中交流互鉴,共同进步,或许未来正是在中西对话中“行中庸,达中和”。
4.1 提出“共生交往”新观念
华夏传播学的基本观念首先便是“华夏”,便是“中国”。“华夏”是“中国”的美称,其精神实质体现在“中国”上。因此,我首先提出“中国”是一种传播观念,进而分析指出这种传播观念的内核是“共生”,因为“中国”是以“中”立国,而“中”体现着中心与边缘,内与外的关系,并将关系致于“中和”的价值目标之中,以达“适中”“共赢”的效果。循着这样的思路,我发表了《共生交往观的阐扬——作为传播观念的“中国”》《中华新文明主义的共生交往特质》《构建人类沟通共同体的理论依据、可能路径及其价值取向》等一批有显示度的学术论文,并带领团队共同推进研究,进而结集出版了《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一书,努力向世界阐述中华文明具有的共生交往独特气质。
4.2 深化“华夏文明传播学”的研究旨趣
“文明传播学”是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杨瑞明及其团队提出的一个研究思路,他们还出版了《文明传播的哲学视野》《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等书。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领域,于是我努力将“文明传播学”的视角引入华夏传播研究,试图用中国的中庸、天下、和谐、礼乐等中国式话语来阐述华夏文明的沟通智慧,向世界说明华夏文明的特质是以追求“天下太平”为己任,秉持“和而不同”观念的共生交往观。我能获批“华夏文明传播的观念基础、理论体系与当代实践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华夏文明传播学的理论体系、教学模式与实践探索的综合改革研究”省教改项目,主持的团队获批“华夏文明传播研究团队”,得益于我将研究着眼于探讨华夏文明的传播智慧这一时代需要。在日益全球化的当下,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就亟须向世界说明中国。最好的做法便是中国经验,世界表达。文明研究是国际学术界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华夏文明传播研究的旨趣就是将中华文明放置在人类文明竞争的舞台上,进而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价值,向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却又为西方话语所需要、所能接受的传达方式。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中国式表达可能是天下大同、家国天下、天下一家这样的话语,西方不容易理解,因为“家”不是西方理解世界的起点,如果我们要向世界传递这一理念,就需要用“共同体”这种流动于马克思理论和康德的哲学观念中同时又为西方学者熟悉的方式来表达。这种表达在无形中又传递着中国的传播智慧,我称之为“共生交往”。“共生交往”理念非常类似于马丁·布伯的“我和你”思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念。
学术研究需要有较高的学术站位,才能回应时代命题。以我的被厦门大学列入一流本科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目录的华夏传播概论课程为例,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我努力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融入华夏传播研究之中,深化华夏文明传播研究。例如,我一面聚焦“华夏文明传播”这一议题,潜心研究中华文明蕴藏的传播智慧,一面积极回应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人类文明互鉴的重要论述,撰写了《天下一家:新时代人类文明交往观的中国气派》《文明共生论:世界文明交往范式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思想体系》等系列文章,同时在研究生课程中开设“华夏文明传播专题研究”,合作出版《华夏文明研究的传播学视角》一书,带领团队进行中西传播思想的比较研究,即将推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新境界——中西传播思想的分野与对话》一书,不断深化华夏文明传播研究。
4.3 提出“生活媒介”新概念
在教学相长思想的激励下,我带领和引导博硕士不断开拓出华夏舆论学、华夏媒介学、华夏自我传播学、华夏身体传播学、华夏礼乐传播论等华夏传播学研究新领域,与他们共同探讨研究课题,撰写论文,组织读书会,研读中西经典,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培养华夏传播学研究的接班人。在倾力培养博硕士的过程中,我的体会是,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要把他们当成学术上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展头脑风暴,甚至一起申报各类课题,总之,把自己成为一名学者所经历的所有工作都让研究生有所参与和体验,于实战中培养学生,增强他们毕业后的竞争力。我常勉励学生说,我不是世界冠军,但我力争成为培养世界冠军的人。比如刘翔的老师不是世界冠军,而他却能培养出世界冠军,这正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为师者当力求成为伯乐,学生当力争成为千里马;老师爱教,学生爱学,如此才能一起并肩站在学术研究前沿,开创华夏传播研究的新境界。
以2019 年为例,我从欧文·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获得启示,我想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媒介共同联系着人们,从而造就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这些生活中的媒介在我们的世界中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而不是“在手”,我们日用而不知。目前学人更多关注的是大众传播媒介,而忽视了日常生活中众多交往的媒介。于是我在讲授中国传播理论研究这门课时,组织博硕士从媒介学这一新兴的角度,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牌坊、茶文化、礼文化、长江、门、十二生肖、陶瓷等媒介,进而推出《华夏传播研究:媒介学的视角》一书。在授课过程中,我也撰写了《媒介哲学视角下的老子之“门”新探》(《山西大学学报》2020 年第2 期)一文。写这篇文章给我的感受是,压力出效果,为了尽快写出初稿以便向学生讲解自己的研究心得,就强迫自己处于亢奋的写作状态,连续作战几天,形成了初稿。由于初稿字数较多,后来将“作为生活媒介的门”这一类似综述的部分单独成篇,而论述《道德经》五章中出现的“门”的媒介意义部分,就独立为另一篇论文。这次研究再次成功证实了我以往写一篇论文可以分解成多篇的经验,也让我明白,对传统文本的研究,如果能引入新的视角,可能会有别样的发现。受此激励,我今后还会继续从事“老子与媒介学”的专题研究。
行文至此,该给为《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华夏学人”专栏撰写的“我与华夏传播学体系的建构”系列文章做个结语了。感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的邀请,让我有一次梳理自己心路历程的机会,这真是一种不期而遇的因缘。我相信有了这种因缘,我与华夏传播学“三大体系”建构的因缘也必将结出“平安喜乐”的善果。
我虽鄙陋,却也有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情,因为我始终怀着与学界同仁共建“华夏传播学”的雄心壮志,把锻造传播学“中华学派”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为此,我将秉承老子“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的思想,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与担当,与华夏传播研究的同仁乃至整个中国传播学界一起直面中国现实,关怀人类未来,立足中华文化传统,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创未来”的原则,向世界贡献传播学的“中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