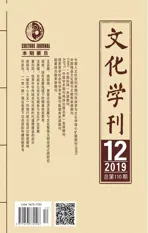庾信赋中桃意象的嬗变
2019-12-26胡悦
胡 悦
庾信的赋作“华实相扶,情文兼至”,这与他在赋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象是分不开的。在诸多意象中,占据主要篇幅的植物意象群格外引人注目。南朝时期的庾信与父一起出入禁闼,为文轻艳绮丽,赋作中常用春树、杨花、蒲桃、香草、杨柳、石榴、芙蓉等明媚纤细、欣欣向荣的植物意象,是东宫学士“出丽华之金屋,下飞燕之兰宫”[1]的优游岁月的写照。羁留北周后,故国的衰亡和人生的变化在他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此后,庾信笔下的明丽色调不见了,几乎很难在其后期的赋中再看到“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这样生机勃勃的意境,取而代之的是“桂何事而消亡,桐何为而半死”的凄怆悲凉。在后期的赋作中,他偏爱“枯树”“庭槐”“菌苔”等表现孤苦心迹的意象[2]。然而,“桃”意象始终贯穿于庾信赋前期、后期创作,其意蕴的嬗变是他由南入北后心性大变的映射。桃花形美色丽,素来是春日忽略不过的盛景,出现在庾信前期的赋作中无可厚非,但在其后期的赋中仍能频频看到“桃”的身影,不由得引人深思。创作后期,庾信偏爱冷色调植物意象,仍付诸笔墨描绘的“桃”意象定然别有深意。探析“桃”意象在庾信前期、后期赋作中的嬗变,或能对庾信由东宫少年的“香艳绮靡”到北地栖客的“沉郁苍凉”的心境变化有更深刻的了解。
一、庾信前期赋中的桃意象
“桃”意象最早可追溯到作为文学源头的《诗经》。《诗经·周南·桃夭》载:“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灼灼桃花林,娇俏新嫁女,盼其婚姻美满顺遂,往后家庭光景便都如这春日熙熙。《诗经》比兴,咏桃并非止于描摹物状,这里的桃花与新嫁娘并不是路边景色与过客的关系,鲜艳的桃花已然是娇俏少女的化身,桃花灼灼其华的样子便是女子新婚最好的象征。庾信的前期赋作中的“桃”意象便带有这种“桃花美人”的意蕴内涵。
《春赋》载:“出丽华之金屋,下飞燕之兰宫。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影来池里,花落衫中。”[3]
此赋将眼前盛景与历史佳话相融,尽写游春之乐。这一段描绘的是一幅“仕女游春图”:不觉璀璨金钗重、唯恐多情春风乱发髻的仕女们,仿佛是从昔日陈阿娇的金屋、赵飞燕的兰房椒壁中摇曳而出,娥眉更比柳叶翠,人面恰若桃花红。美人的一蹙一频倒影在清波池水里,纷纷落花沾染在罗裙衣衫上。春风荡起池水的微波,吹落枝头的花朵,却都不及仕女们盈盈动人。这样融古入今的繁典、细腻的情思正是“徐庾体”的风格。彼时庾信少负才名,与父俱仕南梁,出入禁闼,深受皇恩,更有志同道合的好友徐陵一同交游唱和,正是春风得意少年时。所见是“二月杨花满路飞”,所闻是“新年鸟声千种啭”,所想是“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潘岳栽桃满县的河阳,刹那间成了灿若云霞的桃花天堂,石崇那驰名遐迩的金谷园中更有万株花树吐艳争辉,一如东宫少年意气风发的内心世界。不论是“桃花美人”或是“桃花天堂”,庾信前期赋作中的“桃”意象都十分生动美好,正是优游岁月的体现。
二、庾信后期赋中的“桃”意象
(一)“银角桃枝”的“不贰臣”意味
庾信后期的赋作中,“桃”不再仅仅以其鲜艳美好的外在形象出现,而是具有了更深刻的内涵意蕴。《竹杖赋》载:“桓宣武平荆州,外白:‘有称楚丘先生,来诣门下。’桓公曰:‘名父之子,流离江汉,孤之责矣!’及命引进,乃曰:‘噫,子老矣!……寡人有铜环灵寿,银角桃枝。开木瓜而未落,养莲花而不萎。迎仙客于锦市,送游龙于葛陂。先生将以养老,将以扶危。’”[4]
桓温听说楚丘先生来访,便想赠送给他一枝银角桃枝的珍贵手杖,供他养老扶危,楚丘先生则引经据典极言自己心忧生民,不计个人安危而委婉谢绝。这篇赋盖作于庾信初入北时,他以楚丘先生自喻,将周文帝宇文泰比作桓温。汉武帝曾因杨彪有政德,将一枚银角桃枝赐予他。曹魏建立后,杨彪受封光禄大夫,未免有“贰臣”之玷。文章中,庾信不愿接受“银角桃枝”,借以表示自己不愿仕北,表白自己不贰臣的心迹,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赋中的楚丘先生拒绝了桓温的“银角桃枝”,庾信却没有拒绝孝闵帝宇文觉给他的高官厚禄。庾信出使西魏后不久,恰逢两国交战,西魏出兵攻克江陵,梁元帝箫绎殒难,庾信因而滞留西魏都城长安未能归梁。他被西魏政权先后任命为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楚丘先生与庾信在面对“银角桃枝”时做出的不同抉择便是庾信内心矛盾的展现。庾信是“名父之子”,自小接受的家学便是儒家思想。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首义是“忠孝”,他渴望能成为君臣伦理与个体利益发生尖锐矛盾时坚守道德的“儒家君子”,因而塑造了“楚丘先生”的形象,这是他理想人格的化身,但庾信毕竟是生于官宦人家、养尊处优的诗人,未经历太多磨难坎坷,即便是入北后也备受优待,人生可期时,轻易赴死殉节谈何容易。正因如此,国难当头之际,他才未能坚守心中的“忠孝”理想同国家共存亡,且做出身仕敌国的无奈之举。“银角桃枝”象征了庾信这种失节行为与心中“不贰臣”的君子理想的悖离,这种人格理想与现实行为的矛盾导致他的心境从曾经的东宫少年的春风得意变为北方羁臣的苦闷煎熬。
(二)“梨桃百树”的隐逸理想
“桃”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源远流长的内涵便是“仙境”。《山海经·海外北经》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5]
神话传说赋予了桃林神秘的色彩,夸父手杖幻化成的桃林便是仙境般的存在。晋陶渊明一篇《桃花源记》更是将“桃林”的这种仙境意蕴发展为士人心中对抗现世黑暗的理想社会的写照,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桃花源”或“桃源”便蕴含了文人对理想乐土的向往及逃避俗世的隐逸思想[6]。彼时优游岁月的庾信或许还不能完全从心底与陶渊明的“桃源”隐逸产生共鸣,真正意义上的“桃源”理想出现在庾信的作品中,是在其后期创作的《小园赋》中:“若夫一枝之上,巢夫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况乎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座;嵇康锻灶,既烟而堪眠。……纵横数十步,榆柳三两行,梨桃百余树。拔蒙密兮见窗,行敧斜兮得路。蝉有翳兮不惊,雉无罗兮何惧!”[7]
一枝一壶便可让巢夫壶公安巢容身,诗人也想像管宁、嵇康那样避世归隐,寻一处心灵庇所。庾信在文中援引了诸多隐逸名士,借以表达自己出世归隐的志向。他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理想园,园内梧桐纷落,柳下清风徐来。棠梨苍翠,酸枣盛多,沿着八九丈错落有致的小园,纵横徐行几十步,没有靡靡丝竹音,得见三两行榆柳,还有百余树梨桃,拨开嫩枝细柳即见窗台相映,走过蜿蜒的幽径可得前路迢迢。不畏酷暑炎炎,不悲秋风瑟瑟。
经历过侯景之乱、南梁覆灭、滞留北地的庾信终于懂得陶渊明的“桃花源”是怎样一处安顿心灵的乐土时,却已深陷身仕敌国的煎熬之中,因此,他充满感情地描绘小园带给他的避世生活,渴望借此暂时摆脱身心的煎熬。但他终究不是陶渊明,而是抱怨“苦李无人摘,秋瓜不值钱”、追问“长门一纸赋,何处觅黄金”的庾信,他没有办法说“归去”就真的去过“带月荷锄归”的生活。“梨桃百树”的小园的遁隐之念只是他煎熬内心的一剂镇痛药,非他真正安顿心灵的理想园。庾信终究不是陶渊明,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使他耻于仕北,但个人的人生追求又使他难安于隐,“梨桃百树”是庾信这种欲隐还仕的矛盾心理的表现。
(三)“河阳县花”的乡关之思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士人不仅难以实现自己安身立命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往往还要面临颠沛流离的生活境遇,少有能安享天年者,故而感叹人生苦短、时光易逝是魏晋诗歌的一大传统主题。从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到曹植“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再到孔融“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无一不是感叹人生短暂、人事无定。“桃花的这种生而绚烂却易枯萎的‘短命花’特征与魏晋文人的生存状态相契合,故而‘桃’意象在魏晋文人笔下又生出了一层时光易逝的生命忧患意识。”[8]庾信笔下的“河阳县花”不仅具有这种人事消亡的生命之感,还饱含了其独特的“乡关之思”。《庾子山集注》中所载的赋作中,“河阳县花”共出现了两次,分别是在前期《春赋》中“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一句和后期所作的《枯树赋》中。
《枯树赋》载:“东海有白木之庙,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陆以杨叶为关,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则丛桂留人,扶风则长松系马。岂独城临细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建章三月火,黄河万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9]
在《春赋》中,“河阳县花”“金谷树园”还是灿若云霞的桃花天堂,是万株花树吐艳争辉的勃勃景象。如今,建章宫的栋梁被大火焚尽,往来黄河的万舸木筏腐烂在水中。金谷园里的柏树凋敝零落,河阳县的十里桃花枯萎不存。昔年在东宫出入禁闼的少年也已然变成了贰仕北周的羁臣,就如同凋敝的树园、枯萎的桃花不复生机那样,南梁时期的优游岁月也一去再不可能复返。就如同被移动的大树流着眼泪,受伤的树根鲜血淋漓,繁茂可爱的树木也因时序变迁枯败凋零,人又要如何去抵挡时光的无情呢。庾信借助桓温“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典故,道尽自己由南入北、儿女罹难、家国俱亡的辛酸苦楚。“候景之乱”时,庾信本有机会守护对他乃至他的家族宠命优渥的南梁朝廷,敌军至时他却弃军而走,没有在朝廷危亡的时候挺身而出,滞北之后却又深深眷恋故国。乱后不久,庾信被遣北魏,正值魏骑南下,江陵覆没,自此故国消亡,庾信归无可归,昔年笔下的“河阳县花”成为了心底最遥不可及的“乡关之思”。
三、桃意象与庾信的矛盾人格
意象是诗人心灵的窗户,笔者在关注其文学创作的意象时也希望能加深读者对庾信的精神人格的了解。桃意象贯穿于庾信前、后期的赋作,见证了诗人从仕与南梁到羁宦北朝的心理变化。庾信前期赋作中的“桃”意象都十分生动美好,“桃花美人”的细腻情思、“桃花天堂”的缤纷景致无不体现了诗人在南梁优游岁月时期意气风华的少年心态;入北后,庾信笔下的“桃”不复前时的艳丽绮靡,有着更加深刻的内涵意蕴,也昭示着诗人经历过国破家亡的人世沧桑后的复杂内心。“银角桃枝”体现了诗人初入北时抗拒贰臣于敌国的思想,但现实却又和他向往的美好品质悖离;诗人向往成为儒家君子,现实的仕途前景却更令他渴望。“梨桃百树”的小园是诗人仕北后难以承受失节的痛苦时,转向道家思想、转向隐逸避世、寻求一时精神解脱的理想园,表现了诗人“欲隐还仕”的矛盾心理。“河阳县花”曾经是诗人意气风华的写照,而今桃花枯萎,故国不复,人事的沧桑使得诗人内心饱受痛苦,那一县灼灼的桃花林也就成了诗人心底归无可归的故国念想。庾信赋中桃意象的嬗变投射出其一生复杂苦闷的心态和矛盾的人格特征。
庾信的文学作品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宝藏,后人研究其“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艺术成就时,也当了解庾信在那个南北动荡的历史岁月里的人生经历,并通过对其作品意象的分析来体味他复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