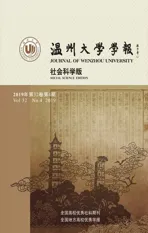琦君笔下的温州形象及文化记忆
2019-12-22邹淑琴
邹淑琴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作家琦君的前半生在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度过,而她的后半生,从33岁迁台,除去旅美的二十多年,其余光阴都在台湾度过。这样的人生势必造就了其独特的怀旧文风。与第一代迁台女作家类似,她把满怀的故土幽思诉诸笔端,在自己的文本中走向了记忆中的故乡。这些记忆无疑是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和个人情感的空间、历史、文化记忆。琦君作品对故乡的美好回忆,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特殊时代的温州形象,隐含着独特的传统文化审美意蕴。
一、跨时空的地域书写与文化记忆
在远离故土的异乡,琦君作品以“自我”与“他者”双重视角的时空转换书写,展现了作家在远离故乡多年后对故乡形象的记忆和怀念,这既是一种回忆性的、带有一定的主观想象性意味的书写,又是对地域历史文化记忆的真实重现。
琦君原名潘希珍,童年生活于溪流翠竹、三面环山的温州永嘉,这里风光旖旎,是历来被文人墨客们吟咏称颂的山水名胜之地。琦君的童年时光是快乐的,故乡优美的山水自然景观始终萦绕在她的脑海中,且历历在目。
琦君笔下的故乡是一幅风情万种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江南水乡图。读其作品,仿佛来到温州乡间的绿野平畴,陶醉于那一湾蔚蓝的溪流、一望无垠的麦浪里,烟雨中的笛声、纷落肩头的桂花、碧叶丛中的粉荷、白雪中明艳的红梅、弯弯曲曲的小径、古朴深邃的小巷等纷至沓来,令人心旷神怡。《清明劫》中描绘了家乡瞿溪乡间的田园风光:“水田里的秧苗,细细软软地像绿色的毛绒,随着风儿微微抖动,太阳晒着潮湿的田岸,发出一阵阵泥土和野草的青草气息。”①参见:琦君.琦君散文选[M].林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11.下引该书原文不再一一注出。在收获的季节里,“晒谷场……望去一片开阔,太阳晒在一束束麦秆上,闪着象牙般丰盈的光泽。”在作家的笔下,永嘉之美如绵绵细雨,烟雨迷蒙、温婉清雅,萦绕在古典诗词的意境中,又如散文《何时归看浙江潮》中,“晨曦自红霞中透出,把薄雾染成了粉红色的轻纱,笼罩着江面。粼粼江水,柔和得像纱帐里孩子梦中带笑脸……”还有“故乡矮墙外碧绿的稻田,与庭院中淡雅的木犀花香”[1]。在《桂花雨》中淡如烟雨的桂花纷纭摇曳,恰如故乡的梅雨天,绵绵不休。记忆中的故乡恰如这飘香的桂花,沁人心脾,这不禁令人心醉神往。田野、花香、橘园、细雨、溪流、石阶、青苔等景致共同营造了这江南水乡独特的温润之美。
故乡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致孕育出醇厚悠久的人文风韵,成为积淀在作家内心深处的文化记忆。琦君对故乡那充满传统伦常观念的乡土民俗、人情风习书写是其作品中最精彩的内容之一。
琦君作品描绘了一幅幅瑰丽的温州瓯海民俗画卷,生动再现了20世纪初商贸名镇瞿溪丰富多彩的民间生活。在《春酒》《喜宴》《桂花雨》《春节忆儿时》《压岁钱》《看戏》《灯景旧情怀》等散文中都详细描写了当地各种年节礼仪庆典、习俗,如春节前喝春酒、喝会酒,腊月二十七八“解冬”(送冬祭祖)、大年夜“点喜灯”、正月初七八的迎灯庙会等,还有元宵节农民们舞龙的场面(《灯景旧情怀》)端午节水上划台阁(《小仙童》)中秋节吃“月光饼”:“每到中秋,家家户户及商店,都用红丝带穿了一个比脸盆还大的月光饼,挂在屋檐下。廊前摆上糖果,点起香烛,和天空的一轮明月,相映成趣。”(《月光饼》)等。
琦君的许多作品十分真实、细腻、全面地再现了瞿溪乡间日常民俗,如《春节忆儿时》中详细写了人们迎春前后的忙碌,从宰猪、掸尘、捣糖糕、分岁酒到拜年、迎神提灯,一整套年节习俗程序紧凑而又有条不紊,充满了仪式感。琦君作品还写到一些民间日常生活习俗,如《桂花雨》中,当家乡桂花盛开的时候,人们铺篾簟、摇花、拣叶、铺晒,以备日后泡茶、做糕饼。各种饮食也极具地方特色,如《桂花雨》《玉兰醉》《想念荷花》中写到以花入食,还有制作玫瑰露、红豆糕,端午的“灰汤粽”等花样繁多的传统饮食,其蕴含的文化内容也异常丰富。当地的民间歌谣“水神经”“孩儿经”“月光经”等也带有浓郁的地方风情。
除此之外,琦君还写了故乡的婚俗,如《喜宴》《故乡的婚俗》等散文中写到瞿溪嫁女儿当晚的“请辞嫁”习俗,母亲要在女儿出嫁的宴席上亲手做道菜,并且一边抹眼泪一边为新娘说吉利话;新娘子上花轿一出大门就把大门关上,因为害怕新娘带走了娘家的风水;婚礼过程中的“坐筵”习俗等。另外还有一些日常禁忌、人生礼仪等,如故乡的女性每年只七月七洗一次头(《髻》);还有的篇目中写到某些传统文化中的陈规陋习依然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如《阿荣伯伯》中,阿荣伯伯回忆孝子的往事:父亲为了给爷爷治病,半夜燃香祷告,甚至“用刀子割下自己手膀上一块肉,熬了汤给爷爷喝”。当地的民间歌谣这些习俗都体现出当时温州乡间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
民俗是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观念的集中体现,是民族精神构成的重要内容,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琦君在她的文学作品里籍涵着丰富的甄越文化、民俗、风情、物产诸方面地域文化的特色,并以此作为物化审美、生态伦理、情感寄托,表述了深沉的乡愁恋情的感情。”[2]怀乡即怀人,思乡之情是对当年故乡生活的人情温暖的记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乡美好的亲情、友情、乡亲邻里之情,更是使作家流连难忘的文化记忆。父母兄弟、异姓姐妹,尊敬的老师,和蔼可亲的乡邻、长工和乞丐等,儿时乡村生活中的各色人等都是琦君怀旧文本中的构成内容。琦君笔下的故乡人亲切、真诚、善良、仁爱,乐观豁达,与故乡的山水相互依存。
母亲是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母亲那个时代》《母亲的手艺》《母亲的偏方》《髻》等一系列散文中,共同塑造了家乡的传统旧式女性形象。她们勤俭、宽忍、慈善、温婉贤淑,谨遵传统仪礼、相夫教子。母亲乐善好施,如《粽子里的乡愁》中,母亲精心为乞丐们准备着“富贵粽”;《新春的喜悦》里,母亲倡议家境好的人家设立善款,接济穷人。可以说,母亲是传统女性观的集中代表。琦君笔下的女性也多是恭顺忍化,像母亲形象一样,都往往是旧式温婉柔顺的旧式妇女形象,与强调反叛、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截然不同。琦君还写了不少儿时的伙伴儿,如《一对金手镯》中,和“我”同年同月生的阿月是乳娘的女儿,“我”小的时候被托付给三十里外邻村的乳娘抚养,于是两人成了不分彼此的姐妹,虽然后来各自命运不同,但美好友情的回忆一直令琦君念念不忘。如《小小颜色盒》里也写到了作者儿时要好的玩伴儿。此外,作品中还写了淳朴而又慈善好施的乡邻,如《看庙戏》写故乡新年时,阿荣伯的慈善好施和乡民的憨厚朴实等。琦可见,君笔下的故乡充满了人情人性之美。
琦君笔下极富地域特色的故乡形象,融入了作家绵长悠远的情思。在长期的空间隔离下,由于乡情的浸染,记忆深处故乡的一切已不是它原本的面目了,作者自己也很难完全以冷静、理智的心态去面对它。这种跨越时空的地域书写很显然带有想象性因素,尽管如此,这些文本仍蕴含着民国时期温州地区的历史文化记忆。
二、传统文化与宗教情感的交错融汇
琦君从小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在创作中处处渗透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精神。作品中无论人物形象还是人伦关系、家庭教育、礼仪习俗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明显的对传统伦理规范等方面的关注。如传统贤妻良母的美好形象、邻里街坊之间的关爱互助,社会氛围的仁义和善、温柔敦厚等。,由于琦君的成长过程也深受宗教情感的熏陶,在其作品中,这几种文化内容相互交错融汇,共同构建起了20世纪初故乡形象中独特的思想文化交错融汇于一体的形象特征,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色彩。
首先,琦君的作品表达了对传统伦理道德、礼教观念等思想的认同与传承。琦君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的作家,她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传统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念的推崇,体现在她的小说、散文中。琦君的作品多是以旧式家庭中的妻妾、儿女、仆婢为书写对象,反映了新旧交替时期温州地区农村生活及女性命运。其笔下的女性多是恭顺忍化,委曲求全,散发着传统女性的美,并依循传统伦理的规范行事,与强调反叛、独立的现代女性主义观念截然相反。“母亲”是琦君着力刻画的形象,她的一系列作品都是以这个一生没有子嗣而孤独留守的女性创作的,“母亲”恪守传统礼仪,从一而终、任劳任怨。可以说,“母亲”是琦君塑造家乡传统女性群像的原型,她的《完整的爱》《婧姐》《失落的梦》《橘子红了》等小说中的家乡女性都体现了这一点。这些作品对传统婚姻观念持认可的态度,作品中的女性往往践行“贤妻良母”的标准,她们操持家务,管教仆从,保持自身作为女主人的身份与尊严。在琦君描写弃妇、寡妇的小说里,“从一而终”“夫死不嫁”等礼教观念,不再是来自于外界压力而接受的教化,而往往是女性的自发诉求,如《琴心》《百合羹》《紫罗兰的芬芳》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同时,她们又以牺牲自我来成全他人实现她们心目中所谓的“爱是完整”的思想。这种忍辱负重似的成全注重的是精神和伦理层面的完善,其文化依据明显来自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它与作家对传统文化深刻的认同感紧密相连。也正因此,其作品强调“爱的牺牲”。如《失落的梦》中,慧面对丈夫的不忠,却以“你们志趣相同,你们将因合作而更有希望”来成全他人牺牲自己,而小说中的另一个女性朱丽,在得知自己所爱之人已有妻室时,也是甘愿退出甚至交出孩子来成全他人,显然这些女性形象都是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琦君小说《阿玉》中的阿玉、《韦月的哀伤》中的玉姨、《橘子红了》中的秀芬都来源于同一个人。《橘子红了》中大妈为了留住丈夫,收买了家境贫寒的少女秀芬,十八岁的少女秀芬成为了传宗接代的工具。小说是对20世纪初温州乡间浓厚的传统男权文化氛围的文学记忆与书写,作家在作品中一方面肯定了女性的宽忍付出,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思考了女性自身的传统痼疾。总之,琦君笔下的女性人物,一方面有着传统女性的一切优点,另一方面又在这种传统的包围乃至裹挟中默默承受着苦闷、孤独和伤痛。
琦君的作品风格较为完整地营造了一种温柔敦厚、委婉和谐的整体情境,其没有大起大落的激烈情感波动,而是对家乡故土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娓娓道来,不疾不徐,如缓缓流淌的河水,令人回味隽永。如《金盒子》中,把对早年失去哥哥和幼弟的痛苦情感寄寓于凝聚了兄妹和姐弟情谊的金盒子上,娓娓道来。她笔下的乡村人物也往往是和蔼亲切、温柔随和的,邻里之间和睦友爱,长工阿荣伯伯、桥头阿公、阿标叔、阿月、阿菊、小阿喜,还有富于幽默感的童仙伯伯等人物都是如此。在艺术创作中,儒家思想主要表现为追求中和之美,主张情感的适中与节制。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使得琦君的散文、小说温润平和,哀而不伤。总之,琦君的文风或以其善良、淡泊的心性去节制情感;或以风趣幽默的笔调来化解过度的伤感;或将浓郁的情感投射到某一象征物上,来避免情感的过度抒发,其作品含蓄蕴藉。在她的笔下,让人们看到上世纪初温州乡间极富传统文化色彩的祥和宁静的社会文化风貌。
其次,琦君作品还深受宗教思想文化的浸润。瞿溪美丽的山水与寺庙的佛教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琦君的创作,她笔下的很多人物也都倡导宽容,在《父亲》中,“我”的父亲曾是一位相当仁慈的军人,他是一位治军严明的儒将。他罢官在家闲居后,手里时常念经。在《家庭教师》中,作家写到启蒙老师终日茹素,每月六天斋期,过午不食。为此,劝善、宽忍、慈悲思想可以说是贯穿在琦君的创作之中的。
要想解脱就要做到现世的宽容、忍耐。琦君笔下被多次书写的母亲形象,就是这一观念的集中代表。母亲毫不抱怨地忍受了丈夫半生的漠视,默默忍受着她自己辛苦养育的两个儿子相继夭折悲痛,承受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人生磨难。在《南海慈航》中,作家写到,母亲每当她心烦意乱时,她就念经……以此消除烦恼。她是以此作为转移忧愁的方法,这也成为母亲逃避人生苦难的精神安慰。
琦君作品中处处体现了慈悲的思想感情。《母心·佛心》写到母亲爱护生灵,见到牲畜有病痛时,就合掌念经,希望借此可以使他们脱离苦难;《春酒》中,母亲乐善好施,每到过年喝春酒时,她都自发带头并动员大家捐出家里的粮食、钱财或生活用品,来帮助穷人;《粽子里的乡愁》中,每到端午节时,母亲就为乞丐们准备许多“富贵粽”,来接济他们;《童仙伯伯》中会治病的童仙伯伯自己出钱为穷人买药治病等。宽恕和善待他人也是慈悲观的体现。在《外祖父的白胡须》里,“我”的外公抓到小偷并不喊人,而是劝小偷改邪归正;在《秘密》中,一位邻居老太太把女儿偷的“我”家的鸡蛋当作礼物送回来,“我”要揭发,母亲却劝“我”做人要厚道等。慈悲之心还包括对世间万物的生命尊重和珍惜。在《诫杀篇》中,看着人们津津有味地吃活闷炝虾、活蒸螃蟹、活剥蛤蜊等,她无比痛心;在《惜生随感》中,作家举出煤油活活烧死小鸡,油炸活鱼、醉活虾等血淋淋的事实,再次痛劝世人要惜生戒杀,否则一定会受到惩罚。琦君甚至在散文中感叹花草树木都有生命,一样要爱护,体现了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观念。对他人的同情和施予、宽恕,对万物生命的珍惜和关爱,同时,又与传统文化中的“仁恕”思想相联系,体现了琦君作品中思想的交融统一。
上世纪初期,宗教思想在温州乡间广泛传播。琦君前后有十年之久在教会女校读书,同时,她上的大学是之江大学,那里的老师很多都信仰宗教,同时她身边也有较多人信仰宗教,为此,她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并在作品中给予显现。在散文《阿标叔》中,她写了阿标叔每周日都要放下手头工作去祈祷。由于信仰不同,阿荣伯十分排斥阿标叔,处处为难他,但是当阿荣伯扭伤腰时,阿标叔不计前嫌赶来照顾,这令阿荣伯很受感动。她在作品中强调爱他人,不但要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友邻,还要互爱。如作品《青灯有味似儿时》里,白姑娘是位宗教信仰者,她常常教导“我”要满怀感恩,把爱回报给父母和社会。为此,琦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早年温州地区思想的传播和影响的文化记忆。
总之,琦君的小说、散文中渗透着中国传统思想和宗教文化的因素,这些文化内容相互交错融汇,其所显现的文化特征构筑了琦君笔下故乡温州独特的传统而又不失多样性的文化形象。
三、琦君作品对温州形象的审美建构
琦君作品对特定时期温州形象的建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意蕴。作品将真、善、美、爱融于一体,彰显出独特的地域美学风格。
(一)爱、美统一的美学原则
琦君在《我对散文的看法》一文中说:“风格就是文格,也就是作家人格的表现。”一个作家的风格“只有两个字,就是‘亲’与‘新’,‘亲’就是真诚,文章一定要有一份平易近人的亲切感。如同你见到一位态度诚恳,言谈侃侃的人,自然愿与交往”[3]。在琦君看来,真情实感是写出好作品的第一要义,而真、善、美的统一则体现了我国传统审美观的核心内容。
琦君在远离家乡几十年后,以沉静之思,凭质朴的文笔回顾往事,述说家乡和自己的童年生活,作品传达出爱与美相偕相融的、极富传统美学价值的意蕴。楼肇明先生曾这样评价琦君的散文,“在琦君的心目中,人世间的教堂不是别的,童心和童年即是审美的教堂。她已将童年演化和提升为一种鉴别真善美和假丑恶的价值尺度了”[4]。童心之真与善,是琦君文学创作的根基。作者将自己化身为六岁的小女孩,以童心观察和书写社会人生,使作品传达出真实的力量,才能触动人、感染人,而善既包含着对弱者的怜悯、同情和关爱,又有对他者的劝喻,与佛教的慈悲观一致。在《灵感的培养》一文中,琦君谈到“我认为有志从事写作,第一有广大的同情心,时时体验人情,观察物态,然后以温柔敦厚之笔,写出真善美的文章”[5]。
散文《外祖父的白胡须》以儿童视角叙写了外祖父的善良。对于前来偷窃的小偷,外祖父装成财神爷送给小偷两块银元,并劝说他去学手艺;明知受骗还要再次施舍给乞丐铜钱;顶风踏雪去给最蹩脚无趣的腊月封门戏捧场递银元等。对于那个给了钱又再来要的女乞丐,外祖父让“我”不要生气:“一枚铜子,在她眼里比斗笠还大,多给她一枚,她多高兴?……我有多的,就给他们。也许有一天他们的日子好过了,也会想起从前自己的苦日子,受过人的接济,他就会好好帮助别人了,那么我今天这枚铜元的功效就很大了”。外祖父形象之美并不仅仅表现在他自身能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希望通过自身的言行来感化他人,从而使真善美的品质流传扩散,产生更广泛、深远的影响。可以说,真诚善良的品质已经代代相袭地渗透在温州的山水乡土之中,构成一种地域文化之美。琦君记忆中的温州,正是纯真与仁善之心的聚结。
(二)和谐冲淡的田园审美
前文已述,琦君的怀旧作品往往具有一定的想象性甚至虚构性色彩。由于时空远隔,琦君、林海音等第一代赴台女作家在内外种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她们只能以写作的方式倾诉思乡之情,创作出一批独特的怀旧之作,作品中对故乡的记忆往往有意无意地掺杂了自己的主观想象性的因素。她们笔下的故乡,可以指涉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是空间文化、家族记忆的渗透。作家通过一定的想象,在文本中建构出自己所向往的一个空间,她们在这个空间里以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出对家族、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的记忆,并藉此在自己的回忆性文本中实现了“回归”“故乡”的美好愿望。故乡温州是作家琦君的情感凝聚地,“故乡,因此不仅仅是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6]不过,这些女作家大多无心营造宏大视野下的家国叙事,但在她们的娓娓道来的叙述中,让我们同样看到了一个凝固在家国空间上的集体记忆。当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同时作用于创作过程时,于是,琦君笔下就出现了一个极具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和田园美学风格的故乡形象。
琦君的怀旧作品虽描写的是20世纪初风云动荡的社会时代背景,但其笔下的江南却如古典田园诗一般,全无剑拔弩张、战火硝烟的气息。毕竟,外界、社会的波澜壮阔只是时间中流过的一个点,唯有那些饮食男女的平凡悲欢才是生命的原生态。作品中的瞿溪山水秀丽,民风淳朴,邻里相亲相爱、谦和礼让,人们的生活宁静平淡,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宛然一幅田园山水图。这里几乎不存在20世纪初新文学乡土派小说作家笔下所描述的农村社会的场面和情境,而是文化传统中所蕴藏的人间纯美与至善之境,是传统道德之美与和谐人伦关系交融互渗的理想社会。如果说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营造了一个充满人性人情之美的世外桃源般的理想之境,那么琦君则以其真诚善美的文笔建构了一个饱含传统道德、彰显伦理之爱而又极具田园风格的温州形象。
琦君说:“我深感这个世界的暴戾已经太多,为什么不透过文章多多渲染祥和美好的一面呢?”[7]她倡导以悲悯之心“化人生的烦恼为菩提,化社会的戾气为祥和”,呼吁建立和谐有爱的理想社会,反对暴力和仇恨,提倡用爱和宽容去缓解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沈从文为实现自我的文学理想而建构的“湘西世界”不同,琦君笔下所建构的深蕴田园之美的温州形象,不仅是异乡游子的精神家园,寄寓着作家的审美理想,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寄寓着作家的某种社会理想,从而引发人们对回归传统文化和理想社会形态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