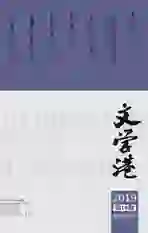为林逋卸妆
2019-10-24柯平
柯平
庆历年间的幽灵
建炎四年深冬的明州,一个流亡中的皇帝慌不择路的偶然途经,让这座以美丽富饶著称的城市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短短十来天的逗留,带来的后果是尸骨遍野,十室九空。尽管后来历史学家们异口同声将这归罪于金兵的残暴,事实上真正的罪犯却是他手下的官方武装。无论是所谓中兴五虎将之一、对后来岳飞之死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张俊,还是几天前刚接替李清照新夫张汝舟担任市长的刘洪道。受的是阻敌护民的重任,干的是乘乱抢劫的勾当。前者如王明清所记“俊兵在明,乘贼先,而恣掠卤。时城中人家少,遂出城以清野为名,环城三十里居民皆遭其焚劫。或以金帛牛酒饷之,幸免;与纷争,杀之”(详《挥尘录》引王颖秀日记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后者如“洪道微服出城,既过东岸,恐人追袭,乃使尽揭浮桥之版。居人扶携沿絙索而渡。卒复邀夺其所赍,拥排遏抑,坠水者数千,哀号震天地”(王颖秀日记建炎四年正月十三日)。相比全祖望《鲒埼亭文集嵊县子铙歌序》里“张俊高桥之捷,旋卷甲鼠窜,吾乡人尚夸其功,愚矣”的直接抨击,《三朝北盟会编》只称“明州之人是以怨张俊,得小胜而弃城,遂致大祸”,还算是比较客气的。
更为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半个月后金兵前脚走,姓刘的居然后脚又回来了,“洪道留奉化县,比向日诛求益甚,而所将精卒暴横市肆。与张思正(副市长)纵其麾下斸民居窖藏。逃遁之家偶脱死,馁饿甚矣,归故址取所藏给朝夕,则群卒强夺之。虽焚余椽楹藩篱可为薪者,人不得有。公遣数百辈持长竿大钩捞摝河陂池井间,谓之‘阑遗,钱物输公十不一二。洪道复苛配强敛,并得四万缗献之行朝,欲蒙失守之罪”(王颖秀日记建炎四年二月十六日)。“比向日诛求益甚”,则其穷凶极恶之形跃然纸上;“钱物输公十不一二”,则其借公肥私之实暴露无遗。至于只在奉化局部施暴,没进府城大肆掠夺,自然不会安有什么好心,而是他原先的办公室里已有一位金国选派的蒋市长坐在那里,不敢去打扰而已。《宝庆四明志》称“虏自明州引兵还临安。既去,以修职郎蒋安义知明州,进武校尉张大任同知明州事。”可见一正一副,班子配备相当周全。两个政权同时存在,堪为特殊年代里四明山的特殊风景,金国扶持那个虽是伪政府,却必定住在城里,宋国自己那个虽货真价实,却只能扎驻山上。这就有点像是老市长陈布衣回忆录里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玩法,至于当地最古老的地方志为什么不称《明州府志》而叫《乾道四明图经》,或许也有了更合理的解释。
这场浩劫给当地带来的阴影是如此的深重漫长,以致发生在其间的那件重要事情为后世所忽略或有意掩盖,这就是《鸡肋编》里记的那篇署名‘京兆逸翁深甫的墓志。犹如老子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如果说整个灾难期间除了哭泣、饥饿与无望以外,还有一丁点儿的光亮、或让人想起来能感觉温馨的东西,应该就是它了。假设你能穿越时空隧道光临建炎四年初春的宁波,在硝烟还没完全散去、路边尸骨尚待掩埋的府城西门的壕堑边,将有幸看到它正在那里被挖出来。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烧毁的建筑和人为破坏的桥梁固然让人心痛,但跟此碑的价值相比或许也不算什么。因墓志只不过是它的外在形式,上面记的却是一千年前国家历史最真实的部分。可惜存留下来的版本不像被刘某掠去的那四万缗银子货真价实,而是经四库馆臣精心修理,被认为绝对安全后才敢拿出来给我们看的,自然早已面目全非。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某种疏忽(我更相信是神意),其中最重要的作为宋代明州地标的它山,在刀砍斧削中依然顽强屹立,使得所有围绕它的那些沤心沥血、倾尽才智的努力,如改宋代为唐代、明州为吉州、洞中为铜钟、吾子为吾季之类,最终都只能被证明是枉费心机。
“建炎三年己酉,金人至浙东,破四明。明年退去,时吕源知吉州,葺筑州城,役夫于城脚发地得铜钟一枚,下覆瓷缶,意其中有金璧之物,竟往发之,乃枯骨而已。众忿其劳力,尽投于江中。视铜钟之上有刻文云:
唐兴元初,仲春中已日,吾季爱子役筑于庐陵,陨于西垒之巅。
吾时司天文,昭政命令晦明。
康定之始,末欲茔于它山,就瘗于西垒之垠。吾卜兹土,后当火德。
五九之间,世衰道败,浙梁相继,丧乱之时,章贡。
康昌之日,复工是垒,吾亦复出是邽。
东平枭工,决使吾爱子之骨,得同河伯,听命于水府矣。
京兆逸翁深甫记。
按唐兴元元年甲子岁,朱泚李怀光僭叛,德宗自奉天移幸梁州之岁。二月十二日甲子李怀光反,中已盖十七日己巳也。康定之始,则六月甲辰,泚始伏诛,七月壬午,至自兴元之时也。迨建炎四年庚戍,三百四十七年矣。如火德、浙梁相继康昌、东平水府之谶,莫不皆符。但五九之数未解,而复出是邽,未知为谁。则逸翁之术亦可谓精矣。”
这就是出现在作为四库重点工作对象的《鸡肋编》里的原始版本,典型的辫子史官风格,半虚半实,传信传疑。若有其事,查无此人,又因所涉内容的性质,需要有多重防护,连带该书作者的身份问题也只好跟着变得含糊不清。不过文字既然受到过摧残,就难免会留下痕迹,全文三个自然段,如果将它比做一条冷冻柜里翻出来的鱼,不说中间的鱼身即铭文部分肉少刺多,形状怪异,即便一头一尾亦有明显破绽。首先这个鱼头是宁波港的海鱼而非鄱阳湖的淡水鱼,事情的发生地在明州无可怀疑,就算没有当地人民热爱的王长官的它山愿意站出来作证,像“金人至浙东,破四明。明年退去,时吕源知吉州,葺筑州城”这样没逻辑性和因果关系的白痴句子,相信连中学语文课考不及格的学生也会嗤之以鼻。如果需要有所谓学术方面的支持,也不是不可以,考《宋史》卷第一百五十八郑瑴传有上高宗书称:“钱伯言与黄愿皆弃城,吕源与梁扬祖皆拥兵而逃,今愿罢官,扬祖落职,而源、伯言未正典刑,非所以劝惩。”又同书本纪第二十七高宗四:“(绍兴二年九月)癸酉,以右朝请大夫吕源为浙东福建沿海制置使,治定海县。”又同书卷第二百一十四马伸传亦记其上高宗书:“吕源狂横,陛下逐去,不数月,由郡守升发运。其强狠自专如此。”则吕某在建炎末绍兴初的宦绩是:建炎三年金人南伐时拥兵而逃;四年削职罢官,听侯处置;绍兴二年在高宗庇护下升任浙东福建沿海制置使,驻地即为明州府城东门外的定海(今之镇海)。又据《永乐大典》卷八○九引《吉安府志》:“府城,绍兴三年太守吕源增垒。”《读史方舆纪要》江西五庐陵城条也称:“宋开宝中重加缮治。绍兴三年增垒浚濠。东临赣水,三面凿濠。”则吕源任吉州太守已是绍兴三年的事,四库馆臣不过用上了今天美国人的长臂管辖术,让他提前上任而已。而在铭文所记的时间段内即建炎四年,明州前后有四位市长,即四月以前在任的刘洪道,四月至八月的向子忞,八月至十二月的吴懋,以及当月晚些时候跟李清照分手后再次出任的张汝舟。还有金国方面派来的蒋市长也不能给忘了,这样实际上应该有五位。至于在如此錯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情势下,究竟是他们中的哪一位面对战后的满目苍夷尽职尽心,重筑州城,无意中挖出了这件宝贝,从地方志留下的线索来看,《宝庆四明志》卷三公宇庆元府门下所记“治事厅,建炎末,守张汝舟建”,应该是唯一与此相关的记录,因此这件功劳有可能要算在他的头上。后面的鱼尾部分,即假托作者对此铭的所谓考证就更荒诞了,即以首句“唐兴元初仲春中已日”为例,年代用的是模糊指称,后面的月日却又精确如此,这又是上穿T裇下着棉裤的玩法。“中已”又是什么玩意,十二干支里没听过有这一号,而居然可以断言“盖十七日己巳也。”或许这样的推理连造假者自己都无法被说服,因此只好通过手中掌控的资源,不断推出其它的不同版本以混淆视听,以便让对它有兴趣的人知难而退。如果你是一个魔术爱好者,想必会为自己有此意外眼福而庆幸,如果不是也没关系,至少作为一种高级的智力游戏,对开拓眼界提高思维能力亦不为无益
版本一:《独醒杂志》卷五
建炎二年,庐陵城颓圯,太守杨渊兴役修治之,掘土数尺,得一石函,中有朽骨,旁有一镜。役工方聚观,或以告渊。渊令取镜洗而视之,其背有文曰:唐兴元之初仲春中巳日,吾季爱子役筑于庐陵,殒于西垒之垠。未卜窆于他所,就瘗于西垒之巅。吾卜斯土,后当火德。九五之间。世衰道败,丧乱之时,浙梁相继。章贡邦昌之日,吾子亦复出于是邦。东平鸠工,决使吾季爱子听命于水府矣。京兆逸公深甫记。渊览而异之,急遣问石函所在,则役夫以为不祥,弃之于江矣。
版本二:《文献通考》卷三百物异考六金异
建炎三年,吉州修城,役夫得髑髅,弃之水中。俄浮一钟,有铭七十六字,大略云:唐兴元吾子殁,瘗庐陵西垒,后当火德。五九之际,世衰道败,浙梁相继丧乱,章贡康昌之日,吾亦复出是邦,东平鸠工,复使吾子同河伯听命水官。时郡守命录之,仅录毕,而钟自碎。近金为变怪也。
版本三:《天中记》卷四十三得铜钟铭
建炎二年岁在戊申,杨渊守吉州,是年车驾驻驆维扬,江南诸郡日虞金人深入,时修城,得铜钟于城隅,其上有文云:唐京兆季爱子墓志:唐兴元初仲春中巳日,吾季爱子筑役于卢陵,殒于西垒之颠。吾时自王文昭政令命晦朔。康定之始,未欲茔于它山,就瘗于西垒之垠。吾卜兹土,后当火德。五九之间,世衰道息。浙梁相继。丧乱之时,章贡。康昌之日,復工是垒,吾亦复出是邦。东平鸠工,复使吾爱子之骨,得同河伯,听命于水府矣。京兆逸翁深浦记。渊方有版筑未成,明年今日犯维,车驾幸浙东。金人遂渡江,分两路一犯明越。车驾登海舟,驻永嘉。一犯洪吉,太母保章贡。渊失守。既经兵火,不知钟所在。癸丑,吕源来守,下车即修城,不数月壁垒皆立,东平鸠工之言亦验。此铜钟铭得之刘僩《退斋笔录》。
城建主持者由吕源让位于杨渊,时间也从建炎四年退回到建炎三年甚至二年,铭文的载体由特殊材料制成,形状也具有自动调节功能,可以是铜镜,可以是铜钟,也可以是死者的髑髅即头盖骨,更神奇的是技术能量方面的强大,代表古代科技的最高水平,即扔进水里的髑髅,通过某种秘密手段催化后浮起来就能成为金属。如果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倾情表演者是江湖术士或段子名家,自然可以一笑了之,问题是他们并非寻常人物,在历史上都有着各自显赫的身份,如《独醒杂志》作者曾敏行,周必大跋称“有博古通今之学,知几应变之才。”《天中记》编撰者陈耀文,四库提要誉为“尤能於隶事之中,兼资考据,为诸家之所未及。”《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就更不用说了,著名历史学家,就因为这部书,名气要远远超过他曾任咸淳朝丞相的老爸马廷鸾。如此响亮的招牌,如此不堪的文字,这就不仅仅是令人生疑的问题了。曾某笔下那面铜镜,竟能刻下被他恶意删改后的墓志一百一十四字(全文一百四十七字,已删去它山等关键词),尺寸想必一定不小,至少比他的脸皮要大,而到姓马的那里又只剩七十六字,不仅它山被新时代的愚公移走,连明州亦遭屏蔽。另此文最早的源头为书前自序署绍兴三年二月五日的《鸡肋编》,四库断为庄季裕所著,陈耀文又称出自刘僩《退斋笔录》,而今本此书如梅尧臣序和靖诗集所谓‘百不一二,全书仅存佚文四条,作者又署侯延庆。这样一个圈子绕下来,准保连鲁迅那样的智慧脑袋也会成为一桶浆糊,怪不得当年他对这本做过阉割手术的《鸡肋编》如此愤怒,而这正是幕后的别有用心者想要达到的效果。或许,唯一事实清楚、较少争议的只有那位被派去帮吕源圆谎的杨渊,可惜漏洞越补越大,城究竟有没有筑只有鬼知道,反正金兵还没打到吉州他就提前开溜了,至少现存所有南宋史著都这么认为,无论官方版本如《宋史》称“金人犯吉州,守臣杨渊弃城走”( 宋史卷二十五高宗二建炎三年十一月丁卯),还是私人著述如赵鼎称“敌犯吉州境,知州杨渊而下弃城而去”(建炎笔录建炎十二月二十日),所记难得一致。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清袁氏贞节堂抄本《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所记“金人寇(改作攻)吉州,知军州事杨渊弃城走。杨渊闻金人犯境,即弃城去。金人驻於城下,不入城,不甚虏掠(删此四字)”。这个版本跟前面介绍过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二稿本性质相似,可以让我们懂得历史是怎样到了清朝才炼成的,括号内文字为馆臣原批。按理说清人的基因不用化验就知道跟金国有秘密血缘关系,难得有作为敌国的宋代历史学家说他们祖先军纪好,不焚烧抢掠,连高兴都来不及,却偏要下令将此四字删去。奥妙在哪里?答案很简单,就因为那篇墓志的关系,既然历史的改写者经过周密规划,毅然决定让它的出土地点由明州变为吉州,如果那里城市无损,不甚虏掠,显然就失去了重筑州城的合理性,马脚就会穿帮。在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只好舍熊掌而取鱼了。
剥去了前后的伪装,再来对付中间的鱼身部分,或许相对就会减少一些难度。至少里面最大的那两根鱼刺已经找到,即号称‘唐兴元初的‘宋宝元初和装扮成‘五九之间的‘庆历之间,尽管只是利用字形相近进行篡改,却被卡住了很多年,不像那两位吉州市长那样一眼就能识破,可见造假的艺术也跟武功一样,越是寻常的招数或许欺骗性越强。这两个年号既然已经露出原形,加上文中或出于疏忽或故行险着的‘康定,一条清晰而有效的时间链出现了。按正史,此为北宋仁宗中期所使用,彼此相连,证明铭文所记之事是何等的真实。其中宝元二年、康定一年、庆历八年,前后十一年,换成西历就是公元一○三八至一○四八年。无论作为儿子的墓主的死亡年月,还是作为父亲的墓志的写作日期,自然都发生在这一时段中。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它与西夏国王赵元昊的兴起过程是重叠关系,即公开称帝于宝元元年,意外死亡于庆历八年,是不是运气特别好,又买彩票撞上大奖了。至于它精神文明方面的含义,不妨可以请欧阳修代为科普,因《归田录》里有一篇正好是谈这问题的:
仁宗即位,改元天圣,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议者谓撰号者取天字,于文为二人,以为二人圣者,悦太后尔。(老妈垂帘听政,同圣之义)
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为明字于文,日有并也,与二人旨同。
无何,以犯契丹讳,明年遽改曰景佑,是时连岁天下大旱,改元诏意,冀以迎和气也。(辽景宗耶律贤小字明康,西夏王姓赵名德明,避皇帝讳)
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宝元。自景佑初,群臣慕唐玄宗以开元加尊号,遂请加景佑于尊号之上。(南郊封禅,唐玄宗封禅老前辈,因以为精神老师)
至宝元,亦然。是岁赵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恶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复加于尊号。(‘恶之之‘恶,或当为‘讳)
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谥尔。明年又改曰庆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于是又改元曰皇佑,犹景佑也。(‘谥尔疑为‘益辽,九年即皇祐元年。大旱,奉化陈氏《通鉴续编》作大水)
六年日蚀,四月朔,以谓正阳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
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复,又改元曰嘉佑。
自天圣至此,凡年号九,皆有谓也。
墓志的时间背景真相大白,宝元、康定、庆历三个年号的寓义亦已经清楚,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内容的分析,尽管忧伤而令人动情,但它依然不是故事,而是真正的历史,比今天贴上各种权威标签、陈列在国家图书馆里的任何文字都要可靠。一位父亲和一位儿子同时为皇室(或为自己)效力,时间按北宋纪年为宝元元年,西夏纪年为延祚元年。父亲的职责是司天即主持国家的精神命运与日常祭祀占卜,同时又先后两次出任当地的太守;儿子负责一项重要的建筑事务即修复经战争毁坏的皇陵。由于已经明确事件的發生地是在明州,因此这个地方可基本断定就是州西南的梅山,不过具体工作区域一为山顶(天台)一为山穴(雪窦)而已。必须强调的是,在开头的几年内天下很不太平,因那时正是西夏与宋国交战最激烈的年头,而墓主的不幸死亡,不知是殒躯战场,还是因工程事故献身,情况不明,但他兼任明州知府的父亲不愿将爱子葬于它山,只暂瘗(停棺待葬)于西垒即庐陵是可以肯定的,作为资深星象家,在康定年初需要作出决定时,他已经预测那里将兵火之灾。果然次年好水川(亦名三川口,很容易写错为三江口)大战爆发,且以宋军惨败、主将任福战死而告终,证实他的预言是多么的准确。此后情况进一步恶化,战争成为两国常态,直到喜欢文治的仁宗和腹内藏十万雄兵的小范老子都不想再打下去了,乃于庆历四年签订和约,条件是应允夏国自设国祭,并参照向契丹纳贡例,每年进贡银帛二十五万两匹,当然按注重礼义的宋国自己的说法该称赏赐才对。战争结束后父亲重守明州(以地方志对应之,《宝庆四明志》郡守表所载“司封员外郎张弇,司封郎中王周”当为重点怀疑对象,暂不展开讨论),并将爱子未完成的工程进行下去。不过太平日子相当有限,仅仅过了两年多一点,又有所谓攻占甘陵的东平贝卒起义,史称王则之乱,梅尧臣诗《甘陵乱》称“守官迸走藏浮埃,后日稍稍官军来。围城几匝如重鋂,万甲雪色停皑皑”,可见战事之激烈。不知跟攻占甘州的西平王丌卒(元昊别名)又是什么关系,至少两人同年同月死,就不知是否同年同月生。“僭称东平郡王,以张峦为丞相,卜吉为枢密使,建国曰安阳,牓所居门曰中京”,后来奉化本土历史学家陈桱这样告诉我们,同时还透露以“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为宣传口号,将士脸上都刺字曰“宜军破赵得胜,旗帜号令率以佛为称”(《通鉴续编》卷七庆历七年)。由于战争中宋方使用了此前诸葛亮用过、此后蒋介石也用过的决河掩敌手段,证实《宋朝事实》所云“霸州以来,颇多溏水,决河东注,于我为便”确实有效(《详该书卷二十经略幽燕》),碰巧此时鄞县县长王安石的东钱湖工程也大功告成,“遂至决河为田,坏人坟墓室庐、膏腴之地,不可胜纪”(《邵氏闻见录》卷十一,《王荆国文公年谱》卷上庆历七年十一月条下所记同),致使“吾爱子之骨,得同河伯,听命于水府矣。”铭文所记事件的主要内容,大概就这么个样子,顺便将破译后的密电码抄在里:
唐兴元(宋宝元)初,仲春中已日(仲淹中祀日,按范仲淹年谱,宝元元年十一月出任越州太守),吾季爱子役(吾子受于役),筑于庐陵,陨于西垒之巅。
吾时司天文,昭政命令晦(守)明。
康定之始,末(不)欲茔于它山,就瘗于西垒之垠。吾卜兹土,后当火德(灾祸)。
五九(庆历)之间,世衰道败,浙梁相继。丧乱之时,章贡(停工)。
康昌之日,复工是垒,吾亦复出是邽(邦。陈耀文引文亦作邦)。
东平枭工(攻),决使(河),吾爱子之骨,得同河伯,听命于水府矣。
京兆逸翁深甫(林逋)记。
很多年前读金庸的《连城诀》,对书里那部令江湖好汉闻风丧胆的《躺尸剑谱》的威力,实在是神仰得紧。尤其里面的招数如“哥翁喊上来,是横不敢过”、“落泥招大姐,马命风小小”之类,让人忍俊不禁,印象深刻。后来才知是《唐诗剑谱》之讹,前招实为张九龄《感遇十二首》之“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后招实为杜甫《后出塞五首》之“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但错成这样并非此谱得主戚长发文化水平不高、传写有误,而是为阴险的私欲驱使下的恶意误导,甚至以自己女儿和爱徒为牺牲品也在所不惜。这让我在读书中养成一个习惯,或称怪癖,就是对古代的东西基本持怀疑态度,尤其那些获四库馆臣表彰的名作或文献,心里总会先问一下自己,这是否有可能又是一部《躺尸剑谱》?几十年下来,自觉收获还是有的。比如铭文作者署名京兆逸翁,逸翁就不用解释了,京兆即大名鼎鼎的永兴军,在北宋名气甚至要超过东京,只要你是官员,几乎没有不在那里干过的,偏偏最早的永兴即为萧山也就是西陵,他不会告诉你。而将开头的“仲春中已”还原为“仲淹中祀”,既有年谱宝元元年十一月任越州太守之记,亦有《范文正集》内作于是年的《赠张先生》为证,诗称“应是少微星,又云严君平。浩歌七十余,未尝识戈兵。”少徽星者,处士之别称也。严君平者,隐逸之典型也。七十余者,逋逸于天圣六年(1028),时年六十一,至范某守越之年(1038),时年七十一,正合七十余之咏,不多不少。未尝识戈兵者,逋生于宋有天下后之第八年开宝元年(968),截止元昊篡立以前,国家一直号称太平盛世也。加上同时所作《与人约访林处士阻雨因寄》的“方怜春满王孙草,可忍云遮处士星”,《和沈书记同访林处士》的“山中宰相下岩扃,静接游人笑傲行”,《寄赠林逋处士》的“几姓簮裾盛,诸生礼乐循”,《寄西湖林处士》的“巢由不愿仕,尧舜岂遗人”,则两人正式相识实始于此年,而这位不书姓名有违常例的张先生,除了其时使用汉名张元夷名野利任天都大王那位,几不作第二人想。
这篇铭文,同样描写过甘陵战事,称“凶徒盗覆甘陵城,白日堂堂枭呼鸣”的郑獬,大约也看到过。按《宋史本传》,在皇祐五年获得会试第一即俗称状元以前,他的个人历史一片空白,这首赠东平前線宋军主帅明镐的诗,因此有个另类的诗题叫《代人上明龙图》(《郧溪集》卷二十五),好在那只白日呼鸣的怪枭,跟铭文中“枭攻”的枭应该是一伙的,包括解释方面,无论《说文》的“鸟头在木上”还是《汉书高帝纪》的“悬首于木上”,这一图像不仅早为我们所熟悉,进而已能心领神会了。只因他后来还有一首《送惠思归杭州》称“湖上秋风满,归怀岂易宽。身随秦树老,梦入浙江寒。为客久应厌,到家贫亦安。石房旧书在,重拂绿尘看。”诗题自然是有问题的,暂且不管,但因结尾两句的提醒,想起墓志前面那个同样使用《躺尸剑法》的开头差点忘了,也得交代一下才是,赶紧将复原后的文字抄在这里:
建炎三年己酉,金人至浙东,破四明。明年退去,时吕源知吉州(张汝舟知明州),葺筑州城。役夫于城脚发地得铜(洞),钟一枚(中一物),下覆瓷缶,意其中有金璧之物,竟往发之,乃枯骨而已。众忿其劳力,尽投于江中。视铜钟之上(洞中壁上),有刻文云。
缶中之物就是瘗于西垒之垠的爱子尸骨,刻文即为前面已交代的铭文,或许,只有将那些后人恶意设置的障眼物如铜钟、铜镜、骷髅之类搬开后,才能看到它的发布平台实际上只是洞壁,当然风雅一点也可称是摩崖石刻或诗壁。包括无论署真名林逋或假名张元的那些杰出诗作,最初发表的地方应该也在这里。当然你也可以叫它崆峒或空同,因雪窦的窦字,字书的解释就是“空”或“入地隧曰窦”。还有他同样被剥夺著作权的那部《省心录》,当年因工作性质的关系,夜间于洞顶司天,观星察斗,白天就在洞里睡觉、思考、著述,心忧天下。四库本《省心杂言》李景初跋末称:“筮仕苍梧,在舆(颜师古注《汉书》:輿,地道)则见其倚于衡(仍于衕。衕,古文洞),犹以六经,佐三尺法。”宋明州大儒王应麟对三尺法的解释是“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困学纪闻》),即以六经为思想基础,起草国家法律文件,这才有点中书令或天都大王的派头,根本不是现在流传的那样弄些治家格言来唬人(此书情况复杂,当另著文详述)。兵乱河决,陵谷迁变,沉埋地下近百年,直到建炎四年才有幸重见天日。两年后的绍兴二年七月当沈诜为《和靖诗集》作跋,尚感慨“和靖先生孤風凛凛,可闻而不可见;尚可得而见者,有诗存焉。耳(闻)是邦泯然无传,岂不为缺典哉?因得旧本,访其遗逸,且与题识而附益之,刊臵(古文假)漕廨,庶几尚友之意云。”所谓“因得旧本,访其遗逸”,大约就是在新发现的山洞内有意外收获,因以旧本《和靖摘句图》增补而刊行。沈诜为德清龟溪沈与求子,其父建炎元年明州推官,绍兴六年明州知府(《宝庆四明志》郡守表失记),时或侍父上任,因有此一番作为,与当地因缘亦可谓不浅。用孤风凛凛形容其人及诗,令人神往追慕,而“是邦泯然无传”之婉讽,相信一定不是针对热爱文化的当地人民,而是说给北宋那些皇帝和历史学家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