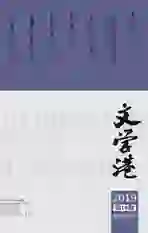闯入城市的狗(组章)
2019-10-24庞余亮
庞余亮
那时候的书房
写下“那时候”——我心里一震,像一根被扯断的晾衣绳。
那时候的书房,是安了简易木门的书房,四平方米的小棚屋。
那时候,还有蟋蟀。三只蟋蟀。
我根本不知道那三只蟋蟀是什么时候搬进书房的。
那时候,我的小书房在乡下,书房外便是学校的泥土操场,过了一个暑假,操场上就长满了草。到了开学,学生最初几天的课程便是劳动课:拔草。
草被拔出了一堆又一堆,有的草扎得很牢,学生用带来的小铲锹要围剿很长时间才能围剿完。各班把草统一抱到校园的一角晒,晒干了正好送食堂当柴烧。
晒草的某一天中午,我捧着新发的教科书回到书房里去,突然被一阵浓烈的草香味所打中,简直令我不能自持。
——草怎么可以这样香啊!
草香一直弥漫到晚上,我坐在我的书桌前,听到了几只蟋蟀的叫声,它们是在提醒我,为什么到现在才坐到书房里来。我不会跟它们说明那寂寞中的烦躁,默默估计,这几个小家伙肯定是在学校组织拔草时搬家搬到我这里来的。
那时候,我的小书房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纸:以前的备课笔记、学生的试卷、练习簿、班级日记、花名册、报纸,还有我这么多年像燕子衔泥一样从外面邮购来的书(我买不到我要的书)。我不知道这几个小家伙躲在什么角落。每天我读完书,会用水壶给书房墙角的晚饭花浇水(这是春天时老教师给长得太密的小晚花间出来的苗),子夜的晚饭花的开放已到了高潮,这与校园的晚饭花有了呼应。
那时候的书房,晚饭花那么香,连蟋蟀们都开始打喷嚏了,它们一只又一只地叫了,开始我还不知道有几只,我的耳朵里全是它们的歌声,像是重唱,又像是回声。后来我听清了是三只,三只蟋蟀在伴奏——这是秋天对我的奖赏!而我,则是这无词曲的主角。我想起我的童音颤颤的学生们,还有头发越来越白的老教师们……
在那个秋天,我在蟋蟀声的陪伴中读完了《我爱穆源》《三诗人书简》《钟的秘密心脏》《雪地上的音乐》等一些可爱的书。我的三个小家伙,也是我的三个知己,还陪着我读完了一本叫《寂静的春天》这本书(是上一个冬天朋友买给我的)。再后来,秋天越来越深,天也越来越冷了,外面操场的蟋蟀已经不歌唱了,晚饭花也越开越小了,它的球形果实像串珠一样在秋风中滑溜溜地滑到草丛中。而我的三只蟋蟀还在歌唱。在此前的一段时候,我向朋友诉说了我在乡下的深深的苦闷。朋友回信说:“里尔克有句诗叫,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我多想把这句话送给这三只蟋蟀,送给我身边的这些书本……
后来,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假如我死后,我的书会不会散落各方——我那么年轻,居然那么伤感。我在乡下见过许多离开主人后面目全非又不被珍惜的书,这是多么没有办法的事。我想这个问题时弄得我泪流满面,我裹紧了那已掉了带五星纽扣的黄大衣,那个晚上可真静啊,静得我内心一阵喧嚣又一阵喧嚣。我的三个蟋蟀朋友也感应似的哑了口……而外面的冷气一阵又一阵袭来……我向外一探,外面下雪了,这是那年的第一场雪呢,雪花很小,像我的小小的忧伤。
可现在,连忧伤也没有了——能说些什么呢?说命运,还是说昔日重来?还不如不说话,把晾衣绳上的衣服重新洗一遍吧。
那时候的书房,有喜悦,有奇迹,也有清水鼻涕。
那时候的书房,我的书比我还能耐寒。
一起“划桨”的书
我和我的书一起“划桨”的“码头”应该是1983年的素面朝天的扬州。在那样一个素面朝天的扬州,却有两个藏着宝贝的读书好港湾。
一个好地方是四望亭里的阅览室。就在这个四望亭里,我“谋划”到了一本好书之“桨”,后来却丢失了这把“好桨”。
当时汶河路上的榆树很高大,西侧的四望亭还没有空,里面是一个阅览室,那里的书很多。只要学生证加两块钱押金就可以在四望亭里办一份阅览证,我就在那个四望亭看到了大学里不可能见到的《人啊,人》。这是戴厚英写的。因为这本书是被“上头”点过名的,当时属于“禁书”。我当时借的时候就有一个决定,不还了。过了三天,我去四望亭,假装很可怜地向四望亭阅览室的老师傅做口头检讨,说书丢了。老人按照规定没收了我的两块钱押金。虽然少了两块钱,但我暗中兴奋(这书本定价一块三),但谁能想到,我去宿舍一炫耀,不出两天,《人啊,人》真的就丢了。谁都说没有看见。这本我用小计谋得来的书就这样离开了我。至今还记得里面的主人公,女主人公叫孙悦,男主人公叫何荆夫。因为太喜欢了,我三姐的孩子生下来,让我取名字,就用了男主人公的名字。很多年后,汶河路上的榆树没有了,四望亭路也被开发出来了。我早就拥有了新版的《人啊,人》。而那本有阅览室书线穿过的《人啊,人》和四望亭里戴着老蓝布袖筒的老师傅就这样消失在了记忆深处,我永远欠着他们一个道歉。
另一个好地方就是扬州国庆路上的新华书店。我们的大学是中学式的教育,我的专业又不是中文专业,对于读书,我还没有学会辨别,只知道熱爱,当时很盲目,省下零花钱,疯狂地买书,只要是诗与散文的新书我都要想方设法地买下来。我买了一大堆品质不良或者没有营养的书。但有一次──我就买到中了一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俄苏名家散文选》。这本书封面很朴素,上面仅有两株白桦封底上仅仅署“0.31元”。这本仅有79页的散文集一共收到八位作家十八篇散文──当时我们读多了类似杨朔的散文,类似刘白羽的散文──我一下子有点目眩。有屠格涅夫,有蒲宁,有普里什文,有契诃夫,有帕乌斯托夫斯基,有托尔斯泰,有柯罗连柯,还有《海燕》之外的高尔基。我过去的关于“起承转合”的散文写作方式一下子被冲垮了……
我至今还记得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给予我的冲击,我似乎醉了氧。“去年,为了在伐木地点做一个标记,我们砍断了一棵小白桦树;几乎只有一根狭狭的树皮条还把树身和树根连在一起。今年我找到了这个地方,令人不胜惊讶的是:这棵砍断的小白桦还是碧绿碧绿的,显然是因为树皮条在向挂着的枝桠提供养分。”简单,直接,清爽,准确……读这本书的那几天,我晕乎乎的。我还不甘心,又找了一个本子把这本79页的书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了下来。柯罗连柯的《灯光》,屠格涅夫的《鸽子》,契诃夫的《河上》,蒲宁的《“希望号”》,高尔基的《早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黄色的光》。等等。我一直把这本书当成我撞开文学之门的钥匙,我的系列散文《乡村教师手记》得到许多朋友的称赞,其实,如果看过这本书,应该可以找到我的文学中的汩汩溪水来自哪里。
这本后来就成了我的案头书,经历了多次搬书,它也没有从我的身边走散。从扬州到黄邳,又从黄邳到沙沟,在沙沟又经历了几次,再到长江边的小城靖江,但这本书依旧还在,像一条从童年起就陪伴我的老狗。这本书的忠诚啊,我想想就要翻翻他,他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31年,有多少灯光之夜我们面面相对,默默无言。多少艰难的日子里,我和这本书在使劲地划桨……不过,在前面毕竟有着──灯光!……是的,前面仍然有着灯光,有着一片蔚蓝的天空。
惊蛰时节的虫子同学
惊蛰至,雷声起。
这雷声约等于小学校的上课钟声,可能怕懒虫们睡懒觉睡得太久,忘记上学了,我们的雷公校长就果断敲响了闲置已久的漆红大鼓。
鼓声隆隆,称为之“惊”。懒虫们听到了,惊醒了,所以叫惊蛰,又名:春雷一声动,遍地起爬虫。
但是,惊蛰时节,最先醒过来的虫子是哪个?
有人说“蛰”字下面的“虫”是“长虫”。即蛇同学。也有不同意见,为什么不是蜈蚣同学呢?蚯蚓同学?青蛙同学?或者,蚂蚁同学?要知道,这些睡懒觉的同学都在等待雷公校长的鼓声哦。
比如蛇同学,越冬常常因陋就简,随便将就。我曾在老屋的墙缝里摸到一排蛇蛋。如子弹样的椭圆形的白壳蛇蛋,并排粘在一起。我记得是四枚,我在众伙伴的怂恿下打开了蛇蛋,有蛋清也有蛋黄,蛋黄里已有小蚯蚓一样的幼蛇。这是冬眠前的蛇生下来的。
除了人为的破坏,大自然的考验也很残酷,我看过一份资料,到了惊蛰时节,听到雷公校长鼓声,也就是能继续上学的,最多七成。如果冬天太寒冷,那只有五成活到了第二年春天。
相比蛇同学的粗心,蜈蚣同学准备更充分,蜈蚣们会钻洞,钻得很深很深,钻到寒冷无法侵入的深度,有时候,能钻到1米深的地方。不吃,不喝,不动。如此沉睡的时候,蜈蚣最怕的是公鸡。公鸡是蜈蚣的天敌,它们的利爪总是在旷野里扒拉。如果蜈蚣冬眠的地点太浅,正好是公鸡的食物。蜈蚣为五毒之一,为什么公鸡不惧怕蜈蚣?父亲说,蜈蚣和公鸡是死仇。
为什么?
父亲说不出原因,就像他说不清他如此地辛苦劳作,却依旧喂不饱他饥饿的子女们。
蚯蚓同学与蜈蚣同学类似,它们的冬眠常常会遭遇钓鱼人的暴力拆迁。很多钓鱼人,在那么寒冷的冬天,将浮到水面上晒太阳的鱼钓上来,总觉得有乘人之危的味道。
我和朋友讨论过这事,还没说到蚯蚓们的委屈,朋友就说这世上从来都是田鸡(青蛙)要命蛇要饱。
朋友这话用学术语言翻译就是“丛林法则”,可凭什么,不让冬眠的蚯蚓们等到雷公校长的鼓声?!
作为歌唱家和捕虫专家两栖界的青蛙和癞蛤蟆,它们冬眠时会异常安静。在我家石头台阶下,我发现过扁成一张纸的癞蛤蟆,真成了张薄薄的癞蛤蟆纸!它们把喉咙里的歌声也压扁了吗?它们的骨头呢?它们的内脏呢?后来学到“蛰伏”这个词,我一下想到了这张扁成纸的癞蛤蟆:最低的生活标准,最艰难的坚持,还有沉默中的苦熬!
有精品房的蚂蚁们越冬准备超过了人类。在入冬之前,它们先运草种,再搬运蚜虫灰蝶幼虫等这些客人,请这些客人到蚁巢内过冬。但它们的友情不是无私的,而是实用的,蚂蚁们将这些客人的排泄物作为越冬的食物。等到贮藏的食物吃得差不多了,雷公校长的鼓声就该响了。
但如此精心如此努力的蚂蚁们,如果遇到我们手中的樟脑丸,如果碰上了我们淘气的一泡尿,它们会立即被淘汰,没有惊呼,也没有叹息,连一声悼念都没有。
生存不易,梦想更不易,都得好好惜生。春雷响了,正好九九,九九那个艳阳天啊,那久违的温暖总会使所有越过冬天的众生感慨不已。
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上课的铃声要响了,众生们背负着自己的命运奔跑着去学校。春耕季节来了,父亲说:没有闲时了。
是啊,九尽杨花开,农活一齐来。没有闲时忧伤了,也没有闲时快乐了,季节不等人,一刻值千金。恍惚之间,这世间最忙碌的虫子,是在这块土地上过日子的人。
最漫长的一天
记忆中最漫长的一天就是割稻了。
为了准备这一个漫长的日子。父亲俯身在磨刀砖上磨了很长时间的镰刀。
磨刀砖是块砌城墙的砖——是父亲去县城护城河里罱泥罱到的。父亲一边磨着,一边往镰刀的刃口洒了几滴水。不一会,磨出的泥浆慢慢爬到了置放磨刀砖的凳子上。
磨刀的父亲非常专注,有只苍蝇盯在他的后脖子上,他也没空理睬,每磨一会儿,他就用大拇指试着镰刀的刃口。父亲的手上也粘了泥浆。
砌城墙的砖头质量太好了,磨了好多年了,城墙砖仅仅磨出了一道好看的凹面。
一把,兩把,三把,父亲会一口气磨好三把镰刀。这三把镰刀并不代表明天有三个人割刀,其中有一把是父亲的备用镰刀。
磨好了镰刀,父亲嘱咐全家早点睡。父亲的口头禅是:没钱打肉吃,睡觉养精神。多睡点,就有力气干活了。
在最漫长的一天到来之前天晚上,我又看了搁在院子里的镰刀,镰刀很亮,更亮的是头顶上的月亮。秋天越深,月亮越白,天庭上的月亮比大队部的汽油灯还亮。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但醒来的时候,月亮还在西天上,还是很亮。我怀疑父亲都没有睡觉。我再看母亲,母亲煮了两大锅饭,一锅饭早上吃,一锅饭带到田里,充当午饭和晚饭。
早上吃饭是很少见的,我吃得太快,竟然噎住了。父亲有经验,用筷子猛然抽打我的头。我丢下碗筷,双手护头,竟好了。
吃了早饭就上船去田里割稻,离开村庄的时候,整个村庄还没醒来,有雄鸡在长啼,但我们已快到我们家稻田了。
月亮是在我们上了岸不见的。天暗了下来,但东边已有了鱼肚白。田埂上全是露水,冰凉冰凉的,打了几个冷颤,上牙磕打着下巴,由于肚子里饱饭,一点也不冷。
父亲的镰刀到处,呆在稻田里的蚂蚱们到处乱跳,有的撞到了父亲的脸上,有的还逃到了我的嘴巴里。父亲顾不上它们,我也顾不上它们。父亲母亲割稻,我要负责捡他们割漏下的稻呢。
东边的天色渐渐亮了起来,我们家的稻田已割掉了一小部分。隔不远处,也有人家来割稻了。
整天田野里,弥漫着好闻的青草味——这是稻根被割后的味道,是天下最好闻的味道。
捆稻的要子是父亲割的稗子棵,一分为二,两头打个结。那些稗子长得很高,也很有韧劲。父亲用镰刀搂起一群稻子,像哄孩子那样,把它们聚拢在一起,然后用稗子要将稻子们快速扎起。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起父亲捆稻的样子,还有父亲挑稻捆上船的样子,先用木杈的金属杈木杈叉住两捆稻,接着就用柄一头插到前面的一捆稻的腰中,一次三捆,虎虎生风地向我们家船上走去。
稻捆一捆又一捆地上了船,船的吃水线一再下埋。
在我們家木船的吃水线快要到极限时,最漫长的一天快过去了,月亮又升起来了。因为稻捆堆得很高,母亲在船头导航,父亲使用一根长长的竹篙。
咚。哗啦。咚。哗啦。
“咚”是竹篙下水的声音。“哗啦”是竹篙出水的声音。
河水已很凉了,月光也很凉,我的光脚丫更凉,我决定把自己的脚伸到稻捆中间。
——那稻捆里,竟然很暖和很暖和。
秋风吹过去也就吹过去了
想象中的丰收,一天天变成了现实。
比如那一朵朵摘下来的、又晾到了我打的芦箔上的棉花们,新鲜的白,灿烂的白,耀眼睛的白。晒了一上午,母亲会俯身将它们全翻个身。那棉花一定很柔软,很舒服,我刚想上去……被母亲严厉地呵斥道:看看你的鬼爪子,把我的棉花弄脏的。
我把手往身上擦了擦,展开来,看了看,又赶紧藏起了我的手,生怕棉花们看到我的难看的指甲,看到被我咬成了锯齿形的指甲,看到指甲缝里那些黑乎乎的东西……
好在田野里可做的事情太多了:芝麻要割,黄豆要拔,花生也要拔了。父亲教给我的农活技巧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割芝麻的时候得小心翼翼,拔黄豆的时候可以大大咧咧。到了拔花生的时候又必须用巧劲。
母亲不信任我,父亲同样也不信任我,黄豆我是拔不动的(父亲说:还不如让黄豆来拔你)。割芝麻是不会让我割的,弄不好芝麻会“炸”得一粒不剩。我是可以拔花生的。父亲同样拒绝了我,他生怕藏在地下的花生们就会变得七零八落的,那样花生的产量会少许多。其实,我们家的花生地和其他人家的花生地是不一样的,父亲用积攒了一个冬天的草木灰,让本来是粘土质的花生地变成了沙地,拔花生是非常容易的事,而且,拔花生是多么让人欣喜的事,轻轻抓住花生叶子们,慢慢摇晃,再往上一扯,很多藏在土里的花生娃娃就叮叮当当地拔出来了。
父亲只让我做一件事,那就是给邻居分享“水花生”。这里所说的“水花生”不是植物,而是收获的时候没有完全成熟的那些花生们。母亲将它们淘洗干净,放在大铁锅中,煮得喷香喷香的——在灶后烧火的我,一边往灶膛里塞稻草,一边咽着口水。自家的新鲜的水花生,可以敞开肚皮吃的。
水花生很快就熟了。但父亲让母亲用一只碗盛着煮好的水花生送邻居,而送水花生的任务是在我的身上。很不情愿的我必须在父亲严厉的目光中,将本来属于我的水花生送给了一家又一家邻居。铁锅里的水花生快速地少了下去,直到锅底的时候,母亲才停止让我分送水花生的行为。
快要淌麻油了!母亲笑着说,又不是没有,锅里不是还有吗?
锅里是还有,可全是小的,瘪的,吃不上嘴的。我跑出了家门,再次走到田野上,田野上有许多向日葵秆,那些向日葵秆上的葵匾被一一砍掉了,光秃秃的,很是怪异,但它们依旧笔直地站着,它们的叶子在秋风中翻卷着,似乎不知道那葵匾已被割去了。
那天我还是主动回到了家。桌上除了水花生,还多了一碗刚刚煮熟的菱角——这是邻居家刚刚送过来的。我不敢和父亲对视,刚才的委屈似乎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
1994年的秋天,中风多年的父亲去世了。正是秋分后的第三天。所以,每到秋分时节,我都会想到白棉花,想到委屈的水花生,想到邻居家的菱角,想到那黄昏里那被砍去了葵匾的一棵棵葵秆,它们依旧站得很直……我的悲伤就成了一阵阵秋风,吹过去,也就吹过去了。
在人间
“清明”是我最不忍心写的节气。不忍心,是因为愧疚。只要想到长眠在油菜花海中央的父亲和母亲,我就是那棵摇曳不停的不孝之树。油菜花波涛再汹涌,他们也听不到我无力的辩解了。
默念之中,油菜花在肆意地开放。不远处的新公路上,全是来来往往的车,那是去油菜花景区看风景的人们。有几次我陪客人去看过,爬上那高高的瞭望塔,我没敢向南看,5公里外,就是父母长眠的地方。
1994年秋天,父亲去世的时候,是葬在祖父母身边的。我没见过祖父母,只是听村上说过祖父的名言:天下只有用半升子借米的,没有用半升子借字的。
“半升子”是一种量具,一般用竹筒制作,装满了米,正好一市斤。我不知道读过《大学》《孟子》《中庸》的祖父为什么这样讨厌读书。也正因为这样,父亲这一辈就没有读书。吃了不读书之苦的父亲就坚决要求我们弟兄三个读书,他的命令是,只要不留级,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们上学,但如果留级,就回家种田。
祖父的字我是见过的,那是我家的“斗”上,有一个行书的名字。那时刚刚学会了“地主的斗,吃人的口”,于是我就到处宣传,我们家有个“地主的斗”。其实那“斗”上的名字就是祖父的名字。
后来村里建公墓,要求所有的散坟迁到公墓地。我们几个去为祖父母和父亲迁坟。祖父母的坟里竟然有一个船的牌照,还是上海的牌照。大哥说起这只船的历史,这是我们家的船,祖父去世的时候,没钱买木材,只好将船拆了。
因为迁坟,就立了碑。父亲的名字是黑的,那时母亲还在世,她的名字必须是红的。回到家,母亲向我问起迁坟的一些细节,问起了碑上的名字。我含糊地回答了一下,又问起了船。母亲说起这船,说起了等候渡江的八圩渡口,说起了“像粥锅一样的长江水”,说起了黄浦江上的轰炸机。
再后来,母亲去世了,我去八圩采访,那是个初夏的黄昏,我坐在八圩渡口,想象父母是怎样用小木桨一桨一桨地从里下河划到八圩,又是怎么渡过了汹涌的长江,但怎么也想不出来,如一苇渡江,但肯定没一苇的轻盈超脱,而那个沉重的贫穷的家,又是如何在上海和兴化之间走过去的呢?记得姑母劝过母亲念佛,母亲不肯,说,为什么菩萨给了她这样的苦命?
母亲出生后十五个月,外公去世。外婆改嫁。母亲在二外公三外公家长大,再后来,外婆又将母亲许给了她后来改嫁的庞家侄儿,也就是我父亲。母亲和父亲生了十个孩子,我是第十個孩子。谁都不能想象,每个孩子的出生,都是母亲自己给自己接生。母亲跟我讲过接生的细节,但我从不忍写出。
母亲生下我的时候,她已44岁。母亲大出血,送到县城抢救。大姐抱着病猫似的我,到处找食。我没吃过母亲一口乳汁,但我心中最想念的还是母亲。大学时代,我遇到了洛夫先生发表在《芙蓉》杂志上的600多行的长诗《血的再版》,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了,抄完之后,我学会了写诗。这里面的因果,还是因为苦命的母亲。十个孩子,后来活下来六个。母亲跟我讲过很多次那另外的、夭折的四个孩子。
苦藤一般无尽无止的纠缠
都从一根脐带开始
就那么
生生世世
环绕成一只千丝不绝的
蚕
我是其中的蛹
当破茧而出
带着满身血丝的我
便四处寻找你
让我告诉你
化为一只蛾有多苦
在灯火中焚身有多痛
这是洛夫先生的《血的再版》,每到清明,我总会把这首长诗再读一遍,疼痛,又疼痛。读完这首诗,再看地里的油菜、蚕豆和小麦们,它们似乎更茂盛了。于是,在这个茂盛的春天里,清明降临,我们又会记起,我们都是那血的再版。
每年清明扫墓之途,总是我们三个“再版的血”坐一条水泥小船。大哥坐在船头,我坐在中舱,二哥划着木桨。水声哗哗,水面被划出一道长长的伤疤。这水的伤疤一直通向父母的长眠之地。每到清明,这伤疤新鲜依旧,疼痛依旧。我们的苦根依旧。
暮色纯蓝
“我的沉默是我的国家的底色/但是,我要永记蔷薇花。”
这是诗人杨健的诗歌。在沉默的命运中,每个人都有“永记蔷薇花”的时刻。我想,生活在起伏的波浪中,我的“永记蔷薇花”的时刻是在与好书相遇的时刻,比如那本在半瘫的父亲身边读完的《天使,望故乡》,比如在停电之夜半截蜡烛下读完的《最明亮的与最黑暗的》,比如坐在空旷打谷场的一只石磙上读完的《大地上的事》。每一本和我相爱过的书,都像童年的星星一样,潮润,明朗。有了它们,我就能在那些破旧的日子里,做着蔷薇花的梦。
记得我在大学那简陋的图书馆里抄诗,为了抄写洛夫先生的长诗《血的再版》,我的新棉袄袖口上滴满了清水鼻涕。记得我在那个小镇上为了寻找能够夜读的煤油而去接近镇长的儿子。记得我在乡村学校的课堂上为孩子们朗诵诗歌,我为他们朗诵过许多诗歌,朗诵孙昕晨的《一粒米和我们并肩前进》的那个黄昏,我记得窗外的暮色开始是红色的,后来变成了紫色,再后来就变成了纯蓝,孩子们的眼睛里全是纯蓝的光芒……朗诵完毕,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那么好的诗歌,就这么与我相遇。蔷薇花,蔷薇花,沐浴着诗人王家新的歌声,诗人海子的歌声……还有我的好兄弟们的歌声。因为钢笔总是漏水,所以我爱上了圆珠笔。为不用白天工作时的蓝色圆珠笔,就到处求购黑色的圆珠笔芯。当我抄到曼彻斯塔姆的“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我全身止不住地战栗。到现在,我还记得此首诗的翻译者为荀红军,这是一位上世纪80年代初出道的诗人,如今已消失了。再也看不到翻译曼彻斯塔姆翻译得那么精妙的诗人了。
像荀红军一样消失在80年代的诗人,有多少啊——就像蔷薇花,不断地落,又不断地开。包括那么温暖的《诗歌报》,套红的鲁迅体的“诗歌报”,蒋维扬,乔延凤,都带着我们一起穿越过蔷薇花丛……再也没有那样的报纸了,每一字都值得珍惜的报纸啊。有次开会,我遇到了叶橹先生,问候了一声,竟然失语了——他的头发依旧那么白,我内心满是愧疚,对青春和诗歌的愧疚。
但蔷薇们总是平静如初,上面积满了生存者的无奈和灰尘。我最企盼的是要一本好书,到了晚上,能够逮住我的好书。在好书的面前,沉默和自卑轻轻在星光下张开,任由蔷薇上的针刺被夜色染得坚硬。
也许只有那时,蔷薇和篱笆都是清醒的。这个世界上,除了越来越稀罕的好文字,我已经没有多少开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