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还需要读《红旗谱》吗
2019-09-16张勇
张勇
在我的阅读视野中,以《红旗谱》为代表的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革命历史叙事类作品,一直都是一部部很难忘却的经典。它们在看似简单的情节描述和历史叙事的背后,却隐含着特殊的时代命题和史学价值,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前移和变迁,作为革命历史叙事题材代表的《红旗谱》也不断生发出崭新的美学内涵,具有时读时新的现实魅力。
《红旗谱》完成于1954年,经过了两年多的修改后于1957年11月出版,自问世以来它既收获了出版后社会各界一致赞誉之声,迅速成为时代文化的焦点,甚至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将其誉为“全国第一部优秀作品”,茅盾更是将作品称之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但也因鲜明的主题阐释,在特殊历史时期一度成为批评的焦点,被当作“写错误路线”的代表,随着历史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红旗谱》很快恢复本有的进步价值,重新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并荣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图书之列”,新时代《红旗谱》的阅读依然具有无限阐释的空间和现实意义。
壹
《红旗谱》从创作者和文本本体两个角度来讲,它的最大价值便是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自觉的时代进步性。它借助于完美的艺术形式构造,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并且融多种历史事件于一体,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小说创作的基本模式。《红旗谱》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得益于作者梁斌秉承着强烈的使命感,在激越的情感追述中进行了作品的构思和创作。
作者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是《红旗谱》创作的现实基础。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红旗谱》以真实的历史叙事手法,全面真实客观地展示了冀中平原地区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反割头税”斗争和保定二师的学生爱国运动,特别展现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九·一八”事变时间段内,中国北方社会中波谲云诡的阶级关系和斗争形势,借此还原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革命斗争的伟大历程。既然是宏大历史主题的叙事,那么就要求作者必须具备熟稔的历史事件阐释能力。对于《红旗谱》中“反割头税”“学生爱国运动”“武装暴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梁斌都再熟悉不过了,有些甚至亲身参与其中,即便是没有参与到其中,他也与历史的亲历者相熟。1929年在他的家乡就爆发了农民群众自发进行的“反割头税斗争”,时为共青团员的梁斌便义无反顾地参与其中,到了保定二师上学期间,他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氛围的感召下,积极投身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进步活动之中。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残酷革命斗争的人生经历,不仅仅为梁斌的创作提供了厚实的素材,更形成了他展示历史场景的严肃心态。
新中国成立后,梁斌先后担任了湖北襄樊地委宣传部长,《武汉日报》社长,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务,但是为了专心完成《红旗谱》创作,他辞去了所有的行政职务,只保留了河北文联的编制,专心进行素材的收集和作品的构思。他为此曾表示“如果我写不好这部书,无颜见家乡父老”。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促使梁斌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沉寂于创作之中,在此情境下《红旗谱》得以顺利完成。
梁斌把自己全部的感情都投入到作品创作之中,并将人物的塑造与现实的经历相对照,发现事中之情,揭示情中之理,反映出革命斗争历史时期人物关系的特殊性和情感的复杂性,特别是“在那个时代,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伟大的爱情:父子之爱,夫妇之爱,母子之爱。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伟大的友情,敦厚的友谊。当我发现了旧中国时代这些宝贵的东西,我不禁为之钦仰,深受感动,流下了眼泪”。(梁斌《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文艺月报》1958年第5期)他深深地被自己所要描述的对象感动,他也抑制不住自己激越的情感,因此《红旗谱》中我们随处都可以阅读到诸如“泪眼对着窗外的天空……照着她惨白的脸庞”的虔诚表达。
作者炙热的情感不仅仅映射到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方面的描述上,而且还对在紧张革命斗争之外的自然环境描写也投入了最真挚的情感。“滹沱河打太行山上流下来,像一匹烈性的马。它在峡谷里,要腾空飞窜,到了平原上,就满地奔驰。夏秋季节,涌起吓人的浪头。到了冬天,在茸厚的积雪上,汩汩细流。”“黄色的平地,屋舍的树林,土地河流,正落向车后。路旁柳树青青,阳光通过绿柳,射进车窗,将淡绿色的影子照在他们身上。”将一条普通的河流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给裸露在大自然的植物赋予了斑斓的色彩,对于这些存在于艰苦社会环境中的一草一木,一水一山,如果没有强烈的情感投入是难以有如此的词句表达。
就《红旗谱》文本本体而言,明确而强烈的使命感一直贯穿于始末,作品的开头与结尾遥相呼应的情节设置,也进一步凸显了作品崇高使命感的内涵,作品是以便充满紧张的情境描述作为起始,朱老忠与父亲一起进行了保钟护地的斗争,但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因此朱老忠不得不流亡于外,姐姐也因此含冤而亡。复仇的火种在朱老忠的心中扎下了根:
他一个人,在关东的草原上走来走去:在长白山上挖参,在黑河里打鱼,在海兰泡淘金。受了多少年的苦,落下几个钱,娶下媳妇,生下孩子,才像一家人了。可是,他一想起家乡,心上就像辘轳一样,搅动不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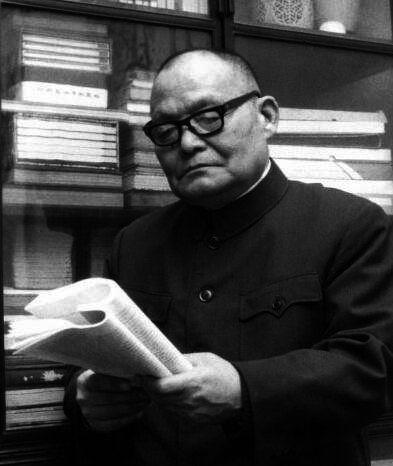
如此浓重的复仇意识,便生成了朱老忠明确的使命感,在使命感的催促下朱老忠对于完成复仇的使命是有清晰地认识和明晰地规划的,“将来我叫大贵当兵去,这就是一文一武。说知心话,兄弟!他们欺侮了咱多少代,到了咱这一代,咱不能受一輩子窝囊。可是没有拿枪杆子的人,哪能行?你看大财主们的孩子,不是上学堂,就是入军队”。(《红旗谱》P47)
《红旗谱》采取了开放式的结尾写作模式,它并没有将人物的结局明确化和固定化,而是采用意犹未尽描述方式,展示了故事本有的多元化走向,“这时,朱老忠抬起头来,看着空中,辽阔的天上,涌起一疙瘩一疙瘩的浓云,风云变幻,心里在憧憬着一个伟大的理想……这句话预示,在冀中平原上,将要掀起壮阔的风暴啊!”(《红旗谱》P477)朱老忠由开始时自发的复仇意识,成功地转换成自觉的革命使命,使命感的心理机制的变化,完成了《红旗谱》作为经典读本价值内涵的建构和美学意蕴的考量。
难怪洪子诚在其《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不无感喟地写道:这样鲜明的主题,不仅使我们看到作者对那个时代中国农民命运的思考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也使我们体会到革命战争小说的创作理念和时代背景。
贰
在阅读《红旗谱》时感觉到除了曲折故事情节发展引人关注外,朱老忠等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更是栩栩如生,让我印记深刻。我时而服膺于梁斌对于朱老忠理想化塑造以及带来的持续性震撼;时而惊讶于朱老忠百折不回的坚定复仇信念;时而又折服于他热情洋溢的斗争激情;时而更是感受着朱老忠关键时刻总能以清醒的理性思维对复杂关系和形势的预判与分析。
梁斌认为“对于中国农民英雄的典型的塑造,应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在此种明晰而刻意的创作意识和理念的支配下,具有理想化人物形象的朱老忠便呈现于读者面前,他也成为了中国红色革命人物画廊中最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之一。
朱老忠身上具有理想化英雄人物形象的所有质素。当他很小时就经历过荡气回肠的抗争,情绪和思维一直浸染于惨烈的斗争场景之中无法忘却,由此也自觉生发出了英雄主义的情怀,在抗争中时为小虎子的朱老忠“在一边看着,他气呀,急呀,两眼睁得滴溜圆。看着冯兰池,凶煞似的,拽得父亲流星波拉地。他眼角上掯着泪珠子,攥紧两只拳头,撑在腰上,左右不肯离开他爹。……小虎子一看,油锤就要击在父亲的脑壳上。他两步蹿上去,搂紧爹的脑袋,哭出来说:‘要砸死我爹,得先砸死我!”(《红旗谱》P10)义无反顾的反抗意识开启了他由复仇到革命的英雄抗争人生。
长大后朱老忠的英雄斗争气概更加强烈,特别是在“反割头税”斗争中:
朱老忠看那两把刺刀,在江涛眼前闪着光,眼看要戳着他的眼睛,把大棉袄一脱,擎着两条三节鞭闯上去,两手向上一腾,咣啷啷,把两把刺刀打落在地上。一下子又上来五六把刺刀,照准朱老忠冲过来。朱老忠气冲冲走上去,拿起三节鞭,劈劈啪啪打着,迎挡着。(《红旗谱》P321)
他以自己实际行动,诠释了传统农民所本有的英雄潜质以及抗争的心理基础,也形成了革命时期英雄主义的特殊内涵。
朱老忠的英雄形象不仅仅只是呈现于他以暴治暴的硬汉精神气概,他为了帮助运涛凑足学费,卖掉了自家唯一的牛犊,为了到济南探望入狱的运涛,他毅然决然的奋力前行,他率先在自家门前义务为乡亲杀猪,以对抗冯老兰的“割头税”,为了营救在学潮运动中被困的学生,他冒死成功救出了学生的骨干张嘉庆。越是在困难的时刻,越是显现出朱老忠果敢的性情。这种性情的展示明显是经过作者理想化处理和加工后的革命典型形象,使朱老忠在百折不回中锤炼意志,明确了方向,尤其是在他入党仪式时,仅仅只是江涛“找了一张年联的纸来,剪面红旗贴在墙上”(《红旗谱》P333),虽然形式简陋,但意义重大,由此生成的足够克服一切困难和险阻的革命初心和信念,是坚不可摧的。
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传统农民,一直以来受到封建思想桎梏的压制,对于自身的解放缺乏信心。他们深爱土地,受命于土地,但又受制于土地,他们希望拥有幸福的生活,但他们却在一次次抗争失败后甘于沦为底层的命运,严志和在将自己祖传下来的宝地抵押给冯老兰后,手捧着曾经属于自己土地上的泥土塞到自己嘴里,他那种绝望无助的神情恰恰便是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的中国传统农民的真实写照。而朱老忠的形象出现后,无异于使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朱老忠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抗争者,而是一个时代的代表者,代表着经过思想改造后理想化的农民出现与存在,他给读者阅读带来的不应仅是一个简单人物形象快意恩仇的行为,而应是一段有关民族理想精神记忆的复现与寄托。总之,朱老忠是旧中国农民典型的代表,也是新中国农民成长的方向,他有传统老中国农民坚毅、执着的优良品质,更有新时代中国农民理性、先进的新质内涵,他的存在价值和教育意义远远超越了曲折故事情节的推演和复述。朱老忠身上所展现出理想化基因对于当下社会民众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都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叁
顾名思义,《红旗谱》的书名有明确地树立红色革命旗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明确意指,它具有鲜明时代图标色彩,但除此显在的意蕴之外,它其实还预示着红色革命的基因将以谱系的模式生发、长成和延续,它通过一连串斗争事件的链接、一系列人物关系的建构等创作手法,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多元化的谱系结构,如借助于“砸钟保地”“夺鸟换地”“反割头税斗争”“二师学潮”“高蠡暴动”等历史事件的串连,将革命运动由自发转变为自觉,由小事件转变为大革命。从内在情感关联的角度来看,《红旗谱》的最显在谱系特征是,通过朱老忠、严志和、朱大贵、朱二贵、严运涛、严江涛等人物形象,明确地预示了革命薪火的代代相传,革命斗争方式的多样选择和主题内涵的深刻性。特别是对于张嘉庆形象的塑造,进一步说明了红色革命基因和谱系生成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多年以来,在我的阅读体验中一直把《红旗谱》主要描写人物本能界定为以朱老忠为代表的中国农民阶层上,的确朱老忠是《红旗谱》中最主要的人物形象典型,但如果仅仅只是这一条人物发展线索,《红旗谱》也不可能具有如茅盾所言的“深厚而豪放的风格”。以朱老忠为代表的农民反抗压迫的革命运动,由小及大,由自发转为自觉,并最终走向党的领导是革命历史主义叙事作品的叙事策略,也是此类题材作品的作者所惯用的创作手法。但如果仅此而已,《红旗谱》便会落入浅显而生硬的革命书写的窠臼和一般化的模式之中,其实在朱老忠等农民形象之外《红旗谱》还着力构建了另外一条线索,也就是以贾湘农、张嘉庆等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观念的转变和思想成长的书写,这种类型人物谱系的建构,也解析了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因素。
在众多知识分子中,梁斌着力塑造的便是张嘉庆这一人物形象。张嘉庆出身于“十亩园子百顷地,住的是青堂瓦舍,穿的是绫罗绸缎”的家庭之中,但是他完成了从被改造、被革命的对象到先进革命典型的巨大转变。在转变途中,特别是在他即将远离家乡投身到实际的战斗之中时,他“回过头看了看他住了几年的城池。贾老师还独自一人站在土岗上,呆呆地愣着。他要亲眼看着年轻的同志走远。张嘉庆看着他严峻的形象,暗暗地说:“父亲……父亲……”(《红旗谱》P340)张嘉庆与贾湘农的关系,从简单师生间人际关系到潜意识中亲情认同的转变,表明了以张嘉庆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已经从谱系上,纳入到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先进队伍之中,从而在人类伦理谱系的更高层级上重新界定了党与群众的之间的血脉相联的密切关系。因信仰的变化和现实革命的洗礼,“张嘉庆像出了笼的鸟儿,两手握着车杠,伸开长腿跑得飞快。……正当夏日时节,平原上庄稼长得绿油油的。张嘉庆拉着这辆洋车,在田野上跑,像撑着一只自由的船,冲破千层巨浪,浮游在绿色的海洋上,飘摇前进!”(《红旗谱》P476)轻松愉快词语表述,映衬和预设着革命理想最终取得成功的可能。
如果说,以朱老忠为代表的人物谱系的思想观念转变与成长,是农民阶级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话,那么张嘉庆接受并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更加显示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观念和方略的历史先进性和强大的生命指征。
微观到单一家庭生活模式的维持,宏观到民族國家整体发展运行的秩序,都是通过某种完整谱系的建立和扩展,才能维持其基本运行的规律和方向,并最终形成普遍共识性的历史脉络走向。《红旗谱》的创作便通过诸多完整谱系的建构,牢牢把握住了繁复深奥的新时代、新社会良好秩序发展的方向。从这个角度来看,《红旗谱》的更大意义和价值在于它为我们当下文化秩序的运行和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路途和方式。
作为曾经红极一时的革命历史叙事题材典型代表的《红旗谱》,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削弱它本有的独特价值,今天读来鲜活依旧。它以鲜明的主题思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增强了全民族的历史使命感,特别是对新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秩序全面的建构和理想主义的宣扬,《红旗谱》超越了具体特定历史阐述和精神塑造,是一部既具有时代特性,又葆有历史价值的典范之作,无愧于历史给予的高度评价。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