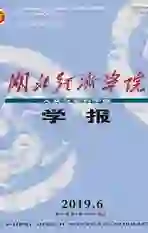论居易·德·莫泊桑《羊脂球》的“替罪羊”主题
2019-09-10马益平熊宇箐
马益平 熊宇箐
摘 要:《羊脂球》是法国小说巨匠莫泊桑的经典之作,具有鲜明的“替罪羊”模式特征。小说通过社会各阶层对底层妓女羊脂球的集体暴力迫害,猛烈抨击了普法战争时期法国世俗社会的虚伪软弱、自私丑恶。本文运用神话原型批评来详细解读小说的“替罪羊”主题,并从强权政治、社会阶级、宗教理念等多个角度展开了分析,认为羊脂球成为“替罪羊”是法国世俗社会差异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羊脂球》;世俗社会;集体暴力;替罪羊
一、引言
居易·德·莫泊桑(1850-1893),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巨匠,出身于法国西北诺曼底地区的没落贵族家庭,青少年时期的教会学校生活及多年的军旅生活,使其亲身见证了19世纪下半叶法国世俗社会的万象[1]。莫泊桑一生创作了350多部中短篇小说,小说大都以19世纪法国空前的世俗社会为时代背景,通过对各种典型人物形象的刻画,充分展现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状态,表达了对腐朽、自私、虚伪上层社会的讽刺与批判,同时也突出了对底层人民淳朴、无私、爱国情怀的高度赞扬。《羊脂球》是莫泊桑的代表作,以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法国里昂城被普鲁士军队占领为时代背景,此时的法国进入到空前的世俗社会。小说讲述的是妓女羊脂球和商人鸟先生夫妇、纺织厂主卡雷·拉马东夫妇、贵族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两名修女以及民主党人高奴代同乘一辆马车离开敌占区诺曼底,途经托特镇前往迪埃普所发生的故事。
“替罪羊”意指代人受过者,最先由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廉·廷德尔将希伯来文译成英语《圣经》(旧约)时采用[2]。在《旧约·创世记》中,上帝为考验亚伯拉罕,要求他将自己的独子以撒献为燔祭,在他即将动手时,上帝相信并阻止了他。于是,亚伯拉罕就用一只无辜的公羊代替其子作为燔祭献于上帝。“替罪羊”作为在“驱邪”活动中的一种赎罪的象征,在世界各地被广泛使用,为人们驱除一切邪恶,带走所有的罪孽。整个“驱邪”活动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驱邪”前,和平的存在与混乱的发生。其次,是如何“驱邪”,即替罪羊的选择与处理。最后在“驱邪”后,即替罪羊被处理后,重回和平与宁静。这就是“替罪羊”的原始涵义。后来经过不断的演变,“替罪羊”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后多指无辜的人。法国著名哲学家勒内·吉拉尔在《替罪羊》中提出:“替罪羊”在西方社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爆发,它是必然会出现的[3]。它深刻地反映了特定历史背景下个人命运、他人命运、国家命运三者之间复杂矛盾的关联性,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暴力迫害,具有鲜明的社会象征。纵观西方文学作品,运用“替罪羊”模式来表达作品主题思想广受青睐。从居易·德·莫泊桑《羊脂球》——世俗社会的“替罪羊”到赫尔曼·麦尔维尔《比利·巴德》——社会政治的“替罪羊”;从雪莉·杰克逊《摸彩》——原始迷信的“替罪羊”到纳撒尼尔·霍桑《年轻的布朗先生》——宗教理念的“替罪羊”,再从威廉·福克纳《干燥的九月》——种族歧视的“替罪羊”到伊恩·麦克尤恩《赎罪》——伦理道德的“替罪羊”等等,无不蕴含着这一主题原型[4]。
《羊脂球》作为莫泊桑的经典代表作,被广大学者所青睐,但他们大多从思想主题、文学批评理论、写作手法等角度对该小说进行了研究。到目前为止,极少有人利用“替罪羊”模式对该小说进行解读分析。《羊脂球》具有鲜明的“替罪羊”模式特征,小说情节发展三阶段及主人翁羊脂球内心变化三阶段与“替罪羊”原型的三个过程相一致,即和平——替罪羊的选择和处理——重回和平,小说的主题通过这“三步曲”表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将利用“替罪羊”模式对小说进行解读,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羊脂球成为“替罪羊”的必然性,从而为读者解读类似小说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和平与危机
“和平”的存在。首先,是整个大社会的和平。“此后,城中便是一片寂静,一片静悄悄而又惶惶不安地等待的气氛……生活似乎停止了,铺子都关门闭店,街上阒无人声……”,小说开篇这样描绘了战败后的法国被普鲁士军队占领,鲁昂城陷入一片沉静的景象。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和平”,往日热闹的街道变得冷冷清清,路上空无一人,仿佛似一座空城,看似空荡荡的房屋,透出一双双眼睛窥视这战争的胜利者,成为城市的新主人。最初的恐怖消失后,气氛又重新平静下来。在许多当地家庭里,普鲁士军官和鲁昂人同桌吃饭,随意交谈,守着火炉取暖,完全没有之前的恐惧,气氛融洽。在托特镇更是出现战胜者与战败者和睦共处的奇异场景,“他们看到的头一个士兵在削土豆。再远一点,第二个士兵在给洗发店刷洗屋子。还有一个满脸胡须的士兵正在亲一个哭闹的小孩……”。其次,是小马车里的和平。妓女羊脂球和商人鸟先生夫妇、纺织厂主卡雷·拉马东夫妇、贵族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两名修女以及民主党人高奴代等10人,因为不同的原因同乘一辆马车离开鲁昂城。当羊脂球慷慨无私地将自己一大篮美味食物与美酒分享给了那群饥肠辘辘的虚伪之人后,之前对她的嘲讽、不屑与鄙视烟消云散,转而放松下来与之谈笑风生,从而使得整个马车处于一种虚伪的和平氛围中。最后,是主人翁羊脂球內心的坚毅平静。“她扫视同车的旅客,目光毫无惧色,充满了挑战神情,逼使大家立刻噤声,纷纷低下头”,面对马车上同行旅客的嘲讽与鄙视,羊脂球用一颗坚毅平静的强大内心怔住了他们。到达托特镇,当普鲁士军官要求他们下车时,羊脂球虽然挨近车门,却是最后下来的,在敌人面前始终保持冷静,表现出凛然难犯的气概。
潜在的“危机”。大社会与小马车上的“和平”面纱下蕴藏着巨大的潜在危机。战胜者与被殖民者和睦相处,这种扭曲的“和平”随时可能被战胜者的强权或被统治者的反抗所打破。“我若是个男子汉!我从窗口望着他们,只见那些肥猪戴着尖顶头盔,若不是女仆拉住我的手,我就会扔下家具砸他们”“如果不是有人揪我的头发把我拉开,我就会把那个家伙结果掉”,羊脂球也正是因为普鲁士人要强行住进她家奋起反抗,差点掐死入侵者而被迫乘坐马车背井离乡。此外,性需求是成年人的基本需求之一,大批普鲁士军人抛下老婆家庭来到这异国他乡,当他们的性需求长时间得不到满足时,必然给当地社会带来巨大的安全危机。小马车虚假和平的背后同样暗藏着的危机。鸟夫妇,资本家的代表,酒行商人,狡诈,爱占便宜,吝啬,用尽一切手段牟取暴利;卡雷·拉马东夫妇,资产阶级政客的代表,兼有纺织业精英与省议会议员的双重身份,社会名流,道貌岸然;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贵族的代表,出身于诺曼底的贵族世家,派头十足,虚伪;两名天主教修女,宗教势力的代表,虚伪狡黠,有着病态的身体和道貌岸然的宗教信仰;高奴代,民主党人代表,披着进步民主外衣的政治骗子,一方面故作爱国者姿态,对外来侵略者义愤填膺,另一方面成为附庸资产阶级的小丑与帮凶;最后是女主人翁羊脂球,社会最底层小人物代表,妓女,善良勇敢,拥有一颗爱国的心,有牺牲奉献精神。马车里的十个人有着各不相同的身份,不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代表19世纪法国社会上的相对应的群体、相对应的阶层,他们最终组成了一个法国社会群体,通过“一个马车装进一个社会”[5]。在这样一个“世俗的马车”里,靠无私奉献自己的美食换来的“和平”是无法持续的,一旦有新的危机出现,上层阶级必定会“集体无意识”再次“团结一致”,毫不犹豫地牺牲最底层人民的利益以维护自身利益。
三、“替罪羊”的选择与处理
小说写到托特镇商会旅馆时,真正危机降临了。普鲁士军官将整个马车及行人扣押,要求羊脂球陪他睡一晚,否则不予放行。大社会与小马车上的和平即将被打破,因此必须找“替罪羊”进行“驱邪”,为了满足普鲁士军官的性需求,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强权,为了马车的安全离开,这一角色落到了无辜的羊脂球身上。在“替罪羊”的处理过程中,普鲁士军官不需要强迫羊脂球就范,而是耐心地等待她的“自愿”,尽情展现着一种近乎自然的统治强权,反倒是那群世俗的同胞充当起积极的刽子手。当普鲁士军官提出无耻陪睡要求后,那群自私无耻的人们非但没有给予任何同情,站出来反抗,解救羊脂球,反而是背着她一起开了“圆桌会议”,认定羊脂球为“替罪羊”,自动结成同盟,共同谋划,确定每个人要扮演的角色、要依据的理由、要施展的手腕,以让羊脂球早点就范,来换取大家的自由。在被当成替罪羊进行处理的过程中,羊脂球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这一过程中其内心思想状态不断变化,直到妥协。起初面对普鲁士军官的无耻要求,羊脂球愤怒而坚定,“对那个普鲁士的狗东西说,我绝不,绝不,绝不同意”[6];在同行众人的和颜悦色、绞尽脑汁的劝导下,羊脂球丝毫都没有动摇的念头,当旅店老板问到她是否改变主意时,羊脂球冷淡地答道:“没有,先生”;当本该代表正义和善良的修女引用《圣经》中亚伯拉罕杀子祭祀的故事劝说羊脂球,暗示羊脂球无论做什么,只要动机纯洁,一定会得到上帝的宽恕。修女每讲的一句话,都在羊脂球愤怒的防线上攻破一个缺口,她内心的防垒慢慢在倾塌。当修女表示要赶去照顾生天花的法国士兵时,羊脂球内心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塌。最终,在“同盟军”的精心设计与诱导下,在个人尊严、宗教信仰与国家情怀的相互交织中,羊脂球的“堡垒”被攻陷,牺牲了自己,成为了“替罪羊”。
作者通过羊脂球这一“替罪羊”形象,深刻揭示了法国世俗社会的虚伪软弱、自私丑恶。从强权政治、社会阶级、宗教理念等角度分析,羊脂球成为替罪羊有其必然性,而小说正是利用这些“替罪羊”模式来表现不同的深层主题涵意。
(一)羊脂球——强权政治的“替罪羊”
从殖民政治角度来看,作为殖民统治者代表,普鲁士军官拥有着绝对的统治强权,当自己有性需求时,尽情地展示侵略者的政治强权,扣留马车以迫使羊脂球“自愿”陪自己过夜,以体验这个战败国的下等阶级女性的顺从。然而,在这世俗社会里,恰恰是底层妓女羊脂球面对敌人坚贞不屈。从想用家具砸他们,到差点掐死一个强行闯入的士兵,再到对普鲁士军官的大义凛然,在羊脂球的言行中,无不充斥着对普鲁士统治的反抗,这种反抗强烈的威胁着普鲁士人的统治地位。为了占领战败者的性高地来满足自己的性需求,同时也为了保证强权统治的安定与平稳,选择具有反抗精神的羊脂球当替罪羊有一定必然性。从男权政治角度来看,普鲁士军官把自己当作一位理智的道德家,他没有选择有夫之妇,而是选择了这个底层妓女。普鲁士军官完全可以挑选另外三位夫人或两个修女,却偏偏选中羊脂球这个妓女,他因敬重有夫之妇与坚守宗教信仰而选择了职业妓女,哪怕作为一个战胜者,他仍然维护着男性统治的“合法”制度。在当时社会政治背景下,选择一个毫无庇护的底层妓女,并不会造成什么社会影响,也不会损害到普鲁士的统治地位。所以,羊脂球当“替罪羊”是世俗社会政治差异的必然结果。
(二)羊脂球——社会阶级的“替罪羊”
从阶层来看,小说中主要人物的阶级身份是全然不同的,马车上的十人,他们分别是资本家的代表,资产阶级政客的代表,贵族的代表,宗教势力的代表,民主党人的代表,社会最底层小人物的代表。首先,三对夫妇作为上层、上流、统治阶级之间既有相同之處又有差异,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高贵的”本质是残酷、伪善与无耻,道貌岸然的实质是男盗女娼,不同之处在于各有各的卑污与淫乱。其次,革命的流氓与政治的浪荡子高代奴,他是公认的好好先生与“民主朋友”,一个向上爬的两面派,他毕生的爱好除了啤酒与革命以外,当然还有性欲。一方面,他故作高傲、爱国与有尊严,骂那些富人为无耻之徒,在敌人面前装出不屈的气概,在吃饱喝足后大唱《马赛曲》;另一方面,他不过是资产阶级可耻的附庸小丑与帮凶,在羊脂球成为替罪羊的过程中始终冷眼旁观。然后,天主教修女的病态、虚伪与阴险。当羊脂球告诉旅伴们,普鲁士军官向她提出了性要求时,那两位修女“早就低着头什么也没有说”。两个修女作为宗教势力的代表,可以说病态的头脑与身体是她们唯一的确证。作为救世主在人间的“天使”,她们盗用上帝的意志去欺骗、唆使羊脂球“自愿”去做敌人的“羔羊”。在羊脂球受到凌辱后,她们忙于躲在一旁划着十字进行祷告,不顾资助者与献祭者的饥饿与付出,大嚼浑圆的香肠——羊脂球的隐喻,干净利落地诠释了宗教的贪婪、虚伪与丑恶。最后,是女主人翁妓女羊脂球,社会最底层小人物代表,善良勇敢,拥有一颗爱国的心,有牺牲奉献精神。羊脂球所展现的品质,与这样一个虚伪软弱、自私丑恶的世俗社会显得格格不入。在他们看来,羊脂球不过是社会底层的一只可怜虫,作为一名妓女,社会地位低贱,失身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不用自命清高,如果牺牲一名底层妓女就可以换来他们的安全离开,那是很值得的。所以在这样一个阶层差异巨大的世俗社会里,当小马车遇到危机时,处于底层的羊脂球无可避免地遭受其他阶层的集体迫害,被无情地牺牲,以维护上层阶级的和平与稳定。所以,羊脂球当“替罪羊”是世俗社会阶级差异的必然结果。
(三)羊脂球——宗教理念的“替罪羊”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作者用一个极具讽刺意义的“替罪羊”模式,刻画了羊脂球与修女的人物形象,展示了小说的主题思想。小说中宗教的代表——修女,不过是打着宗教幌子的自私自利、虚伪狡黠的无耻之徒,因为“一个人可以在他身上兼具两种迥异的身份,可以同时是一个走乡串户的商贩和一个最圣洁的人”[7]。在饥饿难耐时,“两个嬷嬷已经不捏她们的念珠了,双手笼在长大的袖子里不再动弹……”;在羊脂球邀请两位修女分享美食时,“两位修女立即接受,她们咕哝两句道谢的话,眼皮也不抬就迅速吃起来”;而当羊脂球为集体牺牲而忘带食物时,“两位修女从腰带上取下长串念珠,一齐画了十字,嘴唇突然蠕动起来,动作越来越快……”,吃完后,“两位修女把吃剩下的香肠卷在纸里,又重新祈祷”。作为救世主在人间的“天使”,她们盗用上帝的意志去欺骗、唆使羊脂球“自愿”去做敌人的“羔羊”,羊脂球不是圣女,却如同“圣女贞德”,而两个修女争相做了出卖他人的犹大。面对普鲁士军官的无耻要求,面对同行人各种诱导劝说,羊脂球始终坚定拒绝陪睡这一无耻要求。然而本该代表正义和善良的修女,竟然用《圣经》中亚伯拉罕杀子祭祀的故事劝说羊脂球,暗示羊脂球无论做什么,只要动机纯洁,一定会得到上帝的宽恕。羊脂球作为一名天主教信奉者,在虚伪狡黠“天使”的歪曲诱导下,内心的坚定开始松动,最终成为了宗教信仰的牺牲品。所以,羊脂球当“替罪羊”是世俗社会宗教差异的必然结果。
四、重回和平与宁静
“驱邪”之后,“替罪羊”被处理完毕意味着一切“邪恶”都被带走,人们往往认为会出现一个平安祥和之年,即和谐稳定的局面再次出现[8]。随着“邪恶”被带走,“寒冬里的大雪停了,太阳明晃晃的,照得雪光耀眼。一大群白鸽子……,啄开冒热气的马粪蛋觅食”,大自然的一切显得那么美好和谐。再次上路的马车也重归和平,那是属于其他九个人的和平。马车里大家轻松愉快地互相交谈,夫人们聊着自己的好友是如此的优秀,有权有势的上层人士聊着息票、期限这些关于金钱的话题,修女们在胸前画着十字,忙着祷告,高奴代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沉思。羊脂球作为世俗社会边缘底层的小人物,先是被当作牺牲品“祭祀”,后又被视为肮脏无用的废物丢弃在马车的角落。再次启程的马车行驶了三个小时后,又到了吃饭时间,大家都各自拿出准备的食物,大快朵颐起来,只有羊脂球饥寒交迫地蜷缩在马车的角落里,“她想起那只大篮子……,她极力忍住,压抑这后悔、羞愧和愤怒的情绪,说不出任何话”。她的上身突然挺得直直的,眼睛凝视前方,苍白的脸绷得铁紧,内心死寂般的平静。
五、结论
综上所述,从强权政治、社会阶级、宗教理念等层面来看,羊脂球成为“替罪羊”是19世纪法国世俗社会差异的必然结果。作者利用“替罪羊”模式很好地表现了小说的主题思想,通过社会各阶层对底层妓女羊脂球的集体暴力迫害,猛烈抨击了普法战争时期法国世俗社会的虚伪软弱、自私丑恶。为此,人们在处理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只顾及自身利益,而让其他群体成为替罪羊。与此相反,人们应该相互尊重,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 张英伦.永恒的流星—莫泊桑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5.
[2] Vickery, John B., J’nan M. Sellery. The Scapegoat: Ritual and Literature[M].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72.
[3] 勒内·吉拉尔.替罪羊[M].冯寿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4] 甘文平.试论美国文学中的“替罪羊”小说[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25(6):81-83.
[5] 杨昌龙.西方文学史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6] 莫泊桑.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M].李玉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7] 阿兰·德波頓.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2007.
[8] Frazer, James. The Golden Bough[M].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