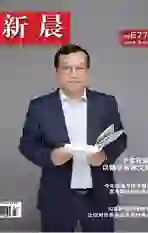金融市场的“恐惧因子”
2019-09-10克劳斯·施瓦布
克劳斯·施瓦布
恐惧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多年前,一位名叫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的飞行员驻足于一家便利店前,想要买些杂志。就在走进商店的一刹那,他忽然被一股莫名的强烈恐惧所笼罩,立即转身走了出来。事实上,当时便利店中正有歹徒持枪抢劫,他离开后没多久,一名进入便利店的警官遭枪击身亡。事件发生后,汤普森和畅销书《恐惧的礼物》(The Gift of Fear)的作者、世界著名人身安全顾问加文·德·贝克尔(Gavin de Becker)对此进行了深度交流,汤普森才意识到,当时的一些细节可能触发了他的恐惧:时值酷暑,店里一位顾客却身着厚夹克;店员过分紧张地看着这位顧客;一辆汽车横在店门前,引擎嗡嗡作响。尽管他事后细思深觉恐惧,当时却没有察觉到这些,因为理论上他从进门到迅速离开的工夫,没有给大脑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处理这些诡异的信息。
人的恐惧如同一台精密敏捷的仪器。神经学家的相关研究表明,人对恐惧的反应是高度发达的,出于恐惧我们可以快速地做户反应,甚至都来不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当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时,我们血压上升,反应变得机敏,肾上腺素分泌也急剧增多,这些让我们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做出“战或逃”的抉择,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一种能力。在此案中,按德·贝克尔的话说,正是这一能力拯救了汤普森的性命。当然,人的神经系统也不只对这类生命的威胁产生反应,当我们在感情、社交、财务上遇到压力时,也会产生类似的恐惧反应。问题是,“战或逃”的快速反应在除了酒吧斗殴或战场上的一些情形下也许有用,但假设有一天股市崩盘,你的养老金一夜间蒸发过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人类的这种“超能力”似乎是毫无用处的。人之所以能够在一刹那果断决定是坚守阵地还是迅速撤离,是过去千百年间人类在捕食者和大自然的各种威胁中不断选择和进化的结果。反观金融,货币的诞生也不过-余年而已,这与漫漫人类进化史相比不过沧海一粟,近代才出现的股市就更不必说了。不过必须承认,正是因为智人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步伐,才给投资者、基金经理乃至我们所有人带来了种种机遇与挑战。
所以我们要以革命性的眼光看待金融市场和人们的行为决策,这也是本书的要旨所在。所谓革命性眼光,我在本书中总结为“适应性市场假说”。其中,“适应性市场”一词主要描绘的是适应性变化对于个体决策行为与整个金融市场的多重作用,而冠之以“假说”之名则主要是为了对应在投资行业与金融学术界被广泛认可的“有效市场假说”。有效市场假说强调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华尔街尤其如此:倘若一种资产的市场价格能充分地反映关于该资产的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即“信息有效”的情况下,谁也别指望靠打败市场大发横财。相反,你应该大力投资于尽量多元化的被动型指数基金,在股市做一个长线投资者。你是否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这个理念早已被各大商学院写入案例和教材,你的经纪人、理财顾问和基金经理早已熟练地掌握了它。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尤金·法玛(Eugene F.Fama)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因为他提出了有效市场的概念。
相反,在适应性市场假说中,是一群生物互相竞争,适者生存,而不是一群非生命体按照机械的物理学定律运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适应性市场假说更像是生物学,而非物理学。这一差别看似无奇,实则耐人寻味。适应性市场假说告诉我们,进化思想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去粗取精,革故鼎新”的基本原则对于我们理解金融市场的内在机制极为有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胜于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经济学分析。举例而言,市场价格一定会反映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吗?未必。要知道市场的参与者——人是有捉摸不定的情感的,恐惧、贪欲等主观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实中的市场价格,使之偏离理论上合理的定价。这一假说也告诉我们,承担市场风险并不一定都能期望得到高回报作为补偿,长线投资股市也未必是良策,尤其在短期中你的积蓄可能被市场一扫而光的情况下。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市场大环境阴晴不定,每个人根据自身状况做出的适应性反应各不相同,而这些即时反应对投资者决策和市场动态的影响不亚于,甚至可能远胜于理性人出于自身利益的周密战略部署。群策群力下智慧的、有条不紊的规划很可能因一个疯狂暴徒的突然闯入而被打得支离破碎。
我并不是说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经济学一无是处,恰恰相反,你看现在华尔街对金融经济学位的青睐有增无减,尤其是如果你用金融学博士毕业生的起薪为衡量标准的话。也就是说,“疯狂暴徒”终会偃旗息鼓,被“理性人群”取代,至少在下次意外打破理性世界的有条不紊之前,它大概不会是市场的主导力量了。相比适应性市场假说,有效市场假说并没有错,只是不完整而已。就像盲人摸象的寓言中,五个盲人第一次摸到大象时的情形。天生的残疾使得他们对于大象的样子没有任何概念:一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腿,他认为大象长得像一棵树;另外一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鼻子,他认为大象长得像一条蛇;诸如此类。所有盲人对于大象的印象在细节上是准确的,但从整体上来看是错误的。在金融领域也是如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理论。
市场确实在一些情形下是有效的,前提是当投资者有机会去适应其所处的市场环境,且市场环境在足够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像那些复杂的、让人云里雾里的保险条款,确实如此。现实中,商业环境风云变幻是市场常态,而所谓的时间是否“足够长”取决于许多同样变幻莫测的因素。举例来说,假设你在2007年10月将你的毕生积蓄投给标普500——一个包含500家美国顶级大公司的高度多元化的投资组合,经过短短的时间,到2009年2月,你会失去51%的财富。这是在你焦虑地密切关注下一点点蒸发的,在此期间你当然有机会及时收手脱身,可是,你的“恐惧因子”在何时会现身,让你幡然醒悟,及时抽身呢?
具体而言,在了解市场泡沫、银行挤兑、养老计划等为何物之前,我们需要先知道我们的大脑是怎样工作的、人是如何做出决策的以及更为重要的——人类行为是如何进化并适应环境的。所以我们要借助的每一个学科实际上都是摸象的盲人之一,他们谁都不能单枪匹马地创造出一个完善的理论框架,但若我们将他们描绘出的一个个图景整合起来,我们想要的“大象”便一览无余了。
请勿擅自尝试
我们常常觉得一人之力之于整个金融市场是何其渺小,并因此对市场有所畏惧。殊不知,在2008年金融危机面前,整个世界都为之瑟瑟发抖。那一年,雷曼兄弟倒台,全世界的股市都随之一落千丈,个人养老金账户遭受剧烈冲击。不论你的投资组合是六成股票加四成债券,还是三成股票加七成债券,都无济于事,因为你的损失早已不仅是超乎预期,可能惨烈到你从未想过也不敢想的程度。当然,再大的灾难也常常有极少数幸免者,对于2008年来说,这极少数包括国库券和现金持有者,以及一部分对冲基金经理。紧接着,这年12月,麦道夫丑闻震惊世界,其骇人听闻的程度足以使庞氏骗局的鼻祖——查爾斯·庞兹(Charles Ponzi)相形见绌。总而言之,2008年这一年,投资者又一次见识了市场的可怕。
面对灾难,我们为何会如此措手不及?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所担心的意外永远不会发生。学者们无不坚信,市场的理性和效率绝非任何个人所能比拟,因为价格可以反映所有已知的信息。投资界的权威呼吁广大投资者,不要妄想打败市场,抑或追随我们漏洞百出的直觉,多看看价格吧,只有价格才是千真万确的。另外,也不要再为设计投资组合大伤脑筋了,倒不如把财经版面铺开,随意朝其掷飞镖来决定投资对象,理论上可以证实这样做所获得的收益与专业人士制订的投资规划所获得的收益相比毫不逊色。他们还指出,我们应该购买并持有一个保守型的多元化债股投资组合,如果是免佣金指数共同基金或交易所交易基金就更好了。总之就是,无须谋划,越任意越好。规划布局是市场的事,市场已经将所有因素考虑周全了,这就是市场,它总是如此严谨周密。
即使在今天,这种理想型市场的观点在很多专业投资经理人看来依然难以接受,但毕竟这一学说已诞生40多年,其间经历了许多理论与现实的验证或考验。资深财经记者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在其著作中将其称为“群体的智慧”,并以此命名该书。他还特意将苏格兰学者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的名言“群众性癫狂”放在了开头。几十年来,学者们的研究一次又一次证实着试图打败市场者的愚蠢。除了随机性的波动,市场的一切规律性波动或大趋势都会立即被投资者牢牢把握并以此获利,由此便自然缔造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有效市场。既然如此,为何不顺势而为呢?这一逻辑不仅帮助法玛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造就了数以万亿美元的指数基金业。
伯顿·麦基尔(Burton Malkiel)在其1973年首次出版的畅销书《漫步华尔街》(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中首先向公众系统地介绍了有效市场假说,也给了投资者一个该投资理论的正式名称。作为一名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麦基尔用醉汉的行迹来描述股价的波动——起伏不定、反复无常、难以预测,这也是那本书书名的来由。按麦基尔的逻辑,一个显然的结论是:既然股价是随机游走的,我们何必破费去雇用所谓的职业经理人呢?倒不如索性把钱投入那些费用最低的且高度多元化的保守型共同基金来得划算。当然,麦基尔的数百万读者的确照着他说的去做了。
无巧不成书,就在麦基尔的著作问世一年后,一个本科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成立了一家共同基金公司并恰好以此为主营业务。这个人你也许听说过,就是世界第一个指数基金——先锋500基金的创始人。在当时还是不起眼的初创企业的先锋集团如今已在业界举足轻重: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先锋集团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员工总数超过1.4万人。先锋最常对客户说的一句话就是:“请勿擅自尝试!”永远不要试图去打败市场,你要做的就是:购买保守型且高度多元化的股指基金,并持有这些基金直到你退休为止。
“笨蛋,关键是环境!”
从现实中我们能得到最直接的答案就是:金融市场并未遵循经济规律来运行。这一点说得通,因为金融市场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应当遵循生物学法则,而未必与经济规律一致。这即是说,诸如变异、竞争、白然选择等决定一群羚羊进化历史的法则同样适用于银行业,尽管具体机制上不可等同而论。
在这一系列法则中,最核心的就是在不断变化环境中的适应性行为。因为经济行为归根到底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而人类行为是千百年来为了适应环境变化而产生的生物进化的结果。竞争、变异、创新以及尤为重要的自然选择构成了人类进化的基本要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然若论丛林法则的严酷性,华尔街大概要比非洲大草原更胜一筹,但毫无疑问的是,用这种生物学眼光分析人们的经济行为再合适不过了。
这种进化论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并非我异想天开,其实进化论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借助了经济学的灵感。因为不仅赫赫有名的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本人,连他的竞争对手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都深受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影响。马尔萨斯预言,在粮食供给仅能呈直线增长的情况下,人口会呈现指数级增长。他由此断定,这样下去粮食短缺终将不可避免,严重的饥荒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灭绝。这简直令人胆战心惊,难怪有人将经济学称作“悲观的科学”。
好消息是现在看来情况似乎并没有马尔萨斯预想的那样糟糕,因为他忽略了创新的力量。人类创造并发展的公司、国际贸易、资本市场,包括金融创新在内的各领域科技创新,都大大发展了生产力,当然也填饱了我们的肚子。马尔萨斯失算了,不过他仍是研究人类行为与经济大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领域的拓荒者之一。这一系列研究让我们意识到,要想更深入地了解错综复杂的人类行为,我们有必要先搞清环境变化在其中发挥了哪些作用,搞清哪些是时过境迁引起的,其中的规律是怎样的。之后应用于金融体系,从而了解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怎样影响这个体系的运作。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好端端的金融市场,有时会突然失灵。长期以来,学术界、业界和政界都已经默认了理性经济行为,而对人类在理性之外的行为视而不见,这些行为游离于他们基于理性假设构造的精准数学模型之外。
现实中的金融市场给了我们一记无比响亮的耳光。直到现在,市场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依然严格遵循着多数人的理性,但如果倒退回金融危机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放眼金融市场,你会发现用“疯狂暴徒”来形容毫不为过。金融市场时而理智、时而疯狂的双重人格并非失常,而恰是我们人性的折射。
进化论告诉我们,我们总是会渐渐适应新的环境,这不仅是短期的适应,而且是以进化时间维度而论的,但不一定是对我们财务上有利的。其实一些市场行为在当时看来不理性是因为我们还未来得及适应周围环境条件的变化。我们可以在自然界找到类似的例子。有一种近乎完美的捕食者——大白鲨,经过4亿年的进化,它不断地适应环境,如今能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优雅和高效率在水中游动。但你若把它从水里捞出来,扔在沙滩上,它只会不断地甩动、挣扎,看起来完全失去了理智和优雅,变得狼狈不堪。为什么大白鲨在两种环境中会有这样的天壤之别呢?因为大白鲨的进化使它完美地适应了海洋,而不是干燥的陆地。
将大白鲨的例子类比于金融市场的人们,就不再难理解那些看起来荒谬的市场行为。人类进化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完成的,人類行为是为了适应特定的环境。当然,市场留给投资者适应的时间与鲨鱼适应环境的漫长进化历程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市场环境与海洋环境相比也多了更多的变数。经济的起起落落是参与其中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环境的结果,当这种变化太过剧烈时,就会出现泡沫甚至崩盘。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战略家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用一句“笨蛋,关键是经济”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克林顿团队的首要目标。借此我想说,生物学家可以用这句话——“笨蛋,关键是环境”来提醒一下经济学家。
作者简介
罗闻全(Andrew W.Lo)
美国MIT斯隆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MIT金融工程中心主任,生物金融学创始人,对冲基金Alpha Simplex Group的创立者兼合伙人。致力于从生物学进化论解释人类行为选择。
他最著名的贡献包括:于1988年提出方差比检验,并实证地指出股价即使对于广义的随机游走假设而言也是不满足的;指出金融学中的经典教条——有效市场假说是不成立的,并提出了适应性市场假说;开创了生物金融学;发展了马科维茨的均值——方差分析框架,提出了均值——方差——流动性分析框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