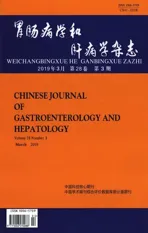幽门螺杆菌与胃肠微生态的研究
2019-03-27魏舒纯党旖旎张国新
魏舒纯, 党旖旎, 彭 磊, 张国新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江苏 南京 210029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ylori)是一种螺旋状的革兰氏阴性细菌[1],亚洲H.pylori感染率为54%~76%,高于北欧及北美[2]。人类消化道容纳着大量微生物,胃微生物密度为102~104菌落形成单位(CFU) /ml[3],其中优势菌门是放线菌、拟杆菌、厚壁菌、梭杆菌和变形杆菌,具体种属及相对丰度如表1所示[4]。研究人员已经证明,消化道微生物群调节宿主免疫稳态且与许多人类代谢紊乱有关[5]。本文旨在对H.pylori与胃肠微生态相互影响的研究及机制作一概述。
1 H.pylori与胃肠微生态相互作用
1.1H.pylori感染对胃肠微生态的影响人体内的微生物群落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作用,而H.pylori对胃肠微生态的影响尚无定论:(1)有研究[6]发现,H.pylori定植能显著改变胃微生物群分布,其中H.pylori阴性个体的胃微生物群组成高度多样化,经DNA测序鉴定出128个门型,代表8个门[7]。使用454焦磷酸测序技术分析确定了262个门型,代表13个门,而H.pylori阳性个体中的微生物多样性降低,共检测出33个门型,其中H.pylori丰度最高[8]。以上现象在最近几项针对成人[9-10]和儿童[11-12]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2)部分研究则发现H.pylori对胃微生物影响不大:KHOSRAVI等[13]发现,H.pylori阳性和阴性个体之间的胃微生物组成无显著性差异。在动物模型体内,微生物的分布也存在一定争议,据OSAKI等[14]报道,H.pylori阴性蒙古沙鼠体内的圆柱状真杆菌和普氏菌含量丰富,双歧杆菌、梭状芽孢杆菌和梭状芽孢杆菌种类较H.pylori阳性蒙古沙鼠减少。HEIMESAAT等[15]证明,感染了免疫病理性H.pyloriB8的小鼠盲肠中大肠杆菌、肠球菌和结肠内拟杆菌属/普雷沃氏菌的载量增加。另外一组数据却表明,急性、慢性H.pylori感染都不会显著改变鼠胃微生物的生态系统[16]。由此看出,H.pylori阴性和阳性个体的细菌群落分布仍高度复杂。H.pylori感染的时间、黏膜炎症的程度及H.pylori等细菌感染诊断方法的不同,都可能导致这些差异性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实验来确定H.pylori与其他胃微生物群之间的相互影响,并更好地了解其在健康和疾病中的功能。

表1 胃微生物的常见菌门和菌属(H.pylori除外)Tab 1 Common phylum and genus of gastric microorganisms(except H.pylori)
1.2H.pylori根除治疗对胃肠道微生态的影响H.pylori感染与否可能影响胃肠道微生态,是否可以通过H.pylori根除治疗逆转H.pylori感染受试者胃肠微生态紊乱始终存在争议,且根除治疗在不同部位导致的微生态改变也存在一定的差异:(1)咽喉部:H.pylori根除治疗导致细菌多样性降低[17]。(2)胃部:LI等[18]分别对接受抗H.pylori治疗前后的H.pylori阳性慢性胃炎和肠上皮化生(IM)患者进行连续活检,发现根除治疗导致细菌多样性增加,螺旋杆菌的平均相对丰度降低,非H.pylori菌群的相对丰度恢复至阴性对照水平。(3)肠道:JAKOBSSON等[17]发现,根除治疗导致肠道微生物组的细菌多样性降低,且粪肠球菌分离株基因组草图示H.pylori根除治疗后菌株种类减少[19]。YAP等[20]发现,根除H.pylori会引起肠道微生物群的破坏,清除感染后肠道内依然存在厚壁菌的增加和拟杆菌的减少。个体菌群本身的差异对疾病和疗效的影响也应纳入考虑。而宏基因组学的进展可能促使研究人员重新整合当前的知识,制定更个性化的根除治疗方案。
1.3胃肠微生态对H.pylori的影响微生物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非H.pylori菌群的改变也会影响H.pylori的生长:(1)共生的胃微生物或它们的代谢物可影响H.pylori的生存能力,并直接调节它的病原性和致癌性[21]。乳酸杆菌可以抑制H.pylori的生长[22],轻型链球菌通过产生并释放扩散因子诱导H.pylori细胞的生长抑制和球形转化[23]。(2)MALFERTHEINER等[24]建议使用益生菌作为根除H.pylori的辅助用药。益生菌和益生元补充剂与三联[25]、四联[26]疗法一起使用可提高H.pylori根除率、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1篇高质量的Meta分析[27]也证实了以上观点。(3)益生菌还能调节H.pylori根除治疗造成的肠道微生态失衡[28],YANG等[29]发现在H.pylori感染的儿童中,摄入含益生菌的酸奶4周可降低H.pylori载量并恢复粪便双歧杆菌水平。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是否可根据具体失调的菌群给予特定的益生菌辅助治疗值得进一步研究。
2 H.pylori感染与微生态紊乱对胃部疾病的影响
2.1消化性溃疡(pepticulcerdisease,PUD) PUD是公认的慢性H.pylori感染的并发症,95%的十二指肠溃疡和70%的胃溃疡与它有关[30]。近年来H.pylori感染呈下降趋势,与PUD发病率的下降趋势一致[31]。吸烟、饮酒、长期禁食(不规则饮食习惯)、NSAID的使用和H.pylori感染都是PUD的危险因素[32]。H.pylori的遗传变异和多种毒力因子可确定PUD的不同风险水平[33]。KHOSRAVI等[13]表明链球菌的分离与PUD间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非H.pylori菌群也可能通过复杂的机制或与H.pylori的相互作用在PUD的发病过程中发挥重要功能,但具体机制仍有待阐明。
2.2胃炎及胃癌近年来慢性浅表性胃炎和慢性萎缩性胃炎发病率呈上升趋势[31]。长期H.pylori感染和慢性胃炎之间的病因联系已有详细记载[34]。且根除试验的16年随访表明,持续感染H.pylori16年的患者进展为更高级别诊断的可能性明显高于清除感染者[35]。但慢性胃炎的发生不仅与H.pylori感染有关。ENGSTRAND等[34]发现,萎缩性胃炎患者体内的链球菌增加,普雷沃菌减少。胃癌是全球第三高死亡率癌症[36]。全球约90%的非贲门胃癌患者由H.pylori引起[37]。国际共识[24,38]也指出,根除H.pylori可以降低胃癌的发生风险。除H.pylori外,还有其他微生物参与了胃黏膜炎症的持续和胃癌的发展[39-40],且在高胃泌素胰岛素-胃泌素( INS-GAS )转基因小鼠模型体内得到了验证[41]。只是目前还无确凿的数据证实微生物群的以上改变是致病的原因还是结果。胃癌与胃炎患者的胃微生物组成有显著性差异,前者特征是微生物多样性降低,螺杆菌丰度下降,厚壁菌、放线菌、梭菌属、梭杆菌属、乳杆菌属及口腔中的P.stomatis和D.pneumosintes富集,其中大肠杆菌和核梭杆菌可作为胃癌诊断的生物标志物[42-44]。但在慢性胃炎中,螺杆菌被检测为最丰富的属。然而,EUN等[45]却发现,与其他慢性胃炎和肠上皮化生组相比,胃癌组微生物多样性更高。甚至有研究[46]表明,H.pylori以外的细菌在胃癌发生中无显著作用。因此,是否可通过检测某些特定微生物作为生物标志物区分及早期诊断胃炎及胃癌仍需进一步证实。
3 H.pylori与胃肠微生态相互作用机制
3.1H.pylori感染影响胃肠道非H.pylori菌群的机制前文已经列举了很多H.pylori与胃肠微生态相互作用的研究进展, 现将H.pylori影响其他微生物群的机制总结如下:H.pylori利用尿素生产氨和碳酸氢盐,其可用作其他微生物群落的基质;此外,可以减少胃酸分泌,为其他微生物的定植产生有利的生态位;H.pylori还可诱导产生细胞因子和抗菌肽,引起慢性炎症,并可能抑制其他局部微生物[47];除此之外,H.pylori可刺激胃泌素释放[48],胃环境pH的初始降低使胃对微生物的生长不利。
3.2益生菌抑制H.pylori定植的机制在H.pylori根除治疗中,益生菌的益处在于改变微生物群,限制腹泻不良反应,从而改善耐受性、依从性和根除率。具体可能通过以下4种途径协助根除H.pylori:益生菌可能具有抑制由H.pylori引起的细胞因子反应的潜力,如嗜酸乳杆菌可以使Th1对H.pylori感染的应答失活[49];约氏乳杆菌1088可直接抑制H.pylori的生长或通过下调G细胞和胃泌素产生来抑制胃酸分泌[50];乳酸杆菌能与病原菌竞争宿主表面受体,从而抑制病原体对上皮细胞的黏附[51];除此之外,益生菌还可以通过黏附胃上皮和分泌细菌黏附素与宿主固有免疫系统相互作用[52]。
3.3胃肠道微生态失衡在胃炎、胃癌癌转化中的机制H.pylori感染及生态失调可导致胃炎,甚至进展成胃癌,该过程的具体机制如下。由于慢性H.pylori感染导致胃酸分泌减少,非H.pylori微生物群过生长,通过促进炎症、刺激细胞增殖、改变干细胞动力学和将硝酸盐转化为N-亚硝胺等多种机制促进胃黏膜的恶变[53]。在胃癌中,微生物群促进(亚)硝酸还原[42]:酸化的亚硝酸盐能够杀死其他细菌[54];硝酸盐可以作为能量来源并改变肠道微生物群,造成生态紊乱[55];亚硝酸盐还原产生一氧化氮,参与保护黏膜完整性[56];(亚)硝酸盐代谢中形成的N-亚硝基化合物是重要的致癌物[57]。大肠杆菌、乳酸杆菌和硝基螺旋杆菌在胃癌中分布丰富,并在(亚)硝酸盐代谢中起作用[55,58]。其他细菌如梭菌、嗜血杆菌、葡萄球菌及奈瑟菌也可能参与上述化合物的形成[59]。尽管在胃癌微生物组中检测到产硝酸盐的菌群,但其存在是否决定了肿瘤的发生及其与H.pylori定植的相关性仍需更多的研究来解释。
目前对胃内疾病相关的菌群研究仅停留在生物标志物层面。H.pylori与胃肠微生态的相互影响仍存在争议,且菌群在具体疾病中的作用机制、与疾病的因果关系尚不明确。根据不同的生态失调类型判断不同的胃癌亚型并制定个性化益生菌辅助治疗方案;进一步分析口腔及粪便中的菌群失衡并将其作为非侵入性诊断标志物;通过干预菌群防治胃炎癌并研究其在营养、免疫、代谢、信号通路等方面的具体机制及H.pylori与其他胃肠微生物在胃内疾病中的相互作用机制都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