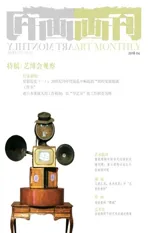当代艺术在商业语境下有多少自由?
2018-11-28马钦忠MaQinzhong
马钦忠(Ma Qinzhong)
一、从伦勃朗的艺术商业谈起
谋生的问题不解决,永远没有艺术的真正自由。这个问题在伦勃朗之前的艺术家从来都不会想,道理很简单,除了王公贵族、教会定制绘画和雇用画家,没有别的生存方式。但在伦勃朗的时代的荷兰有了这个基础。据阿尔珀斯研究,由于荷兰土地面积少,连屠夫和面包师都会买10个荷兰盾以下的绘画作品。可见当时荷兰人收藏和投资艺术之风的流行程度。一方面,伦勃朗坚持不走雇用和为王公贵族们按传统方式服务的老路,另一方面对各种对象的商业定制又坚持艺术原则。这注定了他一定难以完满收场。鲁本斯的做法是把个人作品和商业画区分开,而伦勃朗讨厌这样做。“正是伦勃朗,而不是鲁本斯,发明了我们文化中最具特色的艺术产品:一种通过非工厂化生产将自己的与其他产品区别开来的商品,通过限制其产量来创造市场,这种商品能够体现独特的个人气质以及高昂的市场价格,因此,将它与(资本主义的)创业型企业(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的基本要素捆绑在了一起。”[1]
这个说法针对当代艺术市场有效,而对伦勃朗的时代是灾难。相应地鲁本斯把商品和艺术两分比较靠谱,至少不会像伦勃朗导致官司缠身、债台高筑,贫困而终。
齐美尔在他的《货币哲学》中说,17世纪的画家,如伦勃朗,能够在完美的共生关系中协调形式与灵魂、静止与运动、图像空间和叙述时间的人类自我及自身绘制肖像中,给“存在”打下了生成的烙印,也给生命留下了“存在”的印迹。这对我们的时代来说不再可能。
这个说法是指伦勃朗的作品没有商品画的应酬、世俗气,件件都是他的永远不可重复的“存在”的印迹。但他在协调与社会及经济关系上并不成功。伦勃朗生活的那个城市即“见证了日益复杂的建立在商业和消费基础之上的金钱生活模式”,即从伦勃朗的“生命”中抽走了“他依靠艺术市场生存的基础,展现了齐美尔把这种困境所命名为的文化的悲剧”。
我用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艺术与自由,艺术家的艺术作品的自由品质和艺术市场、艺术媒介、艺术机构关于艺术的利益诉求从来就是矛盾重重,对立、纠结、自由和审美以及种种“崇高”及对艺术的赤子情怀总是由谎言和牟利相伴。
拥有艺术史上最卓越的眼睛和手感的伦勃朗因为自己的艺术自由而在艺术市场上败下阵来。
假如伦勃朗作伪一下如何?或者如鲁本斯,商业是商业的利益,创作是创作的理想和自由,或者言不由衷地说两者都获得自由?
今天的艺术家和艺术市场,我们听到的主要是这样的虚假的声音。
二、艺术经济的神圣化的目标
康德说:“一个世界存在的最后目的,那就是创造本身。”“最后的目的是没有条件的。”“在我们假定世界的东西,在其真正的存在看来都是有所依靠的,而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就需要一个按照目的而行动的最后目的,这个时候,人就是创造的最后目的。”[2]
这是康德对作为人保留下的最后的底线。在现实生活中,它是不存在的。人要生存、要交往、要在烦扰的生命行程中走到终点;与之相伴随的是七情六欲。到了20世纪中后期,各种欲望及身体与快乐的理论合法地变成了康德的“人就是创造的最后目的”,如福柯。
但是,这样的话语依然畅销:艺术家的创造目的是自由,艺术作品是自由的表征;因此,是一个康德问题的艺术定性。即使是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冲动也正是艺术自由的“救赎”而焕发肉身的光辉。
这是纯粹理论意义上的。艺术界关于艺术自由精神的推广和营销也正是把这种纯粹理论意义的自由偷换成了现实物品;就是说,表达的是纯粹自由,盯住的是经济利益。
这源于两个根本问题:
首先,艺术家是一个职业和一种谋生方式。作为职业和所有行当都一样,充满计划、筹谋、欺骗、自私、机会主义、丑陋心态,当然也有真实、冲动、梦想、未来、救世、抗争、追求真理;要把这二者截然分开是困难的,艺术家靠他的制品生活,要让各种买者和权势者支持、喜欢,当然会有讨好、媚俗、献媚、违心等目的在。说得再高尚也抵挡不住饿肚子的恐惧。既然是一种职业,那就一定要有技术门槛,这儿有高技术门槛和低技术门槛。
其次,构成艺术这一“圈子”的三个关键问题:之一利益驱动的核心动力,之二投资者审美的关键是利润收益及趣味偏好,之三占据符号专属化和品牌化,诸如签名、专名、定制,目的在于包装成为符号和象征的文化价值的专享。迪基、丹托的体制论、惯例论等恰好是这种商业共谋的合理性证明;因为这个“自我认证”系统是资本力量完全可以生产出来的,以实现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指出的把这种商业利益最大化的神圣性的企图。
这样,从艺术家生存、渴望成功与艺术圈的利益驱动合成一股共同努力的走势:把没有任何内在品质意义的艺术品打造成为惊世骇俗的伟大的文化成就。
布迪厄非常精准但也毫不留情地指出:艺术品商人“在艺术家和市场之间建立了保护性的屏障”,但同时也“由于他们的存在本身,残酷地揭穿了艺术活动的真相”。这种“真相”是:艺术家是“高度自利的,精于算计,醉心于金钱,为了成功不择手段”。艺术品商人的真实活动则更令人不快:他们对审美的兴趣完全是受“他们对一件艺术品是否能带来利润的投资眼光”所引导(Bourdieu,1993,p.79)。这些断言将布迪厄引向了“一元论”的分析范式:他暗示对经济利益的拒斥不过是掩盖某种类型利益的文化外衣。正如米歇尔·拉蒙(Michele Lamont)在她关于美国和法国中上层阶级的著作《金钱、道德与教养》(Money,Morals,and Manners)中所说的那样,布迪厄与理性选择理论家一样,“将社会行动者定义为社会经济效用最大化者,行动者参与到经济交易的世界中,通过行动最大化他们的物质与符号收益。”(Lamont,1992,p.185)[3]。
谜底揭开了:这种符号制造过程神圣化正是为了掩盖背后的经济最大化的目的。
不明觉厉的批评家见到20世纪后期的疯狂的艺术市场,一个个悲天悯人:
“资本主义已经全面接管了当代艺术,将它量化和贬损为一件件商品。我们的艺术界在商品买卖的大潮中随波逐流,在资本积累的迷狂中失魂落魄。”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论述战后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及其所导致的艺术品难以置信的天价时说:艺术市场对于文化的伤害,就像露天采矿对于自然界的伤害一样。”(Hughes,1990,p.20)还有的把追捧天价艺术品的行为说成是把艺术品变成了一种恋物癖或拜物教,一个“被崇拜、被追寻和被占有的神祇”(Wood,1996,p.263)。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彼得·比格尔(Peter Burger)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艺术品观众对艺术性的、批判性的、解放性的价值无动于衷,而只会对外在于作品的因素,如艺术家的签名或名声抱有关注。不仅如此,艺术品收藏家的收藏动机被发现越来越接近投机,而关注当代艺术的主要目的即是“符号价值”的市场因素。这个艺术品市场的逻辑跟20世纪后期零售市场中出现的品牌的逻辑几乎如出一辙[4]。
这些批评家太崇信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无目的的目的性”的纯粹审美信条了,而且对艺术市场的偷换概念丝毫没有察觉。殊不知,这恰好成了掩盖炒作天价艺术品的动机和企图。之所以能创造这种“经济学的例外”,即把毫无使用价值、甚至也没有观赏价值的物品符号炒成天价,使用的策略恰好是“符号的神圣化”的工具。
经济学家马歇尔说,对艺术品的价格系统解释是不存在的。亚当·斯密说,无法对绘画的生产成本和销售进行合理解释。大卫·李嘉图认为,对稀有的雕像和绘画的价格是劳动价值论的例外。但是,有一个定义非常适合艺术品,即边际效益。这正是画廊、策展人、艺术品商人、金融家大显身手的好地方,以垄断和专属性的某个艺术家的作品,制造出最为公共化的标识和符号,并打造成为最为成功者的财富标配和智慧象征,从而形成最不对称的边际效益。这便是天价的由来。而有钱人的疯狂竞价和快乐地占为己有的心理支撑便是这一符号独享。“经济学的例外”的奇迹出现了!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的“金钱的品位准则”便是这一购买行为的消费经济学的说明。
那么,在这儿,我们还能看到多少“自由”的价值和意义呢?
三、“艺术自由符号”的商业制造
这是一个看似难以结合到一起的悖论:艺术品是针对特定商家和购买者生产的;同时声称这一产品非一般商品,而是充满了自由意义和创新的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这里,我们有必要重复在第一节引用的阿尔珀斯关于伦勃朗的文化产业的说法:“正是伦勃朗而不是鲁本斯,发明了我们文化中最具特色的艺术产品:一种通过非工厂化生产将自己的与其他产品区别开来的商品,通过限制其产量来创造市场。这种商品能够体现独特的个人气质以及高昂的市场价格,因此,将它与(资本主义的)创业型企业(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的基本要素捆绑在了一起。”
这一专事制造“艺术自由符号”的“创业型企业”(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这个词组还可译为“中间商”,且主要是指商业活动的机构),在20世纪中后期才真正形成国际化规模。休斯、阿多诺、比格尔等学者对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艺术界活动的产业化形态基本上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的批评语境还是单纯的艺术活动、在画廊卖画,并通过批评阐释形成社会影响力。真正精准概括这一文化产业的是比他们晚许久的布迪厄和波德里亚等人。
怎样制造“艺术自由符号”呢?
当然,不是随便什么符号抛出来即可被接受,也不是撒网式的社会征集,而是通过伦勃朗首创的“创业型企业”即艺术机构或画廊;根本上不同于伦勃朗的是,这个企业内基本上不会是艺术家,更不可能是像伦勃朗那样的卓越的艺术家。制造者和销售者必须分开,前店后坊卖不出大价钱。
第一方面,挑选自由符号生产者。这是一个自由的天空,对艺术家和画廊都是海阔天空。但一旦认定某人某种符号形式以及各种挖掘出来的自由的精神价值,便进入了完全与自由无任何关系的社会——商业——利润的既定航程。
马西娅·比斯特林(Marcia Bystry,1978)曾经指出当代纽约绘画界中的画廊分工。第一种画廊资助大量的相对无名的艺术家,他们第一次有被严肃的批评家和收藏家观看的机会。第二种画廊从这路人中精挑细选,将那些已经获得一些奖励,作品在批评界名声很好并被一些重要收藏家购买的画家收入囊中。商人以及他们对用于展览和出售的稳定的作品供应的需要形成对艺术家的一些重要的限制,经常建议艺术家下一步应该创作的作品类型,制作足够数量的作品,以维持画廊和艺术家的生涯。由于这两种画廊的共同努力,他们制造了一批稳定的艺术家,并愿意去冒险花费他们的时间、精力和名声来制作艺术品。结果可能会反响强烈,获得成功,也可能湮没无闻;他们发展了一群足以支持艺术家工作的观众:他们还制造出名声,认可在艺术界荣誉系统中的地位[5]。
同时,对于如何在一级市场(直接销售)和二级市场(拍卖行拍卖等)制订价格策略也设计出相应的保护机制,原则是平衡投资者的获利配置。
“通过分析两个分立的圈子(先锋画廊圈和拍卖圈)的价格机制,我努力解释了价格离散特征。两个圈子的价格水平差异不仅是量上的,更是质上的。画廊老板对他们自己的画廊价格作了不同于拍卖价格的解释,并且赋予这种价格以更多的道德内涵,此种内涵产生于画廊关怀、保护艺术家的角色。与此相反,拍卖价格是一种牟利者的价格,牟利者汲汲于从艺术品买卖中快速获利。画廊认为艺术家需要在这种‘不真实’的拍卖价格中受到‘保护’。它们在作品供不应求的时候并不利用价格机制将作品出售给出价最高者,而是用等候名单的机制分配作品,使得画廊老板能够决定谁能得到作品,并使自己能控制艺术家全部作品的长期价格发展趋势。由此价格差异,画廊老板为收藏家创造了套利的机会,这个问题是通过在画廊圈子和拍卖圈子之间竖立界限来解决的:画廊老板通过君子协定避免买家套利行为的发生,甚至他们会通过法律的约束给予自己在收藏家希望再次出售作品时的优先取舍权。”[6]
这个严密的过程,每一次运行都是一次利益再分配的配置实现,而随着价格表的“神奇的”跃升,“艺术自由符号”便成了等同于巨额财富的同义语,被表征为一个时代的可识别的象征。
在这里,艺术自由被兑换为多少数额的金钱。
第二方面,数据制造与艺术批评。
决定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和影响力,出版、批评、收藏起到了重要作用。怎样进行这项工作?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公关和销售的同步化行动。
这位作者这样写道:尤其是在我所谓的“对立论”思想流派中,我发现了一种常见的主题,它将价格作为一方,将质量或价值作为另一方,将两者截然二分:它假设价格是通过非人格化的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力量形成的,并没有考虑艺术品的质量或价值。保守派艺术评论家希尔顿·克莱默注意到在20世纪80年代,“艺术作品极高的价格……与作品质量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此后情况更甚,连普通的价格也很少能反映作品质量了”(引自 Grampp,1989,p.27)。伦敦泰特画廊(Tate Gallery)前艺术指导艾伦·玻尼斯(Alan Bowness)也以相似的逻辑认为,经济上的成功“与作品的质量毫无关系”(Bowness,1990,p.59)。
“过去的实证研究已经支持了艺术品的经济价值和艺术价值一致而非相反的观点,以及优秀艺术家富裕而非贫困的事实。经济学家经常查阅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艺术指南》(Kunstkompass),由已故德国新闻工作者威利·本加德( Willi Bongard)编辑。从20世纪70年代以降,本加德收集了国际市场上顶级艺术家的数据。他记录了100位以上的世界知名艺术家的价格数据,包括艺术家在期刊上被提及了多少次,有多少作品被公立的博物馆收藏,举办了多少次集体展览或个人展览。”例如,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购买一件作品等于增加了一位艺术家300个单位的艺术声望,而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收藏只增加200点的声望。
所以,20世纪后期一大批非常成功的艺术家如达米·赫斯特的卓越炒作、马修·巴尼对Hugo Boss的献媚、杰夫·昆斯的商业运营手段和私生活表演,都是在进行着媒介关注度和新闻点击制造数据;而且令人万分惊奇的,无有不成功的,逢史必书,逢论必说;而艺术批评在这儿成了杜撰“重大意义”的引发争议的陷阱,造成越有争议、越有点击率、越有市物追捧的“污名化”效应。这儿,艺术自由换算成了多少新闻焦点[7]。
第三方面,富人趣味与体制承认。
艺术界的体制承认的最高地位是国际上著名的博物馆做个展和收藏。收藏的核心原则正如鲍瑞伊斯所说的“差异导入”的“过去-未来”的唯一性之物品;因为这种物品被假定为是走向未来的“见证者”,所谓生命的“光晕”。这种差异之所以是新的,理由在于它在已存在的视觉差异之物中从未呈现,从而为参观者打开一个世界无限的视角,由对事物视觉形式的关注而转向对隐藏在这些事物背后物的关注以及支撑它们的生命预期。于是过去和现在——通过此物即背后之“生命预期”——呈现作为创新的唯一可能场所[8]。
如沃霍尔所说:“最近有些公司有兴趣买我的‘光晕’,他在《安迪·沃霍尔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Andy Warhol,1975)一书中写道,他们不想要我的产品。他们一直说,我们想要你的‘光晕’。我从来搞不明白他们到底要什么。”
很明显沃霍尔在这里太谦虚了,他很明白那是什么。但是要一直等到昆斯,这种从产品到光晕的转变才成了其毕生之作的主题,甚至一项事业的运作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这类从股票经纪人变成的艺术家,让炒作(hype)成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光晕”的替代品。
如果说昆斯是以完美物品来展现商品拜物教,斯坦巴克则是以差异化的符号来展现它。在对于形式与颜色的一种聪明的并置当中所制造的物品恰恰是“相关而不相同的”。作为商品是相关的,作为符号是不同的。斯坦巴克非常明白这一点在所谓博物馆体制中的学术意义,制造出了非常精微的符号微积分:“他给我们的这些细小的片段都属于一个巨大的难题:一个建立在公平原则之上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不再铲除差异,而是在一种符号交换的微积分中给差异重新编码,充分地开拓和发挥差异。”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几何绘画的运用可谓为这种制造“差异”的典范:“这些不是绘画。它们是绘画的范式。”是一种关于绘画的分析性元语言(analytical metalanguage) 的用词,但其结果反而是一种关于绘画的后历史的惯例主义,一种对于那些堵塞了绘画实践的历史性的种种能指的拜物教。尤其是这种对于那些能指的拜物教,将该艺术交付给了我们的商品符号的政治经济,让它成了对政治经济的一种摘要,而非一种批判。也就是说,这儿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谎言编造的艺术叙事并且售价不菲,结果还是有人拿大把美金捧场,并且说:这是艺术史的“商品”的“光晕”,而由杰夫·昆斯或某某注册成为专名。而在这样的种种“倒转”所促成的艺术世界里,谁是真正的弄潮儿?答案是:“在那里,自然而然地,一位艺术商人能现身为一位解构大师,一位证券经纪人能推定杜尚已经成为历史,而一位投资银行家能将体制批评引为在他们的成长中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9]
这里说出了最关键的人物:商人、经纪人、银行家。他们是如何控制这所谓的“过去-未来”的唯一的创新的时代见证物的体制认证的?
博物馆的最终控制权掌握在理事手中,他们提供了博物馆运作所需的大量资金。在允许财富和财产个人积累的政治系统中,甚至公共博物馆的理事都经常代表着最富的阶层,因为那些富豪可以用赠予金钱和艺术品的方式帮助博物馆,他们这么做,经常是为了换得支配的地位。维拉·佐伯格( Vera Zolberg,1974)在她对芝加哥艺术学院发展的分析中表明,富有的赞助人最初会对博物馆事务施加直接的控制,插手购买、展览以及其他艺术性事务。后来,他们将控制权交到在学术上训练有素的艺术史家手中,他们对于什么是“真正”有价值和重要的,要比业余鉴赏家更有见识。但这种转换并不意味着艺术家就和博物馆之间其乐融融了。就像商人一样,博物馆馆长和他们为之工作的理事的利益可能与那些艺术家的利益分道扬镳;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可能认为自己的行动符合理事的利益,即便理事并没有这种利益。因此,很多博物馆都明显抗拒展出毫不掩饰的当代政治性艺术(尤其是在越战和20世纪60年代的相关事件时期),在那个时期,艺术家变得越来越公开地政治化。汉斯·哈克追踪和展示了纽约东部贫民区中贫民窟财产的所有权的一项研究,博物馆领导坚持认为这是“政治性的”而加以拒绝之例可为明证。这引发了很多当代艺术家对牵涉其中的博物馆馆长的猛烈抨击[10]。
于是,一个见怪不怪且奇妙的现象显现出艺术市场的操纵者和博物馆的赞助商、理事们的高度趋同性:其一,在艺术市场和收藏领域,是同一批弄潮儿;其二,市场的热销品和博物馆购进的某某A或某某B的作品高度地步调一致;其三,风格、流行指数、追捧人物和趣味,市场的风行和博物馆的个展的密度此起彼伏。也就是说,富人趣味和体制认同,是高度一致的。是市场影响了体制认同,还是体制认同塑造了富人趣味?
因此,我们这样说是不会错的:在此,艺术自由转变为博物馆和富人的趣味指数。
四、虚构“艺术自由”
在艺术市场和艺术体制的当代语境中,“艺术自由”表现出严重的杜撰和伪装。我这样说不是否定艺术创造自由的意义与价值。对此,我是毫不怀疑的。
马尔库塞、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它是来源于艺术家的感性的非压抑的本源。由于这种基础,使得艺术成为一种非现实中的产物,从而具有了对社会的批判作用。这是当代艺术作为“艺术自由”产生社会价值的基本讽喻模型的定性。但同时,它存在被偏转向其他方向的隐患。对此,卡罗尔隐讳地写道:“如果讽喻性说明被假设使审美经验扮演一个暗示非工具性、非市场合理性的可能性的角色,那么,既然它所规定的审美经验的特征(无利害和想象力的自由活动的概念)似乎很有争议,这个隐喻就是不确切的。但是即使这个隐喻更有说服力,它是否真正具有理论上的知识性问题还是会存在,因为其他的、非聚合的隐喻——替换性的讽喻——似乎同样可信。”[11]
是的,正是这个“非聚合的隐喻——替换性的讽喻”造成了虚构艺术自由的潜在威胁性。
怎样进行这种替换的呢?
这是“物欲”走向“物恋”即对这种物之恋,“它是一种伪造物、一种人工制品,一种为了展现某种外观和凸显某种符号的劳作”。而现代艺术就是专门制造这些“物恋”的行当。“现代绘画、波普艺术、技术派(racists)等等都没有与什么发生冲突:它完成的是在空间中如同句法构造——这些物从一个符号转向另一个符号,从一个时刻转向另一个时刻。”“它与现实世界一起操控着,并被纳入到同一个游戏。它能够拙劣地模仿这个世界,展现这个世界,伪造这个世界;但它从未触及它的固有程序,因为那个秩序也是它自身。”[12]
这就是讽喻模型的替换,看起来还是自律的、非工具性的,但已经远离它的价值设定了。即是说,鲍德里亚在此给出的这种替代逻辑是:物欲——物恋——人工制品——符号之符号,是自由的、是讽喻性的,但是是没有任何批判性和颠覆性的。在此,“真正的问题、真正的矛盾只是在形式的层面上,即符号交换价值的问题和矛盾。而这正是符号的运作过程试图掩盖的东西。这就是设计的意识形态功能:运用功能性美学的概念,它打着普遍价值的幌子,提出了一种新组合的模式,一种在形式上超越专业化(在物的层面上的劳动分工)的模式”[13]。更进一步,它们以普遍性、元语言的形式陈述着艺术自由,而在根本上是掩盖“物欲”的获取利润的意识形态。于是,比格尔不禁感叹:“新先锋派将作为艺术的先锋很体制化了,从而否定了真正的先锋主义的意图。”[14]人文精神的坚守和对社会强行介入的实质性的自由精神的追求,成为了一场虚拟的假想的“自由的”演出。
在艺术市场和当代艺术体制中,把这种自由的脆弱性揭示得最彻底的是汉斯·哈克(Hans Haacke,1976,1978)等极少数艺术家。那些在艺术市场和艺术体制中翻云覆雨的赞助人满脑子想些什么?艺术自由的意义在他们这儿换算成了什么?汉斯·哈克从一些重要官员对于艺术和商业之间关系的论述中搜集到他们的表述:“我对艺术的欣赏和享受是审美的,而非智性的。我并不真正关心艺术家的本意;它并不是一种智性的思考——它是我的感受。——纳尔逊·洛克菲勒。”“在商业界,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人们越发承认,艺术并非一件无关痛痒的事,它们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包括商业——它们事实上是商业不可或缺的。——弗兰克·斯坦顿。”
“埃克森公司之所以支持艺术,是将它作为一种社会润滑剂。如果商业要在大城市里延续下去,它需要一种润滑的环境。——罗伯特·金斯利(埃克森公司,公共关系部)”(引自哈克,1976,116、117和120)。哈克对一家纽约先锋画廊进行了调查,67%的人认为利润导向的商业与公共利益并不相容。“当代艺术的公众认为,他们最感兴趣的作品基本被如下人掌控着:他们对艺术事业的观点与公众背道而驰。”[15]
我们能相信,被这样的群体操纵所表达出的一个又一个“自由艺术”是真实的?
当然,我坚信:当代艺术对人类的自由精神的拓展的伟大意义和卓越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同时,我也坚信,这些贡献了自由精神的艺术作品的背后一定隐藏着各种各样的动机。
舒斯特曼认为,艺术的自由根源于人的先天本性之中。他以威廉·詹姆斯的生存经历和哲学心理学的思想的关系,把他的生命过程看成是一个艺术化的意图性的完美诠释。威廉·詹姆斯从年轻时就多病、失眠,心脏和颈勃病严重,长期处于非常痛苦的状态。他年轻时选择医学,渴望得到医治;但结果证明医学对他的任何一种疾病都无能为力。他从此鄙视医学。长期的失眠让他体验到了他的意识的持续绵延不断,于是他提出了对历史影响深远的“意识流”的概念,而身体会随着“对兴趣点的感知而变化,而我们在这类同样的变化发生时所体会到的感觉就是情感”。身体、意识、自由这样三个概念与詹姆斯的一生病症的痛苦相伴,就是“艺术地生存着的典型案例”:“詹姆斯根据‘自由意志’郑重地作出了第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坚信‘自由意志’。这个信念随之激发了他的生命活动。他的巨著《心理学原理》就是这一信念的产物。该书继续强调自由意志的力量;它使我们成为‘生命的主宰’。”(《心理学原理》,第222页)从这个观点来看,艺术的自由就是人原生的、先天拥有的[16]。
巴特认为艺术的自由是纯粹的,原因在于:当语言或者造型形式一旦不服从现实的目的之时,作者的意图对于写作者的相关性就退出了。语句与形式专注于作品的潜在意义便自律性地成为一个纯粹的“中介”、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他说写作是“零度”的。
当然,这是一个有问题的推断。其一,意图和关联能从作品中退出来吗?如果写作的目的就是作者死亡作品自生成,那岂不是谁都可以去写作然后让他自生成?其二,作品的意图预设的规定性不可能从作品中退出,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生成”。“切断”“终止”等等只是从边缘的发问,“断裂”正是作品自身的意图存储的价值显现。“不及物性”的形式主义无法从社会综合语境保证艺术的纯粹乌托邦性质。
关于艺术自由的“文化的悲剧”在这个严密整一的艺术市场为核心的“艺术界”是看来难以避免了!
瓦蒂莫把这说成是“虚构化的实在经验”,一种完成的虚无主义,就像海德格尔的深渊(Ab—grind),召唤我们走向一种虚构化的实在经验,这也就是我们唯一的自由的可能性。因此把艺术作品不当作世界中的某个事物来经验,而是把自身呈现为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新的全球性视角。“纯诗”“纯画”可为此证,即世界之外以见证世界的乌托邦。“艺术作品能够是一真理设置入作品,就是因为它不是某种形而上学的稳定结构,而是一种事件。”这是在“纪念碑、程式和林中空地的微光的词语破碎中发生:‘诗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与那持久的东西……或某座纪念碑一样的东西”。
于是,真理和存在的概念是某种不断解释、重新书写和重新改造的东西,而不是理解为赋予了永恒性和稳定性的客体。真理可被经验,但不能被占有,更无法当成理性和知识传递给他人。所以,艺术的真理一定是短命的,非连续性的瞬间性。历史图像仿佛是一幅虚构的图景,再也不会在“进步行程”和“启蒙辉煌”这样的中心主题支配下写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的“意志行程”的著作。讲述历史和事件的“真理”成了一种精心选择的修饰策略。“微弱思想”是这一写作的基本特征,即一代人的思想景观随着他们的消逝而退场[17]。
于此,我们看到了关于艺术自由的彻底退却:舒斯特曼是杜威的“艺术即经验”的当代版,意志即主宰自我命运即为自由,这是证明“艺术的自由”的先天性;巴特是虚构一个“不及物”形式,切断所有的及物性而达到“零度”,自由因此生成;瓦蒂莫接受一种虚无主义艺术价值观,借助这个“虚构”物回到自身之内呈现为“一种事件”,并经过“瞬间性”占有实现自由;如此等等都把虚构的“艺术自由”放置自我的“生活世界”去当作实现自由来享用。难怪艺术市场会如此繁荣和兴旺,因为艺术品的自由符号成了不断上瘾的毒品。
鲍德里亚说的当代艺术所虚构的“自由”是资本主义操控社会的手段,难道切实实现了?!
注释:
[1][美]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著《伦勃朗的企业——工作室与艺术市场》,冯白帆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43页、149页、152页。
[2][德]康德著《判断力批判》下卷,韦卓民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00页。
[3][荷兰]奥拉夫·维尔苏斯著《艺术品如何定价》,何国卿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4]同[3],第32页。
[5][美]霍华德.S.贝克尔著《艺术界》,卢文超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06页。
[6][荷兰]奥拉夫·维尔苏斯著《艺术品如何定价》,何国卿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122页。
[7]同[6],第148页。
[8]Boris Groys,Art Power,the MIT ,2013,p42.
[9][美]哈尔·福斯特著《实在的回归——世纪末的前卫艺术》,杨娟娟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30页、114-115页、124页。
[10][美]霍华德.S.贝克尔著《艺术界》,卢文超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11][美]卡罗尔著《超越美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2页。
[12][法]让·鲍德里亚著《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13]同[12],第77页,第100页。
[14]比格尔著《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31页。
[15][美]霍华德.S.贝克尔著《艺术界》,卢文超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97-98页。
[16][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著《身体意识和身体美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6页、222页。
[17][意]瓦蒂莫著《现代性的终结》,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82页、127页,16页、6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