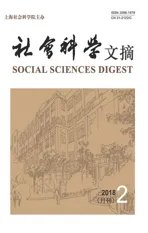传统小说批评的近代转型
2018-11-17
包括古代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事实是,通过不断“损益”更新而得以“因循”发展,其精神血脉与主体格局则自始至终得以保存与延续。然而,这种情形随着晚清以降,大量域外新思想、新观念的不断输入、引进而发生了改变。就中国传统小说来讲,近代小说批评家将域外的新思想、新观念运用到传统小说的批评之中,引发了小说批评观念和思想的巨大变化,促成了具有现代意识的小说批评的出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言的“近代”,大致指维新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之前这一段时间。
从全面否定到重新肯定
在维新变法运动开展之初,梁启超、严复等人对传统小说基本上采取了否定与批判的态度,其直接原因就是他们接触到了欧美、日本的政治小说,并以之为参照来比较与评判传统小说。
其一,从作家身份来看,域外小说家大都是政党领袖、政坛显要、政论大家。令人沮丧的是,我国自古以来就对小说存有偏见,文人才士不屑于染指创作,小说创作大权就旁落到了那些“华士坊贾”“小有才之人”的手中,他们究竟能创作出什么样的小说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二,从小说内容来看,他们认定域外大政治家创作小说是为了教化大众、濬发民智,小说家因而也就成了改造社会、引领未来的头号功臣。而当他们返身察看传统小说时,却极度失望地发现其内容不是“诲盗”,就是“诲淫”,不但一无是处,而且贻害无穷。
其三,从小说社会效果来看,欧美、日本等因小说启蒙而民智大开、国富民强,而中国却在“诲盗诲淫”小说的毒害下,社会日渐窳败,国家日至破落。义和团运动所引发的社会动乱与亡国危机,更为这些忧国忧民的文人抨击传统小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他们言之凿凿地将“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完全归咎于传统小说的祸害。
这些具有策略性的对比论述,催生出了大量将域外小说与传统小说作对立的极端评论:一方面,屡屡将小说在欧美日本的“开化”“变革”中的功效放大,刻意为读者营造出因小说之功而崛起的文明“新世界”;另一方面,传统小说则一再被贴上了落后、腐朽,甚至祸国殃民的标签,完全漠视其价值意义。
其实,外国小说并非没有“诲盗诲淫”之作,而传统小说也并非全是“下三滥”,这本是文学史常识,只是被变革心切的近代文人作了选择性的彰显或遮蔽。不过,随着对域外小说与文学思想了解的逐步加深,近代文人对传统小说的评价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梁启超的友人狄葆贤因东西各国对小说家的推崇,日本人将施耐庵与释迦、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日本学校将《水浒传》《西厢记》列为“讲义”中,也获得了对传统小说的自信心和与有荣焉的自豪感,进而对其大力揄扬。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日本在近代一直是国人效法与追赶的对象,既然他们都如此地褒扬传统小说,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妄自菲薄呢?近代文人一再切入欧美与日本的政治、文学视角,便有诉诸权威的意味,以此来为传统小说的“合法性”背书,洗刷此前强加其上的污名。
有鉴于此,近代文人对梁启超、严复等人此前全盘否定传统小说的偏激做法进行了反拨。他们认为,传统小说经由域外新思想、新观念的阐释,完全可以和“新小说”一样担负起启蒙教化的重任。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批评者是否具备在传统小说中发掘新思想、新价值的眼光与能力,能否将传统小说从“诲盗诲淫”的脉络中剥离出来,将其置入到“新小说”的功能架构之中。
从传统小说中“发掘”新思想、新观念
在许多小说批评家看来,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所要求的“新小说”必须具备的“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等域外新思想、新观念,在传统小说中早就有了,只不过长期以来遭到人们的误解与歪曲罢了。综合来看,近代小说批评家在传统小说中“发掘”出的新思想、新观念大致有以下内容:
与历来正统文人对《水浒传》的“诲盗”指责完全相反,近代小说批评家强调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是“自由”“平等”“独立”“民主”“民权”之类的新思想。许定一对人们将《水浒传》视为犯上作乱的“诲盗”之作大为不满:“有说部书名《水浒》者,人以为萑苻宵小传奇之作,吾以为此即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也。”燕南尚生对施耐庵和《水浒传》高度评价道:“噫!《水浒传》果无取乎?平等、自由,非欧洲方绽之花,世界竞相采取者乎?卢梭、孟德斯鸠、拿破仑、华盛顿、克林威尔、西乡隆盛、黄宗羲、查嗣庭,非海内外之大政治家、思想家乎?而施耐庵者,无师承、无依赖,独能发绝妙政治学于诸贤圣豪杰之先。”黄人则将《水浒传》和近代刚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挂上钩,称其为“所以重人权而抑专制”的杰作。在他看来,一向被视为“诲淫”的爱情小说和《水浒传》之类侠义小说一样,也蕴含着反对独裁政府和专制家庭、提倡自由平等的思想。
近代以来,对尚武精神的提倡是与抵御外辱、追求民族独立、推翻异族统治的宏大目标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近代小说批评家在传统小说中着力“发掘”的一项重要内容。林纾在比较中西小说时就特别提醒世人,西方小说除言情外,喜欢表现探险与尚武题材,我国小说《水浒传》“亦以尚武精神足以振作凡陋”。他认为这类“贼性”是“侠盗气概,吾民苟用以御外辱,则于社会又未尝无益”。被视为“诲盗”的《水浒传》因其具有“尚武”精神而与西方说部为“同调”,从而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在近代,“尚武”精神实际上是和抵御外侮,特别是推翻满清贵族统治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小说批评家往往会别有用心地“曲解”传统小说,以达到宣扬种族革命之目的。这类以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土为职志的小说批评,大抵包含了狭隘的汉民族本位思想。而这类批评能在当时大行其道,显示其背后有一股强大的民意力量的支撑。
近代小说批评家同样擅长在传统小说中“发掘”女权、婚姻自由之类的新思想。浴血生和侠人都充分肯定《镜花缘》“提倡女权,不遗余力”。近代小说批评家主要是在域外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下,通过对传统小说中女性不幸遭遇的揭示,来抨击礼教对女性的束缚与摧残,批判千百年来的婚姻伦理与世俗观念,倡言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他们甚至还将女性平权问题与时代政治风云、与家国命运联系在一起,足见其重要性。
对传统小说所蕴含“科学”内容的发掘,则是出自科学启蒙的急切需要。实际上,在近代小说批评者眼中,我国同样早就不乏“科学小说”了:“中国如《镜花缘》《荡寇志》之备载异闻,《西游记》之暗证医理,亦不可谓非科学小说也。”
可以这样说,近代文人对传统小说中所“蕴含”的域外新思想、新观念,作了面面俱到的发掘与阐释,赋予了传统小说启蒙民智、引领社会进步之功效。这不仅为传统小说批评开示了新的研究指向,也为传统小说与当代社会、政治改革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联,并使传统小说批评因充满经时济世的使命感而获得广泛认同。
这种批评具有功利性、随意性和肤浅性等特征
如众所知的是,近代文人仅是将传统小说作为宣传工具来看待的,他们的小说批评因而具有强烈的功利性与现实性。他们相信读者阅读小说,即会“与其书说中所抱之宗旨,相与而进化者也”。因而,他们不遗余力地在传统小说中发掘改良政治、社会的“新学说”,以期让读者与之俱化。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对小说功利性和现实性的重视,因与重视社会教化功能的传统小说观念一脉相承,故而很自然地为社会所接受。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近代小说批评家对传统小说的解读,通常只是作些简单的类比,也就是用传统小说的某些情节、内容去“印证”一种甚至多种域外新思想观念:“吾尝谓《水浒传》,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金瓶梅》,则极端厌世观之小说也;《红楼梦》,则社会小说也,种族小说也,哀情小说也。”更为夸张的是,一部《水浒传》就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坛出现的所有“新小说”类型与中外圣贤的各种思想学说。就发挥政治、平等、自由、伦理等学术来说,燕南尚生认为施耐庵和孔孟、亚里士多德、卢梭等人没有什么异同。在近代小说批评家看来,施耐庵不这么想,未必就表示读者不能这样读。这也在无形中暗示读者,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诠释作品,“以意逆志”的行为是被允许甚至是值得提倡的。这些小说批评家往往只是告诉读者传统小说中有哪些新思想,而对“为何是”并不在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域外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宗教小说等类别区分的帮助下,近代文人确实“发现”了传统小说中从未被关注的新思想、新内容。这种中西类比式的批评方式虽有替古人在汉服上套上洋装之嫌,但也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熟识感,减少了国人对域外新思想观念的陌生感,带给了读者别样的认知体验。
与随意性相联系的,就是阐释的肤浅性与表面化。虽然不少文人对西学只是略知一二、似懂非懂,但他们都明白西学在当时即意味着进步、文明、时尚,因而不少人乐意在小说批评中显露自己的“新知”。我们从无名氏对《水浒传》中“女权之思想”的分析中就可以窥见其肤浅、牵强之一斑:“男女之最不平等惟中国,而《水浒》之巾帼压倒须眉,女权可谓发达矣。即如潘金莲,必写其为婢女;阎婆惜,必写其为流娼;潘巧云,必写其为醮妇;托根小草,笔墨便不嫌亵。……则中国之女权,发之又早有耐庵。耐庵可比达尔文。”这种批评不可避免地染上粗率、浅薄之类的时髦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作者表达了什么,而在于读者是否别具慧眼地“发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可以说,小说批评家政治情结愈强烈,其思考判断可能就愈简单。但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看,为了“诠释”出传统小说中的新内容,即使歪曲了作者原意,也并非是不能容忍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确实做到了将新的思想观念“镶嵌”到了传统小说之中,将批评者的政治理想、时局愿望等都“寄寓”进去了。我们一方面固然感佩批评者强烈的使命感,一方面却也觉得荒谬可笑。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这种感觉正反衬出这些传统小说的批评者们为了开启民智而殚精竭虑、苦心思索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推动了传统小说批评的近代转型
近代小说批评家在传统小说中“发掘”新思想、新观念,一方面与甲午战败以后全面学习西方、整个社会弥漫着的求新求变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外来强势文化的侵入势必使国人产生种种疑虑、焦灼乃至抵触情绪,也激发出国人的文化危机意识。近代中国是在“新民”“富强”、救亡图存等功利目的之下来宣传、接受西方思想观念的,在国人的意识深处,则始终相信虽然船坚炮利、法律政治之类不如外人,但我们的文学却可以引以为豪。当然,近代文人运用域外的新思想观念来阐释传统小说,自然也和传统小说本身或多或少、或显或晦地蕴含这些新思想观念有关。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当时域外小说翻译的总体水平还不是很高,时常给人以外国小说不如传统小说的感觉。其主要原因在于“非西籍之尽不善也,其性质不合于吾国人也”。这里的“不合”,一者是思想内容不大切合中国的实际需要,所传达的内容和情感始终与国人隔了一层,再者就是不合读者长期浸淫传统小说而养成的欣赏口味与阅读习惯。因此,域外小说虽然被抬得很高,但大众的阅读兴趣仍逗留在传统小说之上。更有甚者,如周作人所指出的那样:翻译域外小说,“原希望可以纠正若干旧来的谬想,岂知反被旧思想同化了去。所以译了《迦茵小传》,当泰西《非烟传》《红楼梦》看;译了《鬼山狼侠传》,当泰西《虬髯客传》《七侠五义》看”。外国小说又不自觉地被传统的接受习惯与阅读心理“同化”了。因而,在传统小说中“发掘”域外“新思想”,既切合读者的阅读口味,也可以让他们从中获得新知,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无论是对小说批评家还是读者来说,都是轻车熟路,更何况还能带来“发现”的乐趣呢。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带有穿凿比附的成分,但它带给传统小说以新的生命,并产生足够的威势以扫除人们对传统小说的鄙视,使人们的阅读心态也随之发生变化。传统小说被置入启蒙救国的语境之中,原本带有的“诲淫诲盗”烙印被换上了域外新思想、新观念的标签。大量前所未闻的域外新思想、新观念的词汇,高密度地充斥其中,其中正蕴藏着国民改造、新民论述等救国救亡的目的论。词语变化的背后是时代、思想的变化。当某一词语使得各种思想者都不得不使用,就意味着其所表示的观念在这一时代已成为时尚,拥有了某种“话语权力”。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提倡“人的文学”,确实受到近代小说家宣传的影响。就此而言,近代的传统小说批评和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动向息息相关。
结语
清末小说家、文学史家黄人曾指出:“中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灌输脑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近代小说批评家不再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思想资源来改造、消解外来文化观念,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别求新声于异域,运用具有“异质”色彩的新思想观念来解读、阐释传统小说,使各种固有的与外来的思想观念在不断的碰撞、渗透与交融中,得以衍生转化为“新种”,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传统小说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当然,在“以西释中”的大背景之下,传统小说的思想内容在某种意义上也以“潜在”的方式限制甚至左右着研究者的视域。其一,在受到域外文化侵袭不断加强的趋势中,近代小说批评家苦闷、焦虑、希望等情感姿态和复杂心理,必然影响着他们对传统小说解读与阐释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其二,近代小说批评家对传统小说的揄扬,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其中所表现的旧伦理、旧道德、旧制度的拥护,事实上正好相反,他们宣扬的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民族独立之类的现代观念,其目的正在于批判专制统治的残暴、颟顸与腐朽,有的批评者甚至“明目张胆”地号召人们去推翻满清贵族统治;其三,由于近代小说理论家对域外新思想、新观念的掌握还比较肤浅,对域外小说也远非谈得上熟悉,他们对传统小说的研究与批评甚至还缺乏真正的学术兴趣,再加上他们对外来文化或多或少的戒备心理,因而,在“以西释中”的传统小说批评过程中,手法还比较粗糙、笨拙,他们对传统小说价值的发掘与释义,有不少地方失之牵强甚至荒谬,带上了新旧交替、中西杂糅等过渡时期的特点。但无论如何,传统小说批评在此后,便逐渐脱离传统架构,进入到了“现代”的通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