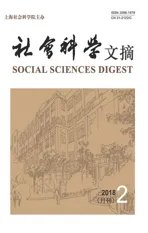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语境
2018-11-17
国际传播研究始于电子媒介的产生与发展。罗伯特·福特纳认为国际传播具有六个特点,即目的性、频道、传输技术、内容形式、文化影响和政治本质。作为传播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国际传播包罗甚广,以致福特纳只从字面意义上将其界定为发生在国家边界之间的传播。对于国际传播研究,托马斯·麦克菲尔定义为对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传播与媒介模式及其效果的文化、经济、政治、社会与技术分析。他认为讨论国际传播议题,要将国际传播环境、全球政治经济与当代传播科技三者结合起来考虑。
具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组相互关联的事件或趋势,深刻改变了国际传播领域的面貌。一是冷战结束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各种变化;二是经济全球化及国家之前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其影响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冷战结束以后,发达国家的媒体对国际新闻关注度显著降低,但“9·11”事件使得恐怖主义成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敌人,涉及阿拉伯世界的国际新闻,迅速跃到重要媒体的显著位置;第二,经济全球化促进区域媒介市场快速成长,特别是半岛电视台的跨国传播能力,令国际传媒界刮目相看;第三,基于互联网的全球性媒体,虽不依赖于特定的民族国家,但语言和监管方式等带有民族国家的特性,这种混杂性表明,即使在文化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分析单位。
现实关切和时代需要始终是学术研究的最大动力,国际传播研究也不例外。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日趋复杂,对国际传播的学术发展影响很大。在国际恐怖主义勃兴、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扩张的背景下,我们尤其要关注“非西方”文化生产中心的崛起、全球公民社会与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传播科技进步与传播研究的国际化等基本问题。事实上,法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知识界,已对“西方是最好的”观点产生质疑;中国、印度、南非、俄罗斯等国家,也在重新评估自己传统文明的价值和意义。欧洲中心论受到广泛挑战,去西方化的风潮席卷全球。
对西方模式提出挑战的主要力量来自东方,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全球权力正向东方转移。2014年11月,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北京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在1400年前曾经引领世界,但在后来的“大分流”中衰落了。他将“大分流”现象比喻为手机应用软件,认为西方社会之所以发达,主要得益于六个应用软件的安装,分别是竞争、产权、科学革命、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它们搭起现代社会的框架,保障着西方经济快速发展。弗格森认为,当今世界处于“大合流”时期,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金砖四国”,将会超越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发达四国”。造成这种“大合流”的部分原因,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下载那些应用软件,而西方发达国家却正在删除某些应用软件。东方经济体的创新能力逐步增强,人们的职业素养逐步提高,消费社会正在由西向东迁移。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以中国、日本、印度、韩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生产中心正在迅速崛起,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仍然是全球文化生产与传播的主导性力量。未来很长一个时期,美国仍将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运行规则的制定。
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全球治理
“非西方”社会崛起与权力东移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家独大,无论是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硬实力,还是文化方面的软实力,都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美国模式才是最好的选择。
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各种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据《国际组织年鉴》统计,2000至2004年,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数量,由9988个增加到11430个。他们活跃于世界各国,建构起超领土或超边界的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各种公民团体开展对话与合作的桥梁纽带。
有些学者将全球公民社会视作一个跨越国家边界的领域,其主要行动者是各种追求价值目标的非政府组织。星野昭吉对全球公民社会的定义是:为人类共同幸福而开展各种活动的舞台,它以实现公民基本人权为宗旨。保罗·韦普纳对全球公民社会的定义稍有差异,认为它是处于国家之下、个人之上、自发组织起来的超越国家边界的领域,不受国家边界限制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科学团体、志愿者协会、跨国公司等,是全球公民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规范意义上讲, 全球公民社会代表着一种可能超越传统国家权力和市场体系局限性的力量, 一种有利于促进全球性民主建设的选择。它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国家与社会关系架构, 推动了理论范式从“以国家为中心”向“以社会为中心”的转移。
1991年苏联解体,国际冷战体系崩溃,全球化运动兴起,是全球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节点。从此以后,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大幅增加,在教育、扶贫、环境保护、社区发展、疫病防治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目前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的规模都比较小,掌握的资源也很有限,每个平均只有10名专职人员,年均资金预算不到100万美元。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完全依靠说服力,不具备其他国际性组织的强制性,因此,在国际交往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
传播技术进步与网络社会形成
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人们能够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并与他人讨论公共话题,从而形成一个全球化的网络社会。克劳斯·布鲁恩·延森认为,数字媒体是一种元技术,既能整合文本、图像和声音,也能再现人际传播中的互动性和多元性,催生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网络化交流方式。媒体融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交流与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因此传播研究的焦点,应当从作为技术的媒介转向作为实践的传播。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全球网络社会的特征,就是对其自身多样性的肯定,网络社会的文化是一种通信协议文化,该协议能从根本上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通信,但不一定要共享价值观。也就是说,这种文化不是由内容组成的,而是由过程组成的,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文化意义网络,各种文化不仅可以共存,而且能在交流的基础上相互改变。
当然,传播技术进步与网络社会的形成,没有彻底改变国际传播权力的格局。不少学者的研究表明,全球数字鸿沟依然存在,网络在线信息仍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中心,从那里流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生产的文化娱乐商品,仍然主导着全球文化消费市场。诚如赵月枝所言,新兴的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不会自动摧毁现有的等级制度并重新分配权力,不会自动促进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的对话。曼纽尔·卡斯特也认为,并非任何地方的人们都已进入全球网络社会,相反大多数人暂时还处于网络社会之外。
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
进入21世纪,国际传播研究与国际社会生态保持一致,呈现出积极互动、有机协调、多元发展的样态,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学者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虽然这一领域仍以西方学者为主,但非西方国家的学者人数正在增加,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际传播研究的多元性和现实性。
国际传播研究交叉性比较强,与其他学科联系密切,因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随着国际传播研究难度日益加大,单一学科知识已经难以应付复杂的传播问题,必须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来优化知识结构,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在此背景下,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机构、不同国家的学者们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并形成一些研究社群。
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新兴的亚洲学派,对西方传播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提出建立亚洲中心主义的传播学,希望以此来终结欧美中心主义的传播学研究范式。随着亚洲国家政治经济地位上升和文化影响力逐步增强,亚洲在国际传播研究中的重要性也凸显出来,引起一些西方传播学者的热情关注。尽管亚洲学派的研究成果质量还有待提升,但毕竟成为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一股有生力量。
结语
总之,冷战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朝着多极化不断深入发展,目前,除了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三大经济中心,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经济后起之秀和中东国家也取得了重大发展,在国际舞台上,这些国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为了在国际政治博弈中谋求更多话语权,各国均十分重视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尤其是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中东,他们凭借强大的财政支持,倾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机构。与此相关联的是,国际传播研究也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种种变动之下,我们应该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例如国际传播牵涉哪些主体(国家、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全球媒体、全球公民),这些主体在哪些层面与哪些场景下互动,在国家之间区域之内全球范围流动的讯息包括哪些,这些讯息生产、流动与消费在什么文化与制度环境下发生,讯息的跨国流动带来哪些理论、实践、政策问题,全球化到底产生何种影响,等等。
在国际恐怖主义勃兴、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扩张的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应该重点关注“非西方”社会崛起与权力东移、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全球治理、传播技术进步与网络社会形成等基本问题,从而回应现实关切和时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