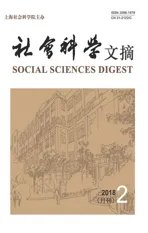家国之间:柏拉图的家邦关系论述
2018-11-17
家国关系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本文基于柏拉图的《法律篇》的解读,并参照《理想国》,试图再现柏拉图关于家邦关系的系统论述。
柏拉图对家庭性质的界定
柏拉图对家庭的性质做了细致界定。首先,血缘作为家庭之本质。家庭神在柏拉图心目中举足轻重,这也反应在他对家庭血脉延续的重视上。《法律篇》中拟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法律明确规定男人必须在30~35岁之间结婚,原因不外乎传宗接代是神赋予人的不可违拗的职责。婚姻的唯一目的是延续血脉,除此之外一无是处。因此,把每个个体的血脉记录在案是必不可少的。遗产继承亦以血脉延续为唯一鹄的。没有继承人的死者,其名字要从家族神龛的牌位上清除。血脉之关联的意义不局限于家庭和个人,还关乎政治。在选择官员时,选举人不仅应该写下其心仪的候选人的名字,而且要加上候选人的父亲、部落以及所属区的名字,同时也要写下自己的名字、父亲名字、所属部落和所属区等信息。在一些特殊职位如男女祭司以及解神谕者(Expounder)的遴选上,必须考察候选人的家庭背景,不仅考察个人的健康和守法情况,而且考察养育他们的家庭的情况,这些家庭的道德标准应该比其他家庭高,他本人、他的父母都应该没有犯杀人和诸如此类有违上苍的污点。
其次,父慈子孝是家庭的基本功能。《法律篇》就子女如何孝敬父母以及处理同父母的关系所做的规定详尽无比,一个人“必须认识到,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生他养他的人”。因此,第一,“他必须首先用他的财产,然后用自己的手和脑来报答他们,惟其如此才能满足老年人在他们那个年纪特有的最为迫切的需求:回报他们倾注在他身上的所有急切的照顾和关注,这是他们在他还是孩童时就给他的长期借贷”;第二,“作为儿子,终其一生必须非常小心地注意自己同父母说话时的语气,表达若粗枝大叶和漫不经心,就应受到严惩。……父母如果发怒了,他必须顺从他们,无论他们是用语言还是行动表达他们的愤怒,他必须原谅他们”;第三,“父母离世后,应该安排最适当的葬礼”,“应该年复一年地以相同的献祭行动来敬拜离世者……把自己收入的适当比例用于祭奠逝者”。
复次,家庭作为抵御犯罪的载体。《法律篇》第九卷着重讨论了各种刑事立法,明确规定在家庭中处于不同位置的成员承担着捍卫家庭权益的不同责任。法律一方面强调家族在保护其成员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把家庭成员相互伤害的处理同剥夺伤害者的家庭生活权利链接起来。法律规定:(1)如果父母在愤怒中杀死了自己的子女,必须接受灵魂净化,并被流放三年,流放结束后不得与配偶重合,也不能再有孩子,不能与被其剥夺了儿子或兄弟的人共餐和共同生活,或参加宗教仪式;杀死自己的兄弟姐妹的处理办法亦如此;(2)夫妻之间若发生蓄意伤害,施害方要被判永久流放的惩罚,儿女成年之前由委托人代为看管孩子和财产,孩子成年后自己占有财产,但对罪犯没有赡养义务,若无儿无女,则由罪犯的亲戚,最多到男女双方的堂表兄弟姐妹的孩子负责召集会议,并同法律看护人协商,在5040户家庭中指定继承人;兄弟姐妹之间的蓄意伤害,则会以死刑来惩罚施害者。
最后,家庭权利与权力分配的血缘亲疏逻辑。谁有资格成为一个家庭的血脉延续者和遗产继承者?柏拉图描绘了一幅以家庭的核心男性(父亲)为中心,血缘关系从亲到疏的差序图。譬如女孩订婚的最终决定权的分配:处在决定权之核心的是新娘的父亲,若新娘没有父亲,决定权则由其祖父操作,若这两位都不在世或失去了家事决定权,则由她的同父兄弟来把握;如果她没有父系方面的这些亲属,决定权就转移到其母亲一方的亲戚,权力传递顺序同父亲一方;如果发生意料之外的不幸,最亲的亲属应该被授权同女孩的监护人一起采取行动。这里所谓的“最亲的亲属”,指的是她的堂表兄弟姐妹。那么,在婚姻决定权上就形成了如下的亲疏顺序:父亲—祖父—同父兄弟—外祖父—同母兄弟。在遗产继承问题上,遗嘱首先面向儿子,且只有未婚的儿子才有继承权;如果只有女儿没有儿子,那么父亲必须在遗嘱中指定一名男子作为女儿的新郎并同时作为他的儿子来继承遗产。如果一个男子死时没来得及订立遗嘱且仅留下女嗣,那么立法者在安排他女儿的婚事时主要考虑两个条件,即近亲和遗产安全。总结起来,遗产继承权的嬗递具有明显的亲疏远近之别:死者的同父兄弟—死者的同母兄弟—死者的兄弟的儿子即死者的侄子—死者的姐妹的儿子即死者的外甥—死者父亲的兄弟即死者的堂叔伯—死者堂叔伯的儿子即堂兄弟—死者父亲的姐妹的儿子即死者的表兄妹。
柏拉图关于家庭的立法一方面把家庭的本质界定为血脉延续之基本载体,另一方面确立与血脉延续相关联的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责任和对违背责任的惩处。正因为家庭的本质是血脉之延续,故相应地确立了先男后女的家庭权力和权利原则,并根据同家庭统治者父亲在血缘上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不同成员的家庭权力和权利,父亲的堂表兄弟姐妹的子女作为家庭边界,一旦超出这个边界,家庭事务的处理权力就被城邦收回。柏拉图的制度设计与古希腊的事实有着重要的出入,譬如:柏拉图突破了宗族和外戚的分割,而根据自然的血缘亲疏把外戚纳入家族继承和家族责任的范畴中,三代以外的宗族关系被排除在这些权利和责任之外;柏拉图虽然支持男尊女卑,但在继承权上并没有完全剥夺女性的权利,而是建立了男先女后的原则。这种制度安排,基本上是贴着基于血缘的自然情感所内在的亲疏远近逻辑建立的,客观上保护了家庭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和独立性。
家庭与城邦彼此依存又相互冲突
虽然柏拉图承认了家庭的合法性,并在立法上努力保持家庭的独立地位和自然功能,但并不意味着家庭具有与城邦同等的地位。恰恰相反,在家邦关系问题上,《法律篇》的着眼点并不是《理想国》的对立物,而是在城邦的普通公民层面接续了《理想国》以及更早完成的《克力同》关于家邦关系的基本判断。
首先,家治与邦治的分离。在《法律篇》的第三卷,柏拉图想象了一个洪水之后的人类生活场景:人数很少;洪水之前的所有生活知识被荡涤得一干二净;初民之间保持自然的爱慕和友爱;食物丰富,穷富尚未分化,战争罕见。在此场景下,政治体系由简到繁渐次形成:孤立的家庭和居所中的家长制统治是最原始的统治模式。第二个阶段,农业发展,围墙耸立,由若干家庭联合而成、以共同农场(homestead)为单位的更大共同体涌现,各个家庭把以前的习惯带入共同体并代代相传,致使共同体内部法律和习惯林立,彼此扞格。因此,共同体必须选择一些代表来审视这些迥异的规则,然后公开地向各头领即“王”建议吸纳哪些规则进入共同体。这些代表即立法者,他们任命这些领导为官员,从而在高度多样的极权体制之外建立贵族制(aristocracy)或王制(kingship)。到第三阶段,各种政治体系及其变种都被允许,并在实际的城邦中平等地呈现其多样性及变迁。
其次,家治与邦治在目的上的扞格。不同家庭结合成更大规模的共同体,意味着城邦的产生,也意味着家邦冲突崭露头角。从一般角度来看,冲突表现为各个家庭独有的权威、习惯、规则之间以及它们同城邦法律之间的各种不相协调;从理想城邦的角度看,冲突则表现为对“由谁统治”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柏拉图承认,就服从和统治这一点而言,家庭和城邦是一致的。他先后列举了八种遴选统治者和服从者的原则,并批评道,这些原则单独看都有其合理性,但若把它们放在一起,冲突就会凸显,因此都不能作为安排城邦中统治和服从的依据。在这一点上,柏拉图同现实的希腊城邦出现了分歧,他提出,遴选“治邦者”的唯一原则是谁是法律的仆人:最高级的官员是为神服务的,必须分配给最好地遵守既定法律且在城邦中在这方面获得成功的人;获得第二等奖励的人被授予服务上帝的第二级位置……由此可见,虽然家庭和城邦都有统治和服从,但是,家长制与理想城邦应有的贤人治邦原则之间必然是冲突的,即便在特定条件下会出现年长者与贤人重合的现象。不能把家治模式照搬到城邦政治的另一个原因是:城邦政治体系的任何极端形式,即要么民主制而极度自由、要么君主制而极度专制都不是真正的政治制度。他在赞扬斯巴达和克里特的政制而否决波斯的政制时说:“你们操作的是真正的政制(constitutions)。我们刚才所说的政制压根儿就名不副实:它们仅仅是操纵城邦的一堆方式而已,所有这些方式的实质就是一些公民受其他公民的支配,像奴隶一样屈辱地活着,城邦仅仅根据每一具体统治阶级而命名。如果你们的新城邦想坚持根据统治者来命名这一原则,那就应该以神来命名,是神真正统治着具有充分理性能力从而乐意接受神之统治的人们。”相形之下,家治模式就是奴隶制。由此可见,家庭虽然构成统治的最原初形态,但与柏拉图所想象的次优的邦治模式背道而驰,惟有走出家治模式,理想的城邦政治才能成长。除统治模式外,家邦之间最根本的分裂表现在目标的对立上。家庭的目标是情欲,城邦的目标是“至善”;家庭的目标是私利,城邦的目标是共同善;家庭是不自足的,城邦是自足的。家庭与个人一样,不只难以超越情欲的控制,而且连必要的情欲都不可能自足,更别说对整全德性的追求了。“城邦”是在家庭显现其不足的地方涌现的,其原初目的是“必要情欲”的自足,但又不局限于此,理想或正义的城邦是“至善”的“自足”,其目标是“让公民们在尽可能最大的相互友爱环境中过最幸福的生活”。这样,家邦之间就在目标上表现为私与公的对立,情欲与德性的对立,不自足与自足的对立,私人利益将置城邦于死地而共同善将整合城邦,因此,只有控制了私人的和家庭的利益,才能不仅保护个人而且保护城邦。
最后,在功能上,家庭作为城邦的工具。基于家邦间的上述差异乃至对立,柏拉图强调,如果“把私人生活排除在其立法的范围外,而期待公民们时刻准备在作为共同体的公共生活中遵纪守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因此,全面规制家庭生活是城邦立法的出发点。
城邦的总体规模被限定在5040户人家。这个规模是次优城邦的基础,不能突破。单就这一点而言,家庭和个人在城邦中的位置就被固定了。为保持城邦总体人户规模恒定,柏拉图发明了后来被福柯称为“人口学”的技术。第一,男子和女子必须在最适合生育的年龄段结婚;第二,性生活的唯一目的和合法性基础是生育,同性恋是非法的;第三,结婚后,“新娘和新郎应下定决心向城邦输送他们能生育的最好和最优秀的孩子”;第四,离婚之后是否结婚以及跟谁结婚必须根据男女双方已育孩子的数量来确定:“如果关系不和的夫妻没有孩子或只有少数几个孩子,生育孩子就应被纳入新家庭组建的目标之中;若已经有足够数量的孩子,那么离婚和再婚的目的应该是促进晚年的同伴关系和相互帮助”;第五,在鳏夫和寡妇是否再婚问题上,一方面应考虑女性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生育和抚养孩子才是本体性的。
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应以城邦的整体目标和运行为对象。第一,男女结为夫妻后,不仅新郎要离开父母择地自居,而且,为防止新婚夫妻过分沉溺于私人生活而忘却城邦责任,并“为应对紧急情况,新婚夫妻应该像婚礼之前那样参加公餐”;第二,孩子不是家庭私产而是城邦公产,因此,对儿童的教育是必要的和强制的;第三,财产虽然表面属于家庭,但最终还是城邦的,城邦保留对家庭财产的最终决定权;第四,薄葬是丧葬的基本原则,死人不得与活人争夺有限的土地和食物资源。
总之,在柏拉图的语境中,家庭只有被放置在城邦背景下,其地位才能确立。在这个对比下,家庭一方面是城邦的原始起点和城邦目标实现的工具,二者有一些共同要求,如反对同性恋,另一方面其诉求同城邦目标又有错位甚至对立,因此,家庭不能独立于城邦而自存,而必须接受城邦的限制和改造,如城邦虽然必须重视家庭血脉延续的要求,但其制度设计必定在有益于城邦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由此可以说,关于家庭的法律实质上是关于城邦的公共法律体系的内在构成部分。这样,家庭和城邦成了一对矛盾体,虽然彼此依存,但又始终处在冲突中,柏拉图的所有努力就是消除家庭对城邦的各种反动,而使之完全成为城邦目标自我实现的工具。
柏拉图为何抬高城邦而贬低家庭?
在家庭和城邦之间,柏拉图为何抬高城邦而贬低家庭?回答这个问题一要考察柏拉图所处的社会背景,二要回到柏拉图关于“人”的讨论以及人的品性与城邦品性的类比中。就现实因素而言,家庭独大与城邦利益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的主要问题。因此,柏拉图贬低家庭的真正动因是家庭在现实中确实构成了威胁城邦团结的最大力量之一。
关于人之讨论,柏拉图认为人可以分为肉体和灵魂两个部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认为肉体是暂时的,一旦死去就不再有意义,灵魂则是永远的。人之成为人,端赖于灵魂而非肉体,灵魂是自我的真正界定者,肉体只是灵魂的工具。只有灵魂习得并葆有了德性,肉体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因素如财富才能保持在合适或者中庸的状态,实现个人在肉体与灵魂、幸福和快乐、善和德性上的统一,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灵魂与肉体之区分,隐喻着公私之分,肉体无法达成公共性,相反,心智虽然看起来是私人的,但其实是公共的。灵魂最基本的部分是理性和情欲,前者通往德性,后者通向邪恶。情欲有必要和不必要两种类型。必要情欲无法躲避,其满足给肉体带来益处;不必要情欲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尤其有损于理性和自我克制精神,惟有通过教育和制度驱除之。在这些分类中,肉体基本上处在被动状态,受灵魂不同部分的支配:必要情欲即是肉体发出的正常物质需求,是理性不可或缺的物理基础,不必要情欲则同理性绝然对立,是德性实现的掣肘和走向邪恶的根源。
人的二分和灵魂的二分同“自然”(nature)的二分直接对应,形成柏拉图语境中的“双重自然(dualnature)”,并进一步表现为家和理想城邦的二分,家庭表征的是肉体和情欲,理想城邦表征的则是必要情欲和理性;个人灵魂的状况表征了家庭和城邦的状况。这些双重自然之间的紧张,直接导致柏拉图把家庭视为城邦的敌人。
当然,柏拉图没有否定肉体的价值,相反,他认为身体不朽是普通人的一项神圣事业。有鉴于此,消除家邦冲突的次优方式是保留家庭,但要对私人生活进行统一管理,既让家庭成为城邦的得力工具,又为城邦的一般法典奠定坚实基础。这样,从友爱的角度看,柏拉图一方面把初级自然的友爱之火种保存在家庭中,让家庭充满温情,另一方面又把这种自然友爱通过德性的提升引入到城邦中,试图使城邦的政治生活在接受理性之沐浴的同时也洋溢着公民之友爱。这一点,对于霍布斯之后的西方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