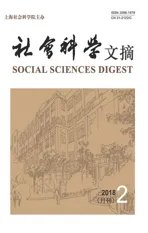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研究
2018-11-17
族性安全是一个族群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自18世纪以来族群对族性安全的追求从未间断,仅在20世纪族裔族群主义运动就经历了三次浪潮。然而直到今天,族性安全的目标仍未完全实现,这突出表现为族群冲突的不断滋生。据联合国统计,2014年武装冲突和暴行造成十多万人死亡,研究预测这些族群的暴力性行为在将来仍会继续普遍存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惨剧的发生?
族群冲突的文献分析
族群冲突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群之间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边界等问题而产生的争端。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为寻求其发生之源,不同学科的学者有诸多的论述与解释。
(一)个人层面的生物政治理论、心理理论、族群接触理论和精英理论
冲突有内外两方面原因,它既源于人们所处的外部环境,也源于个人心理。基于此,学界在个体层面形成了生物政治理论、心理理论、族群接触理论和精英理论等的解释。生物政治理论认为族群冲突取决于族群的生物基因。与生物政治理论观点不同,心理理论认为族群冲突与人们的社会心理相关,尤其是关于族群冲突的集体记忆会成为族群敌对、仇视和冲突的心理根源。此外,族群冲突还来自于人们关于荣誉的分配。与心理理论相比,族群接触理论更加关注现实。族群接触理论通常认为族群接触可增强族群间的了解,消除误会,有利于构建和谐的族群关系。但在一定条件下族群接触会增加族群的冲突,因为文化和语言的不同会扩大对族群同化的张力。族群冲突的精英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族群的精英利用其优势进行族群动员,为自己或族群争取利益;另一方面,族群精英的身份被作为一种族群动员精神和符号工具。
(二)族群层次的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
族群主义是族群层面的主要理论,为族群获得更多权益提供理论依据,有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类别。原生主义认为族群的情感和认同是由诸如血缘、裙带关系等自然因素决定的,具有情绪化、非理性和排外色彩,往往视其他族群为非诚信的、敌对的,乃至仇恨的,因此易引发族群冲突。原生主义者们注重对文化差异和历史仇恨的分析。工具主义认为族群的情感和认同是由政治精英操控的,是一种理性行为,往往成为精英获取政治权益、征收其他族群土地和遣散人口的工具。建构主义认为族群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族群的情感和认同是被建构出来的,认为族群冲突是由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相互冲突的各种认同引起的。
(三)国家层面的国家建构、国家能力和制度主义
族群的冲突有族群间的冲突和族群与国家的冲突之分,在前者中国家充当治理者的角色,后者中的国家是统治者。围绕着国家在族群冲突中的角色分析,产生了国家建构理论、国家能力理论和制度主义理论等。国家建构理论关注国家在多族群的社会中是否客观公正、公平地对待每一个族群,族群冲突往往与国家沦为主体族群统治的工具有关。国家建构理论认为政府的建构方式和类型也会影响族群关系,若沿着族群界线进行建构,易增加族群冲突的概率,因为这种建构方式会让族群间的界线更加突出,造成族群结构的极化。建构手段的专制化也会增加族群冲突的风险。国家政府建构的类型也会影响族群关系。国家是否具备调停族群冲突的能力同样重要,在族群关系中的国家能力主要涉及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和分配发展红利的能力和国家在多元社会中的嵌入式能力。族群的冲突多处于以族群为界线的碎片化社会里,国家能否在这种社会里实现其国家意志,便是其能力的体现。在多族群的社会里,国家希冀通过族群平等、和平的政策,但由于不相容忍的族群造成社会碎片化,致使国家的政策难以实现,族群关系也越加紧张。近些年发生在非洲国家的族群冲突多是因为弱国家的缘故。
(四)国际层面的帝国主义论、国际规则、国际干预和全球化
族群冲突看似多为国内事务,实则倍受国际因素的影响。第一,殖民者们“分而治之”的政策对现在一些国家的族群冲突影响较大。第二,国际规则有时会成为族群冲突的理论依据,如一战后形成的民族自决原则成为民族公投的法宝;人权原则亦是强国干预或诱发其他国家族群冲突的借口。第三,国际社会对军火交易的管控程度也会影响族群冲突。第四,族群冲突的外溢效应会引发其它地区的族群效仿。
通过族群冲突的以上梳理可见,目前学界对于国际秩序对于族群冲突的关注不多,虽然也有学者在“全球化与族群冲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与族群冲突治理”和“族群冲突与国际社会”等方面有所建树,但对于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间关系的研究仍不多见。
从历史上看,国际秩序的变革往往充满暴力,那么这种转型对于族群冲突有无影响、如何影响呢?
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
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的各个国际行为体在一段时间内,依照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位置,按照普遍原则、规范来处理彼此间关系的格局。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主要行为体的实力格局、政治经济结构、管理机制;二是行为体的目标、行为规则、保障机制;三是主要大国的核心观念、利益分配;四是原则、规范、目标、手段、运行机制、整体态势。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大国间的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因为从历史上看,国际秩序几乎总是为大国服务,是特定强权国家间政治游戏的规则。
大国间权力分配的稳定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前提。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决定着国际社会中国家权力增长的差异性,因此国际权势的转移便成为国际秩序变动的起点。在整个国际社会发展史中,人类共经历了古典城邦秩序→帝国秩序→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维也纳秩序→凡尔赛秩序→雅尔塔秩序,其中每一次的转变都与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相关。
从历史上看,国际秩序的每一次变革都与战争相伴,正如权力转移理论学者们所述“‘新来者’挑战‘现有领导者’从而导致‘权力从一群国家向另一群国家的转移’,进而引起国际秩序变革”,权力的转移总是难逃“修昔底德陷阱”。罗伯特·吉尔平也曾指出霸权衰落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场霸权战争的结束是另一次的成长、扩张,并且是最终衰落周期的开端。不平衡发展规律继续重新分配权力,从而破坏上一次霸权争斗建立起来的现状。不平衡代替平衡,世界走向一轮新的霸权冲突。不过随着“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和“科技创新制胜”机制的作用,大国之间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小的冲突不会发生,而这些小的冲突多是沿着族群方向进行的。据统计,2015年全世界有118 788人在冲突中死亡,其中,在族群冲突中丧生的人数为97 766人。
国际秩序变革始于国际社会权力在大国间的转移,意味着大国间竞争的加剧。大国权力在一个地区/国家的减弱,会导致该地区或国家内族群竞争的加剧;大国之间在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和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会促进族群间的竞争,影响族群冲突,导致族群冲突增多。
(一)大国实力下降导致族群冲突
首先,大国实力下降会加剧国内族群竞争。当今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20个国家由单一族群构成,多数是多族群国家,族群问题仍是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国家基于国家能力通过认同管理、政策治理等手段,保持着多族群国家的统一。大国实力的下降,同时也标志其国家能力的减弱,而缺乏必要能力治辖下的族群问题便会浮出水面。换句话说,失去了国家这个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者,各族群会重回丛林法则,族群精英为获得更多的利益,会对族群进行政治动员,而族群中的理性人也会发现在冲突中有利可图,两者一拍即合,精英们出钱,普通民众出人,这便是族群动员理论的精髓所在。
其次,大国实力的下降会引起其势力控制范围内国家的族群冲突。虽然我们都倡导,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中,各个国家都是主权平等的独立行为体,但在国际社会中确实存在着等级制。因此当大国实力下降,它对其所控制国家的影响力势必减弱,在这些国家会出现一定的权力真空,如此一来便给争夺权力的各个族群提供契机。
(二)大国间的竞争导致族群冲突
二战之后,大国之间由于毁灭性核武器、相互依赖和科技制胜等原因,大规模的直接武装冲突减少,但相互之间的较量从未间断,具体呈现为与第三世界军事结盟、意识形态和物质援助以及直接干预或代理人战争等方式。第三世界国家的族群关系往往成为超级大国或地区大国的兴趣点。他们通过鼓动第三世界国家内的族群间冲突,以达到争取盟友、打击对手的目的。
首先,在经济上的竞争加剧了族群间的冲突。经济上的竞争主要表现在资源、市场、资金,大国在某一地区或国家内的竞争,会引起族群间收入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加剧了族群间的竞争和冲突。国际经济竞争影响族群冲突的历史可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殖民者通过与殖民地的族群联盟来达到攫取资源、输出商品的目的,如欧洲殖民者在18世纪与北美印第安人的联盟、19世纪在非洲与班图人的合作、20世纪与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的合作等,无不是欧洲列强与当地族群进行合作的例子。然而这种联合促进了族群之间的分化,一方面与欧洲列强合作的族群可通过接触欧洲先进技术和商品,获得一种类似于买办性质的经济优势,造成族群间收入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欧洲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也促使他们找寻不同的合作者,同样也会造成族群间的冲突,发生在18世纪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易洛魁族和乔克托族间的冲突便是如此。国际军火贸易是国际经济和军事竞争的结合,二战后,苏联和美国为了争夺盟友展开斗争,通过武装反对国家的族群来破坏敌对国家的稳定和主权。这样既可以促进他们军火工业的发展,也可以实现相互之间的军事平衡。如1975—1987年的玻利萨里奥阵线与摩洛哥的战争和1974—1991年的厄立特里亚反抗埃塞俄比亚的冲突,均有美苏军事贸易的背景。
其次,大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会引发族群冲突。在历史上此种例子比比皆是。苏联在战后支持伊朗北部的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的独立运动,以获取在伊朗和波斯湾石油通道的战略利益;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普什图人的族群运动的支持,无不体现其与苏联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争夺;近期围绕着克里米亚的西欧和俄罗斯之间的争夺,引发了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族间的冲突。
再次,大国在意识形态、文化上的竞争也会诱发族群冲突。冷战时期,东西方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加剧了美苏及其盟友在国际市场、资源和地缘上的争夺,这种争夺在客观上促使他们支持各种持不同意识形态的族群运动,以达到巩固阵营的目的。
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的实证分析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变革与族群冲突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决定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和苏联,因此,本文以美苏之间的实力变化来分析国际秩序变革是如何影响族群冲突的。
本文虽将族群冲突界定为两个或以上的族群之间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边界问题的争端,但为了数据分析的可行性,在以下的分析中将族群冲突的定义范围缩小为军事冲突。只要这种军事冲突有族群诉求(消除歧视、族群平等),追求族群目标(族群自决、独立或分离),或者以族群之名进行叛乱,都将其视为族群冲突。
目前有许多关于军事冲突的数据库,如战争相关性(Correlates of War,COW)数据库、失败国家(State Failure)数据库。与COW的数据库里面只包含在冲突中每年牺牲1000人以上的数据不同,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军事冲突数据库(PRIO Armed Conflict Database)将标准降低为25人。然而在这些数据库里面,并没有明确族群冲突,为了进一步收集到准确的数据,本文通过以下方式对这些数据进行了筛选:(1)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的数据库中关于每个冲突的简单描述;(2)根据危险中的少数族裔(Minorities at Risk)中关于世界上200多个族群进行的深度描述;(3)根据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中关于每个族群的描述。
分析筛选后的数据可知,战后族群冲突有三个峰值,即1965年的7起、1991年11起的和2011年的7起。亦可将其分为三个时间段:1963—1967年、1989—1993年、2009—2011年。在这三个时间段里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实力变化较大,在1963—1967年间美苏之间的实力变化较为明显,苏联实力大增,几乎与美国平衡,致使苏联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权。以国民收入为例,195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只占美国的31%,1965年达到65%;从军事常规力量来看,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与美国相比苏联处于劣势,虽然苏联陆军数量方面与美国大致相当,但武器装备远不如美国,海军也落后较多。经过1962—1972年期间的迅速发展,70年代,苏联在常规力量方面大致与美国均衡。从战略力量来看,古巴导弹危机之前美国占绝对优势,从1963年到1973年,苏联战略力量发展迅速,双方开始形成均衡,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在1989—1993年的时间段里面,苏联解体,国际社会的权力转移到美国。苏联解体一方面造成加盟共和国内的族群冲突,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拉托维亚等的族群冲突;另一方面苏联在其他国家控制力消失造成的权力真空,以及美国的介入,诱发或加剧了这些国家的族群冲突。
结论
本文从大国实力的下降和大国间竞争两个方面阐述了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间的关系。大国实力的下降影响族群冲突:一是随着大国实力的下降,国内各族群为了争取利益,而进行族群动员,引发族群冲突;二是大国在国际范围内收缩其控制范围,由此出现的权力真空会引发族群对于权力的竞争。大国间在经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也会增加族群冲突。为了进一步阐述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间的关系,本文对1946—2015年间的族群冲突进行分析后发现,族群冲突的死亡人数与苏联和美国的实力变化存在一定的趋势匹配。当美苏之间实力变化不大,竞争缓和时,族群冲突的牺牲人数也相对减少;当两国之间实力起伏较大,竞争加剧时,族群冲突会有增长趋势,特别是苏联解体后,权力由苏联转向美国时的那几年,族群冲突异常激烈。
历史上国际秩序的转型总是与大国间的战争相伴,国际社会权力的转移似乎难逃“修昔底德陷阱”。不过随着毁灭性核武器产生的核恐怖平衡、世界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深化和科技制胜理念的盛行,大国间的直接战争似不可能。正如文中所述,大国会在其他弱国家寻求斗争场域。而与以前不同的是,大国寻求弱小国家作为代理人的战争将会减少,即国家间的战争会减少,而寻求碎片化多族群国家中的族群作为其代理人的可能性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