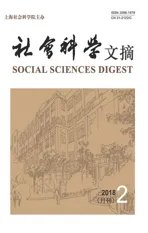中国外交转型与制度创新
2018-11-17
外交制度转型的世界性趋势
外交部是外交制度和过程的枢纽和组织保障,是各国协调国际与国内关系和矛盾的核心。冷战结束以后,外交部的“信誉”开始“遭到质疑”,国际上研究外交学的学者注意到并开始研究外交部所面临的挑战和转型趋势。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和外交具有更多的国际性特征,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是世界各国外交转型的一个缩影,外交制度的创新则体现了外交制度的中国特色。
从国际外交制度转型的角度来看,当代外交制度存在着“分散化”和“集中化”两个显著的趋势。所谓“分散化”是指,随着国际交往的范围和频度的扩展以及领域的增加,一些工作范围原本仅限于国内的政府部门开始参与对外事务,外交部作为国家对外政策唯一或主要落实机构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其权力在横向上向其他部委分散,纵向上向地方和基层分散,外交部已经沦为为其他专业职能部门和专业人员提供服务的“后勤协调员”。所谓“集中化”是指,由于对外政策和外交的国内影响及政治含义增大,国家领导人不仅是对外政策的制定者,而且在决策之后也频频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对外政策的执行者。
当前,对于中国外交制度演变和转型的研究成果都反映了中国外交在新时期所呈现的分散化趋势。它们或从宏观层面进行笼统的概括和总结,或采取案例分析的方式提出中国外交转型的发展趋势,但至今尚没有对这种特点和趋势的具体实证研究。比如,如果说中国外交在走向多元化、分散化,那么分散到了哪些领域?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些特点和现象又有什么样的含义?中国在应对这些趋势的时候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进行了哪些制度创新?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为对象,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个粗浅的回答。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缘起与发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是中国外交制度中的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反映了中国外交制度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初期就有设立发言人的实践,但直至1983年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才正式确立。其主要职能包括“发布重要外交活动信息,阐述对外政策,负责国家重要外事活动新闻工作”,“承担国家重要外事活动有关新闻工作”,“收集分析重要信息”等。
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布的新闻和答记者问的内容,既是外部世界了解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外交的窗口,也是中国民众了解中国政府在国际问题上立场观点和对外政策的重要渠道,因而也是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权威依据。作为中国外交的积极支持者和热心观察者,我们在追踪和阅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时注意到,近年来,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越来越多地以“我没有这方面消息向你提供”“目前我还不掌握相关情况”“请向主管部门询问”“我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我目前没有消息可以发布”等类似的方式回答,这样的回答无疑给外界造成了很多困惑。
我们无从得知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哪些是不了解相关信息、哪些是为了有意保密、又有哪些是“外交语言”的运用,但一个显著的趋势是,这种不能提供信息的情况不断增加,俨然已成为一种“新常态”,这也是引发本项研究的直接原因。借用其他领域的概念,我们把外交部发言人这类回答所涉及的问题视为外交部发言人所面临的“信息盲区”,这种日益“常态化”的“信息盲区”是否有明显的分布规律?这些特点是否能够反映出中国外交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和特点? 这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外交部的信息发布工作更加制度化和透明化,从2010年3月4日开始,外交部发言人发布的新闻和答记者问的材料都公布在外交部官方网页上。通过对从2010年3月4日到2016年12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的所有材料进行分析,足以管窥中国外交多元化和分散化的特点。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信息盲区”及其议题分布
经过对2010年3月4日到2016年12月31日这一期间所有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的统计和归类,我们发现,除有关香港、两岸关系和西藏等非外交问题外,外交部发言人共有454次不能提供记者提问所要求的信息。
从纵向上来看,外交部信息盲区的分布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在2010年到2013年间,出现信息盲区的次数曾呈下降趋势,2011—2012年间曾有小幅上升,但变化不大,2013年降至最低水平。此后,从2013年开始,外交部的信息盲区呈逐年递增的趋势,2016年则达到近年来的最高点。同时,从横向上来看,外交部所面临的信息盲区主要集中在经济、军事、朝鲜问题、首脑外交、领事、边界与海洋事务、网络安全、中日关系、恐怖主义和国际热点问题这十个领域,超过总量的85%,有着明显的分布规律。
(一)经济领域
外交部发言人信息盲区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经济领域,共有103次,超过盲区总量的五分之一。在经济领域内又主要集中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商务和金融这三个领域,分别出现过40次、29次和34次。在中国企业“走出去”领域的信息盲区包括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外企业项目合作等方面的内容;有关商务领域的议题包括中国对外双边经贸关系、对外援助、经济合作等内容;涉及金融领域的议题主要包括国家的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合作、财长和行长互访等内容,其中,外交部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信息盲区最为典型。
(二)军事领域
外交部发言人共70次以“不了解相关的情况”等类似方式,回答记者提出的涉及军事领域的问题,具体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外军事合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活动两大类。其中,外交部发言人共有28次对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外合作的内容表示不能回答或无法提供信息,对于中外军事交往的问题,外交部发言人也多不能提供信息。除军事合作外,外交部发言人有42次对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活动的问题也表示不知情。
(三)中朝关系与朝鲜核问题
从2010年3月到2016年12月,外交部发言人前后共有49次对记者提出的涉及朝鲜的问题表示不知情,超过盲区的10%。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涉及中朝高层官员互访,有14次;二是与朝鲜发展核武器或核试验相关,共13次。在被问及有关中朝高层官员互访的问题时,外交部发言人在表示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时也表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是主管部门,要记者向中联部询问。还有记者多次问到两国高层官员访问的消息,对此外交部均表示“我不了解,没有消息向你提供”或“请关注有关部门发布的消息”。有关朝鲜发展核试验情况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盲区,外交部发言人有13次表示不掌握实际情况,这种回答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
(四)首脑外交
首脑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形式。但在本文所关注的时间范围内,外交部在回答有关首脑外交议题的问题时,有34次表示不掌握情况。涉及最多的是领导人互访的消息,共有13次涉及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其中关于201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的情况和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巴基斯坦的情况被多次问及,外交部都不能提供应有的信息。
(五)领事保护
随着近年来中国出国人数不断增加,有关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案件频发,外交部在海外公民安全领域面临的信息盲区也日益扩大。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内,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涉及领事业务的问题时,共有34次表示不能或没法提供任何信息,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共出现15次。
除了这五个领域的信息盲区外,外交部在边界与海洋事务、网络安全、中日关系、恐怖主义以及国际热点问题这五个方面也存在着信息盲区,分别出现了30次、21次、20次、17次、15次,这五个方面的信息盲区虽然相对数量较少,但也值得我们关注。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信息盲区的特点和含义
从增长速度的角度来看,经济领域一直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时的最大盲区,增长也比较快,但是增长最快的盲区是军事领域,第二位是朝鲜问题,第三是领事领域的问题,第四是经济领域的问题,第五是首脑外交。虽然军事领域信息盲区的总数量没有经济领域的多,但如果按照现在的增长势头,军事领域盲区的数量将很快超过经济领域,说明军事领域将是中国外交未来扩展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领域。
从盲区的性质来看,这些盲区的分布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分别代表了外交制度面临的两种挑战:一种是外交议题向其他领域扩展所产生的问题,这些议题本不属于外交部业务范围内的事,因而出现了一些盲区;另一类情况是原本属于外交部工作或职责范围内的事,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一些新趋势、新情况对中国外交部职能构成了挑战。两类情况具有不同性质的含义,也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予以应对。
第一类挑战是协调方面的挑战,体现在包括经济、金融、军事外交和党的对外关系等领域的内容。这些领域的问题原来就不属于外交部业务范畴之内,但是近年来这些领域的议题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记者就这些问题提问,标志着这些领域是中国外交近年来扩散的主要领域。具体来说,经济和军事这两个重要的领域是外交扩散的主要方向。其中经济领域的经贸合作等问题是存在已久的老问题,因此盲区数量比较大,金融领域的盲区属于最新扩散的领域。至于军事领域的情况,其既有属于旧问题的内容,但也有新的含义。朝鲜问题的情况则反映了当今中国外交的某种特殊性。
第二类挑战涉及外交部职能转型,具体表现为外交部发言人在首脑外交和领事保护方面的盲区。外交部发言人在首脑外交方面信息盲区的增加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一是近年来首脑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二是媒体对首脑外交高度关注;三是这些盲区并不是偶然的、一时的,而是制度化的,并且呈现上升的趋势。考虑到承办首脑外交是外交部的第一职能,因而这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如果借鉴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盲区所反映的问题尤其需要认真对待。
这两方面的趋势或挑战,需要从不同的层次出发考虑应对方法和解决途径。第一个层次的挑战是国家层面的,即国家应该如何应对外交议题日益分散到其他领域的趋势问题,或者说对于不同领域的外交,如何加强不同部门的协调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作为传统上唯一的协调和联系内外工作的部门,外交部对于如何协调外交规范的普遍性与中国外交制度的特殊性,如何协调涉及越来越多机构和部门的不断扩展的多领域外交等问题,既没有清楚的党内规范文件或国家法律作为依据,也没有建立起责权清晰的保障机制。因而,这方面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或者明确外交部的责任和权力。
第二个层面是外交部本身必须应对的挑战。外交部的主要职能是落实对外政策,在中国就是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过去外交部是对外政策的主要执行者,随着外交领域扩展到经贸关系、金融合作、军事合作、党际关系、防范与打击恐怖主义等更加专业化的领域,外交部或者外交部的干部是否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与能力来落实有关领域的政策?在负责相关领域业务的部门都发展各自的外事机构,更多参与本领域对外政策的落实时,外交部如何避免沦为仅仅是为其他专业职能部门和专业人员提供服务的“后勤协调员”?这就要求外交部在人员招录、职务晋升、知识储备等方面都应该有前瞻性,并做好针对性的准备工作。
第三个层面的挑战是刚刚参与到对外关系的部门,或者说负责外交最近扩展或分散到的那些新领域的部门。从政府与媒体或公众之间的关系来看,外交部发言人这么频繁地要求记者向其他部门或相关部门咨询,至少说明其他部门在公开化方面,或者与媒体的沟通方面,还没有外交部那样成熟和完善,也反映出多数记者对相关部门的职能缺乏了解,习惯于从传统视角看待外交问题,一遇到问题就抛向外交部。这种状况需要从两方面加以调整:对于相关部门来说,要完善制度,不能仅从国内角度考虑自己的政策或在国际上采取行动,在参与对外合作的过程中应该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范,照顾国际社会其他方面的关切和基本要求,绝不能仅仅按照国内工作的习惯开展工作;在信息发布方面可以借鉴外交部的做法,增加透明度,在信息提供方面注意时效性。对于媒体来说,要增加对中国的了解,不能以传统的思维方式看待中国外交,要了解部门之间的业务分工,提出问题要有针对性,有的放矢,才能及时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制度优越性和外交创新
中国外交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也是中国外交制度的特色,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外交不仅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也要为巩固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服务。
制度创新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发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的领导作用,召开相关外交工作会议,在相关外交问题上统一思想,确保外交行动上的协调一致。十八大以来,中央分别召开了三次专门的外交外事工作会议: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以及2015年的全军外事工作会议和第十六次武官工作会议。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精力办大事的特色和优势。
推动涉外部门的协调机制建设,理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完善相关法律,是外交制度创新的又一主要内容。如十八大以来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对于加强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全局统筹、协调与合作将发挥重要作用。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中国进一步完善了涉外安全领域的法律,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此外,强调顶层设计,狠抓政策实施,确保中央战略意图的落实,也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制度建设、做好对外关系统筹和协调创新的关键。
当前,中国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中国外交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亟待解决。同时,新时代也需要新的理论创新、机制创新和实践创新,从而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