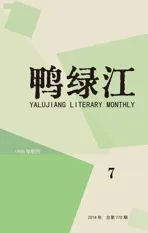相逢一个个童年
2018-11-12陆梅
陆 梅
山家坡
春天在起起伏伏过山车一样的冷热骤变里终究迎来了它真正的初夏。
那天,我偷闲半日在长江的入海口——崇明岛西沙湿地栈桥上走,两边是羽叶新发的水杉林,眼睛里满是清透的嫩绿。我被这汩汩的绿包围,徜徉着不忍离去,灵魂出窍般,我变身成两个人,肉身随同行人上了车,神魂却留在了栈桥上,一下回到了我的小时候。
我在两排水杉林里走。这是一条笔直的乡村小道,铺成水泥路前一直是煤渣子路。倘以我念书的华阳镇为中心,这条还算开阔的华长路在华阳镇的正南方,一路贯通南部的村庄,最后消隐在黄浦江北岸的某处田野。眼前这两排浩浩荡荡漫延而去的水杉是我外公种的。我从没写过外公,我写爷爷是因为小时候的大部分记忆和他有关,而外公,是那个个子高高、眉毛粗黑、言语不多却和气蔼然的种树老头儿。如果爷爷是山冈守墓人,外公就是种树老头儿。
外公爱种树,起码我的记忆里他总扛着一把铁锹逡巡在华长路上。那曾是他的工作。水杉相挨着一棵又一棵,齐刷刷站得笔直,简直跟勤务兵一样。有时我放学回家,会撞上正弓腰曲背在给水杉填土松土的外公,捎带平整坑洼不平的煤渣子路。不是走亲戚却意外遇上了亲戚,尽管这亲戚还是外公,我也会尴尬,我不知道要说什么,轻轻喊了声“外公”。外公抬起头,眉眼温顺地笑道:“放学啦?快回去吧!”说完接着做他的事,再没半句寒暄。外公的态度很令我舒心,我当即雀跃而去。若是和姐姐在一起,她总要停下说上一阵才走,可见外公心里明镜儿似的,他体恤我的腼腆。小时候我不爱说话是出了名的,我去上海的奶奶家过暑假,回来得了一个“哑巴”的诨号——这个留待下面说。
水杉长起来快,很快就粗壮挺拔,可惜枝叶尽往上伸,暑天里泼下一个小圆,我们都爱踩着这一个一个的圆弧绿荫走。
此刻我正往外公外婆家。其实去山家坡我很少走这条路,是水杉把我带入另一个童年。山家坡是我小说里的叫法,真实地名是山家桥。我的故乡华阳镇也叫华阳桥镇,镇上还有好几顶桥:三里桥、东杨家桥、西杨家桥、永济桥……桥是古桥,元明两代的居多,一顶古桥横跨盐铁塘两岸,桥名也成了地名,连接起一截截的历史风云、名人逸事和炊烟袅袅的水乡生活。我在桥上桥下疯跑的日子,也叠印着童年和少年深深浅浅的脚印。
在桥畔摘几朵野蔷薇,踩踩桥石缝里顶出的车前草绿苔藓,站桥上窥看刚好经过的船上人家:一个女人立在甲板上梳头,舱内一角叠放着几层薄被,男子在摇橹,穿红肚兜的小孩趴着正往舱外爬……这悠然一闪总令我神思摇荡。我想象自己就是那个肚兜小孩,一出生就在船上,船虽也靠岸,但总没离开过,晚上睡在船舱里是什么感觉?船在水上走,遇见风浪怎么办?对船来说,陆地是不是平移的水面?……我的童年太寂寞了,一条小船就够消磨半天。
我很少写到外婆家。小时候对外公外婆家的印象是家族庞大,亲戚一堆,连作为客堂和祠堂的大屋也一阵住了外公的老父亲。我总是搞不清这么多的七大姑八大姨,要么装作没看见远远避开,实在躲不开就阿姨婶婶舅妈地乱喊,这些婆姨们听了鸭子一样嘎嘎嘎笑,还小题大做学给外婆和我母亲听。外婆好脾气,一笑而过。母亲急性子,劈头敲我一记脑门:“你这木瓜脑袋,跟你关照过几回啦,怎么还记不住?!”母亲的大嗓门哇啦哇啦,很快灌进七大姑八大姨们的耳朵里,她们躲在门背后哧哧笑。我恨透了这帮告密者,从此对走亲戚生出莫名恐惧。
外公姓山,山姓是山家坡的大姓。我至今搞不清外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到底有几门儿女。在我的记忆里,他已经很老很老了,我打他门前走过,他缩在大屋的前天井里晒太阳,他根本就记不住谁是谁。我很高兴他记不住我。我跟东厢房的小红打了个招呼,我们同在双梅小学念一年级。我们是亲戚,可一到学校我们各管各就像是不认识一样。外公有四个小孩,老大就是我母亲,老二是我姨,老三老幺是我大舅小舅。家族里也有倒插门进来的外姓男子,我唤作姨夫的,基本没他们的声音。过年时,我姨我母亲拖儿携夫回娘家,其他几门嫁出去的女儿也都回来了,这时候,这个家族里的“少数派”,我的几个姨夫们突然活跃起来,他们自动组成一个联盟,抢着派发香烟,眼神一对就聊上了。祭拜完祖宗,晚上喝酒守岁,更是他们表现最出彩的时刻。他们生动谈笑,勤奋敬酒,红着脸跑去放炮仗烟火,兴奋得跟个小孩一样。通常这时候,他们的老婆大人虽也在吃喝,虽也热火朝天地家长里短,可是眼梢很不耐地一瞥一扫各自的丈夫,明明是在意的,却装出不屑来。我觉得还是这些姨夫们可爱,虽然我跟他们隔着一个星球的距离,我这么小,他们那么“老”,他们兴高采烈的谈论我一句也搭不上。
山家坡在我的记忆里就是迷宫一样的房子和剪不断理还乱的大堆亲戚。倒是种树的外公清透地印在我脑海里,就跟那天我在栈桥上看到的水杉林一样,鲜绿透亮,只遗憾我跟外公交集太少。如今华长路上那两排漫天而长的水杉连同整个山家坡都被悉数砍倒推平销声匿迹了。
生活就是不断地割舍和失去。抹去旧的,迎来新的;抛下旧日子,走进新日子。我们都这样在新旧交汇里走走停停,再怎么走都逃不脱时间这张大网。好在有记忆,有书写,有时记忆和书写就是时空的延伸、想象的延伸。那是另一个盛大的世界,再大的网也网不住。
另一个童年
小学三年级前,我基本是一个顽劣儿童。口袋里装满小石子躲在暗处袭击人;玩斗草游戏作弊偷往自己篮子里多加草;同村里孩子一起偷邻村地里的瓜果蚕豆玉米;爬树捣鸟窝偷走鸟妈妈的蛋;讲鬼故事吓唬人却把自己给吓着了;在青水河里摸蚌壳螺蛳差点被旋涡卷走……顽劣事情一桩桩。
有一次和姐姐怄气,我抓起剪刀剪手边的袜子,姐姐一把抢过剪刀也乱剪一气,好端端一双尼龙袜成了姐妹俩的出气筒。和姐姐的怄气升级,有一回两人又拌嘴,不管不顾在上学路上丢了问同学借来的一个闹钟和父亲新买的一件衬衣,忘了是她丢我折回去捡还是我丢她跑去捡,总之再也没找到,就那么几分钟时间,新衬衣和闹钟就长脚跑了。我和姐面面相觑一下愣在原地,接下来怎么办?怎么和同学交代?两件一模一样的新衬衣,突然少了一件,又怎么跟父母解释?姐姐垂头丧气,我也偃旗息鼓,脚踩棉花一前一后去了学校。傍晚回家,两个人谁也没得着便宜,母亲把我俩痛扁一顿,父亲默不作声不再从旁相劝。那时候生活拮据,我和姐赔不出一个新闹钟,亏这个同学宽宏大量,不要我们赔钱赔闹钟,此事算了了。
除和姐拌嘴怄气,我还特别馋,为解馋可是想尽办法——比如我用糖精泡开水灌在玻璃瓶里提去学校喝;大冬天,我把母亲做的萝卜咸菜干偷藏在棉衣口袋里当零嘴吃;我还偷过父亲喂食给长毛兔的麦乳精和奶粉,奶粉受潮结块,我就整块整块往嘴里塞;家里有一个很老的五斗橱,最大一个柜子玻璃缺了半块,母亲把过年时迎来送往接的礼锁在这个柜子里,我偷偷撬动玻璃后的那块挡板,小手伸进去把母亲藏着的纸盒饼干一点一点地抠出来吃个精光!等母亲发现为时已晚,母亲冲上来要打我,我早有准备,跑得比兔子还快……
童年的那些糗事,如今想起来竟也不可思议地像是在和另一个自己镜中对话:“那是我吗?我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那不就是你!”——镜中的我不客气道,“你还做过更多糗事……”
“还有?”我诺诺地表示抗议。
“你自己想想。”镜中的我态度冷然。
于是我又想。想起一个大冬天,父亲好不容易搞到两张戏票,小镇电影院上演舞剧《小刀会》。晚饭时,父亲跟姐姐交代:饭后他和母亲要去镇上看演出,晚上和妹妹早点睡,关好门……姐姐还没应答,我却哭将起来,说什么也要跟着去,姐姐来解劝也不管用,我放下碗筷哭闹着跑出门。冬天的傍晚黑得快,外面风呼呼响,我不管不顾一根筋地哭着跑着。父亲出来追,母亲和姐也紧跟着跑出来。我索性围着稻草垛兜圈子,跑太远我还怕赶不上去电影院呢。一个跑,一个追,父亲跟在后面好言相劝,“妹妹、妹妹”地叫,我仗着父亲疼我,跑得更起劲。母亲一下子光火了,说谁都不要去了,戏票撕了算。父亲又去安慰母亲,说一起去,妹妹也去,我来想办法……
这场戏对一个年龄屈指可数的小孩来说,简直是瞎子点灯,白白辜负了一场哭闹——我已经记不清父亲是出钱买了半票呢,还是托人静悄悄放我进的影院。如今还依稀记得舞台上的一幕幕场景:城墙,大炮,火光冲天的码头,码头上顶着烈日弯腰驮粮的苦力工人。有一天,劳工里站出一个人,一声长啸,工人们集结一起跟清兵作战……也是因为得了这样一层印象,读书后上历史课,提及太平天国、洪秀全、清政府腐败……我就记得特别牢,《小刀会》里有这些影子。没记错的话,爷爷大屋里还有“太平通宝”的旧钱币,一枚一枚扔在一个碗碟里,爷爷用它来刮痧,有时也用它刮老黄瓜的瓤,手起瓤落,干脆利落。这旧铜钱据说是小刀会起义军转入上海时铸造的,也在松江、青浦、宝山一带流通……历史虽说在遥远的远处,有时也会灵光一闪跳将出来,啪一击给你醍醐灌顶:“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谢谢你,让我回到另一个童年。”我对镜中的我说。
镜中的我报以淡然一笑,神思浩渺道:“一个作家的写作,最终要回到他的童年。”
“……”我看着她,回味再三。
“别那么看我,这话不是我说的,”镜中的我粲然道,“把功劳记在老托尔斯泰身上吧。”说完阖目,隐身不见。
我怔怔地望向白茫大镜,眼前仿佛浩渺烟波,横无际涯。
一条电光石火闪向脑海:我究竟是谁?我和镜子里的我是一个人吗?我怎样认识我自己?是不是一个人的童年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换个说法,一个人在童年里所有的意识和无意识,都会在某一天某一刻发酵、点醒,成为这个人性格组成、命运轨迹的一部分?就跟一条河一样,任它浩浩汤汤、蜿蜒曲折,汇合伸展或消隐在某处,总有一个起始的源头。
是不是我把童年看得太重了?或者老托尔斯泰只想强调,当你有机会成为作家——一个以文字为业的人,你该有能力回到自己的“童年”。这个童年也就是你的赤子本心。童年时我们眼里的一切,大抵是见什么是什么,及至长大,目迷五色,烦恼心起,我们眼见和闻说的,太多我们的偏执和偏见。——偏执偏见未必不是我们的正见,可是终究,因为羁绊太多,不再矫捷的身心难免负重。好累啊!我的身体里咔嗒咔嗒发出这样的声响,连我自己都惊异,明明就在昨天,我还猴子一样灵巧爬树,还天不怕地不怕,还耳聪目明眼望千里……唉,我悲哀地想到,我的身体里住着的那个小孩在渐渐离我远去!——如果老到白发苍苍,反而就好了,那个小孩又会回来,我这样以为。所以,一个人无论长成什么样,如果有能力看见自己的童年,也能够聆听到别人的童年,更能够创造一个个不一样的童年,那么我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诗人。我努力去做这样一个诗人。
奶奶和哑巴的暑假
这个哑巴不是我。可是奶奶的左邻右舍却慷慨地把这诨名给了我。
一年级时的暑假,父亲把我送到上海永年路的奶奶家。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真的是远!那时候没地铁没出租车,父亲手里有一张爷爷书信寄来的“手绘地图”,那上面连写带画,标注得密密麻麻,怎么搭乘长途汽车到人民广场,怎么找71路公交车,哪站下,中间换乘24路“辫子车”,马当路下,看到什么标志,过哪条马路,拐哪个弄堂……父亲按图索骥一路摸去,赶了一天远路的他牵着八岁的我,终于在黄昏时踩进上海奶奶家的石库门。
这一幕从此刻进我的成长记忆。这趟远门也预示着我和我未来的缘分——冥冥中似乎已经有了安排,我总能考进上海的大学,我会暂住在奶奶家,我安营扎寨工作生活在上海……几十年后,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似乎一切都是天意,理应如此,可事实并非我写的那么简单。我只是一个八岁小女孩,从没见识过大上海,上海话我都听得磕磕碰碰,更别说开口讲了。我立时成了一个哑巴。我不愿搭理人,顶顶不喜欢弄堂里阿姨爷叔左一句右一句地寻我开心。这些整天坐在弄堂口剥毛豆挑鸡毛菜、穿了背心裤衩淘米洗衣的阿姨爷叔可真是精力充沛。起先是好奇,看我总不开口就想寻个开心,“有本事侬叫喔子开口。”——“喔子”是“哑巴”的沪语发音。张家姆妈努努嘴朝我看。她手里剥着毛豆,跟水池边刷牙的隔壁爷叔说笑。隔壁爷叔瘦得排骨精,扫我一眼,闷声不响。我才坐在板凳上等奶奶买早点来,听张家姆妈这一说,我立起来就走,噔噔噔爬上奶奶家的阁楼。
奶奶一辈子住在阁楼里,年轻时把好不容易分来的一室半给了儿子,她和爷爷只好住阁楼。永年路的阁楼,黄陂路的阁楼,搬来搬去都是阁楼。奶奶也有一个雅号,叫“亭子间老太”——上海人管二楼半的阁楼叫亭子间,弄堂里大家都这么呼她。住久了,我发现上海人都是起绰号高手,“阿尼头”就是张家老二;隔壁爷叔抽烟上瘾妻子不许他抽,背地里大家喊他“气管炎”(妻管严);张家姆妈也是特定称呼,不会搞错,弄堂里有同姓就加个前缀:×号里的张家姆妈……这些诨名叫熟了就是老房子老弄堂的暗号,暗号一对,立马表情生动。哪天来个外人,说谁谁谁在吗?要说的是诨号小名,阿姨爷叔会很客气地朝里一指或领你进去;要是一口土语普通话,又是连名带姓,阿姨爷叔眼睛一扫,晓得来人是个“阿乡”,也不跟他搭腔,伸长脖子高喊一声:“阿尼头,有人寻侬!”
我老不开口,阿姨爷叔们也失了兴趣,我只跟爷爷奶奶搭腔,其他人一概装哑巴。我很乐意他们不再盯着我,整个暑假,他们眼里的哑巴却开启了一个新天地。我认识了一个大我一两岁的楼上女孩,她就住三楼,小脸清瘦雪白,眼睛很大很黑,扎着朝天辫,这么好看一个女孩却是个真哑巴!难怪左邻右舍表情活跃窃窃私语:“又来了个喔子”,也难怪奶奶听了这话兀自叹息——会说话的要装哑巴,真哑巴“呜呜呜”太想说话却没一个人听得懂。
现在,我和哑巴女孩认识了,我能听懂她说的话。
我跑上阁楼躺在地板上。晚上我就睡在地板上。奶奶的阁楼一张大床、一架衣柜、一个黑白小电视,门墙的钉子上挂满东西,余下空间就是白乎乎一片老旧纹路的木地板,白天放置座椅,晚上收起打地铺。光影从楼下走道一侧透进来,我从一格一格木窗棂里望出去,楼下人的动静一目了然。这是我窥探世界的一方天地。
一个身影突然闪进来,就是楼上的哑巴女孩,可那时我还不知道她是哑巴。女孩冲我粲然一笑,指指上面,我点点头。她又指指楼下,点点我跟她,手舞足蹈玩乐的样子,我又点点头。女孩笑得更灿烂了。这时候奶奶回来了,她不见我在楼下,就动静很大地上楼,手里拎着早点,不用猜,扑鼻香味已报告了内容,纸袋里是刚出炉的生煎馒头。没等奶奶进屋,女孩小身子一闪,不见了。
我问奶奶:“楼上的女孩叫什么?”
“怎么,喔子来过啦?”
“嗯,她跟我打哑语,约我一起玩。”
“她只会哑语——”奶奶叹息一声。
“她是哑巴吗?”我龇牙咧嘴,生煎太烫了。
“是啊,你来她可乐坏了,她观察你好几天了……”房间里空间实在有限,奶奶肥硕的身子一转,就把门口给堵上了,“吃完就下来吧。”奶奶拖着大脚一步一步下楼。
奶奶有一双气壮山河的大脚,两条腿粗得跟大象腿一般,小时候我并不知那是病——现在也还是搞不清,究竟这双大脚是怎么造成的。奶奶往人前一站,就跟美国电影里那些女管家一样,很威严很有气势,一说话却是刀子嘴豆腐心,她是弄堂里的热心人,楼上楼下阿姨爷叔最喜欢跟她聊天,拜托她事也最放心。
我的这个“奶奶”和我乡下的奶奶曾是好姐妹,就是舞台上那种生死之交,共患过难。可惜乡下奶奶死得早,没看到上海奶奶的后福,一嫁嫁到了上海。上海奶奶不忘本,一直记着俩人的情分,就移情给我,把我当成嫡孙女一样来爱,我也叫她奶奶。我跟她的缘分此刻我还不知,果然后来我考进上海的大学,很多个周末回的家就是奶奶的家,奶奶变着花样给我做糖番茄、番茄炒蛋、番茄雪菜焖黄鱼……那个时候我番茄吃不厌——其实是为了减肥,奶奶还真以为我超爱吃黄瓜和番茄呢,每个周末都备好这两样,生吃凉拌随我。我会在奶奶家住一晚,临走提上两格饭盒子,里面装满新上市的炒蚕豆,碧绿鲜嫩的蚕豆上沾了切得很细的小青葱。这是春天。秋天是生煎馒头、鲜肉月饼、糖炒栗子,冬天换成香煎带鱼、红烧肉冻、炸春卷……我对奶奶的回忆充满了食物的气味,奶奶肥硕的身子总在厨房里忙进忙出。我曾在一个小说里写到奶奶,敲下第一句话时泪如雨下。这个小说叫《彼岸花》,第一句话是:奶奶去天国了。
如果算上山家坡的外婆,我就有三个“奶奶”,我的这些奶奶都温和善良,上海的奶奶上面写了,我从未见过面的乡下奶奶宁愿自己饿着也会把最后一口留给孩子和她的姐妹,山家坡的奶奶温良得像个菩萨,她确实经年茹素……我这样写着她们,其实也在清理自己,因为我把她们遗忘得太久了,我只顾一径往前,走得太快就把负重给一样一样丢了——是时候平缓一下心情,停下来回头看看了。我在看的时候就一点一点把那些负重给捡回来,它们其实都是有用的石头。可是那时我经见太少,眼光也短浅,我还不能体会有用的石头就是宝石,它们只对眼睛清亮的人发光。所以当我有一天从一本图画书里读到一句话:“有时候,人必须远行,才能发现近在咫尺的东西。”我热泪盈眶!是这样的,奶奶!
我这样写不知孩子们能否理解?有时远行不一定是地理意义上的出走,隔着时空的距离,远行还是一味药,总得慢慢熬。火候不到,药量不对,配伍不全,都发挥不了药性。而得到这味药,你会豁然而喜,喜极而泣。人生啊,就是这般五味杂陈!这味药,专治健忘症、思乡病,乃至一切和故乡、亲情有关的疑难杂症。
这是我来奶奶家的第七天。父亲住了一晚就回家了,我慢慢习惯了爷爷奶奶家的生活,对全新环境也有了自己的判断和观察方式。一日三餐,午睡,看电视,听奶奶讲古,无聊发呆,爷爷还带我逛了大世界城隍庙和豫园……街上人山人海,天又那么热,爷爷脚力好,我根本就比不过他,走走就走不动了,我不想再这么大老远地逛。我自以为见了世面,足够回去和姐吹嘘了。这时哑巴女孩出现,我很高兴得着这么一个新朋友。
我写过一个小说《哑女米莉》,就是以这年的暑假生活为蓝本,小说里的米莉大半有哑巴女孩的影子,姑且这里我就叫她米莉。每次都是米莉来找我,我无聊发呆的时候她突然降临。我们比比划划,有时连蒙带猜,总能够心领神会。在米莉面前,我很乐意做一个哑巴。我变得很顽皮,其实那就是我的本性。我们一起去后天井探险,跑到复兴公园捉知了、找无花果树上的天牛,凑齐了钱买冰砖和刨冰吃……这些我都比米莉在行。米莉开心得哇啦哇啦,奶奶逗她:“你说啥呢,满嘴跑火车?”米莉黑玉般的眼珠子一瞪,继而又嘿嘿一笑。那意思我明白:不跟你老太一般见识!我扑哧笑,奶奶也乐,不再一声声叹息了。
我竟然没见过米莉父母,起码没留下一点印象。难怪我在小说里把米莉父母写成沉迷麻将、整天吵架的一对自私男女。事实是每次都是米莉下楼来找我,我们一起玩也顾不上问她家的事。倒是多年后,我再去奶奶家过暑假,奶奶还在永年路的阁楼里,隔壁和上下楼邻居换了不少新面孔,米莉一家也搬走了。奶奶是个念旧的人,她很怀念以前的旧日子旧邻居,遗憾人们总是更向往新生活新环境。奶奶在回忆里度过了她的一生,没有那些旧日子,她活不了那么久。她是在爷爷走后多年、又一次搬家后过世的。那时候我已在上海安营扎寨结了婚。有一天,我接到姑姑电话,姑姑说奶奶走了,我从床上惊起。我正在发烧,脑袋昏沉,姑姑一个电话把我的病吓去一半,我披衣下楼向奶奶家赶去……
如今我的奶奶又少了一个。米莉我也再没见过,不知她现在好吗?我跟她的友情维系了几个暑假,以为总是会见上的,没想着要互留地址——留了又如何呢?未必真就会联系。有些人,有缘同行一段,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后总有新的人加入,再继续着路上的旅程——我们一生,要经历多少这样的聚散离合生死遗忘!每一段,都是不可复制的人生。那些有幸记得的,都不曾远去,最终还会回来,与你促膝相对。
遇见父亲
我写过了爷爷和外公,写过了我的奶奶们,我也在别的散文里写过姐姐和母亲,却是没有很好地写一写我的父亲,而我和父亲的感情是最深的。童年里,如果“遇不见”这样一个父亲,我就长不成今天的样子。
对,和父亲不该说“遇见”,可我真就觉得“遇见父亲”是我的幸运。我的所有和父亲有关的童年记忆,都是快乐和阳光,连忧伤也是好的。他更像是一个大朋友,带我冒险玩乐,有伤心委屈,他来温暖和安慰。在我们家,“严父慈母”刚好是倒过来的——严母慈父。父亲对姐姐也不凶。倒是母亲,我从小记得要么躲着她要么顺着她,可终究,躲还是躲不过的,我和姐姐小时候没少挨过她骂。
父亲就不同了,他是我们村的“知识分子”。20世纪70年代,知识分子的标志是的确良白衬衫配风纪扣中山装,胸前口袋插一支钢笔,帆布包里装着笔记本和书。这些刚好是父亲的标配。父亲宽和安静,一手钢笔行楷流畅潇洒,闲暇时爱钻研书,若不是爷爷需要一个壮劳力以缓解捉襟见肘的家境,父亲该是村里他那一辈唯一的大学生,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大学没读成,他做了村里会计。我见过他账簿,端雅小字和一串串数字,每一页都清俊爽目,连记账都这么认真,可见他多么一丝不苟。父亲因敬业勤勉,由村会计到村长,又一路上调到大队部、农科站、农业公司、副业公司、乡政府,官职历经站长、经理、主任,直至在政府信访办主任的位上退休,一辈子清正廉洁。小时候那个缺了半块玻璃的五斗橱柜里,夹着一张张父亲的红本本,人大代表、先进个人、结业证书……当时没想着要替父亲留存,恍然我也到了记忆里父亲那样的年纪,心里一惊:我是如何错过了父亲的峥嵘岁月!
这么写的时候,脑海里翻出一个个大作家笔下的父亲:鲁迅的父亲,朱自清的父亲,汪曾祺的父亲……鲁迅的父亲病倒在床,少年鲁迅不得不一次次去请医生,那个医生开出的药方子古怪离奇,蟋蟀一对,还要原配,还得是同窠,拿各种奇奇葩葩的药引子来折磨人,少年鲁迅由此结下一个愿,长大后读医科,懂一门医术……朱自清的父亲中国孩子都熟稔在心,初中语文课本里收有朱自清的散文《背影》,那个着深蓝棉布袍、在火车月台爬上攀下给儿子买橘子的肥胖身影,成了舐犊情深的经典画面。汪曾祺的父亲有趣好玩又多才多艺,会画画会刻图章会弹琵琶拉胡琴扎花灯……他对汪曾祺的影响果然是全方位的,汪曾祺也多才多艺有趣好玩,真真“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的父亲没这么伟大,也不见得多才多艺,舞文弄墨仅限于工作内的二三赏识者——他没少写过发言稿、总结稿,给各路报纸和地方广播的新闻素材(还不是“稿”)。可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父亲,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于我,却是唯一。他热爱草木和自然,懂一些草药,会抓好看的蝴蝶和蜻蜓给我玩,年轻时热衷田野实验,比如水稻田里养鱼。杭州的作家周华诚向久居城市的人发起一个“父亲的水稻田”活动,响应者众,居然成了城里孩子亲近土地的一次田野之旅。我的父亲很早就有这样一片水稻田,他优选种子,水稻长成投入鱼苗,经他悉心照料这块实验田长势优良。父亲还尝试过养殖长毛兔和鹌鹑,土法配制各种“营养饲料”——我偷吃过的奶粉和麦乳精就是父亲喂给长毛兔的营养品。唉,那时候连人都舍不得买来吃呢,父亲却给兔子开小灶……我着实不平,得逞几次,竟也光明正大地偷。父亲看到,佯装一个毛栗子,脸上却是笑着的,我捂住嘴溜得飞快。
父亲年轻时候身手敏捷,摸鱼虾螺蛳、捉黄鳝螃蟹是他的擅长,而我是他的好搭档。烈烈夏日午后,我提着竹篓立在山冈上,父亲一身短打浮潜在青水河里。父亲一个猛子扎进水深处,不见动静我就很紧张,急得要哭,父亲腾一下顶出水面,两个手里攥着河蚌螺蛳。我表情夸张地向他投来的“战果”奔去,破涕为笑。
最紧张的是捉螃蟹。父亲随手掐一根细竹竿,在河岸边查探。他能八九不离十甄别哪是螃蟹洞、哪是蛇洞、哪是黄鳝洞。可有时这些家伙们也偷懒混居,黄鳝洞和蛇洞还很像。每回父亲用竹竿试探一个个洞时,我就胆战心惊,提前在脑海里想象蛇突然刺溜出洞咬住父亲手的可怕场面。我虽白白替他捏一把汗,想着晚上有美味的大闸蟹和鱼虾螺蛳吃,也就心里七上八下着不管不顾了。我天性里淳朴喜静、对自然天地亲近神往的因子,都是父亲给的。没有任何说教,一切都是潜移默化。
还有一个,称得上是“我们家的桥段”,我去学校给孩子们讲作文时常提及。小时候我和大部分孩子一样写作文头疼,面对一个空茫的作文题总是束手无策。我愁眉苦脸挤不出半句流畅的话,于是就使出我的“撒手锏”——哭。我一哭,父亲就放下手头事坐下来启发我,看我还是一脸愁苦,就“捉刀”给我写一个开头,我照着父亲思路接下去,快到结尾时又卡壳,一旁做着功课的姐看不下去,一把抓过我的本子,一目十行——差不多也就十行的字数,刷刷刷给我按上一个“光明的尾巴”。我小学阶段的作文大抵是这样完成的。
升入初中,我有幸遇到一位好老师,他也姓陆,与我父亲相识,那个时候父亲在乡政府工作,我们的华阳中学和乡政府一墙之隔。有一次写周记,我忘了哪里抄来几段,结果就是这抄来的几段话被陆老师用红笔画上好看的麦浪曲线,这篇周记也在语文课上被朗读和表扬。我坐在第一排,跟讲台上的老师靠得那么近,心里的汗颜和不安就像小鹿奔突,手心里全是汗,神魂出离待在座位上……还好,下课铃及时解救了我!
可是此后,每一次周记和作文我都写得很认真,不再哭鼻子搬救兵,不再原样照抄范文。我的作文越写越好,语文也是我的强项,我最期盼的就是上语文课。父亲的捉刀代笔和语文老师的无心插柳,于我都是关键的帮助。这话说来有点事后诸葛亮,或许还有偶然性,可我觉得这不失为写好作文的一个法宝。台湾作家张大春透露过一个锻炼作文的秘诀,让孩子挑一篇自己喜欢的故事,用自己的语言复述一遍,不能用“后来”“然后”“结果”这样的连接词,用一次扣十分,口述完成而能够不遗漏故事内容的,就拿满分。我觉得这个办法跟我父亲的“捉刀”启发法不谋而合,还更有操作性,父亲写一段,我跟着父亲的思路接着构思、组句、谋篇,相当于把一篇作文拆解了自己理一遍,理的过程就是学习怎么文从字顺地写好一句话,说明一个事件,掌握一段情节。写作文终究还要自己悟自己实践,而万事开头难,父亲就把最难的事给我解决了!
语文老师的无心插柳我怀疑是“激将法”,多年后我问起此事,父亲笑笑不答。我把这事写成文章收进了书里,我送书给父亲,父亲宠辱不惊道:“回头再给我本,这本我送陆建华。”——陆建华就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我问父亲:“你碰到陆老师啦?他怎么样?”我在上海工作后很多年没见陆老师了,父亲偶尔会在小镇街上遇见早已退了休的陆老师。“他问起你,说你是他教过的学生中最出色,也最让他骄傲的。”父亲燃起一支烟,抽了口,望向郁绿田野,眼前大片灌浆的水稻。这片稻田不再属于父亲和村里的任何人。几个外乡人承包了我们村的大片土地,他们轮着种水稻和玉米。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和结束。村里人纷纷买房搬进了城里,大批外乡人租下空村谙熟地生活在他乡,作为外来务工者,他们散落在小镇周边、工业开发区和村庄的角角落落。那是另一个“他者”的世界。——他者,何尝没有自我的影子?
父亲已然苍老。他不再是我记忆里那个戴着草帽、一身短打、精力充沛走在前面,我手提竹篓吧嗒吧嗒跟在后面的父亲了。他把精力和使命传给了我,我得提起精神,对付功课懈怠、写作文同样一个头两个大的女儿。将心比心,我没有父亲做得好。
父亲说这话时老家还在,大规模的动迁还只是一个不太确信的“众说纷纭”。时过数载,老家被夷为一片平地。很快,小镇方圆几里将新起一个郊野生态园,我童年的乐园将以焕然一新的面目迎接四方游客。然而,虽说故乡,已没有家!父亲想是惆怅的吧?
我很高兴父亲可以看见这一切。遇见父亲是我最好的命运。“一切的起点都将是终点。”时间,纷至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