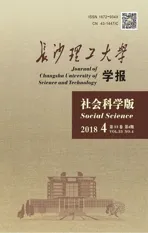人工智能研究的三大流派:比较与启示
2018-03-20王广赞易显飞
王广赞,易显飞
(长沙理工大学 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114)
随着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问世,人类拉开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历史序幕。一般认为,人工智能是对人脑的模拟和扩展,是研究以人造的智能机器或智能系统来延伸人类智能的一门科学[1]。人工智能研究者基于对“智能”的不同理解,形成了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三大流派。本文拟通过对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三大流派进行比较与分析,从中获得相关的有价值的启示。
一、人工智能研究的三大流派
人工智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学界公认的三大流派: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符号主义作为最成功的流派而一枝独秀[2],20世纪80年代之后,符号主义逐渐衰落,联结主义与行为主义趁势而起。在这交替变换中,人工智能的研究也逐步地发展。
符号主义,也被称之为逻辑主义[3],它是基于还原论的理性主义方法。该学派认为智能的基本元素是“符号”,人的认知过程是一个信息加工过程[2],通过对符号的逻辑演绎与推理等方式可以将智能活动表达出来。他们将信息加工系统也就是通常所理解的“认知系统”看作是一个巨大的符号加工系统,将智能系统理解为物理符号系统[4]。设计好的信息处理程序将智能活动形式化为某种算法,通过算法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逻辑处理,使得机器最终输出智能结果。由于符号主义以逻辑推理法则作为其主要思想[5],因而蕴含了深厚的数理逻辑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历史地看,从1956年到1986年,符号主义经历了从一枝独秀到逐渐衰落的过程[6]。究其原因,主要是还原论的理性主义方法无法对复杂系统的问题进行有效处理,简单的线性分解会使得系统复杂性遭到破坏,并且形式化的处理方式对常识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常识问题对于人工智能而言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2]。于是,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趁势而起,通过最新的研究成果,开始逐渐占领人工智能的领地。
联结主义,也被称之为仿生学派[4]。通过模拟人类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联结主义试图使机器拥有智能。在人工智能研究兴起阶段,联结主义与符号主义各自沿着自己的研究模式前进。由于联结主义排斥符号主义,引发了同符号主义关于认知架构的学理论争[7]。20世纪60年代,联结主义在与符号主义对项目和资金的残酷竞争中失败,导致联结主义陷入困境[6]。人工神经网络科学研究是联结主义研究的重要部分,但由于随着网络层数的增加,训练过程无法保证“收敛”曾严重受挫[5]。可喜的是,随着脑神经科学研究的进展,联结主义的研究也逐渐取得新的突破。直至2006年,深度学习技术瓶颈的突破,打破了深度网络难以收敛的局面。从此,深度学习迅猛发展,特别是号称“学习从零开始”的AlphaGo Zero,在通过几天的自我博弈后,将曾击败李世石的AlphaGo Lee打败,从而引发学界的震动。深度学习算法加上强大的计算能力,使得机器在一些领域拥有了超越人类平均水平的智能表现,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越人类智能甚至最终取代人的激烈讨论。
行为主义,也被称之为进化主义[4]。行为主义认为智能行为就是通过与环境交互对感知结果做出相应行为。基于控制论的“感知—动作”模式,行为主义希望能够通过模拟生物的进化机制,使机器获得自适应能力[2]。早期的行为主义研究着重在“控制论动物”的研制上[4]。行为主义认为从模拟动物的“感知—动作”开始,最终复制出人类的智能。20世纪80 年代,智能控制与智能机器人系统的出现,使得行为主义又登上一个新台阶。20世纪末期,行为主义正式提出了智能取决于感知与行为,以及智能取决于对外界环境的自适应能力的观点。作为一个新的学派,正式在人工智能研究的舞台亮相[4]。与联结主义一样,行为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处于符号主义光芒的掩盖之下。当符号主义走向衰落,行为主义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该学派终于同联结主义一样“从幕后走向了前台”[2],并且由于行为主义与传统观点的迥异而备受关注。
二、三大流派的比较分析
对于智能的不同理解,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与不同的研究方式。符号主义认为智能是基于逻辑规则的符号操作,人的认知活动是符号计算的过程[8]。可以说,通过程序对信息的处理实现智能活动是符号主义的研究方式。联结主义认为智能是脑神经元构成的信息处理系统,人类的认知是脑神经元运动的经验结果。大脑是由神经元构成的神经网络联结而成,通过模拟人类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信息进行处理,来实现智能活动是联结主义的研究方式。这两种研究方式可看作是人类智能中的两种主要思维能力:逻辑演绎与归纳推理,两种流派可以与这两种能力分别对应[5]。与两种流派相区别,行为主义认为智能就是通过感知外界环境做出相应的行为,认知活动是对外界环境“感知—动作”的反应模式。行为主义不重视对信息的处理,在与环境交互下,模拟相同智能行为的实现是其研究方式。
首先,符号主义认为智能是基于逻辑规则的符号操作,他们从“符号是智能行动的根基”出发,认为有机体是带程序的“活生生的机器”[9](P142)。“智能的核心就是根据某套规则作出理性决策”[10],符号主义对于智能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模拟人类逻辑思维去设计信息处理程序,对搜集到的信息符号化并按照程序进行逻辑处理,最后输出知识或行为完成智能的表达。符号主义主张功能模拟方法,坚信只要建立出一个通用的、万能的逻辑运算体系,就可以使计算机模拟人类的思维[4](P16)。作为智能的一部分,符号主义认为人的认知活动就是基于逻辑规则的符号计算过程。诚然,知识是对信息的积累以及重新组合,智能的基本元素是符号的观点同人类的逻辑演算能力相契合。符号主义学派曾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并被应用于实践,包括专家系统与机器定理证明等。从而在很长一段时间,符号主义处于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地位。但是符号主义的研究方式也被很多人所批判,最典型代表当属现象学哲学家德雷弗的批判,他认为符号主义对于智能的观点“完全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遗产”[6]。在他看来,符号主义研究者是企图绕过大脑和躯体,利用对行为的形式化去认知世界的本质的“最后的形而上学家”[11]。现实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得万能逻辑推理体系将会面临无限多的形式系统。在智能活动发生之前,逻辑运算体系就已经建立好了,同人类相比,符号主义实现的智能行动中,心灵仿佛没有了自我创造的潜能,虽然其中的心理学派将心灵也视作一个计算系统[9](P10)。但正如批评者所认为的,在信息处理任务中,心理学派忽略了基础的、无意识的方面,并且将模式匹配这一对算术来说至关重要的因素看作理所当然,从而使得科学性相对缺乏[9](P13),并且模块理论家们认为对于“较高层次的心理过程”无法进行详尽的解释[9](P13)。同时,由于注重智能对信息的逻辑运算结果,而不注重对信息的归纳总结,从而引起了联结主义的强烈排斥,与联结主义形成了很大的理论分歧。
其次,联结主义认为智能是脑神经元构成的信息处理系统,他们认为大脑是由神经元构成的神经网络联结而成,而人类智能的实现过程就是通过神经网络中神经元之间的交互而实现,所以智能是大脑神经元组成的信息处理系统。联结主义通过对神经网络模型的建立来实现对大脑的模拟,同符号主义不同,联结主义主张结构模拟,他们认为智能行为同功能与结构紧密相关[12]。联结主义通过模拟人类神经系统的结构功能来实现对智能行为的模拟,认为相互连接的人工神经网络中,通过对传递规则、连接权重以及阈值的设定进行运算形成认知的基础,动态变化的连接权重能够在不断训练中实现对情境认知效率的提高,这些正是“形而上学”式的符号主义所缺乏的[7]。所以相对于符号主义的“认知就是计算”的观点不同,联结主义认为人类的认知是脑神经元运动的经验结果[8]。近些年来,由于大数据技术的出现,通过深度学习等技术,联结主义对于知识结构的分析获得了较多成果。深度学习算法运用多层神经网络,以无监督学习的方式,通过对数据特征的逐层递归使得学习结果获得质的飞跃[13],可以视为是对人类归纳推理能力的“再现”,这种自下而上的范式,更加容易实现实践领域上的应用价值。于是,在符号主义逐渐衰弱的时候,联结主义的发展似乎一路高歌猛进,在模式识别、游戏博弈甚至艺术创作方面都获得了超越人类正常水平的表现[5]。德雷弗斯在晚年也曾对联结主义表达过期待,认为联结主义与符号主义的还原论传统不同,他们将自己视为整体论的神经科学[9](P418)。但是由于联结主义依赖于人类对自身脑神经系统的了解程度,而目前人类对于大脑的结构并未有了解透彻,其对人脑的模拟程度被现有神经科学水平所限制。况且,整体性的人类生命远远不只有人脑神经网络[2],所以对人类智能实现“真正”模拟依然任重道远。
最后,行为主义认为智能是通过感知外界环境做出相应的行为。智能行为就是通过与环境进行交互,从而对感知结果做出相应反应。对外界信息的交互感知,是行为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行为主义根据“感知—动作”型控制系统模拟人对行为的控制与实现,认为相同智能水平上的行为表现就是智能,而并不需要知识、表示与推理,所以对于认知活动,行为主义认为是对外界环境“感知—动作”的反应模式。行为主义主张行为模拟,认为只有在真实环境中的反复学习,才能够最终学会在复杂的未知环境中处理问题。基于“感知—动作”型控制系统,行为主义利用感应器对外部情景进行信息感知,模拟生物体在该情景中所表现的反应,通过从感知到动作的映射规则,力图使智能体在相同情景下产生相似的经验行为。与联结主义一样,行为主义也认同功能结构同智能行为的密切关系[12]。他们通过仿生学原理,模拟生物体结构制造出机器人,用其进行对生物体行为的模拟。由于行为主义的经验主义表现[2],在智能的实现过程中,不存在符号主义里无限的形式系统的尴尬,也不像联结主义那样需要对人体结构极度透彻的了解。它只需要智能体通过“感知—动作”型控制系统,以进化计算或强化学习的方法,通过对外部感知而做出的反应进行进化和学习,同时找寻合理的协调机制对智能体内部进行自我协调与主体间协调[14]。其中,自我协调使主体内部每一模块之间避免冲突,主体间协调通过多个主体之间进行交互,避免主体间发生的死锁或活锁情况,如此即可使智能体的自适应行为逐步进化。与符号主义及联结主义相比,行为主义不再执着于“内省式”的沉思,而是在与外界交互过程中用具体行为去拥抱真实世界。行为主义同样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范式,相比联结主义,行为主义无形中应和了德雷弗斯对于人工智能发展所表达的“身体—情景—心智”的整体性观念[6],使其在实践领域中更加具有应用价值。然而,从单细胞生物进化到人类的时间相当漫长,行为主义的自适应机制想要通过进化实现出具有人类智能的机器,或许路还要很长。
三、启示
对于当前发展得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均表达关切,可以说学界呈现出喜忧参半的心态。通过对人工智能三大流派的比较和分析,或许对这些关切可提供有价值的回应或启示。
首先,人工智能实实在在地延展了人类认知。基于对智能的理解不同,三大流派对“认知”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符号主义是对人类逻辑演绎思维的模拟,联结主义对应的则是人类归纳推理思维的再现。二者的研究成果都是模拟人类智能的产物,无论是“认知就是计算”还是“认知是脑神经元运动的经验结果”,其运行方式与人的颅内认知方式有相同之处,逻辑演绎与归纳推理是人类智能中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5],即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的研究成果使得延展认知从理论上成为可能。符号主义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能够帮助使用者迅速获得对象的必然性规律,联结主义通过无监督的方式获得数据分布式特征的强大能力,能够帮助使用者迅速获得关于对象的特征属性或一般性结论,两者够帮助人们快速适应各种工作,其效果远超“奥托的笔记本”[15]。从控制论出发,大脑以外部神经为媒介控制身体进行各种活动[16],人机接口技术的实现可以认为是行为主义与联结主义的共同成果。通过将人脑神经细胞的“碳基”同计算机的“硅基”联结从而实现“人机合一”[17],使得延展认知在事实上成为了可能。计算机与人类自身的认知系统共同构成认知的载体来对环境进行认知活动[18],通过人机接口技术,在认知活动中实现人与机器的“合体”,共同完成认知活动。“延展认知”论题虽自提出就备受争议,基于信息技术的认知延展却可以为延展认知的哲学假说进行辩护[19]。“人在以世界为背景的情景中与技术打交道”[20],通过信息技术与人机接口技术,心灵的边界将变得更为模糊,身体、大脑、环境、技术、社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相互融合的“智能体”[19]。人类认知的延展使人类能够更加便捷的面对世界。
其次,对人工智能的技术悲观主义态度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仍显过早。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人工智能会带来巨大技术风险,甚至担心会将人类取代[21]。通过对三大学派的分析与比较可知,三大学派在对机器实现人类智能的道路上各有困境。多样而复杂的现实世界,使得符号系统无法周全地完成万能逻辑推理体系,从而开始走向衰落。逻辑演绎并非人类智能的全部,对符号主义而言,非逻辑思维是其无法实现的障碍;对人类直觉思维、情感思维以及联想思维等的模拟,是符号主义的“短板”。联结主义深度学习技术的突破大概成为当前人们担忧人工智能技术的主因,“AlphaGo Zero”通过自我博弈打败了它的“前辈”,从而加重了人们的技术恐慌。但是,联结主义的深度学习算法是通过“多层神经网络”对大脑结构功能的模拟,从而实现智能行为输出的,受限于人类对于自身脑神经的有限了解,当前的深度学习并不能完成对大脑结构功能的真正模拟。技术理应是更好满足人类生存需求的东西,对自身生命密码的探索,一直是人类不懈的追求,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彻底了解了自身的生命密码,到时设计一个具有同自身相当的智能体来或许风险亦已不存在。行为主义由于自适应机制在应用中的实用性受到重视,但智能的进化道路极其漫长,通过模拟生物的进化而实现人类智能尚需很长一段时间。符号主义已经式微,联结主义与行为主义要充分实现人类智能尚需很长时间才有可能,故技术悲观主义者对人工智能的担忧略显过早,而且这种过度担忧,某种程度上会迟滞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或许某一天人工智能真的可以超越人类,但也许就在这个时间区间,人类必定已经寻找到了与其和谐共处的方式。
最后,人工智能各流派的融合发展是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趋势。德雷弗斯认为,处于某种情境之中的智能体才是真正的智能[6]。那么智能的真正实现必须是一种在某种情境中的具身认知,是一种在“身体—心智—世界”相互交织的关系中实现的智能[6]。人工智能三种学派的研究方式各有优劣,“精确性”可以通过运用规则、符号进行表征而获取,但“灵活性”却需要通过统计性描述才能得到[7]。三大流派的方法可以说各有所长,符号主义擅长知识推理,联结主义擅长技能建模,行为主义擅长感知行动。三大流派中的算法也各有优劣,通过相互融合,可以取长补短,获得更高级的智能表现,例如模糊逻辑算法与遗传神经网络等,通过不同算法的融合获得了比原来算法更好的性能[3]。事实上,三大流派并非真的泾渭分明,譬如符号主义在联结主义方案中仍然大量存在[6],“人机接口”更是行为主义与联结主义相互融合的典型例子。从当下发展现实来看,人工智能若想要在“身体—心智—世界”交织关系中,对人类心智进行整体性关系框架的模拟,联结主义、符号主义、行为主义三者的融合发展,是其未来发展的趋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