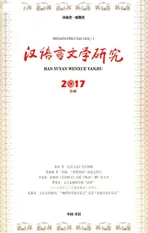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事实的历史
——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2017-12-10王富仁遗作
王富仁 遗作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事实的历史
——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王富仁 遗作
一
如果我们不怕过于绝对的话,完全可以说,樊骏先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莫不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史,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事实的演变史。我们用“民主”“科学”的思想阐释“五四”时期的文学,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概括上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大文学派别的文学,用“无产阶级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小资产阶级文学”或“左”“中”“右”概括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用“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说明解放区文学,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概括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文学,好像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作家文学思想变化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更细致地感受这些 “文学的思想”,实际它们又不是真正“文学的”思想,尤其不是文学作家自己的“文学的”思想,而更是政治的思想、政治家的思想,即使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创作方法的观念,也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是作为一种文学概念从西方文学理论中直接移植过来的。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它们更属于外在于中国作家主体的“客观”的思想、“科学”的思想,更是西方的文学史家或文学批评家从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并用于分析和评论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的,而不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与此同时,我们所用来概括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事实的这所有的文学概念,因为多数都是政治家的思想或政治化了的思想,所以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这种特征突出表现在两点:其一是绝对对立的排他性,其二是层次分明的等级秩序。而这两点,都是和真正文学的思想背道而驰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套用政治教科书中表示物质和精神关系的那种表达方式,我们完全可以说,在文学和文学观念、文学理念、文学思想的关系中,文学始终是第一性的,而文学观念、文学理念、文学思想则是第二性的。文学观念、文学理念、文学思想必须是从对文学、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感受和理解中产生出来的,而不能仅仅是为了实现某种非文学的目的而对文学提出的主观要求(不同的读者向文学提出不同的要求是无可非议的,但文学能否满足读者的这些要求则是另外一回事情,因而它不能成为文学创作的根据和评论文学的标准)。而文学,不论是旧文学还是新文学,不论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只要是文学,就既不等同于政治宣传、道德说教,也不等同于思想认识和理性判断。政治宣传、道德说教是直接指向行为的,是在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思想认识和理性判断是直接指向人对事物的认知的,是在认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文学需要的则是人的心灵感受和体验,既不是为了知道当下应当怎样做,也不是为了知道当下应当怎样想,而是为了感受到某种过去未曾感受过的事物或情景,体验到某种过去未曾体验过的情景或过程。文学,不论是悲剧的还是喜剧的,不论是抒情的还是叙事的,都是能够使读者从平时的、常态的、习惯性的、有规律可循的现实生活情景和心境中脱离开来,从而进入文学作家以语言的形式虚拟出来的一个新的有意味的情景或过程中,以获得一种新的感受和体验。对于人类的政治意识、道德意识和理性认识,文学与其说是一个进仓的过程,不如说是一个清仓的过程,它让人暂时忘却平时堆积在自己心头的所有记忆、所有思想、所有喜悦和烦恼,而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一样,仅仅带着自己的心灵,跟着文学作家的语言的魔棒,进入到他为读者所创造出来的文学世界之中去。但这个过程又是一个有限的过程,是必须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来的过程,而绝对不能是一个有去无回的过程。至于他从文学阅读中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有了什么变化,是包括读者在内的任何人也无法说清的。正是因为文学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个新的心灵感受和体验的对象,所以文学与文学永远不是二元对立的,不是相互排斥的,杜甫的诗排斥不掉李煜的词,曹雪芹的《红楼梦》排斥不掉施耐庵的《水浒传》,欣赏鲁迅小说的人同样可以欣赏张爱玲的小说,喜欢戴望舒的诗的人同样可以喜欢艾青的诗。文学家与文学家相互排斥的事情是常有的,但那绝对不是他们的作品之间的相互排斥,越是成功的文学作品越是能够相互兼容,相互沟通,因为它们可以成为一个文学读者的不同的感受和体验的内容。恰恰相反,如果从文学阅读来考虑,我们就会知道,文学除了排斥所有的伪文学(瞒和骗的文学)之外,同时还排斥所有干扰读者进入一种新的感受和体验过程的非文学的因素,其中也包括僵固在读者头脑中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道德观念、思想观念等等(当然,这种排斥也是暂时的,它们会在文学阅读过程结束之后重新到读者的意识中来“登记”,从而也为它们以变化了的新形式出现提供了可能)。在我们的观念中,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好像都是一些文学质量的标签,并且越是后起的越是先进的、优秀的,越是在前的越是简单的、粗糙的。实际上,即使在西方文学史上,这些前后继起的创作方法也只是文学创作自身形态的变化过程,并不是文学作品质量高低的鉴定标准。在任何创作方法的基础上,都有可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也都有可能产生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文学作品的质量不是由文学作家的主观愿望决定的,更不是由一个作家的文学理念决定的,如若如此,我们当代所有的文学教授就都可以成为比曹雪芹、鲁迅、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更加伟大的作家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是由文学作品本身决定的,是需要历代读者的重新阅读,重新感受、体验、阐释和研究的。与此同时,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还与不同读者的不同感受和体验有关,即使同一个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境域之中,也会有不尽相同的感受和体验。在文学的世界里,是绝对不可能建立起像政治官僚之间那种明确而又严格的等级关系的,我们的文学研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文学的世界。企图用一种文学观念、文学理念、文学思想代替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事实的具体细致、不断深入的独立研究,不但是不可能的,还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必须意识到,在中国古代社会,向来就没有为文学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而创造的一套相对系统的文化理念、文学理念和文学思想,中国文学向来是被作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学说的附庸而看待的。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道德学说就像一个饺子皮,把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化都包了进去,成为一种拥有绝对霸权地位的文化,它的判断标准也就成了判断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一切事物的是非和优劣的最高标准。中国古代也有各种不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但都不是从文学的视角感受和理解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文化的,所以并不具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性质,而更多停留在方法论和技巧论的层面。这不但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温柔敦厚”的“艺术特征”,也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文化专制主义制度。在这种文化制度中,国家政权不必经过任何具有法律性质的事实举证,只要从文学作品中找出只言片语甚至一个字的用法、写法,就可以直接治人死罪。中国古代文化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即当时绝大多数的社会群众没有文化(不是书面文化的接受者和创造者),所有书面文化包括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读者都是知识分子,并且大都是官僚知识分子。这些官僚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是辅佐皇上治理整个国家,是负有维护国家现实政权的稳定性的政治责任的,而文学则更是他们的“个人之事”,是他们个人才能的表现形式,充其量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方式(面向更广大社会群众的文学在当时是通俗文学,是不登 “大雅之堂”的,它们的作者和读者更不需要较为统一和系统的文学思想)。对于这些官僚知识分子,文学自然没有与国家政治相提并论的资格,文学自然不能违背国家意识形态的那些基本思想原则,所以文学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性,文学家也不可能有完全超越国家意识形态的独立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这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才有既不完全从属于政治、也不完全从属于科学的文学和文学的思想。这当然是因为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归根到底,仍然与那时的具体文化“情势”有关。整个“五四”新文化,就不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发动起来的,但也不是在反政府党的领导下发动起来的,而是由几个有了世界文化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己搞起来的。他们都不是官僚知识分子,因而也不负有维护国家现实政权的稳定性的职责和义务,与当时的国家政权和官僚机构没有主与从的关系(只有鲁迅在当时供职于教育部,但他不是以教育部官僚的身份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即使在这些知识分子之间,也是一种平等联合的关系,而没有上下等级的主从关系。他们体现了中国现代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他们代表的是独立的个人,但这些独立的个人又是关心着整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命运和前途的,不仅仅是为了施展个人的才能,也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情感交流,这就使他们的文化创造及其思想具有了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具有了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性质。在这里,由于各自关注对象的不同,又有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其一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倾向,其二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学院知识分子的学术(科学)思想倾向,其三就是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学倾向。这三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实际体现了三种不同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彼此虽然有联系,但却是相对独立、无法通约的,因而也不能像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学说那样,用一个将其它两个完全包起来,成为一家独大的思想,成为一种新的专制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说,“五四”之后,在中国社会实际已经有了三种不同的文化,也有了三种不同的思想:政治和政治的思想、科学和科学的思想、文学和文学的思想。文学和文学的思想正式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出现在中国社会上。其独立性的基本标志就是:它既不能完全代替政治和政治的思想、科学和科学的思想,政治和政治的思想、科学和科学的思想也无法完全代替它。磕磕碰碰乃至相互撕咬是常有的,但一个完全吞掉另外一个是不可能的。
二
从理论上来说,构成“五四”新文化的这三种不同的文化倾向是完全平等的,各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也各有其独立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但在中国现实的社会条件下,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不论在任何社会制度之下(奴隶主义的、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都是覆盖整个社会的,因而国家政治的思想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子游语)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无所逃遁的思想,若说普世性的价值,它也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它不但能够覆盖整个社会,而且对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强制性的约束力量。中国古代的隐士在口头上可以不承认政治,但在行动上却不能不服从国家政治的管辖;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定政治的,但同时也必须承担政治权力的直接压迫。国家政治的这种高覆盖率和强制性的力量,也决定了革命政治的基本特征:它必须首先将自己提高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然后才“有可能”发挥自己改革社会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如果说国家政治是现实性的,革命政治则是理想性的;如果说现实性的国家政治主要依靠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以保障其政治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不能仅仅是一些空头支票或标语口号,革命政治则主要依靠宣传,从而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唤起社会群众的追求热情并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参加者或拥护者。但不论是国家政治还是革命政治,在中国现实社会都会有极大的覆盖面,并且二者经常处在此消彼长的变化态势之中,在各自的范围内也是具有政治权力的强制性的。完全自由的政治团体是没有的。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科学和文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只是极少数现代知识分子的事情,在更广大的社会范围中,还是只有政治的意识、国家的意识,还是仅仅依靠政治上的妥恰性(只要在政治上感到是妥恰的,他就认为一切都妥恰了)。在中国,政治不但是社会教育的基础,也是社会教育的目标,甚至连阿Q这样一个穷苦的无业游民,也是“无往而不合于圣道”的。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只有笃信科学的人才有,在他们的意识中,科学的真理是绝对的,所有那些不科学的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都是不可信的,因而也是不真实的:任何强权都无法战胜真理,任何的主观愿望都无法代替真理;文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只有热爱文学的人才有,在他们的意识中,文学,伟大的文学才是人世间不可征服的力量。不论你对他讲了多少政治上和科学上的道理(文学的道理除外),他喜欢的文学作品还是喜欢,不喜欢的文学作品还是不喜欢,即使你因此将他送上绞刑架,也无法改变他内心的事实。热爱科学、热爱文学的人也生活在政治社会之中,也在社会政治的制约之下,在政治、科学、文学没有直接的矛盾冲突的条件下,他们和其他人都是一样的;但一旦政治与科学、文学处在尖锐矛盾着的状态中,这些真正忠诚于科学和文学的人,就与一般的社会群众不同了,他们就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文化立场乃至社会立场了。在中国现当代社会上,真正信仰科学和热爱文学的人都是极少数,但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到底是有明确性和直接实用性的,是为政治家和广大社会群众都不能视而不见的,所以在中国现当代社会历史上也有了更高程度的普及,越到后来,政治对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越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不像晚清保守主义官僚那么蛮悍地对待科学了。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化的一个显著的进步。文学,特别是新文学就不同了。直至现在,在整个中国社会上,文学读者,特别是新文学读者还是极少数,连学生家长和广大中小学教师都将文学作品、特别是新文学作品视为“闲书”,即使收入中学课本的那些少得可怜的文学作品(新文学作品只是其中一部分),也是作为升学考试所必须的“知识”来掌握的。中国社会极少量的新文学读者,其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也往往是在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和现实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和文学思想虽然从“五四”新文学产生之日起就已经成为一种区别于政治和政治思想、科学和科学思想的独立的文化品种,孕育着一种独立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但它的传承只能靠新文学作品本身的传承,新文学本身发展的不充分以及政治和政治思想无所不在的覆盖性、科学和科学思想的现实实用性,使新文学和新文学思想的传承即使在中国现当代社会也成为极其困难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认为文学和文学思想到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倾向和独立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是有鲁迅的文学创作及其言论作为实际证明的。实际上,鲁迅早在留日时期写的《科学史教篇》中,已经明确区分了科学和文学艺术的界限,并将整个西方文化史概括为由科学和文学艺术两种文化潮流相互激荡、相互促进,同时也相互区别、相互抵牾的历史。他针对中国知识分子(其实他们都是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只重视西方科学而无视西方文学艺术的现实,特别强调了文学艺术的作用。到了《文化偏至论》中,他又具体解剖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两种主要思想倾向,一种是片面追求船坚炮利、富国强兵的洋务派的思想,一种是片面宣传“制造商沽立宪国会之说”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而他提出的则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立人”思想。实际上,这种“个体的”“精神上”的人就是以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的人,是在整体社会联系中对构成这种联系的个人的精神特征的心灵感受和体验,任何“仅仅”在政治实践的需要中或在科学理性的概括中所呈现的人,丧失的恰恰是人的这种“个体的”和“精神的”特征,恰恰只是工具性的人,因而也是不完整、不真实的人。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介绍了“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西方摩罗诗人,他们的具体特征就是“为个人”“为精神”的,而不是“为集体”“为物质”的,他们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现实作用完全是他们个人精神的象征,而不是他们压抑了自我个性而刻意追求的社会效果(这类人也有,但这类人在文学家看来在精神上是残缺不全的,不给人美和崇高的感觉),正像公鸡要打鸣是其自然的本能,而人们可以作为司晨的工具一样。近年来,部分中、日两国的鲁迅研究者十分重视鲁迅从日本归国到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这个时期的思想的研究,并一致认为这“沉默的十年”是鲁迅精神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十年。其重要性就在于,这个十年是鲁迅精神十分苦闷的十年。但在这里,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恰恰应当是:鲁迅当时的苦闷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家的苦闷,也不是一个实业家的苦闷,甚至也不是一个科学家、学者的苦闷,而是个体的、精神的苦闷,是个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感受和体验到的精神的苦闷,因而也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文学家的苦闷。在迄今为止我们的政治家、历史学家的描述中,这个时期恰恰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而实现了中国社会由古到今的伟大历史转变的时期,是一个政治成就辉煌伟大、政治英雄辈出的时代;这个时期也是西方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乘机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其经济上的成就也是不容抹杀的;这个时期还是中国学术迅速发展、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得到确立、现代自然科学的传统正式形成的历史时期,王国维、章太炎、严复成为迄今为止仍然为人难以企及的第一流的学者和思想家。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的政治家、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没有理由将其描绘成为一个昏暗苦闷的历史时期。鲁迅的苦闷分明只是一个文学家的苦闷——个人的精神的苦闷,这使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文学作家,而与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思想特征: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相信地上本来就有路,自己则是找到了正确的思想道路的人;而鲁迅则始终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认为地上本来就没有路,路是靠人、靠自己走出来的。这也等于告诉我们,他不是一个政治家,所以也不会完全相信政治家替社会做出的现实的政治判断;他不是一个学者和教授,所以也不会完全相信学者和教授所讲的那些人生的哲理和社会的真理。他要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心灵感受,并认为人的最可靠的思想是在自己的心灵感受和体验的基础上所体悟出的那些东西。总之,他是一个文学家,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本身就是文学的,而不是政治的、科学的,这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他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分头发展:陈独秀、李大钊成了职业的革命家,胡适成了更加纯正的教授和学者,鲁迅则更是一个文学作家——学者、教授对于他则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三
上世纪20年代的文学,除了鲁迅、周作人的作品更加丰满和老辣之外,其他所有人的作品,包括胡适的《尝试集》在内,都无法掩盖其单纯和幼稚,其多数作品甚至还可以说是粗糙的。但就其文学谈文学,这个时期的作品却显得更加纯正和真诚,这是因为当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大都是涉世不深的青年,其中很多还是在校的青年学生。但在这里,我们却更能清楚地看到文学和文学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特异性。为什么这些涉世未深的小青年的作品反而表现出更加纯正和真诚的文学性呢?因为他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被政治化和学理化,他们观念中的政治和学理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些耳食之言罢了,并没有形成他们裁判社会和人生的固定的标准和尺度,他们对现实世界和社会人生的态度还是建立在直接感受和体验的基础之上的。尽管浅,尽管更是个人之事、身边之事,尽管带着点无病呻吟的特征,但却不假,更不装腔作势、故作高深,一副教师爷的派头。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一套成熟的人生哲理要宣扬,没有一套深厚的社会理论要表现,其作品也具有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呢?其意义和价值又何在呢?如果我们也运用一下科学概括的方式,就会感到,它们体现的其实是人对爱与自由的真诚渴望与追求。人除了物质欲望的要求之外,在精神上还有什么必不可少的东西呢?那就是爱与自由。人从呱呱坠地起,生命必需的物质欲望是由父母、首先是母亲满足的,为什么父母会主动满足他生命必需的物质欲望呢?因为他们 “爱”他,在精神上需要他,他们满足他生命必需的物质欲望不是为了扩大内需,也不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爱是本能的,是不求回报的(儒家伦理道德用“养儿防老”的思想破坏了这种爱的真纯性,因而也不反映父母、特别是母爱的基本特征)。正是因为他们的爱是不求回报的,所以他们也给子女成长和发展的充分的自由。也就是说,人从幼儿起,甚至连生命必需的物质欲望的满足,也同时表现为被爱与自由的感觉,就已经能够实际地感受到爱与自由的幸福和无爱与不自由的痛苦了。这就是人性,就是人性中的必有之物,同时也是人不断成长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人是在不断渴望并追求着爱与自由的过程中成长的,并在直感直觉中感到,能够给予他爱和自由的事物是美的事物、崇高的事物。实际上,这就是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一种文化形式的根本原因,因为人在文学、特别是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所获得的,恰恰就是这种爱与自由的感觉,就是这种美与崇高的感觉,同时他也愿意将这种感觉传达出来以让别人也产生这种感觉。人早在成为政治的动物、经济的动物、理性的动物之前很久很久,就已经成为各种形式的文学的接受者和一个潜在的或实在的创作者了,文学也成为他们成长和发展的文化的阶梯,并且能够伴随他的终生,成为他精神生命的有机构成因素。这也就是鲁迅之所以将文学与“立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原因。
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家的鲁迅,却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只是一般地感受到当时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只是一般地感受到当时国家政治的黑暗和腐败,他同时也实际地感受和体验过洋务派官僚为了富国强兵而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上所做的努力,实际地感受和体验过中国的革命者为了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他是在经验了这一切之后而走向文学和文学创作的道路的,他是在承认所有这一切的相对合理性,但也知道它们在中国社会所遭遇的困境,以及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之后,而认识到文学的独立价值和意义的:科学和科学思想是重要的,但不是建立在对爱与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基础上的科学和科学思想将是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最严重的欺骗;经济与经济的发展是重要的,但不是建立在对爱与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基础上的经济与经济发展,将是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最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国家和国家政治是重要的,但不是建立在对爱与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基础上的国家和国家政治将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最可怕的杀人机器;革命和革命思想也是重要的,但不是建立在对爱与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基础上的革命和革命思想将导致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最无节制的破坏和杀戮。“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文化偏至论》),而在各种利益冲突、权力争夺的社会矛盾中能够传承和传播这种爱与自由的福音的,到了近现代世界上几乎仅仅剩下了文学艺术,特别是文学。瞒和骗的文学不是没有,但真正能够在人类社会上持续发挥自己的精神影响作用的,却只有那些传播着爱与自由的福音的优秀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但对于上世纪20年代的青年文学家,世间的一切都还只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各种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些人生道路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是作为一种整体的、客观的、抽象的、理性的判断形式而存在的,而在这种判断背后起作用的,仍然是传统儒家那种大而化之的拯世救民的社会理想。他们更是在现象的层面看待文学与各项社会事业的关系的,其中也不无个人成名成家、出人头地的思想因素在起作用,其对文学,特别是新文学的看法实际还是零碎的、不完整的,并且与其它各种相关与不相关的思想观念混杂在一起。这使他们无法像鲁迅那样,始终如一地从对爱与自由的真诚渴望与追求出发,亦即从文学、新文学的立场出发感受和体验现实社会及其浮动与变迁,他们对文学的追求还缺少佛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精神上的“定力”,西方大量现成的文艺思想学说作为庄子所说的“成说”也严重干扰了他们对自己文学道路和历史使命的切近而坚实的思考。与此同时,这些青年文学家大都还停留在自爱向他爱转化的人生阶段。人的精神发展总是从被爱的感觉出发的,只有在被爱的基础上首先感觉到被爱的幸福,然后才有可能(但却未必)希望别人同样能够感到被爱的幸福,从而主动地施爱于人,施爱于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自由的感觉也是这样。从个体的爱与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向普遍的人类爱与自由的渴望与追求转化,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漫长的过程,是在连续不断地自觉追求和努力中进行的,同时它也是一个容易迷失自我的人生过程(这也是中外历史上文学作者极多而真正称得上伟大作家的人却极少的主要原因)。这一切都导致了上世纪20年代青年文学家文学观念上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整个中国社会思想的不自由状态更成为他们难以挣脱的有形与无形的桎梏。我认为,作为上世纪20年代文艺思想的终结的,就是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创造社、太阳社的诸君子们,就又一次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完全合并到政治之中去,并且将裁判文学、文学作家的权力完全交给了政治家。包括鲁迅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能够阻止创造社、太阳社的这样一个出让行动,这说明包括鲁迅在内的所有人的文艺思想在迄今为止的中国社会上,都是没有真正的力量的,因而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也没有直接的说明性。这到了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就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形式:政治的价值和意义重新被确定为整个中国文化的总价值,科学的价值和意义与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则是从属性的,是以对政治的作用和意义得到承认和衡量的。虽然在其思想具体形式上,已经由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学说,演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在其本质的特征上仍然属于一种思想定乾坤的儒家文化传统,它也把儒家文化绝对的排他性和严格的等级秩序重新带入到文学和文学研究中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文化结构形式被推向极致之后的一种变形表现。在这里,存在的仍然是文学社会职能的特殊性的问题。
毫无疑问,文学是有其社会职能的,但即使其社会的职能也必须首先表现在个体的精神世界里,而不会直接进入群体的物质实践过程之中去。郭沫若的《天狗》之所以是一首出类拔萃的新诗作品,就是因为它是诗人个体的精神的表现,是没有直接的现实性的,它把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推向了极致,同时这也是个体精神向崇高性的一次冲刺行动。但如果这首诗改写成“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胡适来吞了,/我把鲁迅来吞了,/我把茅盾、郁达夫、叶圣陶来吞了,/我把新文学来吞了,/我就是我了”,这就不是一首好诗了,因为它表现的已经不是诗人的个体精神,而是诗人的物质欲望,形式上好像都是对个体自由的追求,但性质变了。实际上,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子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绪,已经不是文学的思想情绪,甚至也不是革命的思想情绪,而只是在权力欲望极盛的中国社会上一种个人独占欲望的不自觉的流露罢了。---作为一批青年文学家企图超越文学前辈独领中国文化风骚的一次莽撞的文化造反,是应该谅解也必须谅解的,但因此而在中国文化界以新的形式所复活的这种极为陈旧的文化理念,以及在这种文化理念的长期统治下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却是令人无法漠然视之的。与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子相比,鲁迅在政治革命运动面前的态度就要冷静得多、客观得多了。在鲁迅一生的文化活动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现实社会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行为的揭露和攻击,但这并没有使他将整个身心都无条件地投入到任何一次政治革命的行动之中去。在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在当时革命青年的“鲁迅往哪里躲?”的呼声中,他却说“我还要看一看”。在蓬勃发展的革命势力面前他还要看什么呢?我认为,他要看的恰恰是一个文学家应当关心的,即这些革命者要争的是原来的统治者手里的政治权力呢?还是中国人的爱和自由的权利呢?这使他即使参加左翼文学运动之后,都没有因为政治革命而丧失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敏感。他反复告诫左翼作家不要以为革命胜利之后工农政权就会让他们吃牛油、面包,他始终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而关注着中国政治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变化的:他关心政治,但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不轻视政治,但更重视文学。——他是个文学家。
四
只要我们在政治与政治思想、科学与科学思想、文学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中考虑问题,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大陆“文革”文化向新时期文化的转变,实际更是中国知识分子通过科学与科学思想打破政治与政治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带来的“思想”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是有其象征意义的:一个文学作家通过科学研究成果的独立价值和意义而颠覆了政治思想的唯一性与权威性,从而也打破了政治与政治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并曲折地传达出作者对思想自由的渴望。但是,这里的独立性仍然表现为“思想”(科学、理性)的独立性。“哥德巴赫猜想”的价值和意义仍然是一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客观价值,陈景润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是通过“哥德巴赫猜想”这个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客观价值体现出来的(假若他是一个阿Q,他还值得同情吗?)。在当时的文学界,首先流行的还是“第二种忠诚”的观念,显而易见,忠诚、第二种忠诚、不忠诚,仍然是在“政治”立场上立论的,仍然属于政治的思想。从总体而言,新时期早期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也莫不立足于政治,好像政治兴则万事兴,政治废则万事废,过去的错误仅仅是政治路线的错误,现在的正确也完全取决于政治路线的正确。这种政治决定一切的观念,不但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同,也与中国古代的思想观念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到了后来,五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才逐渐在思想文化领域占了“上风”,并与依然覆盖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政治思想发生了多方面的矛盾和摩擦。但是,直至那时,文学和文学的思想仍然只是作为社会思想的一翼——社会科学的一翼而得到承认的,还是作为五四“科学、民主”的“思想”传统而受到重视的,甚至连我们文学研究者自己,也很少有人把文学和文学思想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作为一种与政治和政治思想、科学和科学思想具有完全平等的文化地位的独立文化力量而看待(直至现在,很多文化名家仍然经常说鲁迅只有破坏,没有建设。难道他的文学作品不是一种“建设”吗?对于一个文学家,除了文学作品之外,你还要求他“建设”什么呢?)。这也孕育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新的危机:有了西方那么多先进的哲学、社会思想学说和文学理论,我们中国现代文学还有什么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呢?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意识到的“文学边缘化”趋势已经曲折地折射出这种新的危机的到来。时至今日,当我们仰望着我们这个“崛起的大国”的GDP数字的时候,好像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已经黯然失色——我们的文化观念里已经没有文学,更莫提中国新文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在“五四”之后,即使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间,即使到了现在,我们的文学理念都是极其混乱的,我们按照这种极其混乱的文学理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不是越研究越混乱吗?实际上,新文学的理念、新文学的思想,绝对不在新文学的外部,而就在新文学的内部。鲁迅《阿Q正传》的思想就在《阿Q正传》这部作品中:你感觉到了它的思想意义,它就有了思想意义;你没有感觉到它的思想意义,你就不知道它存在的根据,你就不知道它的思想意义。同样,你感觉到了曹禺《雷雨》的思想意义,它就有了它的思想意义;你没有感觉到它的思想意义,它就只是一些汉语字词的杂乱堆积,你就不知道它的思想意义。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观念,理应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事实的感受和理解、研究和分析抽象出来,并用以分析和评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的。它不但不会完全等同于中国和外国政治家的思想学说、中国和外国现代社会科学家的思想学说,甚至也不等同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自己对自己作品的认识和评价。樊骏先生没有正面论述过这个问题,但从他的全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论述中,我们仍然能够清晰地感到,他首先重视的不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文学观念,也不是他们信奉中国和西方哪些文学理论家的思想学说,而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发生的那些真实的文学现象以及这些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方法的问题,他不满意那种从理论到理论的推理性论述,而提倡用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事实说话。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现代文学事实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文学观念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文学观念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事实的一部分,而不能代替对中国现代文学全部历史事实的叙述和研究。——我认为,这应是樊骏先生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念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
【责任编辑 穆海亮】
编者按:樊骏先生在世时,王富仁先生就给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布置了一个课题:研究樊骏先生的学术工作。学生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但王富仁先生还有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即撰写专著《樊骏论》。樊骏先生去世后,王富仁先生相继发表了《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学科魂——〈樊骏论〉之第一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期)、《中国现代文学:它的存在就是它的意义——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樊骏论〉之一章》(《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1期)等文章,这些文章即《樊骏论》的部分章节。王富仁先生去世后,家属在他生前使用的电脑里发现了《樊骏论》的未完稿,共计23万多字。为纪念王富仁先生,同时也为纪念对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多有扶掖的樊骏先生,本刊特征得王富仁先生家属授权,发表《樊骏论》的未刊章节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事实的历史——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王富仁(1941-2017),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