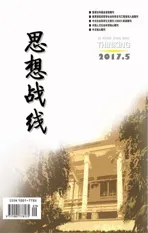身“体”与意“识”:中西方绘画的写实方式
2017-04-11
身“体”与意“识”:中西方绘画的写实方式
刘连杰
20世纪以来,在物质救国的紧迫形势下,理论界逐渐形成了“西画写实,中国画写意”的误判,遮蔽了中国画的写实成分,尤其是中国画的写实方式。实际上,写实是中西方绘画的共同追求,但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它们分别形成了各自的写实方式。西方绘画注重理性主义传统,强调理性对视觉经验的整理,试图对视觉经验进行“科学”地表现,重在意“识”之实。而中国画注重“根身性”,认为视觉经验是身体经验的一部分,强调将视觉经验放入整体的身体经验中来表现,重在身“体”之实。从这一角度来讲,中国画对视觉经验的处理无疑要更加全面,更加合理。
绘画;写实方式;身 “体”之实;意 “识”之实
明末以来,西方绘画不断涌入中国,在刺激国人视觉神经的同时,也逐渐开启了对中西方绘画性质的理论思考,至20世纪初,更是掀起了一场中国画大讨论。这本是一个极其自然的文化交流现象,但在物质救国的紧迫形势下,却形成了“西画写实,中国画写意”的误判,不仅遮蔽了中国画中的写实因素,更是遮蔽了中国画独特的写实方式。百年之后,随着各种理论反思的日渐成熟,对中西方绘画写实问题的探讨也应该被提上日程。
一、“写实”概念在中国画论中的出场及其影响
“写实”概念本非中国画论所固有,而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西方艺术理论范畴,对其意义的理解也有一个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最早将“写实”概念引入中国,与“理想”相对,作为一般性的小说分类标准,即“理想派”和“写实派”,后来还明确表示汉乐府中的《孤儿行》已是“写实派正格”。*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84页、第3952页。受梁启超影响,1908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将“文学及美术”分为“理想与写实二派”,并据此分析中国的作品。可见,在他们那里,“写实”概念并非西方艺术所专有,且不与“写意”相对,而是与“理想”即“虚构”相对。*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页。不过,梁启超将“写实派”称为“科学的文学”,并倡导“科学化的美术”,*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974页、第3962页。大力推崇西洋的赛先生,王国维认为“摹写精能,欧美发明之术”,*周锡山编校:《王国维哲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25页。中国画“绘影绘声则有所短”,*郎绍君,水中天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8页。说明在他们心目中,“写实”虽非西方所专有,却也为西方所专长。
如果说,在梁启超和王国维那里,写实还只是一个风格问题,仍然是中性的概念,那么,到了康有为那里,则具有了价值上的褒义色彩。他认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郎绍君,水中天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21页。而始作俑者乃是文董之变。1904年,他在《意大利游记》中感慨:“基多利腻、拉飞尔,与明之文徵明、董其昌同时,皆为变画大家。但基、拉则变为油画,加以精深华妙;文、董则变为意笔,以清微淡远胜,而宋、元写真之画反失。彼则求真,我求不真;与此相反,而我遂退化。”*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7~378页。在此,康有为最早将“写真”与“意笔”对立起来,也就是将“写实”与“写意”对立起来,为后来“西画写实,中国画写意”的误判埋下了祸根。不过,康有为论画“以复古为更新”,重古今之异,而不强调中西之别,“写实”“写意”只是中国画内部的选择。在他看来,“写实”仅仅意指“专精体物”,“尽万物之性”,可以“黄筌写虫鸟鸣引颈伸足”为典型,因此认为“今欧美之画与六朝唐宋之法同”,*郎绍君,水中天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21~22页。甚至极尚“写实”的油画也可能是马可波罗从中国传至欧洲的。*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3页。不过,其“当以郎世宁为太祖”*郎绍君,水中天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25页。的观点确实也开启了中国画唯西画马首是瞻的先例。
康有为提倡绘画“变法”,而且有恢复古法之意,为中国画“写实”问题的探讨保留了极大的自由空间,而陈独秀则更为激进地要求“美术革命”,且专意中西之别,将“写实”明确归于西方,否定了中国画的写实传统,遮蔽了中国画特有的写实方式。其云:“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这里,中国画之所以要“改良”,就是因为它“专重写意”,而用来“改良”中国画的“写实精神”,他又特别强调是“洋画的”,这就明确作出了“西画写实,中国画写意”的判断了。尽管他也说:“中国画在南北宋及元初时代,那描摹刻画人物禽兽楼台花木的功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郎绍君,水中天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29页。但值得注意的是,用“近”来表达中西画法的关系,别于康有为的“同”:“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此近世欧洲之时代精神也。此精神磅礴无所不至:见之伦理道德者,为乐利主义;…………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新青年》1915年第1卷第2号。可见,所谓写实精神,在他看来,是西方近代所孕育出来的一种文化观念,此种观念断不可能为传统中国所有,即使有相“近”之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相比于陈独秀,蔡元培则更为具体,他用“科学方法”这一义项,将“写实”概念牢牢地锁定在了西方背景上,彻底否定了中国画的写实传统。其云“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像及田野风景……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不仅将“实写”与“洋画”并举,而且认为国人学画“非文人名士,任意涂写。即工匠技师,刻画模仿”。*郎绍君,水中天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37页。总之,没有半点写实。这样,“写实”概念的内涵便从康有为的“专精体物”演变为了“重视自然科学”,从一种宽泛的绘画风格演变为了一种特定的绘画技法。
更有甚者,在救国救亡的时代背景下,用科学原理造型甚至成了“真确一途”“真美之精神”,“本其天性所感触自然之景象”。*郎绍君,水中天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32~34页。从此,只有西画才有写实精神,退一步说,只有西画的写实方式才是唯一的写实方式,舍此绝无其他写实方式。这一“写实”观念,即使是对坚持传统的国粹派,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如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指出:“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郎绍君,水中天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67页。用中国文人画的“写意”来反对西画的“写实”,恰恰落入了“西画写实,中国画写意”的窠臼之中。他还将中国的“画家之画”类比于19世纪以来的西洋画,讥之为“照相”,这就完全忽视了中国画特有的写实方式。
总之,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画大讨论之后,对于“写实”“写意”的价值评判,各家立场虽有不同,但“西画写实,中国画写意”的观念却得到了各方认可。也就是说,只有用西方科学原理造型的“写实”才是“求真”,才是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中国画主要在于表现情感,尽管其中不乏真情实感,至多也只能算是具有面向现实的精神,但绝不是“写实”。即使是承认中国画中有写实传统,如康有为的“六朝唐宋之法”、徐悲鸿的“宋人尚繁密平等”,也是按照西方的写实标准遴选出来的,绝没有自己的写实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宗白华独树一帜,在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间曾多次提出西方绘画表现的只是“主观景界”,而中国画才是“全面的客观的”。*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页。这一观点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停留于对“写实”“写意”的简单选择上,而是从根本上触及了“写实”的标准问题,即中国画特有的写实方式。可惜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也未能引起进一步的探究。邵大箴在20世纪末也曾发问,“传统艺术中有没有写实的传统?倘若有的话,是不是仅仅是诸如‘宋人的繁密平等’之类的画体?”*郎绍君,水中天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下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738页。似有对中国画写实传统进行全面研究之势,可惜也未能展开。
21世纪以来,随着视觉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学者们对“西画写实”的研究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其立论方式主要是从视觉出发,认为“西画写实”主要是指视觉真实。这就为中国画写实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如果说西画写实主要是视觉写实,那么中国画是否可能是视觉之外的另一种写实呢?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形势显然不容乐观,人们不但没有能够意识到中国画特有的写实方式,反而从视觉的角度,进一步巩固了“西画写实”的原有观点,甚至还以此标准进一步歪曲了中国画的写实方式。如叶青就认为,中国画自战国晚期之后,便走上了视觉写实的道路。*叶 青:《应物传神——中国画写实传统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0页。从其举证来看,自然有其道理,但如果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对中国画来说,未免有失公允。
刘继潮试图用“视觉感受”和“视觉经验”这一对概念来表达中西绘画的差异,并从“本体之观”的角度全面论证了宗白华的观点,指出中国画乃是对自然“全面的客观的看法”。这对于中国画写实方式的研究自有其贡献,但遗憾的是,他依然保留了“中国式的写意”“西方式的写实”这一说法,未能彻底突破近代框架。究其原因,乃在于他所谓“写实”乃是指“视网膜映射的视域节选”,并认为这是“视觉的真实”;而所谓“写意”乃是指画家“不依赖单一的视觉”,而是“化之想象”“融以情性”“想象为之”,这是“艺术的真实”。*刘继潮:《游观:中国古典绘画空间本体诠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53页、第58页、第36页、第164页。这等于是从视网膜成像的角度为“西画写实”找到了更为具体有力的证据,而且西画对视网膜成像的复制已经达到了技术上的巅峰,中国画无从超越,只能回到抒发性灵的老路上下功夫,强调“写意”。
同样,李倍雷也试图用“视觉视象”和“视觉心象”这一对范畴来表达中西绘画的差异,并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证,但他同样认为,西画追求“视觉的真实”,而且“这种视觉的真实集中反映在素描、色彩、透视、光影明暗、结构、体积等观念与因素的具体运用于绘画而造成的视觉图像上”。*李倍雷:《中国山水画与欧洲风景画比较研究》,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6年,第75~76页。而“视觉心象”,顾名思义,自然也是“化之想象”“融以情性”“想象为之”,与刘继潮一样,落入了“西画写实,中国画写意”的近代框架之中,难以自拔。难道“西画写实”的定论真的就无法突破吗?难道中国画除了“写意”真的就别无他途了吗?
二、对“西画写实”的重新解读
在中国,很多学者喜欢用“辨证”的眼光看问题,认为中国绘画中也有写实的成分,西方绘画中也有写意的因素。尽管证据确凿,却无法掩盖中西方绘画的明显差异,而如何言说这种差异才是关键。当然,也有学者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西方绘画自印象派之后已经偏离写实路线,走向了写意,但这无疑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既使我们的探讨失去了中心,也不利于理解西方绘画发展的实质,更不利于思考中国画未来的发展方向。
为了对“西画写实”观念的探讨更具有针对性,我们不妨将问题集中在“视觉真实”上。之所以认定西方绘画达到了“视觉真实”,主要在于它用科学原理造型。我们不妨探讨一下“用科学原理造型”与“视觉真实”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科学”是否就意味着“真实”?这里我们以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法、明暗和色彩为例。
先说透视法。透视法由于符合光学成像与几何学原理,向来被认为是最客观的,具有无可反驳的“真实性”。但这一看法却在20世纪中期遭到了挑战,而且还是来自西方内部,例如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说:“透视法是由人发明的把被感知世界投射在他面前的一种方法,而不是世界的移印。”*[法]梅洛-庞蒂:《符号》,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8页。美国学者麦克卢汉也认为:“三维透视绝对不是自然的人类视觉。”*[加拿大]麦克卢汉,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这就是说,透视法尽管符合科学原理,却并不符合人类的自然视觉。例如,透视法对“近大远小”的强调,这在照相机的成像原理中可以成立,但在人类的自然视觉中却并不成立。除非两人相距特别遥远,否则在人类的自然视觉中,我们并不会觉得前景人物就比远景人物大,他们在感觉中是一样大的。17世纪中叶,荷兰有一位著名的画家扬·弗美尔,在他的画作中,“近大远小”的透视比例被安排得非常夸张,前景人物的大小可以是就在身旁的远景人物的4倍之多,这在当时的绘画界是难以被人接受的。但弗美尔其实并未违反透视法的原理,他只是让观察者向前景人物多走了几步,由于与前景人物过于“逼近”,因而导致其被“不正常”地放大,但这只是采取了“不正常”的立脚点,而并非“不正常”的透视法。他的画之所以难以被人接受,显然不是由于“不科学”,而是由于在人类的自然视觉中显得“不真实”。与其说他的画实践了透视法原理,不如说是在提醒我们透视法不符合自然视觉的“缺陷”。
也许有人会说,透视法的“真实性”在于精确地复制了视网膜映像,如上文提到的刘继潮就认为“西方式的写实”在于“视网膜映射的视域节选”。然而,视网膜映像并不就是我们真实见到的景象。凡是在我们视域范围内的景象都会在视网膜上有其映像,但我们显然不能同时看到视域内的所有景象,而只能看到被我们关注的景象。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转动眼球依次将不同位置的景象变成关注的焦点,但每一次转动眼球,都必然会导致视网膜映像的变化,这些各不相同的视网膜映像是不可能被自然地组合在一个整体中的。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为视觉加上画框,将注意力集中在视域内的某个景象,这同样不会使视网膜映像与真实所见相一致。例如在看两可图时,尽管视网膜映像没有任何变化,随着眼睛对图形-背景的重新组织,也可以一会儿看到酒杯,一会儿看到两个侧面像。这充分说明了,即使透视法能够精确地复制出视网膜映像,也绝不能说它就获得了视觉的真实。
再说明暗。西方“写实”绘画受雕塑影响,强调以面造型,重视明暗。初学者往往从画石膏头像开始,甚至还要打上强光,以造成强烈的明暗关系。但在自然视觉中,人脸上是否真的有明暗阴影呢?如果我们让一个模特处于室内,不用强光照射,然后让两位画家分别从模特的左右两边作画,就会发现两位画家的画在明暗上是不同的。处于左边的画家的画中模特鼻子的右边有阴影,而处于右边的画家的画中模特鼻子的左边有阴影。这一结果是无法解释的,既然模特的受光情况是一样的,它就不会随着观察者位置的不同而改变,那么两位画家所画模特的阴影部位为何会有不同呢?再进一步追问,模特脸上的阴影真的是客观存在的吗?因此,与其说阴影是模特脸上客观存在的部分,不如说是画家用来造型的方式,是使一张脸呈现出来的方式。也可以说,与其说初学者在画室中观察客观的石膏头像,不如说是通过一个受光夸张的石膏头像学习一种独特的观察事物的方式。从此以后,他将用这一观察方式到处生产事物,而不是记录事物,正如人们戴上有色眼镜看世界。
这种观察方式不是人类的自然视觉,对于没有受过明暗训练的人来说,看到人脸上整块整块的阴影是极为不适应的。正如当郎世宁在人物面部画上阴影时,雍、乾二帝极为反感,以至于郎世宁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一画法。如果说明暗只是一种造型方式,那么它也不是唯一的造型方式,中国画受书法影响,强调以线造型,就是一例。尽管立体感不足,但它同样可以生动地将一张脸呈现出来。
再说色彩。西方绘画注重固有色、光源色和环境色,甚至还将色彩科学的理论运用于绘画,特别是印象派,显得极为“科学”。但这种“科学”色彩也绝不等于自然视觉的“真实”色彩。因为有些“真实”的色彩感觉是无法用“科学”来表示的,也就是不可能被照相机所拍摄出来。例如,据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站在日光下看到屋里的灯光呈现为黄色,而一旦走进屋内,黄色的灯光就会呈现为无色,而此时窗边剩余的一缕日光则呈现为近蓝色。这是因为,当颜色分别作为对象和环境的时候,由于眼睛的不同适应性,它所呈现出来的视觉感受是极为不同的。这种尽管“主观”但却“真实”的感觉,对画面中的色彩是有影响的,如果面对太阳画面前的一个草垛,那么坐在草垛的阴影里与坐在阳光里,所看到的色彩是极为不同的,画面也会相应地有所不同。再极端一点,如果我们严格根据光度计的测量结果记录物体的色彩,那么画面就会显得极不“真实”,不符合人类的自然视觉。
可见,“用科学原理造型”并不符合人类的自然视觉,不能说它是“视觉真实”,更不能说它是客观写实。其实,西方绘画诞生于西方文化之中,背后体现的乃是西方人的“艺术意志”,与其说它再现自然,不如说它整理自然,即根据自身的艺术意志表现出其想要的自然。那么,西方绘画的艺术意志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自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一切视觉经验只有符合理性秩序才能进入绘画之中,而达到理性秩序的方式就是逻辑分析。首先将事物进行分解,仔细辨析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再将它们按逻辑规则在画面中组合起来。因此,西方“写实”绘画不一定符合视觉经验,但却具有逻辑上的清晰性。例如,尽管我们不可能在自然视觉中同时清晰地看见视域中的所有物体,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按照逻辑规则把它们同时清晰地呈现在一个画面中。
最后,我们还得谈谈西方“写实”绘画的“逼真”效果。当利玛窦在明末初次将天主像带到中国时,即使没有受过西方视觉训练的国人,也惊叹于它那“如镜涵影”般的“逼真”效果。这能否算作是“西画写实”的有力证据呢?我觉得这个证据也还是不充分的,因为我们之所以觉得它“逼真”,是因为我们已经被它引导按照它的要求去看它了。例如透视法,它在呈现给视觉的同时,也在要求着特定的观看方式,因为视觉只有按深度组织画中物体,才能解释大小的如此安排。可以说,西方绘画的“逼真”效果,并非事物的真实呈现,也非自然视觉的真实经验,而是一个“逼”出来的真实。
总之,西方绘画的写实,与其说是写视觉之实,不如说是写理性之实,其所写的只是为西方“艺术意志”所“识别”的真实。也就是说,“西画写实”的意义不在于它对客观真实性的诉求,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西方式的写实方式,与之相对的不是“中国画写意”,而应该是中国式的写实方式。这就为中国画写实问题的研究拉开了序幕。
三、中国画特有的写实方式
中国画到底有没有写实成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澄清“标准”问题,即我们打算按照什么标准来判断写实成分。如果按照西方的写实标准,中国画即使有写实成分,也不会对当前的绘画理论和实践有什么贡献,这种研究既无必要也无意义。如果不按照西方的写实标准,那么,中国画是否具有自己的写实标准,或者说,是否具有自己的写实方式呢?这正是我们所要探究的方向。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西方文化注重理性主义传统,强调理性对视觉经验的整理,试图对视觉经验进行“科学”的表现。而中国文化注重“根身性”,认为视觉经验是身体经验的一部分,强调将视觉经验放入整体的身体经验中来表现。从这一角度来讲,中国画对视觉经验的处理无疑要更加全面,更加合理。
其实,西方绘画试图逃避身体,但却一直没能彻底摆脱来自身体方面的烦恼。透视画法必须首先设定一个身体立脚点,只不过大多数绘画将这一身体立脚点放在了一个“恰当”的位置,以至于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而弗美尔的画则通过一种更加触目的方式,提醒我们身体立脚点在获取视觉经验过程中的重要性。两可图之所以会在视网膜印象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景象,同样是由于身体的存在,如果置身于酒杯的位置,我们看到的就是两个侧面像,如果置身于两个侧面像的位置,我们看到的就是酒杯。明暗方面,模特脸上的阴影也会随着画家身体位置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色彩知觉中,置身于某个色彩之中,与置身于某个色彩之外,视觉经验也是不同的。总之,视觉经验是身体经验的一部分,身体位置的移动将会导致整个视觉经验的变化。这是不容置疑,也无可回避的。
同样,中国绘画也并非对透视法全然不知,早在山水画诞生之初,宗炳就发现了“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的规律,甚至其“张绢素以远暎”*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583页。的方法还颇有点西方隔着方格玻璃写生的意味。虽不够“科学”,也还是有所意识的。在具体的绘画作品中,远处的人比近处的人稍小,茶杯的杯口画成椭圆形,都说明了中国画中并非完全没有透视法。但这些透视法终究却没能在中国画中得到更加深入的探讨,除了中国文化中缺乏诞生科学的土壤外,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乃是它不符合中国画的“艺术意志”。科学透视法乃是人立于一点的所见之象,这不利于表现动态的身体经验。
与西方绘画将观者的身体丢在画面之外不同,中国画往往主动地将身体引入画内,并使之游动起来,据此组织画面,强调身体游历的真实体验,追求身“体”之实。宗白华曾说:“中国画在画台阶、楼梯时反而都是上宽而下窄,好像是跳进画内站到阶上去向下看。而不是像西画上的透视是从欣赏者的立脚点向画内看去,阶梯是近阔而远狭,下宽而上窄。”*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页。不仅如此,为了让观者在画面中游动起来,立脚点的位置也是不断变化的。例如三远法,郭熙云:“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中国山水画主峰巍峨高大,则视点必低,人需在山脚;山后之景如能悉见,则人需在山腰;而平远必有“一目千里”之势,且通常伴随“一览众山小”之景,则人需在山巅。
因此,很多学者据此认为,中国画是散点透视,然散点透视仍以西学为参照,实是多个焦点透视的机械拼凑。以英国摄影师霍克尼散点透视的经典作品《科罗拉多大峡谷》为例,这是用60幅在不同地点所拍摄的照片拼贴而成。尽管其整体上不再是焦点透视的画面,但其中的每一幅照片仍遵循焦点透视的原理,是人在60个不同地点所见之象的拼凑,不仅处理方式极其粗暴,造成画面的散乱,而且也仍然停留于西方静态立脚点的思维模式之中,未能使身体真正“游动”起来。
身体的游动,不是仅仅通过增加立脚点的数量就能实现的,郭熙的三远法也并非只有三个立脚点,而只不过是一种论述上的列举法,切不可机械理解之。以中国的绘画长卷《清明上河图》为例,此画非常狭长,横528.7厘米,纵24.8厘米。西方的焦点透视画法在此简直无由措手,但此画也绝非多个焦点透视的机械拼接,而是几乎不分远近地同等呈现。这样在观赏它时,就必须游动起来,观者仿佛是坐在游船上欣赏汴河两岸的景象。只有这样的画法,才能表现出如此丰富浩荡的北宋生活图景。
同时,画中纵向延伸的城墙也没有任何透视效果,从近到远宽度一致,这就使得观者不是停在某处,像在西方绘画中那样,仅仅让目光随城墙向远处延伸,而是要求身体在城墙上不断地向远方游走。为了不至于显得过短,城墙并未与画面垂直,而是呈角度地向远处延伸,有时甚至可以“之”字形随意延伸,以便形成悠远之势。徐悲鸿曾批评中国画“手不能向画面而伸”,*郎绍君,水中天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42页。其实城墙以及道路也不能向画面而伸,这不是中国画技法上的缺陷,而是中国画实现“卧游”的策略。
与强调“游”的造型方式相一致,中国画在“观物”方式上,也不像西方焦点透视那样,仅仅从一个单一的侧面来观察事物,而是强调“身即山川”,以游动的方式对事物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宗炳所谓“身所盘桓,目所绸缪”,郭熙所谓“面面看”,*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143~144页、第498页。即此谓也。身体在游动之中对事物的观察,自然无法像西方定点写生那样,可以按焦点透视法记录于稿纸之上。正如李日华所云:“每行荒江断岸,遇欹树裂石,转侧望之,面面各成一势,舟行迅速,不能定取。”“不能定取”就是不能固定在一个侧面观察事物,而是要“石看三面,路看两头”,*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760页、第596页。或如董其昌所云:“山行时见奇树,须四面取之。”*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141页。
关于这个“不可定取”的画法,在中国画史上还曾有过一段著名的公案。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李成自己的解释乃是,“自下望上,如在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桷”。然沈括却嘲笑他是“掀屋角”。*沈括:《梦溪笔谈》,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21页。李成的画法是从固定角度对事物的描绘,但这却不符合中国画“不可定取”的传统,因而遭到沈括的嘲笑。
西方绘画擅长“定取”,因而其画面是静止的,仅仅要求视觉的参与,而中国画强调“不可定取”,因而其画面是流动的,它不仅要求视觉的参与,而且更要求整个身体的参与,这乃是宗炳所谓“卧游”的真义。如果从中国画所追求的效果来看,正如郭熙所云“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498页。此一“真”字说明中国画也是追求写实的。
总之,“写实”是中西方绘画的共同追求,但西方绘画所求之实乃是不顾身体经验的科学之实,试图再现视网膜映像中的现成之景,而中国画则将视觉经验融入身体经验的整体之中,尽管不符合视觉科学之实,却符合身体游历之实。
(责任编辑 廖国强)
Experiencing with Body vs. Understanding with Consciousness: Different Ways of Achieving Realism in Chinese and Western Paintings
LIU Lianjie
Since the 20thcentury, in response to the urgent need to save the Chinese nation by developing industry and commerce, Chinese theorists have gradually come to the misjudgment that “Western paintings highlight realism while Chinese paintings impressionism”. Such a misjudgment has obscured the realistic elements in Chinese paintings, especially the ways of achieving realism in Chinese paintings. Actually, Chinese and Western paintings share the pursuit of realism, but they have formed different ways of presenting realism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ir rationalist tradition, Western paintings emphasize the rational arrangement of visual experiences and attempt to express visual experiences scientifically, aiming to arrive at rational truth. In contrast, strong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theory of bodily senses, Chinese paintings regard visual experiences as part of the physical experience and attempt to express visual experiences by relating them to the physical experience, trying to reveal the truth of the bodily experience. In this sense, Chinese paintings deal with visual experiences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reasonable way.
paintings,ways of achieving realism,truth of bodily experience,rational truth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少数民族美学与审美教育研究”阶段性成果(2016cx02)
刘连杰,云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博士(云南 昆明,650500)。
J21
:A
:1001-778X(2017)05-015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