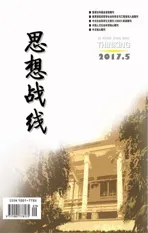多重宇宙论并接的交互主体性阐释
——兼论“做”民族志
2017-04-11
多重宇宙论并接的交互主体性阐释
——兼论“做”民族志
谭同学
阐释法曾被用以应对科学民族志方法论危机。它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也给激进后现代主义留下了认识论上解构的后门,使民族志变为“写”文化甚至走向不可知论。完善它,须明确人类学家与田野对象为交互主体,语言为介质,其本体则是并接的多重宇宙论。当代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强调多重宇宙论比较,但不能武断“异文合并”以求纯化。阐释实为同一世界多元文化主体的话语权实践,仅从认识论上强调“裸呈”田野对象叙事或不同主体视角,并不能消除权力不对等。在此意义上,民族志并非“写”而是“做”出来的,“做”得好坏,不仅与不同主体的认识角度、水平有关,更与阐释的权力实践有关。
阐释;交互主体;多重宇宙论;话语权;“做”民族志
自我与他者,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研究领域中,都是被聚焦的关系。人类学素以重视他者视角著称,并经由百余年探索与尝试,发展出了不少方法论,以克服自我中心主义。民族志作为人类学方法论常用的呈现方式,随之也受到广泛重视。可是,人类学本身却曾遭遇过严重的方法论危机。而且,尽管不少人类学从业者曾尝试革新方法论,以解决此类问题,但至今仍很难说就已经有了公认无疑的答案。本文将结合部分民族志作品分析,对此类问题的历史与当前动态作一个简要梳理,并尝试提出自己的思考,以期抛砖引玉,对促进人类学,尤其是民族志的方法论探讨,有所裨益。
一、现代人类学基本方法论危机与阐释法的应对
以当今的眼光看,古典人类学比起现代人类学来,显得并不精致,更非没有缺陷。以至于,现代人类学家常批评他们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或者“文献民族学家”。*[美]克莱德·克拉克洪:《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吴银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可在其内部及所属时代知识共同体中,古典人类学却没有遇到方法论的危机。就当今人们还熟悉的泰勒、弗雷泽、摩尔根、梅因、麦克伦南、巴霍芬等古典人类学家而言,其观点千差万别,但在方法论和基本时空处置手法上却如出一辙。他们都坚持用比较法,将不同空间的经验材料类型化,按照时间进行排列,空间的类型差别被当成时间的进化差别。这些研究,对其研究对象,也即“他者”,事实上充满了各种误解。但通过对他者哪怕是错误的认识,来重新认识欧洲,也即“自我”,则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不仅是他们,而且在整个文明欧洲的知识界,即便具体观点上有争议,但其方法论都被认为是恰当的。在此类视角下,欧洲是如此的光辉、先进,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说,都应是毫无疑义的中心。
从维也纳条约到20世纪初,近百年大体和平的欧洲被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在欧洲中心的中心,大英帝国的知识界开始了现实反思的历程,其中也包括人类学。新一代人类学家或是出于半自觉(如拉德克里夫-布朗前往安达曼岛),或是偶然客观原因不得不(如马凌诺斯基因战争无法返英),开始基于实地的田野工作撰写民族志。在方法论上,这促成了人类学的现代转向。马凌诺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也被后人视作现代人类学的奠基者。这些研究,与古典人类学另一重要区别是,开始借用他者来反思自我,同时以人类学在他者社会文化中的新发现,来弥补欧洲知识界的不足。
不过,这次方法论革命,却也延续了古典人类学两样东西。其一是科学主义的比较法,只是主要不再拿澳洲与美洲作比较,而是隐性地拿亚、非、拉与西欧作比较。而且,马凌诺斯基还坚持认为,田野工作跟自然科学的实验室观察方法在科学性上完全相同,在此基础上写就的民族志也是科学客观的(马凌诺斯基执教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至今还保持着给硕士毕业生颁发科学学位的传统);其二是隐性的欧洲中心论。这两者叠加起来,使得原本虽然有问题但在古典人类学时代被忽略的方法论,在现代人类学中出现了危机。危机集中暴露并引起人们注意的标志性事件,是马凌诺斯基的田野工作日记在其去世后于1947年面世(此前虽不乏学者质疑民族志的客观性,但未引起普遍的方法论质疑)。在日记中,马凌诺斯基常流露出对田野对象的鄙夷、厌恶之心,将之形容为“狗”“畜生”,甚至认为该“消灭这些畜生”。*[英]马林诺夫斯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卞思梅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3页。这与其常宣称堪比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观察,无疑形成了剧烈反差。而其欧洲中心主义也暴露无遗。
马凌诺斯基的学生辈,如利奇曾为其作辩护,认为作者写日记时根本没打算出版,事实上它也不应该出版并让人无礼纠缠。*Leach Edmund. Malinowskiana,“On Reading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Rain, no. 36, 1980, pp.2~3.很显然,无论就日记事件本身,还是就人类学方法论来说,利奇的回应都是失败的。于前者,写日记时没打算出版,难道不是更能说明当时作者看待田野对象的真实心态?于后者,则根本没有方法论反思和创新的意识。真正开始系统清理现代人类学方法论,并部分成功地解决此问题的集大成者,还是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
首先,格尔茨认为,将亚、非、拉的田野对象当成“原始人”“野蛮人”都是不合适的,而在方法上造成此误区的原因,乃是人类学缺乏历史的眼光。以至于,格尔茨虽然没有像沃尔夫那样集中批评欧美人类学将非西方的他者当做“没有历史的人民”,*[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页。但一直在尝试将历史学注重时间变迁的方法论引入人类学。为此,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极力推动促进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合作交流。这个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混合群体,虽然最后因人事纷纭而散伙,*[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追寻事实》,林经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6~141页。但在理解社会的共时性与历时性方法论上,相互刺激、影响还是明显很深的。*[美]小威廉·休厄尔:《历史的逻辑》,朱联璧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173页。从人类学角度看,这既有对此前人类学方法论中科学主义比较法的修正,也有对欧洲中心论的否定。*不知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和历史学合作失败,格尔茨并未就如何将历史视角引入人类学在方法论上创新(与其同时代及其后的不少人类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努力),尤其是如何与阐释法相结合,再作进一步讨论。而事实上,历史视角应当亦可以融入阐释法,成为人类学方法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主题有异、篇幅有限,在此无法详述,可参看笔者拙文《作为人类学方法论的“文史哲”传统》,《开放时代》2017年第3期)。
其次,格尔茨尝试重新界定田野工作基础上的民族志。依他的界定,田野工作并非对他者如自然科学般的观察过程,民族志也就不是这种观察的科学客观报告。在认识论上,格尔茨认为,田野工作实际上是人类学家接触田野对象,并尝试用自己的语言、同时也是人类学同行看得懂的语言,“阐释”田野对象文化系统的过程。*[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 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7页。也即,人类学田野工作是带有主观性的,民族志也随之带有主观性。不过,这种阐释并不能随意裁剪、夸张或歪曲事实,因为田野对象的文化体系是一个“地方性知识”整体,*[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42页。有其“深层游戏”规则。*[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 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08页。人类学家用民族志,阐释田野对象的地方性知识,揭示其深层逻辑,可谓“深描”。*[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 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3页。不难看出,格尔茨这是以认识论上的相对客观主义(区别于马凌诺斯基的科学客观主义),匹配文化相对论。
“阐释”作为一种方法论,多少回应了人类学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客观性所面临的质疑。它清楚地告诉人们,两者都是相对客观的。由于阐释要注重田野对象地方性知识的整体,也即将田野得到的知识在当地文化体系的“上下文”当中理解,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志摆脱欧洲中心论。阐释成为现代人类学方法论的新起点,此后即便方法论上有争议,也常围绕阐释而展开。从这个角度看,面对现代人类学的方法论危机,阐释法的应对是成功的。不过,阐释的方法也留下了,或者说带来了新的隐患。因为它在为民族志保留主观性余地,质疑科学客观主义和强调文化相对主义的同时,并没有一个刻度或参照系可以让人参照,允许主观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合适的并可为知识共同体所接受。
因为没有这种刻度或参照系,一些激进后现代主义者干脆就认为,其实田野工作彻头彻尾都是主观的,民族志从本质上来说是“写文化”。*[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马库斯:《写文化》,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页。另一些更激进的人则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学家认识他者的可能,将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书写,嘲笑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天真”事。*[英]奈吉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何颖怡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页。既然对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的基本看法激进到了这个份上,田野工作根本也就不必再做,而民族志书写也因靠“虚构”而跟写小说没什么区别,显得没有作为科学研究的必要。事实上,持此类观点的人后来确实要么去了文学、艺术界,要么干脆放弃了学术研究。而格尔茨倾向于认为,田野工作和民族志都是在“追寻事实”,同时实质上又不可避免总是在“事实之后”,因此是“努力从大象在我心中留下的足迹,来重新建构难以捉摸、虚无缥缈、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大象”。*[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追寻事实》,林经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4页。不同人类学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包括对其阐释人类学的“误解”。以至于,格尔茨本人面对此类质疑,从未给出过正面回应。
绝大部分后现代主义倾向的人类学家,当然不可能如以上学者那样“天真”到完全放弃民族志的地步。毕竟,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民族志几乎被认为是人类学的基本技艺(原本田野工作毫无疑问也是现代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但在当代也面临着越来越多交叉学科学者滥用其名的局面)。此类民族志“书写”者在阐释他者的文化过程中,在极度强调自我主体性的同时,当然强调作为田野对象的他者也有其主体性。但在方法论上,此类阐释强调,这两种主体性没有办法进行跨文化的深层沟通,只有当研究者和他者具备同样的文化认知结构时,才可能真正无障碍地理解,并以此为基础对他者社会文化进行阐释。如果二者认知结构不同,则他者虽然客观上有主体性,但在阐释中却没有方法让其主体性呈现出来,实际上只能是被阐释的客体。于是,由于认识论上极端地滑向不可知论,原本旨在克服现代人类学方法论危机的阐释法,也就被扭曲得只强调研究者单方面的主体性了(从而难免导向自我中心主义。在当下人类学格局中因从业人员数量、话语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主要表现为欧洲中心论)。对于这种“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式的认识论,当代认知人类学奠基者之一布洛克在研究“我们如何知道他们如何思考”时,曾批评道:“这类研究失去了人类学这类知识的特殊的丰富阐释学意义,其中的研究者不能持续地重新定义自己在研究中的分析工具……在田野调查期间不断通过参与观察反思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在放弃这种独特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之后……将人类学的婴儿和脏水一同倒掉。”*[英]莫里斯·布洛克:《吾思鱼所思》,周 雷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4~45页。
当然,并非所有人类学家在认识论上都有不可知论的倾向。即使在以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从根子上质疑现代人类学方法论的学者中,也不乏马库斯这样的标志性学者尝试有限度地进行建构,主张通过“深(描)”“浅”(多点、多维反思)相结合的方法,*George E. Marcus,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31.去阐释他者。只不过,此类有限度的建构性尝试,同样也缺乏具体操作方法做支撑,以尽可能保证他者的主体性在阐释中得到尊重。
换句话说,若非如激进后现代主义者那样一味消极解构,而尝试用阐释的方法积极应对人类学研究中的自我(欧洲)中心主义,还得回到阐释法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关键环节。其中,尤其对那些容易让研究者无意识地忽略他者主体性的操作环节,必须进行更细致的探讨。
二、多重宇宙论并接的本体论与交互主体性阐释
若要完善阐释法,则当首先梳理其基本理路。择其要者如,首先,在人类学的阐释中,必定有两个或以上的主体;其次,人类学家不可能从本体意义上变成他者,其所阐释的实际上是他(她)与他者——不同主体互动中可交流、共通的社会文化特质与逻辑化过程;再次,不同主体的互动过程并非完全透明、无障碍心灵直通,而不得不借助于一系列中介,首当其冲者则是语言及其关于世界认知的基本格式(宇宙观),即使不是访谈而只是观察,其思考过程也必定依赖语言及其宇宙观。
在这里,两个以上的主体并非无关的主体,相反具有交互关系(intersubjectivity)。*Intersubjectivity常被译作“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互为主体性”“互主体性”及“主体际性”等(郭 湛:《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考虑到本文所指人类学家对他者的研究,既包含了作为主体的他者和人类学家的认知、理解,也包括两者互动产生的新的认知和理解,在既有译法中,似乎“交互主体性”更能直接、准确地体现此意。对这种关系的基本哲理,哲学家早有深入探讨,只是在人类学中有理论自觉地对它予以方法论上的关照,来得较晚。其理论前身可溯及笛卡尔。针对经院哲学认为有身份的人才有正确认知世界的理性和良知的观点,他说:“那种正确判断、辨别真假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称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本来就是人人均等的。”*[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页。也即,绝对不存在只有某些人有资格作为完整主体,而另外一些人只能作为不完整的主体,甚至只能作为客体的事实。
胡塞尔是首先明确提出交互主体性概念的哲学家。如他曾论述道:“内在的第一存在,先于并且包含世界上的每一种客观性的存在,就是先验的主体间性。”*[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张廷国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不过,对其交互关系乃先验的观点,海德格尔曾批判它的“存在论基础是不充分的”。*[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57页。在海德格尔看来,交互主体性不是先验的,人的存在乃是“他人的共同此在与日常的共同存在”。*[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36页。他在晚年还强调,若不注意此点,哲学将“被逐入人类学之中”。*[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0页。
此后,加达默尔在注重交互主体性的存在论与阐释学(又译诠释学)之间架起桥梁。他认为,主体的存在及其“判断力”首先依赖于与其他主体的“共通感”。*[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8~39页。“鉴于某种被言说的东西,理解为流传物借以向我们述说的语言、流传物告诉我们的故事。这里给出了一种对立关系。流传物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的地带,乃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对象性和某个传统的隶属性之间的中间地带。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这中间地带内。”*[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81~382页。阐释实际上是主体透过语言、时间的中介,理解和再述其与其他主体间的“共通感”。
加达默尔对格尔茨导出人类学的阐释法有重要影响。不过,在美国文化人类学风格的影响下,格尔茨对加达默尔关于阐释中语言的结构性基础不甚关注。加达默尔在倡导“诠释学本体论转向”时指出,“语言观就是世界观(宇宙观)”,因为语言会把主体“同时引入一种确定的世界关系和世界行为之中”。*[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574~575页。此外,他还有几乎是给人类学“量身打造”的忠告:“如果我们通过进入陌生的语言世界而克服了我们迄今为止的世界经验的偏见和界限,这绝不是说,我们离开了我们自己的世界并否认了自己的世界。我们就像旅行者一样带着新的经验重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即使是作为一个永不回家的漫游者,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忘却自己的世界。”*[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581页。换句话说,多重宇宙论并非区隔、平等并列存在的。相反,各种文化的人们其实在面对同一个世界。也即,多种宇宙论实际上是“并接结构”。*[美]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
阐释法在运用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表明,仅将他者的主体性从认识论加以对待,很容易从文化相对论滑向后现代主义的不可知论。所以,对此问题的追问,还得重新回到本体论,尤其是交互主体性的本体论上来。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对注重结构性关系的部分人类学家,已经开始重新思考本体论问题。
言及此处,得提到两个带有当代世界人类学话语权力不平等格局印记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学生戴斯考拉曾在巴西亚马逊流域做田野和研究,与一个巴西人类学家卡斯特罗过往甚密。两人对当地经验的解释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不乏关键区别。卡斯特罗认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留给当地人(包括人类学家)用当地话语解释经验的余地很小。他以列维-斯特劳斯为靶子,批评人类学从认识论上用西方人的宇宙论代替他者的宇宙论。*Eduardo V. Castro,“Cosmological Deixis and Amerindian Perspectivism”,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4, no.3,1998.而戴斯考拉也结合民族志材料,开始反思这一问题。他指出,在印第安希瓦罗(Jivaroan)原住民阿丘雅人(Achuar)那里,人类社会和文化结构从属于自然结构(一元论宇宙观),现代西方人将之看作与自然相分离(二元论宇宙观),后者才是“异类”。*Philippe Descola. “L’anthropologie de la nature”,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57e Année, no.1,2002他还详细比较了中国、墨西哥、非洲、古希腊等诸多不同文化的宇宙论。*Philippe Descola, Beyond Nature and Culture,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pp.202~224.他认为,古代西方人的宇宙论与其他宇宙论大体相似,只是近代以来才有了不一样的二元论自然主义宇宙论,*Philippe Descola, Beyond Nature and Culture,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pp.386~387.因此它只具有相对主义的地位。萨林斯在给戴斯考拉的序言中写道:“该书给当前人类学的轨迹带来了一次剧变,实乃范式更替。”*Marshall Sahlins,Foreword,in Philippe Descola, Beyond Nature and Culture,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pxii.
对此进行深度回应的学者还有霍尔布拉德、拉图尔、斯科特等。霍尔布拉德尝试重新定义人类学的“证据”。他认为,人类学家关心当地人与神明的道德关系和神启“证据”,但其本土的“证据”观念却与人类学家不同。这两种“证据”需要一个转化过程,而此过程本身又是民族志与理论间关系本体的证据。*Martin Holbraad,“Definitive evidence, from Cuban gods”,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14, The Objects of Evidence: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2008, pp.93~109.同理,还需在“自我”与“他异性(alterity)”视角下重新定义“真实”,人类学的“真实”不是绝对的神谕,而是自我与他者互动之本体意义上的真实。*Martin Holbraad,“Ontography and Alterity: Defining Anthropological Truth”,Social Analysi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and Cultural Practice, vol.53, no.2, What is Happening to Epistemology? 2009, pp.80~93.拉图尔重申了已有观点,“我们从未现代过”*[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 鹏等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委婉批评戴斯考拉认为西方人的古代与现代宇宙论有本质区别)。他指出,人类学应学会如何从多元存在(主义)模式中获益,尊重表象作为“被遗忘的存在”,*Bruno Latour,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 An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s,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62.用他者的语言“说话”。*Bruno Latour,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 An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s,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390.斯科特受其师萨林斯影响甚大,但他认为,萨林斯关于“人类学在充当资产阶级化了的犹太-基督教宇宙论搬运工(促进跨文化理解)”的论断,*Marshall Sahlins,“The Sadness of Sweetness”,Current Anthropology, vol.37, no.3,1996.是原子式的宇宙论。斯科特意欲发展一种反向结构的宇宙论范式:人类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整体,族性和文化将人分开;不同的宇宙论同属族群的和文化的杂糅;混沌与理性乃同一硬币的两个侧面,人类社会和文化结构一直在区分(differentiation)和整合之间摆动。*Michael Scott,“Hybridity, Vacuity, and Blockag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47, no.1,2005.此外,在这场人类学“本体论转向”运动中,斯科特对它仅强调多元宇宙论及其本土特性的倾向,也予以了反思(部分针对戴斯考拉)。他主张的改进措施是:将一元论作为方法使用,在民族志材料理论加工的过程中,比较不同的宇宙论,但不要进行“异文合并”(conflate)并剔除“杂质”以求“纯化”(purification)。*Michael Scott,“Steps to a Methodological Non-dualism”,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vol.33, no.3,2013.
三、同一世界多元文化主体与阐释中的权力实践
既然阐释所涉及的乃交互主体,关键的中介则是语言,而语言又以宇宙论为基石。格尔茨提出阐释法,并非没有顾及认识论上的交互主体性,但对其本体论,尤其话语背后的权力不平等,则关注不够,结果导致他者的主体性在阐释中缺失。梳理交互主体性的哲理脉络,则不难发现,它不仅有而且更为重要的一面,恰恰是本体论。加达默尔的忠告着重即在此。在某种程度上,当下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也可谓对“诠释学本体论转向”的再回应。而阐释若以认识论为基础,重新回归本体论,就需注意交互主体所依赖的多元语言及背后的多重宇宙论。
考虑到当代人类学主要面对的都是复杂社会(地处偏远的所谓“简单社会”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其他社会影响),斯科特的忠告具有非同寻常的建设性意义。客观上当代世界是一个整体,不管是哪里的人类学家与其所要研究的他者,事实上都处在同一世界。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不同人群拥有多元的文化,人类学家可以从同一世界的角度去理解世界,但若进行“异文合并”或将他者原本包含了复杂多元的文化“纯化”,则属武断使用阐释权力的做法。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多重宇宙论的并接结构要求人类学家有必要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力。否则,既是对作为田野对象之他者的伤害,也无助于人类学家贴近实际地理解他者、中肯地撰写民族志,更不利于通过他者重新认识自我。也正从这个角度说,以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为标志,人类学家在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实际上包含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权力实践。马凌诺斯基的错误,并非在认识论上不知道“土著人”的宇宙论与欧洲人有所不同,而是在实践中滥用了自己的话语权。
不过,似乎值得进一步指出,即使在所谓同一种社会和文化中,只要涉及不同主体间的解释,就不可避免会遇到解释的权力实践问题。例如,苏力在调查法律实践的过程中曾提及一个案例:甲向同村的乙借300元买牛,后约定算乙“搭伙”(“搭伙”在当地文化中有清晰含义,乙有权用牛但不拥有增值部分,如牛生崽);10余年后双方发生纠纷,法庭按照合同法“合伙”的条款判案(意味着乙有权获得增值部分的一半),但为避免甲上诉,判定其归还乙300元、另将增值部分约三分之一给乙。*苏 力:《送法下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1~202页。在此案例中,法官“和稀泥”显然是一种不得已的平衡。若不让乙取得部分利益,则有悖法律(法律里只有“合伙”的概念),但若严格按“合伙”的法条判案,则会伤害地方性知识中的正义,而且可能滋生更多案件(当地“搭伙”现象绝不限于此例,其他“搭伙”关系中的一方均可诉诸法律得到更多的利益)。由此,苏力赞赏基层法官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态度,无疑有其主张实践性法理的缘由。但很显然,其分析既未深究法律本身的合理性,也未对甲在实质正义的意义上遭受不公正判决给予同情,更似忽略了以“搭伙”还是“合伙”去解释甲乙买牛这一事实,本质上是可以影响不同主体利益的权力实践,而非仅仅是认识上的概念之争。
从此案例还不难看出,中国无疑是多元文化共生的复杂社会,并且,几乎其中每种文化又是多层次而复杂的。而就人类学而言,迄今为止,我国的研究大多仍集中在国内,其中不少是研究本民族社会和文化。但如此案例所示,方法论上其实也同样回避不了阐释“他者”的权力实践。由此,在中国语境下围绕阐释法,对田野工作和民族志进行反思、完善或创新,就将既要触及中国经验研究的深入程度问题,或多或少也会涉及人类学基本方法论问题的思考(中国人类学显然不可能独善其身)。
围绕此题,国内近年关于自我与他者主体地位和关系的探讨,有相当一部分确实仍在围绕格尔茨的阐释法展开。
例如,刘珩重申了20世纪80年代反思民族志学者对科学民族志诗性的批判,提倡主动反思自我、意识、情感、修辞策略在撰写民族志过程中的作用。*刘 珩:《民族志诗性》,《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张小军等人则延续拉比诺批判格尔茨等人的后现代主义路数,主张从其《摩洛哥田野研究反省》中提到的“互主体性”出发,理解“互经验”,将ethnography由“民族志”改译为“文化志”。*张小军等:《走向“文化志”的人类学》,《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蔡华认为,格尔茨将民族志看作文化解释,有些消极,而若坚持中立立场、严守田野工作程式,完全可以避免民族志的主观性。*蔡 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此外,王铭铭曾直接介入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讨论。他将之与格尔茨及其后的“知识论转向”进行对比,发现它们并非完全替代关系,由此指出民族志兼具知识和本体探索的可能性。*王铭铭:《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同时,他还质疑戴斯考拉将二元自然主义宇宙论看作近代西方人独有的观念。*王铭铭:《在欧亚与民族志世界之间》,《西北民族研究》2015 年第4期。
与以上路径不同,朱炳祥沿着质疑和完善阐释法的思路,对阐释的主体问题予以了持续关注,并尝试提出新的方法论。基于“互镜”概念,他提出用“相互看”的“主体民族志”“颠覆科学民族志”。*朱炳祥:《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他认为,“主体民族志”以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有“自明性基础”,可谓“人类志”。*朱炳祥:《再论“主体民族志”》,《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而撰写“主体民族志”的方法是:表述者自律;表述恒定与开放结合的“符号扇面”;由“互镜”“裸呈”对蹠主体。*朱炳祥:《三论“主体民族志”》,《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此后,他曾给出一个“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样本:田野对象作为“第一主体”讲述其宗教;人类学家作为“第二主体”解读“第一主体”的叙述;民族志评审者(读者)作为“第三主体”重新解读“第一主体”的叙述,以及“第二主体”的解读;人类学家再作总结。*朱炳祥:《“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对以上取向迥异的讨论给出全面评判显非本文的主旨,这里只能对其与阐释法的具体关联略作分析。反思撰写民族志过程中人类学家的自我情感和修辞策略,强调“互经验”,指出民族志兼具知识和本体探索的可能,对于促进民族志更贴近他者的社会经验事实,无疑有益处。不过,其中关键的实践性因素也似乎还有必要进一步理清。至于坚守中立立场即可保证客观性的观点,则很值得怀疑。如马凌诺斯基那样宣称、甚至主观认识上的确诚心价值中立,而客观上在实践中未能做到者,实非鲜见。而原本指向解构的“互镜”概念,*“镜”被罗蒂用来指“对蹠”人的“纯感觉”,即“非物质的表象”([美]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9页)。此概念是他解构本质主义实在论的理论工具([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 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46~147页)。罗蒂深受拉康影响。20世纪30年代,拉康受瓦隆儿童心理学启发(幼童照镜,会误认为镜中“我”是真的),开始用“镜像”指儿童混淆现实与想象情景,并扩展指“假我”(moi)代替“真我”主体(je)的认知过程([德]格尔达·帕格尔:《拉康》,李朝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32页)。由此,“互镜”中相互呈现的应是叠层的虚假影像。若非彻底重构“镜”的概念,而直接用它来建构“主体”,似有难以回避的矛盾。若用来建构“主体”,可能也还需漫长的方法论转化过程,不是“裸呈”,也非增加“解释”主体的数量,即可简单解决问题。
毋庸置疑,提出主体问题以及表述者自律等方法,无疑有其洞见。但人类学家所面对的基本局面,毕竟是经验不会自动论述理论问题。由此,选择什么经验、引向何种理论分析,似乎只能靠人类学家与他者互动。撰写民族志时,人类学家当然可以先摆出一堆详细的资料,优先让田野对象“说话”,以示其作为“第一主体”对某话题(如宗教)的主体性认识。但实际上,田野对象的叙述并不可能是“裸呈”。作为“第二主体”的人类学家对田野对象提问题的过程,在这里不应被忽略(何况,田野工作绝不仅限于访谈。民族志相当一部分资料来自人类学家无声的观察)。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田野对象为什么叙述这些,而不是别的什么。很难想象一个村民无缘无故,或者碰到自己同村的人,就会讲起宗教(而这刚好是人类学家想了解的内容)。如果人类学家当时给村民提其他问题,想必村民给出的答案不会是宗教。若从“交互主体”角度视之,所谓“第一主体”显然绝非不受“第二主体”影响的孤立主体。由此,这样的民族志虽不失为一种民族志写作手法,但并非方法论意义上的新类型,甚至还会让民族志变得更为繁琐,增加读者阅读的困难(此外唯一的用处,似乎就在于可以将人类学家悄然隐藏起来,俨然田野对象叙述是孤立主体在不受干扰地“说话”)。
当然,“主体民族志”样本必定还可更详细,只是在发表时因篇幅限制不得不舍弃了部分材料。但无论篇幅多长,也很难想象人类学家能将田野对象所有语言、姿态、表情都记录下来,并写进民族志。人类学家无论如何都不得不(甚至是下意识地)选择性记录材料,并在撰写民族志时取舍材料。作为第三方的读者,当然也只能将就着人类学家经过两轮筛选过的材料,来看民族志的分析是否恰当、有说服力。此外,如果田野对象知道其叙述将变成给更多的人去阅读的民族志,其叙述的内容和方式或许也会跟仅限于两个主体的对话,很不一样。有些话,田野对象甚至不介意调查者转述给第三人听,但却会介意白纸黑字地让任何人都可以看。在此情况下,田野对象并不在意有第三个主体知道其言行,但却会在意无限顺延n个主体的可能性。若我们不可能亦不必建构起“n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或有必要指出,第三至n个主体虽对田野对象的叙述和人类学家的分析可能有不同看法,但它们首先影响到的是人类学家和田野对象的交互主体关系。也即,在人类学家和田野对象间的对话和权力实践中,双方应当、必须也必然事先就考虑到了,其民族志将会有其他人阅读。
从此角度看,将田野对象叙述的重要性优先排为“第一”,在方法论上不失为洞见。但是,从根本上影响民族志能否呈现出田野对象社会文化经验优先性的,不是多个主体认识的叠加,而是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和撰写民族志的过程中,如何优先尊重田野对象的主体性叙述并谨慎地运用“文化解释”的权力(如在耕牛争议案中,优先尊重“搭伙”还是“合伙”的解释)。由此,从其实践特性来说,民族志并非“写”出来,而是“做”出来的。民族志“做”得好不好,不仅与不同主体认识角度和水平有关,更与“阐释”的权力实践有关。循此理,方不难理解,马凌诺斯基的田野工作虽有诸多问题,但因他至少在运用阐释权力、撰写民族志时尚算克制,其民族志“做”得公认不错;而不少对田野工作中权力与认识论偏见问题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激进后现代主义者,却因过分看重、滥用阐释权力,而“做”不出优秀的民族志,甚至干脆不再“做”民族志(人类学研究)。
总之,就方法论而言,将近代以来欧洲自然主义宇宙论相对化,强调多种宇宙论的存在,有重要意义。不过,同样需注意,多种宇宙论并非平等并列,而是权力失衡的“并接结构”。*[美]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其中,近代以来的欧洲自然主义宇宙论具有霸权。仅从认识论质疑格尔茨及其阐释法,或许难以清晰地呈现交互主体。就阐释法而言,归根结底,人类学家是在“做”民族志。由此,正视并谨慎对待阐释中的权力实践,“做”好田野工作的同时也“做”好民族志,似宜更倾向于以“本体论转向”为基础,考虑操作性措施。首先,人类学家应当有理论自觉地对待与他者的话语权力关系,优先使用他者的话语解释经验材料,然后再转译成人类学可交流的语言;其次,重视多重宇宙论并接结构及其中的权力不平等,将他者宇宙论置放在语言叙述的中心位置;再次,在兼顾认识论的同时,从本体论上注重交互主体性。两个以上主体分别有自己的主观性是一个客观事实,阐释无法绝对消除它,而只能在互动中尽可能注重他者自主性,以达至实践性客观(而非科学主义意义上的客观)。依照斯科特的建议,对多种宇宙论应加以比较,但不要“异文合并”以求“纯化”。而依照伽达默尔的阐释论,则绝对意义上的误解根本就无法避免。*[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07页。但无论是人类学家的田野对象,还是民族志的读者,他们在意的并非这种误解,而是本可避免的、因为宇宙论和话语权力不平等造成的偏见。一句话,如何“做”好民族志,不仅是个知识认识论问题,更是个权力实践论问题。
鸣谢:感谢石汉(Hans Steinmüller)、吴迪博士给予的建设性意见,以及清源(Camille Salgues)、谭玉华博士为文中所涉法语资料汉译提供帮助(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 廖国强)
Inter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Parallel Multiverse Theory——On How to“Do” Ethnography
TAN Tongxue
Interpretation was once used as a method to deal with the methodological crisis in scientific ethnography. It has succeeded to some degree, but it has left radical postmodernism room for epistemological destruction, turning ethnography into the “writing” of culture and even leading it to agnosticism. To correct the situation, we must make sure that ethnography takes anthropologists and their fieldwork objects as its inter-subjects, language as its media and parallel multiverse as its ontology. The “ontological turn” i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emphasizes multiverse comparison but rejects arbitrary conflation or purification. Therefore, interpretation actually is an exercise of discourse rights by multi-cultural subjects in the same world. The inequality in discourse power couldn’t be eliminated only by an epistemological emphasis on “naked presentation” of fieldwork object narration or multi-subject perspectives. In this sense. what anthropologists do is not to “write” but “do” ethnography. How well ethnography is done is determined by not only their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proficiency of different subjects but the power practice of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inter-subjects, multiverse, discourse power, “do” ethnography
谭同学,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广东 广州,510275)。
C95
:A
:1001-778X(2017)05-0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