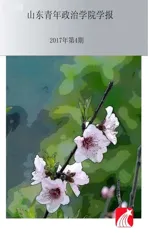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若干问题探讨
2017-04-11安源
安 源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 天津 300400)
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若干问题探讨
安 源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 天津 300400)
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司法办案质量和司法公信力有着重要意义。此次改革意在调整检察权力的运行模式,实现检察机关管理的扁平化,明确检察权行使主体的权力和责任,强化检察权的司法属性。此外,还要认识到此次改革存在的不足之处,改革虽在检察长与检察官的权力配置问题上采取授权制,但没有处理好检察官与检察长的责任承担方式,应当借鉴分权制模式,赋予检察长职务的收取和移转权,在坚持检察一体化框架下,使司法责任主体得以明确。
检察机关 司法责任 改革 检察独立
当前,中央就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行了部署。其中完善司法责任制,制定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是改革中最重要的四项试点任务。完善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对于调整检察权力运行机制,明确检察系统内部权责划分,提高司法办案质量以及提升司法公信力起到关键作用,是此次司法改革的“牛鼻子”。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此次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基于对我国国情条件的深刻把握,是自主选择的适合本国法制发展状况的司法制度模式。我们既要敏锐地认识到此次改革带来的新变化,也要在改革的过程中发现其中的问题,推进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稳步推进。
一、司法责任制改革所带来的变化
(一)调整了检察权的运行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检察机关实行的办案模式是“三级审批制”,该模式按照办案流程分为检察人员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三个环节。“三级审批制”对于案件的审查和决定更加注重上命下从,强调办案的效率性和便宜性,具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三级审批制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进步,该模式在运行的过程中也显现了诸多问题。检察权属于司法权的一类,具有亲历性和独立性。司法权的行使要求司法官必须亲历案件审理的全过程才能作出判断,并且这种判断应当是司法官基于个体的理性作出的判断。现行的“三级审批制”下,审批效力逐级递增,但审批主体对案件审查的全面性也会逐级减弱,形成承办检察官无决定权,决策者不办案的局面,有悖于亲历性、独立性等司法权力运行规律。
检察权分为诉讼检察权和侦查检察权,此次司法责任制改革对这两类检察权运行模式分别作出了调整。诉讼检察权主要指检察机关的逮捕权、起诉权以及诉讼监督权。在行使诉讼检察权的过程中,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为例,检察机关要在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司法机关与当事人的双方对抗之上居中作出决定,具有明显的司法权性质。为保证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意见》第5条指出,“独任检察官、主任检察官对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负责,在职权范围内对办案事项作出决定。”将原有的“三级审批制”中部门负责人的审核权去掉,使得承办检察官直接对检察长负责,实现了管理的扁平化,弱化了检察案件审批的行政化色彩,增强了检察官的办案独立性。侦查检察权是指检察机关对案件立案侦查的权力。而当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检察权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与犯罪嫌疑人对抗的地位,属于侦查行为的利益方,而非居中作出判断的司法官,追求侦查破案的成功和法庭审判之有罪结论,这是侦察检察权的目的。因而侦查检察权的司法权属性较弱,行政权属性较为突出。为保证侦查检察权的公正有效行使,《意见》第6条规定仍然保留了对于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由检察官办案组(或独任检察官)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决定的三级审批模式,一方面使得办案组织内部上下级协同一致,相互配合,增强上级指令的贯彻性,有效组织起足够的人力物力,有效打击犯罪。另一方面,由于侦查检察权先天具有重结果而轻程序,重追诉而轻保障的特点,因此也必须依托“三级审批制”,通过逐级审批的监控机制,在违法行为发生之初及时介入,来达到对于侦查检察权进行内部监督的目的。
(二)对办案主体进行了权责划分
在将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模式“三级审批制”调整为“独任检察官或办案组(由检察官组成)承办,检察长决定”这一新模式后,检察官与检察长的权责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意见》对两者进行了“分权”。检察官对于案件有承办权,并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负责,因而享有认定案件事实的部分定案权,而决定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例如决定批准逮捕)的另一部分定案权则归检察长所有,并对所作决定负责。这一改革措施旨在解决三级审批制下承办责任与决定权相分离而造成的权责不统一,责任主体模糊的弊端,明确了检察长、主任检察官各自的职权,便于追究办案责任。这样一种看似“分权”的改革措施,并不是将主任检察官认定案件事实的权力与检察长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决定权并列起来,因为《意见》指出,独任检察官、主任检察官还须对检察长负责,在职权范围内对案件事项作出决定,也就是说,检察官的这一部分定案权是由检察长赋予的。检察官的这种独立性,是在“由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的检察一体化的大前提下实现的,因此也是一种相对的独立。这样的规定,既体现了检察一体化下的共同责任,也体现出尊重检察官建立在亲历性基础上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与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不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将检察官的职能定位于独立官署,检察厅只不过是检察官办案的场所,检察长对检察官虽然也是领导关系,但也仅限于行政领导,检察官的定案权由法律直接赋予,其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和处理均有决定权,检察长几乎无权干涉。
在办案组织方面,分为独任检察官和检察官办案组两种形式,而检察官办案组又由2名以上检察官以及1名主任检察官作为办案组负责人组成。独任检察官承办案件,当然要承担案件承办的主要责任。而对于办案组的责任承担方式则较为复杂。《意见》规定,“检察官办案组承办的案件,由其负责人和其他检察官共同承担责任。”“主任检察官除履行检察官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以下职责:(一)负责办案组承办案件的组织、指挥、协调以及对办案组成员的管理工作;(二)在职权范围内对办案事项作出处理决定或提出处理意见。”这样的规定,容易产生疑问:既然办案组内的主任检察官和承办检察官共同对案件承担责任,而且主任检察官和组内其他检察官都有权参与办案事项,那么案件的追责主体当如何确定?这样规定是否意味着又回到了过去那种办案责任主体不明的老路上去了?对于这样的疑问,应当结合《意见》的第5条做出这样一种解释:主任检察官与检察官共同承办案件时分工不同,办案组在承办案件时,由于只有组内的主任检察官须对检察长负责,因此只能由主任检察官以其名义对案件事项作出决定,并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负责,而办案组内其他检察官只起到辅助主任检察官办案的作用,其履行职责的范围也应当限于有关案件事实认定之外的事项,因为如果主任检察官与组内其他检察官均要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负责,那么又会陷入追责主体无法明确的困境,也就背离了此次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初衷。因此,在这两种办案组织下,只有独任检察官或是办案组内的主任检察官,才掌握承办案件事实的认定权,并对承办的具体案件负责。《意见》将办案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明确了追责对象,体现了本次改革“谁办案谁负责”的精神,是司法改革的一大进步。
二、司法责任制改革所带来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一)主任检察官掌握定案权的设定并不合理
在本次《意见》出台之前,全国各地都针对主任检察官制度进行了试点改革。2013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方案》,将以主任检察官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在全国进行试点推广。那么,主任检察官制作为基本办案组织,其权力应该涵盖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各地试点做法不一,以基层检察院为例,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上海的闵行区检察院。该院的做法是,在保留原有的业务部门设置的情况下,在部门内设置主任检察官办公室,也就是以主任检察官为责任主体的办案组。办案组按照案件的风险等级划分为两种,一是低风险案件,在实践中掌握在办案风险在四级以下的案件,实行由1名主任检察官和若干名检察官(或者助理检察官)、书记员共6 至7 人组成的办案大组,案件由组内有检察官资格的检察官承办,由主任检察官行使定案权,主任检察官的权力来源于检察长的授权,可以更改承办检察官的意见。二是疑难复杂的案件,也就是办案风险在四级以上的案件,实行由一名主任检察官和1至2名检察员(或者助理检察员)和1名书记员共3至4人组成的办案小组,这类案件由主任检察官亲自办理并行使定案权,办案组内其他人员参与辅助性工作。[1]因此,不论哪一种办案组形式,最终的定案权都掌握在主任检察官手中。
《意见》指出主任检察官对案件事项有决定权,并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负责,故主任检察官享有认定案件事实的这一部分定案权。因此可以说《意见》对于试点改革中主任检察官行使定案权的这一做法予以了认可,但这一做法带来的问题也是突出的。就侦监、公诉等行使诉讼检察权的部门来讲,围绕主任检察官行使认定案件事实的这一部分定案权所组成的办案组,如果在检察业务部门内采用6人以上的办案大组,受单个部门人数所限(基层院业务部门一般在10人左右),所分成的办案大组数量不足,导致每个办案组每年所承担的案件就会远远超过按部门人数分配的案件,办案组承担如此大量的案件,主任检察官要想对每一起案件进行阅卷并进行判断并不现实,势必将案件下放到组内检察官进行承办,而主任检察官自己则包揽组内所有案件的定案权,形成“检察官办案,主任检察官认定案件事实,检察长决定”的又一种三级审批制,再次导致审者不定,定者不审的问题,也就违背了此次改革去行政化的初衷,重新回到了行政审批制的老路,这样的改革,似有“换汤不换药”的意味。如果在检察业务部门内采用3人以上的办案小组,办案组数量增加了,平均到各组的案件数量比办案大组要少,因此各组的主任检察官可能会有足够的精力来进行阅卷,提高了主任检察官对案件的亲历性,但这样又会导致另一个问题,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主任检察官群体的精英化程度,设定的人数不宜过多,实行办案小组的形式,势必增加主任检察官的人数,数量过多的主任检察官会使这一身份与其办案能力相脱节,有异化为某种“身份福利”[2]的可能。
由此可见,《意见》指出的由主任检察官行使定案权并不是符合司法责任制改革目标的一种设定,因为司法责任制的目的在于建立起检察官责任制,而并非仅仅建立主任检察官责任制,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亚类。检察官责任制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谁办案,谁负责,如果仅确认主任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而忽视了普通检察官这一一线办案力量,既有违检察独立和司法改革的精神,也不利于加强检察队伍建设,培养优秀检察官。从应然的角度来讲,想要彻底解决此问题,就不应由主任检察官行使定案权,主任检察官只负责办案组内的组织、指挥、协调、管理等统御性的事务,不承担一线办案责任。同时,将定案权下放到办案组内承办检察官,使承办检察官集办案权和定案权于一身,并对承办案件负责,一步到位实现承办检察官的个体独立。但是,我们还要从我国的司法实际出发,应当看到我国的检察官群体当中,法律专业素养较高,办案经验丰富的检察官终归只是少数,很多从法学院刚刚毕业进入检察系统的干警,只需通过司法考试,再经过1年左右的书记员任期,即拥有办案资格,其专业及实务经验必然不足,因此要想通过改革一次性实现检察官独立也是不切实际的。
司法改革应当是循序渐进的,不能一蹴而就,因此要从司法实际出发,既要将定案权过渡性地下放到承办检察官手中,给予其较为充分的定案权,尊重其独立性,也要让主任检察官担负起对案件的审查、监督的责任,当主任检察官与承办检察官对案件产生异议时报检察长进行核定,而不应直接改变其决定,主任检察官应当在检察官和检察长之间充分行使其协调、管理、指导等宏观统御的职能,成为检察一体和检察独立二者的平衡器。
(二)没有解决好授权制下检察长与检察官的责任承担问题
检察官与检察长的权力配置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分权制,检察长和检察官的权力均由刑事诉讼法及检察官法赋予,检察官对承办案件有相对独立的决定权,检察长的检察指令权仅限于职务的收取和移转权,一旦检察官与检察长对案件产生分歧,检察长不得直接改变承办检察官的决定,而是通过转移案件的承办来间接地对案件结果施加影响。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检察机关均实行分权制。二是授权制,这在美国普遍采用。美国在联邦、各州及各州所辖市县三级设立检察官办事处,每个办事处只有一名检察官,检察官由普选产生,其在辖区内的地位和职责与我国的检察长基本相当,检察官将检察权授予办事处下面的助理检察官,并可以行使检察指令权改变助理检察官的处理决定。《意见》在配置检察官与检察长的权力时,指出承办权及定案权属于检察官,对案件作出处理的决定权属于检察长,具备一定“分权”的色彩。但是《意见》在第5条指出,检察官须对检察长负责,也就是说,检察官的承办权及定案权来源于检察长的授权,而非法律赋予。第10条规定,检察长对检察官承办的案件有权进行审核并通过行使检察内部指令权的方式能够直接改变承办检察官的处理意见,并且这种改变如果产生错误,那么应由检察长来承担司法责任。由此看来,《意见》在检察长与检察官的权力配置上借鉴了美国的授权制。
《意见》虽然在检察长与检察官的权力配置问题上采取了授权制,但从条文中可以看出,检察长并未将完整的定案权赋予检察官,只是赋予检察官认定案件事实的权力,而逮捕、起诉的最终决定权仍然归检察长所有。当检察长改变了检察官的处理决定时,就说明检察长已将检察官的部分定案权收归了自己,一旦检察长的改变决定发生错误,原则上就应由检察长来承担责任,而不能要求没有定案权的检察官来承担责任。与此相矛盾的是,《意见》的第10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检察长对检察官决定进行的改变“明显违法”,那么检察官也要承担司法责任。“明显违法”一词太过于模糊,如何界定明显违法?难道还有不明显的违法?违法与否的判断标准不允许有任何含糊的语言,任何明显的违法都属于违法,而违法的决定当然是错误的决定。因此,该条款后半句就演变成为,检察官执行检察长的错误决定时,也要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这与授权制下检察官不对检察长的错误改变承担责任的原则相悖。《意见》中“明显违法”这种含糊不清的语义会在授权制下造成检察长与检察官的责任承担的混乱,可能再次导致司法责任主体不明等问题。
笔者认为,我国检察机关的组织结构接近大陆法系检察机关类型,与其借鉴英美法系的授权制配置模式,不如采取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分权制模式,以完善《刑事诉讼法》《检察官法》等法律的方式,赋予检察官承办权和定案权,弱化检察长的检察指令权,赋予其职务的收取和移转权,对案件的处理与检察官发生异议而不能达成一致时,转由其他检察官承办,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来改变案件的结果。这既坚持了现有检察一体化的框架,又可以使检察官得以独立办案,使司法责任主体真正明确。
三、小结
对于检察权行使过程中因权责未能统一造成的诸多弊端,各级检察机关早有体会,并在2000年前后启动了“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该制度按照案件的风险等级来确定案件审批模式,对于低风险案件,采取“主诉审批制”,对于高风险案件,采用“三级审批制”。但风险等级的认定权属于主诉检察官,主诉检察官为分担办案风险,将案件纳入三级审批的范围,往往倾向于将大部分案件认定为高风险案件而采用三级审批制,检察长等上级领导也往往对检察官独立办案不放心,导致其放权不彻底。主诉检察官办案制度在实践中也因此逐渐回到了高度行政化的办案制度,改革未能实现其设定的目标,最终名存实亡。在此次检察官司法责任制改革改革中,要吸取“主诉检察官”改革的失败教训,避免改革流于形式,要在检察一体化和检察独立之间找到平衡点,调整好检察权的运行模式,理顺检察官、主任检察官、检察长等主体的相互关系,在坚持检察长对检察工作统一领导下,将案件的承办权和决定权逐步下放到检察官手中,使检察官成为司法办案的权责统一体。既要坚持不懈地推动此次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效,也要在改革中敏锐地查找问题并着力解决,推动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向着既定目标乘势而进并最终取得胜利。
[1]潘祖全.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实践探索[J].人民检察,2013,(10).
[2]张栋.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应理顺“一体化”与“独立性”之关系 [J].法学,2014, (5).
(责任编辑:杜婕)
Study on Some Problems about Judicial Reform of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 Yuan
(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Beichen District in Tianjin,Tianjin 300400 China )
The revolution of the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judicial reform, which has wide significance to case qual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judiciary. Intending to accomplish the flattened management of procuratorate, this revolution rearranged the operatio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secutorial power and made it become clear-defined. Shift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between prosecutor and chief prosecutor raise problems. To recapture and endue the authority of jurisdiction is an appropriat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procuratorial organs; reform of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procuratorial independence
2017-03-20
安源(1991-),男,天津人,助理检察员,主要从事检察理论及实务研究。
D926.3
A
1008-7605(2017)04-009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