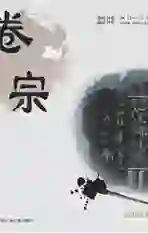琳丽的告别
2016-05-30穆昕
摘 要:本文以白薇的诗剧作为个案,探讨其独特的审美空间、结构、语言,思考她在诗剧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及其诗剧衰微的原因,试图从个案管窥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诗剧生存的文学思潮大背景,理解这场思潮为何只赋予白薇的诗剧艺术短暂的生命。
关键词:白薇;诗剧;文学思潮;浪漫主义;现实主义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与戏剧新思潮的涌动,“五四”时期和二十年代的戏剧创作在艺术上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在借鉴种种外来的戏剧新观念和创作手法的基础上,或模仿或突破、创新,为“五四”后的新文化、新文学开辟了一方崭新的天地。而在这方新天地中,曾生长着一株“空寂又奇穷的薇草”。她,外表柔弱而内心坚韧,历经磨难却坚守对人生的执著信念,不惜倾尽毕生心力,但求奏出一曲凄美的爱之挽歌。她,就是白薇,一个为中国现代戏剧,尤其是诗剧增添瑰丽色彩的奇女子。
作为中国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剧作家,白薇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真挚情感,曲折艰辛的人生经历,卓尔不群的审美感悟力,为现代戏剧注入了诗剧艺术那独特而唯美的气质。尽管诗剧在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史上,只是一位匆匆过客,于20年代初兴盛,至30年代难觅其迹。但探讨白薇如何建构其诗剧的审美空间,分析她赋予诗剧的独特的结构、语言,思考其诗剧的衰微及写剧风格的转变,从中管窥我国20世纪20年代的诗剧生存的文学思潮大背景,不无意义。
为什么中国的戏剧舞台上,会有“诗剧”这一独特样式昙花一现?为什么偏偏是白薇、郭沫若、杨骚等人,将诗剧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还得从“诗剧”的内涵本身着手。余上沅曾对诗剧有过如此描述:“我们所称为诗剧的也不限定是用诗作体裁的戏剧,有许多散文戏剧也是诗剧。凡是具有诗的题旨,诗的节奏,诗的美丽,诗的意境的散文戏剧,我们都称它为诗剧。”①作为国内知名的戏剧家,余上沅从广义的角度对“诗剧”作了审美意义上的概括,是具有一定道理的。众所周知,戏剧是地道的舶来品,其理论支撑源于西方千百年来的戏剧实践。我们透过19世纪以前的西方文论,透过黑格尔的《美学》,将不难发现“诗剧”和“戏剧体诗”有着等价的概念,它是介于“按照本来的客观形状去描述客观事物”②的史诗和“采取主体自我表现作为它的唯一的形式和终极的目的”③的抒情诗之间的一种艺术样式。古希腊的悲剧家们、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又将理论付诸舞台实践,赐予了诗剧不朽的生命力。随着五四文艺革命发展的蓬勃之势,诗剧艺术也随着各种外国文艺思潮被推涌到了人们的面前,并渐渐植入了一群擅长主观抒情、具有浪漫气质的诗人的骨髓之中。正如苏珊·朗格所言:“戏剧是一种诗的艺术,因为它创造了一切诗所具有的基本幻想——虚幻的历史。戏剧实质上是人类生活——目的、手段、得失、浮沉以至死亡——的映象。它具有一种幻觉经验的结构,这正是诗作的文学产物。然而,戏剧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而且也是一种特殊的诗的表现形式。”④白薇恰恰是那群擅长抒情、讲求浪漫的诗人中的一位,她将诗的表现形式巧妙地运用到了戏剧的创作之中,纵情抒发对爱,对恨,对生存,对死亡的感悟,从而产生了带有鲜明的白薇风格的诗剧艺术。
纵观白薇的诗剧作品,以《琳丽》为典型代表,另有《苏斐》、《访雯》等,虽数量有限,但个性鲜明。可以说,白薇诗剧的艺术风格是由于内外两种力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内在之力源于白薇自身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具有先进思想的父亲竟然强制包办女儿的婚姻,迫使白薇孤苦无依流落东瀛,又遭心爱之人始乱终弃,常年身染重疾。白薇尝尽了现实的苦痛,更叹喟真爱难寻;外在之力来自那个特殊时代给人思想上的撞击。作为早期留学日本的新女性,在大量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下,白薇沉浸在莎士比亚、斯特林堡、霍普特曼、梅特林克、王尔德等人的世界里,并亲身实践写出三幕剧《苏斐》。同时,她还吸纳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的精华,借鉴了西方戏剧的结构形式。正是在上述内力、外力的共同作用下,白薇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审美感悟力,通过戏剧这一载体,运用诗一般的语言,将情爱、生死、人性的善和恶、美与丑交织在一起,扣问着人生的终极意义。
张若谷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一书中给予《琳丽》极高的评价,认为那是“中国诗剧界的唯一创作。”细加分析,足见白薇对诗剧的结构、语言有相当独到的把握。“可以看出白薇女士是对西洋歌剧有所研究的,这不但作者在剧中能引入西洋歌剧Sappho、Cleopatre、Faust和《沉钟》等的名词;而是在《琳丽》的本身,结构与情节,都有西方歌剧的意味,所缺少者单没有经音乐家编谱乐曲罢了。”⑤白薇灵活借鉴了西洋歌剧的结构特质,而没有拘泥于呆板的诗的格律范式之中,让心底的呼声自由地飘散出来。这得益于自由的时代,赐予人们自由的率性。“剧中的诗不是附加的词句,而是剧中人心情的自然流露。”⑥的确,白薇全然是以剧中人琳丽的口吻在吐露心声。“我这回只是一团晶莹的爱。离开爱还有什么命?”“早知道不能再吻你的娇唇,该叫我的灵魂早入地狱。”她将现实的自我与剧中人合为一体,全情投入。时而是对心中幻想的理想之爱的热切呼喊,时而是对现实中真爱的遍寻不着的撕心裂肺的悲鸣,“字字吟来皆是血”,如何不叫他人动容?无怪乎陈西滢这般评价《琳丽》:“它的结构也许太离奇,情节也许太复杂,文字也许有些毛病,可是这二百几十页藏着多大的力量!一个心的呼声,在恋爱的苦痛中的心的呼声,从第一页直喊到末一页,并不重复,并不疲乏,那是多大的力量!”⑦白薇的可贵之处在于,用最真实的语言,源自心灵的语言,写诗,写剧。没有矫造之感,没有虚情假意,真实地表现源于真实的东西。虽然,剧作家抒发的是个人诗化的语言,一时难以贴近劳苦大众质朴的需求,但语言上带来的陌生化效应,却赋予了白薇诗剧一种特有的疏离的美感。
提及白薇,提及《琳丽》,自然不能不提杨骚和他的《心曲》。由于二人现实中斩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由于二人相似的写剧风格和审美感悟,由于《琳丽》与《心曲》被誉为20年代爱情诗剧姐妹篇……所以有理由将二人放在一起比照。白薇和杨骚同是抒情诗人,同是周身洋溢着浪漫唯美的气质,同是将目光聚焦到爱、人性、信仰的哲理层面,关注人的精神世界,探寻人生终极的价值取向。但正是以上诸多的相似掩盖了他们的根本不同:《琳丽》中女主人公作为白薇的代言人,对爱(或许可以把这种“爱”延伸为美好的理想)的追求有着异常执著的信念,“惟有恋爱能奏出真而美的生之和弦”。即便最终必须面对爱人琴澜的死,面对爱情的幻灭,但她始终坚信“人生只有‘情是可靠的”,只有灵与肉相结合的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白薇对爱付出的是女子特有的感性驾驭下的孤注一掷,哪怕面对“死神”的形象,也无所畏惧。而杨骚作为一个理性最终战胜感性的男子,在灵与肉之间摇摆,在爱与理想的取舍中彷徨。最终,他以旅人的形象,舍弃了对真对善对美挚爱的森姬,而循着细妹子的歌声慢慢离去。尽管杨骚的诗剧中有着较白薇明朗的基调,“晨光会做我的引导者罢,我惯走的腿子会追得及罢”,但同时也暴露了他在困难面前滋生的某种妥协性,于是他喃喃地道:“然而,然而……”。或许白杨二人对爱,对人生有着潜在的不同理解,导致他们最终成为天涯陌路人。
还是回到本文最初提的问题上来,诗剧这种特有的美感为何昙花一现?白薇诗剧艺术的生命力为何仅仅持续了不到十年?一切似乎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找寻答案。从内在原因上来看,白薇堪称一位优秀的诗人,却算不上一位合格的剧作家。“诗人应尽量少以自己的身份讲话,因为这不是摹仿者的作为。”⑧而她在字里行间纯然是替自己或歌或泣,每一个角色不过是用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声音为其呐喊。强烈的感情迸发使白薇失去了运用逻辑构筑戏剧情节冲突的能力,总是沉湎于自己的炽热的感情之中不能自拔,以致剧作好似掌中的一部诗集,却没法很好地在舞台上表演。而《琳丽》作为一出悲剧,其情节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因为“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性格的重要性占第二位。”⑨事实是大多的诗剧都存在此类问题,一旦剧作缺乏了舞台表现力,就意味着缺乏了生命力。
再看外在的原因,也正是本文通过白薇诗剧艺术的个案分析,最终希冀探寻的当时时代的文学思潮大背景。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不难发现,形式与内容之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充斥在每一次大的文艺思潮当中。“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正值历史大变动、大转折之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新旧思潮的交战,给各种文艺样式提供了肥沃的植根土壤,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在各自崭新的环境中展示着全新的自己。新思潮的推涌与新出路的难寻,让感伤情绪弥漫在“五四”的后十年里,个性的张扬成为当时艺术家们执著的追求。 他们凭借主观的抒情、发自心底的疾呼,借助抽象的审美意向,张显个性的“我”。在“我”的自叙传中,反思人类深蕴的内心世界和人生的终极体验。他们是以主观化的方式来关注客观化的现实问题。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恰逢“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的时期,处处高举的是“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大旗,白薇等人那种浪漫的、唯美的作品已经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抒情、幻想给人的轻曼感觉,成为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曾经在文坛上极力倡导浪漫主义的很多人,也以壮烈的姿态告别浪漫主义。“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口号遍行天下,浪漫、感伤、自我的情调被剔除出局。尤其是白薇等人的诗剧,既充斥着主观抒情,又缺乏舞台表现力,在大众面前不能发挥丝毫简单、直接的教化作用,不能服务于劳苦大众的艺术样式,似乎更有理由销声匿迹。事实的确证明,白薇深受左翼激进思潮的影响,毅然决然放弃了早先对浪漫艺术性的执著追求,勇敢地投身到现实主义的洪流中去。终于,创作出了诸如《打出幽灵塔》这样犀利的作品。更多和白薇有着类似唯美气质的文学家、剧作家们,也纷纷终止了“在诗意上的盘旋”,开始舞动起客观写实的笔。终于,我们眼睁睁地望着白薇诗剧的凋零、逝去,望着那些浪漫个性的凋零、逝去……然而,这就是特定时代、特定思潮给予文化、文学的必然的洗礼。
琳丽已然告别了这个世界,她“周身佩着蔷薇花,死在泉水的池子里面”。然而,真正艺术的魅力,却犹如海潮退去后沙滩上美丽的贝壳,静静地久躺在我们的心底。
参考文献
①余上沅:《论诗剧》,载《晨报·副刊》,1926年4月29日。
③[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7月第1版,第99页,第100页。
④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页。
⑤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朱栋霖、周安华编:《陈瘦竹戏剧论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1356页。
⑦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西滢闲话》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第266页。
⑧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北京,第169页,第65页。
作者简介
穆昕(1978-),女,南京,江苏警官学院,讲师,文学硕士。